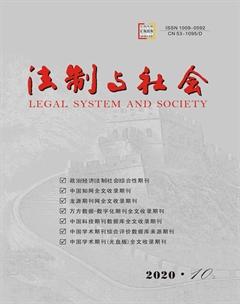犯罪中止自动性判断之限定主观说
关键词 犯罪中止 限定主观说 自动性
作者简介:左倩玉,聊城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10.079
犯罪中止即行為人出于自己的意愿,真诚地放弃未了的犯罪行为,或行为完成后及时有效地阻止结果发生。中止犯的成立条件包括中止行为与中止的自动性(任意性),其中中止的自动性判断最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未遂与中止的划分界限,以及刑法规定对中止犯必须减免惩罚的依据。
关于自动性的判断标准,存在客观说、主观说、限定主观说的对立。客观说是根据一般人的经验对未完成犯罪的原因进行客观判断,如果当时的情况对于犯罪既遂不具有妨害性质的,即一般人认为行为人可以继续实施犯罪,但行为人放弃了,为犯罪中止,反之有妨害性质的,为犯罪未遂。折中说,也称新客观说,它与客观说的区别在于客观说对行为人未完成犯罪的原因进行客观评价,折中说则是对行为人对外部事实的认识进行客观评价。折中说用一般经验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行为人的认识在一般人看来对行为人继续实施犯罪行为有强制性影响,为犯罪未遂,反之,没有强制性影响的,为犯罪中止。客观说的贡献在于对心理因素的判断提供客观标准,主要体现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的实际心理活动有时很难查明,客观说可以为法官断案提供依据。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般人的经验此时成了裁判者一人的经验,该判断自难期公允妥当。退一步讲,一般人的经验也并不明确。更为重要的是,“自动性”终究是主观要素,无论如何都不能无视行为人自身的特殊情况,中止行为是行为人基于自身意思做出的,个体差异之大,情况变化之多,不宜以一般人之客观标准进行衡量,有曲解行为人本意之嫌。
主观说是从行为人本人认识出发,行为人认为客观障碍不足以妨害犯罪实施,但自愿放弃的,属于中止,反之行为人认为自己不能继续实施的,属于未遂。主观说虽然抓住了自动性的根本特征,强调行为人本人的意思,而且有简单的判断公式,一般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弗兰克公式所提到的“能”与“不能”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不同的人可能根据该公式得出相反的结论。主要的争议在于是物理上的“能”,还是心理上的“能”,抑或是伦理上的“能”,因此对自动性的认定并不明确。 例如,同样是因为听到警笛声而停止盗窃,如果因为怕被警察逮捕而未能继续实施犯罪,为犯罪未遂;如果为了保险起见主动停止,则为犯罪中止。
限定主观说相当于在主观说基础上做进一步限定,“基于己意自愿放弃”除了具有自动性,还应当出于反省、悔悟、怜悯、同情等这种动机,也即广义的后悔,对自己的行为持否定态度而放弃犯罪,才成立犯罪中止。也就是说,限定主观说在弗兰克公式上对“能”与“不能”做了伦理上的限定。限定主观说要求自愿放弃必须出于真挚,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如果是被迫的放弃,技穷的放弃,因为明显提高犯罪风险的放弃等都是未遂,这必然大大缩小了犯罪中止的范围。
我个人是赞同限定主观说的。未遂与中止难以区分的原因就在于中止犯的范围太宽,无论是客观说的一般经验、规范说的规范标准、主观说的“能”与“欲”的定义,以及各种学说的融合折中,大多是在主观判断基础上引入另一判断标准,但这种变量的引入往往又使得中止犯的边界变得模糊。边界模糊就无法显示出判断核心,理论就会不稳定,就会飘荡,所以中止犯的概念必须紧缩。犯罪中止不仅要出于自愿,还要有伦理上的要求,例如怜悯、后悔同情、正义、良心发现、宗教情怀等等。出于行为人理性的、功利的计算,尽管自愿放弃继续实施犯罪或自愿阻止结果产生,都不成立中止。例如把某女扑倒准备实施强奸时,发现女方长相丑陋,欲望全无,或发现女方是熟人,从而放弃强奸的,是强奸未遂而不是中止。行为人的自愿放弃并非是对自己行为的伦理要求,而是相貌丑陋的女方不能满足他的性欲,或是怕被熟人认出从而告发自己,这种经过功利计算的放弃并不能成立中止。
限定主观说对中止犯概念的缩限是合理与必要的,这有利于明确未遂与中止的界限,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两者在客观方面都没有完成犯罪行为,没有产生犯罪结果,但是相比未遂犯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中止的处罚“应当减轻或免除”显然更为宽缓。既然客观方面相同,为何中止犯的比未遂犯享有更多的特权?这种宽缓的处罚依据只能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寻找。在行为人因着伦理的自律自动有效地放弃犯罪的情况下,行为人自己不应着手实行犯罪的感情即否定自己行为价值的意识起作用了。正是在这种场合,行为人的反规范性比通常的未遂犯要轻,减免或免除处罚才合适。未遂犯则是因为出现客观障碍妨害犯罪既遂,行为人的内心并未向规范回归,再次犯罪的危险性并未消除,只是比照既遂犯来说没有产生犯罪结果,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并不能获得中止犯那般的处罚特权。并且,立法者在未遂犯之外创设了中止犯的成立条件,并给予优厚的法律奖赏,这可以说中止犯是未遂犯的特列 。既然是特例,中止犯的范围就应当缩限,不能在特例之上再开特例,一旦中止犯的范围不稳定,司法实践中就会出现未遂犯与中止犯的混淆,对普通未遂进行不当的法律优待,所以,对于中止犯的严格解释是合理必要的。
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唯有真诚悔悟者,才不具社会危险性,才值得被宽宥,刑罚权才有节制的必要。经由功利的计算才中断犯罪行为或组织犯罪结果产生的人,以及待时而动、变更犯罪计划的人,都缺乏真挚的感情,性情中还隐藏的危险因素,对于此类人,不值得给予法律上的优待,这是出于特殊预防的考虑。同时,只有原谅真诚悔悟的人,社会大众的情感才不会受到冲击,社会大众对于安全和秩序的需要才不会被破坏,如果宽宥了经过功利算计而放弃犯罪的人,社会大众就可以仿效犯罪人,一旦在犯罪过程中遇到障碍,明显提高犯罪成本与风险,便自动放弃,以求成立犯罪中止获得减免处罚特权,这样,一般预防的目的也难以实现。
学界对于限定主观说有诸多批判。周光权老师在文章中提到限定主观说“一方面,其将伦理观念过多运用到刑法规范判断中,人为缩小中止犯的成立范围,不能及时有效地鼓励有犯罪意思并着手预备、实行者迅速返归社会,对于法益的保护也没有实益。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刑法》第24条的规定,行为人只要‘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就是犯罪中止。这里的‘自动,只要求行为人基于本人的意思放弃犯罪或者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而未将停止犯罪的动机限定为广义的后悔。所以,限定主观说与刑法规定也并不符合。” 对于中止犯范围的缩限,个人认为是合理必要的,理由在前文已有叙述。对于限定主观说的限制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个人认为这种伦理要求未必超出“自动放弃”这一用语本身所可能具有的含义。“自动放弃”是指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思真诚地放弃。评价中止犯,要以未遂犯为参照,行为人犯罪未遂是因为客观障碍,例如技术不到家无法打开保险箱、发现有更好的犯罪方法于是暂且撤回另做打算,这种放弃也可以说是行为人自己的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因为技穷、难以为继、为降低犯罪成本才中断犯罪,这里见不到真诚的放弃。如果不问动机,只要有自愿停止就成立犯罪中止,无论持何种学说,我想都是难以直接接受的。所以中止犯的“自动”必须要有动机的限定,这不仅是中止犯自身定义的需要,与未遂犯进行明确区分的需要,也是为了刑法体系内部的和谐统一,同时也能为司法实践判断提供方便。而且这种严格的解释方法在刑法中也不是没有他例,比如在解释正当防卫的紧迫性时,如果要实施防卫的行为人有加害的故意,则否定存在防卫的紧迫性,这种解释也并没有超越“紧迫性”这一要素的含义。同时,这种限定在其他学说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周光权老师的规范主观说认为:被告人自己决定不再实施犯罪的心理态度对“基于己意”的判断只是提供了基础素材,只有从这种停止犯罪的意思和行为中,能够清楚明了地看出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降低或者消灭,且该停止行为使民众恢复了对规范的信心的,才能最终从规范评价的角度认定为“基于己意”。 這种规范评价其实也是对中止犯的“自动放弃”再一次做了限定。
限定主观说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意识出发,也常被人批评这种先主观后客观的判断顺序有违客观主义刑法,也有人指出如果行为人有悔过的意思,即便造成了犯罪结果产生,也以定以犯罪中止是不妥当的。对于此,个人认为客观主义刑法不等于教条式的“先客观后主观”的判断顺序,它的内核是限制刑事处罚范围,限制刑法对国民生活的恣意干预和定罪范围的不当扩大。先客观后主观的判断顺序是为了防止主观归罪,而犯罪中止更接近与一种出罪判断,是法律给予行为人的优待,这种优待事由并不受先客观后主观的入罪判断顺序制约。而且犯罪中止的中止行为和中止意思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中止行为不仅有身体活动,还要有中止意思的支配,非中止意思支配的行为不能称之为中止行为。客观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采取先客观、后主观的判断顺序,是基于客观行为独立于责任要素的基础上的,其主观要素仅限于支配身体活动的意志即可,不是指犯罪的故意与过失。 所以限定主观说的适用与客观主义刑法并无冲突。至于造成损害的中止犯,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对于自动放弃犯罪但没有有效防止结果发生从而造成损害的,我国法律已经给出明确规定。行为人出于良善动机自愿真挚地放弃犯罪,这不仅表明行为人危险性已大大降低,没有特殊预防的必要,而且对其减轻处罚也不会动摇社会法秩序与大众情感。这种法律也更加体现了法律对犯罪中止的优待之宽厚,于此,中止犯的范围不应扩大而是严格限制。可以看出,中止犯的范围缩限、判断依据、处罚依据都是环环相扣的。
最后也是最让人诟病的是限定主观说混淆了刑法与伦理的界限,将伦理带入刑法作为判断的依据。学者大多努力划清刑法与伦理的界限,让它们各自囿于各自的领域。但仔细想想,法律与伦理是可以截然分立、互不相干的吗?近年来有些文献虽未明确指明,但内涵接近这样的看法:伦理上的自我要求是中止犯成立的要素。例如包曼、韦伯与米契在他们的刑法总论中说道:“中止犯无须具备道德上的高度情操”可是随后又举例说:“弄错了被害人,认为犯罪目的不能达到而中断行为的,不是自愿中止。” 又如王昭武老师在其文章中批评道限定主观说有将伦理性因素融入刑法理论之嫌,可随后又说出于真诚悔悟等伦理性动机放弃犯罪的,属于犯罪中止的属于充分条件。而且他提出的作为主观说的新的限定:“规范意思的觉醒”也排除了因惊愕、恐惧、担心被发现、期待落空一类的中止。在其之后给出的例子中,对于男友出于对女友的爱恋而放弃杀害行为的,肯定了中止的任意性。 可以看出在进行理论分析和实际判断时,我们都不自觉地会用到伦理性因素。即便是提出的种种新的限定,如“放弃法敌对意思”“向规范的回归”,也不过是伦理因素的变种罢了。没有伦理因素的支撑,立法会趋于机械化,从而陷入“存在即合理”的循环论证。没有伦理因素的支撑,我们其实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犯罪中止要享受如此优厚的法律待遇,我们为什么会原意宽宥一个真诚自愿放弃犯罪的行为人。如果仅从客观层面考虑,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几乎相同,为什么我们会对未遂犯有所恐惧与心有余悸而能接受中止犯的“浪子回头”?无论是从政策角度解释还是从刑罚目的考虑,好像都不能给出有力的说服。如果是为了达到预防目的,那么将所有的犯罪分子给予严厉惩戒、不予优待岂不是更能起到预防作用?如果从政策上考虑,脱离了伦理因素,我们为什么会认为中止犯有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值得法律奖赏呢?其实这种伦理性因素恰恰是“犯罪中止”的合理性所在,正是这种伦理性的动机让人们对行为人作出了宽谅、奖赏的选择,让我们相信行为人有回归社会的可能,正是这种伦理因素才是支撑“犯罪中止”的核心所在。
其实在我们进行判断和衡量时,我们无法跨过伦理这道坎,不仅是刑法,其他法律规范也都或多或少地渗透着伦理因素,比如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笔者认为,我们确实是要避免道德归罪,但是对于伦理因素与法律的交融,我们也不必如临大敌,刑法是社会的底线,没有一种犯罪不是反伦理的,伦理给我们提供了入罪的支持,也给我们出罪的理由。刑法是保护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核心道德,这种核心道德正是我们一切社会规范的源头。除掉伦理性因素,法律只是一部冰冷的机器。但作为一部为人所造、为人所遵守并维护社会共同体秩序的法律并非高高在上之物,它应当低下它的头颅,成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触及的有温度之物。
注释:
王磊.中止犯减免根据影响下的中止自动性的认定——以李某抢劫、杀人案为例[J].刑事法判解,2015(1).
林东茂.刑法综览(修订五版)(第1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第162页.
周光权.论中止自动性判断的规范主观说[J].法学家,2015(5).
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王昭武.论中止犯的性质及其对成立要件的制约[J].清华法学,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