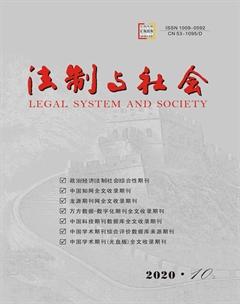域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的发展研究
关键词 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 调解 诉讼
基金项目:本文为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省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社区纠纷非诉讼多元化解机制研究》(项目编号:YB05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岩,兰州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商法。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10.061
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194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10.64%,到2019年城镇化率已达到60%。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法院民事一审案件收案数量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法院面临着巨大压力。根据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全国民事一审案件收案数量为6090622件,到2018年则达到了12449685件。
诉讼案件的井喷式增长也同样出现在西方国家,“诉讼爆炸”也作为一个特有名词而产生。有些国家试图通过诉讼程序的改革来改变这一现象,然而简化诉讼程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司法机关的压力,但也可能引发更多的诉讼而陷入两难境地,于是ADR应运而生。ADR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可从字面理解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所有未经过正式审判程序而解决纠纷的办法都可称之为ADR。
一、发达国家ADR发展模式
(一)美国
美国是ADR的发源地,陪审制、社会文化等因素,使得美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其首次应用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劳动争议解决中。ADR被定义为“并非由法官主持裁判而是由一个中立的第三人参与协助解决发生争执的纠纷的任何步骤和程序”[1]。
美国ADR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起初人们对其持否定态度,直到1983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的修订,首次把和解确定为审前会议的目的,使法院的ADR实践具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法》,鼓励各法院根据自身规则确定该具体项目。[2]至此,美国的ADR开始了迅猛发展,其具体形式主要有:
1.法院附设的调解。调解是美国各级法院使用率最高的一種ADR模式。为保证调解效果,一些州还规定了“强制调解”的配套制度,比如不接受调解的一方若在诉讼中没有得到更有利的判决,要接受惩罚。
2.仲裁。1926年成立的美国仲裁协会,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美国很多州规定在一定金额以下的不涉及其他法律问题的简单赔偿案件,必须先仲裁,仲裁员通常由资深律师担任。如果不接受仲裁结果,要求重新审判,则要求当事人缴纳保证金,如未取得更有利的判决则予以没收。
3.简易陪审团审判。简易陪审制,于1980年由俄亥俄州北部法院托马斯·D·兰布罗斯法官首创。[3]该程序属于评价性ADR,不公开进行,当事人可以借此程序预测法院的判决结果,从而做出相应的判断,主要运用于双方当事人分歧很大的案件当中。
4.早期中立评估。该制度主要是通过中立者的威望及广博的知识促成各方的和解,整个程序秘密进行,并且其评价的结果只具有参考性,如最终双方未能达成和解,该评估对后期法官的判决不具任何影响。
为保证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美国很多州立法规定,在诉讼前必须选择一种或是多种ADR程序来解决纠纷,使得只有不到5%的纠纷最终进入到诉讼程序。
(二)英国
同美国一样,英国早期的立法者与法院对ADR模式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当事人不得通过协议排除法院对特定法律问题的管辖权。但随着案件数量的增加,诉讼周期长,费用高的问题越发严重,ADR模式的优势也逐渐彰显,虽然其起步晚,但得到了有力的理念和制度支持。
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英国立法部门和法院大力支持民间力量开展ADR,自己却不直接参与。比如1995年商事法院发布《诉讼实务告示》公布了法官创造的一种促使当事人采用ADR的“劝导性命令”。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规定,如果当事人未尽义务认真考虑使用ADR,可能会在诉讼费等方面受到惩罚。
英国的ADR模式中最具特色的应属专家决定和早期中立评估。其中,早期中立评估,由专业权威人士在当事人之间作简短陈述,对纠纷作出评价,并提出无拘束力的解决方案,在解决家事纠纷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德国
德国是罗马法的典型国家,有非常严谨的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援助和诉讼保险等制度,加之“是非分明”的社会文化,民众的诉讼热情较高,[4]因此对ADR的发展显得十分保守。
上世纪90年代,因诉讼量增加,德国先后制定了《司法简便法》、《司法负担减轻法》等,同时ADR的优势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德国于1994年颁布的《费用修正法》特别规定律师如能使当事人达成庭外和解,除了可向当事人收取全额律师费外,还可再多收取 50%的和解费。[5] 而德国《律师职业条例》已明确将调解作为律师的法定业务之一。[6]
德国ADR的发展主要以法院内设为主,如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督促程序,以及贯穿诉讼各阶段的和解义务等。有关法院外的调解则显示出按照纠纷领域形成各专业组织的一种倾向,其中家事调解是使用最多的一种民间调解。整体上来看,德国面临的司法危机并不严峻,其民事司法仍有继续发展的空间,所以其发展 ADR 的动因并不急迫。[7]
(四)韩国
受韩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对于费时费力的诉讼来讲,民众更喜欢在法院外解决纠纷。韩国法院对ADR也相当重视,不断对其进行优化。
1.法院负责的ADR。韩国的法院调解强调法官的调、审分离,借此避免审理法官的先入为主。此外《韩国家事诉讼法》中规定,家事纠纷审理前必须调解,不仅有很多程序可供选用,同时还可为当事人量身打造新程序以利于解决纠纷。
2.法院外的ADR。韩国法院外的调解主要有民间调解、行政部署下的各种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制度、仲裁、搜查机关的协议、国民苦衷处理委员会等。其中各种专门的调解委员会如个人信息纠纷调解委员会、电子商务纠纷调解委员会等,同时委员会不仅有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且职责比较明确,就是调解纠纷,并不附加其他任务,在解决纠纷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根据韩国法律的规定,调解员的选任要求较高,一般是退休法官、教授、工程师等具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在多重制度优势的保障下促使其ADR蓬勃发展。
(五)日本
大陆法系的日本,其较低的诉讼率也得益于其较为健全的ADR模式,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民事和家事调停制度。其法律规定了大多数纠纷的调解前置程序,并规定了一些不参与和履行调解的惩罚措施。
2003年《民事调解法》准许拥有5年执业经验的律师以兼职法官的身份担任调解委员会主任。《民事调停委员及家事调停委员规则》规定从社会各层次国民中选拔调解员,从而确保家事调解员的多样性。
日本民间ADR机构发展迅速,从2007年的10家发展到2018年的180家。2019年修定了《ADR促进法实施指导》,对ADR机构的资质、监管等问题进行了规范。日本政府还通过设计标志图案等多种方式,拉近其与民众的距离。[8]
二、发达国家ADR发展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目前的ADR模式
我国目前的ADR主要有调解、仲裁、信访等相关制度。我国有非常清晰、明确的民商事仲裁制度,多适用于经济纠纷,但相对成本较高,对于一般的社区纠纷并不适用。信访制度主要是针对公共事务管理或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时,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或进行投诉等,从广意上来讲也是纠纷的一种解决方式。
调解是我国目前最为重要的一种ADR模式,其中又包括法院内调解与法院外调解。根据我国民诉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内的调解不仅可以贯穿整个诉讼程序,在一些特殊纠纷中还有调解作为前置程序的相关要求。法院外的调解主要有民间调解、社会组织调解和人民调解。
(二)对如何完善我国ADR模式的启示
纵观域外各国ADR模式的发展,现实动因各有不同,价值追求、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在我国,儒家倡导的“和为贵”是非常重要的传统思想,在我国大力发展ADR模式有非常好的文化传统。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社区纠纷无论数量和类型都呈上升趋势,法院压力逐年增加,在这种大背景下,建立多元化的纠纷化解模式势在必行。但如果没有诉讼压力是否就不必发展ADR呢?从德国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其并未出现“诉讼爆炸”的现象,现实需求似乎并不强烈,但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求反而是重要动因。
1.建立多元纠纷化解机制。要想实现良好的诉讼分流,避免更多纠纷盲目的进入诉讼,就必须建立一个多元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以满足更多样的需求,其中英美法系中的专家决定、中立评估方式值得借鉴。这种程序在纠纷发生后能够给当事人一个专业、中立的分析建议,便于纠纷当事人理性解决纠纷。
2.完善法院内部调解制度。从法院内部附设的调解来看,韩国在其法院内部采用的调审分离制度有一定的科学性,可以避免当事人在调解阶段所做的一些妥协和让步对审判阶段造成一些先入为主的影響。
3.提高调解效率。英、美国家中为提升调解效率并保证调解成果的有效实施,设置了保证金制度、诉讼惩罚制度等。这种规定,充分尊重了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自由选择权,又保证了调解成果的实施效率。
4.人民调解员的职业化发展。在我国,随着2011年《人民调解法》的实施,以及相关民诉规则的修定,人民调解的重要性已被更多人认可。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专业性,提高群众对人民调解的认同感和信任度,调解人员的职业化发展道路更具可行性。韩国对于调解员严格的选拔制度,以及其对调解委员会相对单一、明了的职责定位使其发挥了非常好的纠纷解决作用。此外,日本的兼职法官制度,以及将调解纳入律师工作范围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都发展了自己独具特色的ADR模式,我们可以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逐渐完善我国多元化的ADR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 [美]史蒂文·苏本、玛格瑞特·伍著.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M].蔡彥敏,徐卉,译.法律出版社,2002:205.
[2] 韩红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理论与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81-82.
[3] 于丽娜,聂成涛.社区矛盾纠纷化解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38.
[4] [德]皮特·高特沃德.民事司法改革:接近司法·成本·效率[M]//朱克曼.危机中的民事司法.傅郁林,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223.
[5] 齐玎.德国ADR制度的新发展[N].人民法院报,2010-10-29(8).
[6] 邵建东.德国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律师执业[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52,153.
[7] 骆永兴.德国ADR的发展及其与英美的比较[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8] 齐树洁.日本调解制度[J].调解,2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