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或不当意,宫徵成别调”
——施蛰存先生忆鲁迅及其他
■钱 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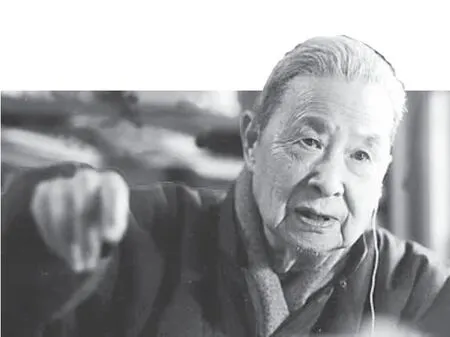
近日偶尔看到一篇题为《施蛰存与鲁迅笔战,鲁迅逝世20年后,他“负荆请罪”成文坛佳话》的文章,作者自称诗人,文中不仅信口开河,谬误百出,罔顾史实,甚至连引起这场“笔战”的上海《大晚报》都误写成了《大公报》,还附了一张旧时《大公报》的影印件,更容易把不明真相的读者引入歧途,产生误解。
施蛰存真的要向鲁迅先生“负荆请罪”吗?笔者以为,这一被遮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的真相应该公诸于众,还施蛰存先生以清白。
“我一直很敬重鲁迅先生”
施蛰存先生曾是笔者大学本科期间的授业恩师。毕业留校后,笔者成了施先生的中文系同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师从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因为跟施蛰存先生熟稔了,曾经很冒昧地问起当年他与鲁迅交恶的原委,他亲口说这其实是彼此误会造成的。
“我一直很敬重鲁迅先生,1920年代末就与他时有往来。我主持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鲁迅先生全力支持。丛书列出12本,鲁迅一人就承担了4本。我1932年主编《现代》月刊,1933年第6期上发表了他的散文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这在当时还是冒一点风险的。”施先生说。
胡乔木先生曾说过:“施先生在《现代》上发表这篇文章,比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它的作用要大得多。”并称赞施先生“您立了一功”!至于后来与鲁迅发生“交恶”风波,则是他完全始料不及的。
查施蛰存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原拟名《新兴文学论丛书》,后因鲁迅先生不赞成用此名称,施先生才改成现在的名称。据施蛰存1980年11月4日所写《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中说,起因是1929年春,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出版了好几种介绍苏俄文艺理论的新著,日本的左翼文艺界称这些为“新兴文学”,将苏俄文学理论称为“新兴文学论”。施蛰存和他的几位大学同窗戴望舒、苏汶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倾向于当时的“新兴文学”,各自购买了日本文论家的几套英文版和法文版的“新兴文学论丛书”,恰逢中共派往上海做“革命文学论争”双方工作的冯雪峰,也从虹口内山书店购买了日文原版书。他们四人都对翻译介绍苏联新兴文论有兴趣。冯雪峰提出各人分工翻译,然后由施蛰存、戴望舒、刘灿波合开的“水沫书店”出版。在此之前,施蛰存他们曾合开过“第一线书店”,出过8期《无轨电车》,其中登载过冯雪峰的《论革命和资产阶级》等。但由于书店不是开在租界而在“中国地界”,在收到警察局送来“查该第一线书店有宣传赤化嫌疑,着即停止营业”的一纸公文后,就不得不歇业了。不久后,他们在日租界北四川路海宁路口公益坊内开设了“水沫书店”。
施先生说:“当时我们考虑了一下,认为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理论是一件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要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先从理论上打好基础。但是我们希望,如果办这个丛书,最好请鲁迅先生来领导。雪峰答应把我们的意见转达给鲁迅。酝酿了十来天,雪峰来说,鲁迅同意了,他乐于积极参加这个出版计划。不过他只能做事实上的主编者,不能对外宣布,书上也不要印出主编人的名字。雪峰又转达鲁迅的意见,他不赞成用《新兴文学论丛书》这个名称。”所以,施蛰存在充分尊重鲁迅意见的基础上,将丛书定名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并由鲁迅和冯雪峰亲自拟定了第一批12种书目,然后各自分工翻译。
这12种书目分别为:⒈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基础》(冯雪峰译);⒉波格但诺夫的《新艺术论》(苏汶译);⒊蒲力汗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冯雪峰译);⒋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鲁迅译);⒌梅林格的《文学评论》(冯雪峰译);⒍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鲁迅译);⒎蒲力汗诺夫的《艺术与文学》(冯雪峰译);⒏列褚耐夫的 《文艺批评论》(沈端先译);⒐亚柯弗列夫的《蒲力汗诺夫论》(林伯修译);⒑《霍善斯坦因论》(鲁迅译);⒒伊力依契、蒲力汗诺夫的《艺术与革命》(冯乃超译);⒓藏原外村的《苏俄文艺政策》(鲁迅译)。在第一辑这12种书目中,鲁迅亲自操刀翻译的就有4种之多,可见他对这套丛书的态度是十分积极和支持的。
从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这套丛书由水沫书店陆续印出了前5种。后来又加进了伊科维兹的《唯物史观文学论》(戴望舒译)和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刘呐鸥译),一共出版了七种。鲁迅译的《艺术论》,后来转给光华书局印行了。后面的几种之所以不能再印出,施先生回忆:“我现在已记不起,不知在什么时候,这个丛书改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大约是在1930年三四月间,可能是由于当时形势好些,我们敢于公然提出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久,形势突然变坏了,《论丛》被禁止发行,第六种以下的译稿,有的是无法印出,有的是根本没有译成。”
1929年国民党控制的中央宣传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同年还颁布了《新闻法》与《出版法》,后者规定凡涉及“党义”的图书须交中宣部审查,实际上,文艺、哲学及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也一样要送审。所以,打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旗号的图书,自然是在被禁之列了。
施蛰存先生还提及关于鲁迅翻译的《文艺与批评》在排印时的一件往事:“鲁迅提出要加入一张卢那卡尔斯基的画像。我们找了一张单色铜版像,他不满意,并送来一张彩色版的,叮嘱要做三色铜版。我们尊重他的意见,去做了一副三色铜版。印出样子,送去给他看,他还是不满意,要求重做。铜版确是做得不很好,因为当时上海一般的制版所,对于做三色铜版的技术还不够高明。这副三色版印出来的样页,确实不如原样。但鲁迅送来的这一张原样,不是国内的印刷品。因此,我们觉得很困难。送到新闻报馆制版部去做了一副,印出来也还是不符合鲁迅的要求。最后是送到日本人开的芦泽印刷所去制版,才获得鲁迅首肯。今天如果还有人收藏鲁迅这本《文艺与批评》,请欣赏一下这一张插图画像,这是当年上海所能做出来的最好的三色版。”
事隔半个多世纪后,施先生还很钦佩地说:“鲁迅有极高的艺术欣赏力,他也极其热爱艺术。他对于书籍的装帧插图,从来不随便。”
甘冒风险发表《为了忘却的纪念》
1932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大型文学期刊《现代》创刊。当时,日军轰炸闸北、分三路向上海中国驻军发起进攻的“一·二八”硝烟尚未散去,而在国民党当局的政策压制下,一些左翼文艺刊物,如郁达夫等编辑的《大众文艺》、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等,均被查禁。鉴于此情形,现代书局的两位老板洪雪帆和张静庐便考虑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纯文学刊物,能够持久地按月发行,使门市维持热闹而带动其他出版物的销售”。于是,他们物色了施蛰存出任主编。那时,他不是左翼作家,虽然才28岁,但已在上海办过两家出版社,编辑过两份期刊。尤其是水沫书店,办得风生水起。施先生吸取了第一线书店的教训,将水沫书店开设在日租界公益坊内,不用登记,店又设在弄堂内石库门房子里,为了不引起闲人注意,只在门上挂一块很小的招牌。1929年至1930年,水沫书店相当热闹。那时常有作家到店里来闲谈或联系稿件,包括徐霞村、姚蓬子、钱君匋、谢旦如等,胡也频和丁玲也来过。而冯雪峰是水沫书店的常客。所以,《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可谓最佳人选。

1934年的施蛰存先生
施先生创办《现代》,他在《创刊宣言》中说:“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施先生的编辑方针是想把《现代》办成“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从此,“施蛰存这个名字和《现代》杂志紧密相连,也和中国现代文学不可分割。”正是本着这样海纳百川、大气融合的编辑立场,鲁迅、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张天翼、周起应、沙汀、楼适夷、郁达夫、巴金、老舍、戴望舒、穆时英、杜衡、沈从文、周作人、李金发、苏雪林等不同倾向的作家都在《现代》上发表过作品。茅盾的《春蚕》、郁达夫的《迟桂花》、张天翼的《仇恨》、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巴金的《海底梦》、老舍的《猫城记》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名篇佳构都始发于《现代》。然而,在这些作者中,施先生对于鲁迅先生的文章格外器重,总是想方设法尽快刊发。除了《小品文的危机》是杜衡约来的稿外,据初步统计:施蛰存为当时处境艰难的鲁迅在《现代》上发表文章或报道计有:《论〈第三种人〉》(第2卷第1期)、《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第3卷第1期,同期刊出鲁迅等译《果树园》短篇小说集广告)、《关于翻译》(第3卷第6期)、鲁迅译德国毗哈的《海纳与革命》(第4卷第1期,同期刊出鲁迅编译的两本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和《竖琴》的广告,同时刊发施蛰存亲自写的有关这两本书的简介) 等。其中有三篇被排在当期之首。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那篇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文尾附记的写作日期是“二月七~八日”,而发表日期,是于1933年4月1日出版的《现代》杂志第2卷第6期。从收到稿子、编辑再到发排、付梓,一个多月应该算是快的。然而,施蛰存先生后来有过这样回忆:“我在二月二十八日写的《社中日记》里曾交代过,大意说此文本来应当在第五期上发表,但是因为文稿到达我手里时,第五期已经排版完成,来不及补编进去,不得不搁迟一个月,才能和读者见面。”据施先生说:“鲁迅给《现代》的文章,通常是由冯雪峰直接或间接转来的,也有托内山书店送货员送来的,但这篇文章却不是从这两个渠道来的。”
鲁迅为什么在完成此文后没有直接将稿子转送给《现代》发表?查《鲁迅日记》,1933年2月7日,他写道:“下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这说明《为了忘却的纪念》在2月7日已经完成,为何却注明“二月七~八日”?施先生后来分析鲁迅的用意:“我以为,鲁迅这样记录,并非表示这篇文章写了两天,而是因为文章中说:‘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可知鲁迅对柔石被害的准确时日,并不明了。鲁迅虽然在日记中写了‘前年是夜’,在文尾却更准确地写了‘二月七~八日’。可见鲁迅这样写的意义,还是为了‘记念柔石’。”
那么,施先生是何时收到鲁迅的这篇文章的?他说过:“如果在二月十五日或迟至二十日以前交到我手里,我一定有办法把它排进三月份出版的第五期里,让读者可以早一个月读到。但是事实上我收到这篇文章已在二月二十日以后。”如今,我们也和当时的施先生一样疑惑:“从二月九日至二月下旬这十几天里,这篇文章在哪里呢?”
众所周知,1931年2月上旬,殷夫、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在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被枪杀,鲁迅曾经强抑愤怒和悲痛的心情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发表于当年4月出版的《前哨》月刊“纪念战死者专号”上。但在那篇文章里,鲁迅虽然悲愤难抑,控诉了“敌人的卑劣的凶暴”,但用的是笔名“L·S”,文中也没有提起这几位“左联”青年作家的姓名。但在两年之后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虽然鲁迅竭力保持“沉静”,并没有像《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那样地厉声痛斥“敌人的卑劣的凶暴”,而是絮絮地叙述着他与柔石、殷夫之间的友谊和交往,完全像是一篇纪念青年文友的悼亡之作。但在此文中,鲁迅不仅明文写出了“左联五烈士”的真实姓名,写明了他们被害地点和遇难时间,还写出了他们被捕后遭到迫害的情景。这些都是以前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透露的,在鲁迅的文章中也从来没有如此直言无忌。施蛰存先生忆道:“那一天早晨,我到现代书局楼上的编辑室,看见有一个写了我的名字的大信封在我的桌上。拆开一看,才知道是鲁迅的来稿。问编辑室的一个校对员,他说是门市部一个营业员送上楼的。再去问那个营业员,他说是刚才有人送来的,他不认识那个人。这件事情很是异常,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后来才听说,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
收到鲁迅的文章后,施先生起初“也有点踌躇。要不要用?能不能用?自己委决不下。给书局老板张静庐看了,他也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于是,我把这篇文章编在《现代》第二卷第六期的第一篇,同时写下了我的《社中日记》。”即第五期已经排版完成,来不及补编进去的说明。
施先生还回忆道,“为了配合这篇文章,我编了一页《文艺画报》,这是《现代》每期都有的图版资料。我向鲁迅要来了一张柔石的照片,一张柔石的手迹(柔石的诗稿《秋风从西方来了》一页)。版面还不够,又配上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这是鲁迅在文章中提到并曾在《北斗》创刊号上刊印过的。但此次重印,是用我自己所有的《珂勒惠支木刻选集》制版的,并非出于鲁迅的意志。这三幅图版还不够排满一页,于是我又加上一张鲁迅的照片,题曰:‘最近之鲁迅’。这张照片,并不是原件,是我在仓促之间从鲁迅和别人合摄的照片上剪截下来的。我现在已记不起原件是什么样子,仿佛是鲁迅在宋庆龄家里和萧伯纳合摄的。但并不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那一张。那一张是鲁迅、萧伯纳、蔡元培三人的合影,就是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提到过的。在那一张上,鲁迅的姿势不是这个样子。萧伯纳是在同年二月十七日到上海来的,所以我题作‘最近之鲁迅’”。

施蛰存先生墨迹
这就是当年的施蛰存为发表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的“内幕”,他不但冒了很大风险,而且还根据文章内容尽了最大努力为此文配上了照片、墨迹与图画,起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文坛“公案”实乃彼此误会
既然施蛰存先生无论对鲁迅本人还是对其文章如此尊重和重视,甚至不惜甘冒风险发表别家刊物不敢发表的敏感文章,为何仅仅在数月之后会发生那场令人瞠目结舌的“交恶”风波呢?笔者问过施先生,他说:“这是彼此误会造成的,可惜后来没机会解释清楚。”
1933年9月,施先生收到上海《大晚报》副刊《火花》的编辑崔万秋寄来的一份类似问卷调查的《读书季节》的邮片,要求收件人在“欲推荐青年之书”栏填写:(1)目前正在读什么书;(2)什么书可以介绍推荐给青年。近代以来,欧美各国由于新闻出版业日益兴盛,为扩大影响力,请杰出学者、著名文人在报刊上为青年学生或一般读者开列阅读书目早已蔚然成风。我国自晚清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一书问世后,流传颇广影响极大。此后近百年来各报刊、书局也常热衷于请文化名人开列书目,以飨读者。
因此,施蛰存在收到荐书表格后便逐栏填写。他在答复“欲推荐青年之书”一栏时,填上了《庄子》和《文选》(并注明: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除此以外,他还填了《论语》《孟子》《颜氏家训》;在“我现在看的书”一栏填上了英国心理分析实验批评家李却兹《文学批评之原理》的英文版,以及北凉时期中天竺僧人曇无谶所译古印度杰出诗人马鸣以诗体记颂释迦牟尼生平的《佛本行经》。表格寄出后,他也没特别在意。《大晚报》于当月29日刊出。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随手写下的这几种书目,尤其是《庄子》和《文选》,之后会引发文坛上的一场轩然大波,以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10月6日《申报·自由谈》上,鲁迅以“丰子余”为笔名发表了杂文《感旧》,文中虽未点名,但语词激烈:指出“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讽刺这是“‘骸骨的迷恋’”,不仅有“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施先生看到了此文,他说并不知道作者是鲁迅,当时为《申报·自由谈》撰稿的作者有很多。他当即写了《〈庄子〉与〈文选〉》一文作出申辩和说明,并投给《申报·自由谈》,此文于10月8日刊出:
今天看见《自由谈》上丰之余先生的《感旧》一文,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
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对于丰先生有什么辩难,我只想趁此机会替自己作一个解释。
第一,我应当说明我为什么希望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
第二,我应当说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为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在此文中他还举鲁迅为例,说:“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可能是鲁迅先生误会了,以为施先生带有揶揄嘲讽之意。他接连写了《“感旧”以后》上篇和下篇,再度提出批评。年少气盛的施先生又发表《我与文言文》等几篇文章,对此进行答辩,说:“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当然也“并不是主张完全摹仿古文学,或因袭古文学”。
施先生说,直到今天他也不明白推荐青年读《庄子》《文选》错在哪里。查施蛰存为此除发表了《〈庄子〉与〈文选〉》《我与文言文》外,还陆续发表了《推荐者的立场》(10月19日《大晚报·火炬》)、《致黎烈文先生书》(10月20日《申报·自由谈》)、《关于围剿》(《涛声》杂志第2卷第46期),表明他的本意“决不是说每一个青年只要看这两部书,也并不是说我只有这两部书想推荐。大概报纸副刊的编辑,想借此添点新花样,而填写者也大都是偶然觉得有什么书不妨看看,就随手写下来了”;自己因为从“做国文教员转到编杂志”,在书目表格上填了《庄子》《文选》,仅是为“青年从做文章(或说文学修养)上着想”。鲁迅仍以“丰之余”笔名接连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感旧〉以后(上)》(10月15日)、《〈感旧〉以后(下)》(10月16日)、《扑空》(10月23、24日)、《答〈兼示〉》(10月27日),严厉斥责施蛰存为“遗少群中的一肢一节”,“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成洋场恶少了”。

1980年施蛰存先生在北京
这就是鲁迅与施蛰存“交恶”的来龙去脉。这场文墨官司,按照施蛰存的天真想法,是“两个人在报纸上作文字战,其情形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这种文人间的笔战,在当时是极为稀松平常的。施蛰存先生的多年挚友、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教授曾评论这场文墨官司:“一位从近处想,读点古书对青年写作有助,一位从远处想,提醒青年不要沉到古书中去,原都有善意在,并不复杂。”施先生后来说,当他得知“丰子余”是鲁迅先生时,曾经想找机会去鲁迅家,想跟他当面解释,可惜没见着,谁知这以后他竟因此顶着“洋场恶少”的骂名蒙冤遭难数十年。
谈及此冤,施老对笔者说:“不值一提,我比鲁迅先生活得长。”他还说,鲁迅虽然脾性刚硬,但还是有雅量的,在出版《准风月谈》时,他把《〈庄子〉与〈文选〉》作为附文收在里面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来龙去脉即是如此。
《吊鲁迅诗并序》与“九死不违道”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于上海虹口区山阴路132弄8号大陆新村家中与世长辞。此后,施蛰存永远失去了向他所敬重的鲁迅先生当面解释并为自己少年气盛而撰文论争致歉的机会。随着鲁迅作为“民族魂”的评价与地位越来越高,被他生前痛斥为“洋场恶少”的施蛰存,在此后长达70年的岁月中,即使后半生的日子十分艰难,他也从未对鲁迅先生表示过任何不敬,无论在其文章中,还是在其言语中。
笔者与他“笔谈”多次,曾听过他对巴金、沈从文、丁玲、胡也频、穆时英、刘呐鸥等文友的真率评价,比如,对于1980年代沈从文及其作品受到文学大师般高度评价和礼遇,他并不趋炎附势,他说:“从文虽然自己说永远是个乡下人,其实他已沾染到不少绅士气”,“早年,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气,似乎已消磨了不少”。还说“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1940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等,一点都不为老友避讳。沈从文去世之后,巴金写了《怀念从文》,我与施先生“笔谈”时提及此篇情真意切的散文,问他是否看过。他点头道:“巴金复出以来,一直说要讲真话,我以前不信,看了他写的《怀念从文》,我相信了,他说的是真话。”但对于鲁迅先生,他从未有过任何怨气与不敬,相反提到鲁迅时,他总是给予鲁迅先生及其文章以高度评价。
1956年10月14日,鲁迅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移出,落葬于虹口公园(现改名为鲁迅公园),并在鲁迅墓旁新建了鲁迅纪念馆。施蛰存先生曾拨冗亲往瞻仰参观,并口占长诗一首,即《吊鲁迅先生诗并序》,以表明对鲁迅先生“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崇敬之情。这首长诗的序文不短,其中写道:
余早岁与鲁迅先生偶有龃龉,竟成胡越。盖乐山乐水,识见偶殊,宏道宏文,志趣各别。忽忽二十馀年,时移世换,日倒天。昔之殊途者同归,百虑者一致。独恨前修既往,远迹空存,乔木云颓,神听莫及。丙申十月十四日,国人移先生之灵于虹口公园,余既瞻拜新阡,复睹其遗物。衣巾杖履,若接平生,纸墨笔砚,俨然作者。感怀畴昔,颇不能胜。夫异苔同岑,臭味固自相及,山苞隰树,晨风于焉兴哀,秉毅持刚,公或不遗于睚眦,知人论世,余岂敢徇于私曲。三复逡巡,遂怆恨而献吊云。
全诗如下:
灵均好修,九死不违道。渊明矢夙愿,沾衣付一笑。谔谔会稽叟,肝胆古今照。沥血荐轩辕,风起猛虎啸。高文为时作,片言立其要。摧枯放庸音,先路公所导。鸡鸣风雨晦,中夕设庭燎。幽人苦夜长,未接杲日耀。我昔弄柔翰,颇亦承馀教。偶或不当意,宫徵成别调。我志在宏文,公意重儒效。青眼忽然白,横眉嗔恶少。来二十年,世变如奔瀑。终见天宇净,公志亦既造。井蛙妄测海,转自惜。犹期抱贞素,黾勉雪公诮。今日来谒公,灵风动衣帽。樽俎见平生,诗书孰宿好。感旧不胜情,触物有馀悼。朝阳在林薄,千秋励寒操。
此诗与序文写得辞恳意切,这在施蛰存的诗文中并不多见。施蛰存先生对于古体诗词,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其所著60万字《唐诗百话》,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初版2.5万册,再版5万册,短期内即销售一空。这本书2014年9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最新修订版,页数厚达884页。可见其对古诗艺术鉴赏力之高与影响力甚大。许多人往往只见“青眼忽然白,横眉嗔恶少”,却不懂“我昔弄柔翰,颇亦承馀教。偶或不当意,宫徵成别调”。更不懂事隔20多年后,施蛰存来拜谒鲁迅新墓和鲁迅纪念馆,“今日来谒公,灵风动衣帽。樽俎见平生,诗书孰宿好。感旧不胜情,触物有馀悼”。他悼念鲁迅先生的情愫与衷肠,至死都没变。

1989年4月8日本文作者与施蛰存老师合影于施宅

1999年2月20日施蛰存先生在赠书《施蛰存散文》扉页签名
钱谷融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与施蛰存先生共事半个多世纪,他曾经这样评价施先生,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用自由主义的眼光观察、衡量一切。重性情,讲趣味,热爱与追求一切美的东西。他对待生活,就像对待艺术一样,随时随地都在追求生活中的趣味,生活中的美”。施先生宅心仁厚,富有情趣;而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嫉恶如仇,这也正是他们两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吧。
1993年6月29日晚,在上海商城剧院举行的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奖颁奖典礼上,年近九旬的施蛰存先生被授予该文学艺术奖项中规格最高的“杰出贡献奖”。这是上海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奖。1995年4月,年逾九旬的他又荣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授予的敬慰奖和“中国新文学大师”荣誉称号。笔者以为,倘若九泉之下的鲁迅先生有知,想必也会一笑泯恩仇吧。
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先生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9岁。凑巧的是,他与鲁迅先生同是19日那天去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