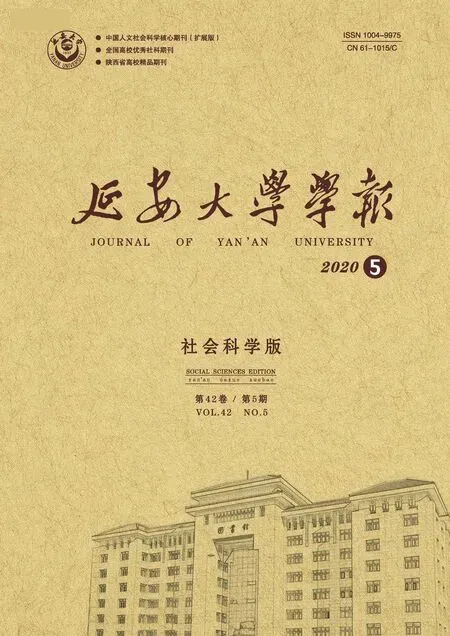简析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筹备与建设
曹 琪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七七事变后,大批知识分子陆续从全国各地奔赴边区,至1938年迎来了一个高潮,“当年夏秋间奔赴延安的有志之士可说是摩肩继踵,络绎不绝。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1]这批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拥有大学或中学教育背景,构成了边区核心技术人员队伍。随着抗战形势恶化,国共摩擦加剧,党中央开始有意识地将在延技术人员组织起来,抽调至一线开展边区建设,筹建了一批军用和民用事业,可视为党和政府在边区组织科技人员开展科技事业的有力尝试。
1939年4月,边区工业展览会召开,中央由此看到了培养技术人才的重要性,拟在既有人员、组织基础上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起初,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准备搞成延安各学科科学技术专家汇聚一堂,从事科学研究的活动中心,也是延致外来科技人员的重要场所。(1)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可被视为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前身,关于该院的具体情况,参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院近期在延安成立》,《新中华报》1939年5月30日。然而随着边区形势日益严峻,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兴办自然科学研究院吸引外来研究人员赴延已经无法实现,而仅仅依靠延安现有人员开展各项科技工作和科学研究,仍远远不够。在此情形下,党中央积极向科学技术人员征询关于边区物质、经济建设的相关意见,决议以现有科技人员为师资,以科学院为基地,既从事科研实验,又大力培养科技生力军。1939年12月25日至31日,党中央责成中央财政经济部召开自然科学讨论会,自然科学研究院全体人员及各机关学校共百余人参会。会上提出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改造为“延安自然科学院”,作为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高等学校;同时另开设“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发挥研究院原本的学术研究功能。自此,“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遂改办为“延安自然科学院”,成为一所理工类高等大学。
针对困难时期是否有必要耗费人力、物力兴办这样一所科技教育机构,以及能够办到什么样的规模,舆论各界一直存在质疑。然而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基础设施建设、招生、教师团队建设等各项工作均顺利开展,于1940年9月正式开学,并迅速成为延安地区的核心科技教育机构,为边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拟结合相关史料对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筹备和建设过程进行探讨,对其历史意义进行反思,揭橥党和政府对于边区科技发展的政策鼓励和保护作用。
一、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基础设施建设
自然研究院最初隶属于中央财政经济部,由李富春担任院长,陈康白担任副院长,屈伯川担任教育处长,卫之任干部处长,陈宝诚、杨作材任院务处长负责筹建。在筹备之初,陈云针对筹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求全、不切实际等问题与筹备组开会商议,“教育大家要根据实际情况办校,不要搞得过份。他强调,要在边区办工业,培养人材,就必须根据延安的情况、边区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办学校。富春同志还提出,边区怎样搞科学和发展经济?就是要从小慢慢发展,不要一下子就搞得过大”。[2]279这次会议为自然研究院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基于党中央的指示,从1940年初至是年9月,筹备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为该院建设了一批基础设施,初步奠定了办学所需的物质基础,下文就筹备过程进行讨论。
(一)择选校址
自然研究院择选校址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兼建设厅长高自立亲自率领筹备处成员前往选址,一直热心边区建设的新西兰友人艾黎也参与了相关工作。1940年元旦前后,院址选定杜甫川口(亦称“马家湾”)中央西北局与光华农场之间。学院建成后可面杜甫川而立,师生们盥洗、饮水都可以直接汲水于此。溯河上行即是附属于该院的光华实验农场,环境幽静,确是“烽火硝烟中可供学习和研究的一方净土”。[3]502
(二)募集资金
院址选定之后,中央批拨了建设经费,由陈宝诚、谌亚选等人负责进行土建工程。除中央拨款以外,该院的建设还极大地得益于国际援助。新西兰人艾黎热心边区建设,曾在1939年和1940年两次到延安,为各项事业捐款,总计数额巨大,据黎雪回忆,具体情形如下:
1940年春节,在一次席间,富春同志对他说,我们成立了自然科学院,为边区培养人材。艾黎同志很支持,表示他可以帮忙,可以捐款。最初,他从南洋群岛募捐了一笔钱,开始拿出一千多元(美金),三百多元给“工合”,一千多元给学校,解决了不少问题。艾黎同志的母亲,对艾黎的事业很支持。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很热心,当时已86岁高龄,在新西兰骑着脚踏车到处为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搞募捐。后来,把她的养老费也送到了延安,捐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艾黎同志的母亲是新西兰妇女解放先锋社队员。她的捐款是经周恩来同志送到的,有一部份是我和芦广绵同志一起带到延安的,我曾排过几千美金到延安。还有些捐款在经过宝鸡时,被国民党分走了一些。艾黎同志的母亲第一次送到延安的捐款记得是九千五百美金,用于办自然科学院、光华农场、振华造纸厂、桥儿沟肥皂厂、难民工厂等。后来,林伯渠主席和曹菊如(当时任边区银行行长)、李富春同志商量,决定把这笔钱主要用在建设自然科学院和光华农场,其他几个工厂少给点。边区政府可以给予投资。第二次送到延安的捐款大约是五千多美金。用在建设自然科学院和光华农场的捐款总起来有一万五千多美金。那时,这笔钱来之不易,而且也很值钱,中央把这笔钱主要花在办学、培养人才上,是很有远见的。[2]380
(三)抽调人员
1940年春节后不久,陆续有学员及教职员被调配到科学院参加建设,教员多为大学毕业生或肄业生,学员多为中学生。最早参加筹建工作的有陈康白、刘咸一、陈宝诚、杨作材、汤钦训、王勋、黎雪等人,陈康白负责组织和领导,黎雪负责人事工作,“先后把林引、石英、李丹、易峰、武衡、谌亚选、华寿俊、王士诊、李苏、林华、彭克谨、胡科、祁君、乐天宇、徐伟英、林宁、朱光、汪鹏(王家宝)”[2]378-379等人员借调过来参加筹备。
上述人员都是当时延安在各领域的专家,能够汇集一堂参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设,充分表明政府对于发展科学教育的决心和信心。但即便如此,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如延安在建筑工程方面缺乏专业人才,负责自然科学院建筑工程的杨作材是3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但并非建筑专业出身,只是因为对建筑史很感兴趣,具备一些房屋设计和制图技能,就被抽调到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参与筹备工作了,(2)杨作材曾在《我在延安从事建筑工作的经历》一文中详细回忆了此段经历,参见杨作材《我在延安从事建筑工作的经历》,师秋朗《心向延安:延安自然科学院校友足迹点点》,延安大学北京校友会1990年版,第7-8页。也反映了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在怎样有限的客观条件下自力更生进行建设的。
(四)校舍建筑
在校舍建筑方面,延安自然科学院也得到了政府的优待。若按抗大、陕公等学校的先例,窑洞应基本靠本校师生员工自己动手建造,边区政府只给很少的开办费。但中央对于自然科学院予以特别优待,基本上全由政府拨款雇工、买料兴建,师生员工只需做些管理工作和辅助劳动,如修整公路、修建厕所、开辟场地等。
从1940年初至8月底,筹备工作大体就绪,校舍建设已初具规模。新建窑洞约50余个,用作教室、办公室、学生及教职工宿舍,“教师三个人住一个窑洞,学生八个、十个、十几个住一个窑洞”[4]。此外还特别打了几个大窑洞充当大教室、图书馆。另在山下平地修了约30余间平房,用于机械实习工厂和开大会使用。1940年底,该院另外盖了一所两层高的石头房子,一楼作实验室,二层作图书馆。由于中央的特别关照,在1941、1942年边区财政经济最困难之际,科学院已有相当数量的房屋、窑洞,生活和学习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中央为了进一步改善其教学、科研设施,继续拨给经费。1941年10月底,该院“兴建了一幢全延安少有的高大建筑”[3]505——科学馆,内设教室、实验室等设施,作为学校集中上课、实验、阅览、开会的场所;又分配给生物、化学等系几个最好的窑洞作为化验、标本专用室。至此,大学部的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系都建立了简单的实验室,能够开展一些实验教学。
(五)教材和仪器购置
相比于基础设施建设,更难以克服的困难是教材和仪器的采买。在战乱之中购置各类科学仪器本已不易,何况当时边区还受到严密封锁。延安自然科学院早期设备主要来自友党(人)捐献、公开征募、政府筹集、教师自筹四条途径。
相当一部分仪器设备系利用艾黎的捐款购得,物理、化学仪器基本上都是艾黎亲自从香港、国外筹办的,其中包括放大200倍的显微镜等先进仪器。部分仪器来自于教员捐赠,例如,黎雪“把从上海带来的计算尺、制图仪器(都是价钱比较贵的精密仪器)都送给了学校。还有一台英文打字机也送给了学校……当时也是非常稀缺的”。[2]381另外,自然科学院还派黎雪等人几次外出到西安、郑州、洛阳等地采购仪器,如1940年八九月间,黎雪与聂春来、崔中、王克等人一起到外地买了几箱子仪器,缓解燃眉之急。
为帮助该院搜集图书资料,边区政府也动用了多种渠道。有学员谈到,“由于图书缺乏,常常从毛主席的藏书中借来有关书刊进行学习”。[3]504周恩来特别关注该院的发展,曾多次委托后方人士进行采购。据司徒慧敏回忆,1942年至1943年,他因病留在桂林休养,周恩来托人带信请他在桂林、柳州以至于广东曲江一带大量搜集购买科学技术书籍。当时正值香港沦陷,由港入内地的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教育界人士为数众多,当这些知识界人士旅费耗尽逼不得已之时,只得把书籍连同衣物变卖给当地旧书店或随处摆地摊出售。司徒慧敏等人通过这一途径搜集书籍,所获绝大部分是大、中学的数、理、化教材,工业、医药技术的教材及其参考图书。后来重庆方面希望书籍范围应当尽量宽广,应包括动植物、矿物、天文、地理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而且除中文图书外,还要收集外文书籍。(3)参见司徒慧敏《周恩来同志为建立自然科学院尽心尽力侧记》,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四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239页。因此,除了经典的中文教本以外,科学院得以用上一批专业性较强的英文原版课本,如谈明《化学》、达夫《物理学》、克兰威尔《微积分》之类,为教学的开展提供了极大便利。
除了上述渠道,该院还通过社会征集的方式募捐图书、仪器。1940年5月至8月,该院在《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上连续刊登图书、仪器募捐启示,(4)启事原文:“本院筹备工作行将就绪,开学在即,急需各种小学、中学、大学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教本和参考书,以及各种仪器和图表,热烈希望各界人士、各学校机关团体热心赞助,慷慨捐赠,凡科学图书仪器,无分新旧,不拘中西,均甚欢迎。如需付给相当代价,索价出让亦无不可,务希各界先进本提高科学之精神,发展科学教育,赞助本院之创立和发展,以期发展科学之威力,挽救民族于危亡,达到抗战建国伟业之彻底胜利,是为至盼。征求办法:一、捐赠:凡欲捐赠本院图书仪器者,请函通知本院以便着人来取。或将捐赠物品交通讯处直寄本院,由本院登报鸣谢;二、交换:凡欲将自然科学图书仪器与本院交换社会科学图书者,请直函本院接洽;三、出让:凡欲将科学图书仪器割爱出让者,亦请来函接洽,本院可酌给相当代价售卖”。(载《新中华报》1940年8月9日)。该院还于1942年8月10、12、16、18、19日的《解放日报》上登载“自然科学院征购图书启事”,希望各界有自然科学书籍、图表愿意割爱出售或捐助者,开列书目或面洽该院教务室。希望各界同仁能够通过捐赠、交换、出让三种方式广施惠赠,陆续得到来自各方的反馈。本次征募,总计获捐图书、仪器情况粗见表1:
该院成立前既已获捐的书籍及各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捐款、捐图书仪器数量亦较为可观,但名单无法统计。另有一些图书、仪器为科学院从出让者折价购得,包括计算尺一具、棱镜罗盘仪一具、绘图仪器二具、跑表一具、英文达夫《物理》一册、两脚规、英文《科学通论》一本等。(5)参见《新华日报》1940年10月27日。
虽然自然科学院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一部分图书、仪器,仍然远远不足,教师需要自己动手做黑板、写教材、刻蜡板、印讲义,做生物实验用的标本,造物理和化学实验用的仪器等,有时还组织学生一起动手。例如,地矿系主任张朝俊和学生一起用高粱杆制作各种矿物晶体模型;教员武衡亲自带领学生到山谷中采集地质标本以充教学之用;化工系教员恽子强编写了《半微量无机定性分析》课本;学习生物所必需的《生物分类检索表》由生物系学员任炎誊写,每人发一册;力学教师武可久因为用英文授课,利用课余时间编订英文教材等等。为解决自然科学书籍匮乏之弊,1941年1月30日,该院同人联合延安自然科学界成立了“自然科学编译社”,拟着手编译各种教本。推举徐特立任社长,康迪为副社长,下设生物、化学、物理、数学等部门,社址就设在科学院内。(6)关于该社的详细情况,参见林珂《生物研究所、编译社成立》,《新中华报》1941年2月12日。
为解决物质条件匮乏、基础设施不足,自然科学院同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这一过程中,中央也在资金、设备、人力等方面给予了很多特别关照,可见党和政府对创办高等科学教育机关的高度重视。这种政策倾斜甚至引起了其它单位的“不满”,认为自然科学院存放于“石头房子”(科学馆)中的仪器图书“来历不明”而与时任副院长徐特立争吵,有意争抢,后毛泽东亲自出面平息风波。[5]
二、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教师群体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一所集研究与教学双重职能为一身的高等教育机构,除了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是组建一支教师队伍。边区人才紧缺,即使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由于部队和地方都急需人才,也难以分配到学校中来,据1941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不完全统计,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学有专长的、大学程度以上的科技人员共有330名。其中,理科110人,工科120人,医科55人,农科45人。当时这些科技人员的工作情况是:“经济建设工作90人,科学教育工作55人,医务工作55人,农业45人,还有20人在学习,其余110人分别在党、政府、军队中担任工作”[6],可见,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仅占其中很少一部分,而能胜任大学教师者,无疑更为稀缺。为使延安自然科学院拥有相对坚实的师资,中央组织部特从延安的机关、部队乃至后方抽调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科技人员来院任教,由于此时从外地陆续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已经空前减少,只要合乎条件都尽量介绍来此工作。
截止1940年9月开学时,该院教师约二十余人,此外还有政工人员和行政干部十余人。其中部分教员及其简历可见表2:

表2 延安自然科学院部分教师简历表
由上表可知,延安自然科学院汇集了一批拥有高等学历和科学从业经验的核心人员充任教师,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具备科学教育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科学理论课程的专业性,也可部分弥补由于物质条件缺乏造成的限制。当所需课程没有合适的教师来教授时,还会临时外聘校外教师,如生物系专门聘请了边区政府建设厅孙齐东任气象学教师。(7)参见牛东辰《回忆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学习生活片段》,华北大学农学院院史编委会《华北大学农学院史记1939-1949》,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随着学员水平的逐渐提高,可以充任教员以弥补师资力量的缺乏,如生物系高年级学生彭尔宁有时到药物学习班讲授药用植物学,也通过教学强化了自身专业水平。(8)参见彭尔宁《延安自然科学院——我的母校》,《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502页。
三、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招生工作
延安自然科学院作为一所学校,招收一批有一定学习基础且有学习热情的学员是开展教学的基础。作为该院创立伊始的首次招生,主要采取了向社会公开招考和由各单位抽调两种方式。
该校拟于1940年9月开学,早在5月17日筹备未就绪之际就在各报刊登出招生启示。鉴于人才不足,本次公开招考,鼓励所有学历合乎要求者尽可能报名,虽然也采取了考试的形式,但录取率较高。据参加招考的学生林伟回忆,他原在陕北公学学习,5月间看到“青年技术学校”(为了对外宣传方便,早期自然科学院对外宣传曾采用青年技术学校(DFE)的名号,学院的大门上也挂着“青年技术学校”的招牌)的石印招生广告,因为自己喜欢数学,想打好基础,就与同学海青云、彭尔宁、焦成等7人一起报名了。6月中旬考试,当月末众人均收到了录取通知。(9)以上据林伟的个人回忆,参见林伟《忆自然科学院发展中的一些情况》,《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429页。彭尔宁自言自己是一个四年肄业的文科生,如今变为理科学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3]502
单位抽调主要是从机关或同级学校中挑选较为优秀老成的骨干和模范同志前来深造。例如刘致中当时“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被评为模范并保送到自然科学院深造”。[7]1940年5月,陈康白至晋西北招生,“中共晋西区党委区乡干部培训班学员肖田、王玉珍、杨如彭等一起被党委组织部选送到自然研究院学习”[8]三人之前一直在党内担任机要工作。从同级学校被抽调而来的学员包括前已提及的付乃时、周驾彦、胡既全、许明修等人,许明修当时正在泽东青干学校学习,调到科学院后,随即被委以重任接收改造科学院实习工厂(下详)。贺敬之当时也从抗大被抽调到初中部读书,但由于对数理化实在兴趣全无,学校很快同意他转学到鲁艺。(10)参见李群林《发扬我党“人尽其才”的优良传统》,《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455-457页。
科学院还接纳了一批自愿转学的青少年,冯毅当时是子长县完全小学的毕业生,因为参观了延安的各类学校之后,拿着学校的介绍信欲投考“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偶遇小学同学,对方告诉他“这个学校出来能当工程师”[9],遂进入了初中预科班;翟作军原本在边区师范学习,看到一些同学转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就给主席写信求助,也如愿转入自然科学院。(11)参见翟作军《一步登天》,《心向延安:延安自然科学院校友足迹点点》,第136页。
起初科学院并无初中部,但因为缺乏生源供应,不得不自办附属中学,为大学部培养后备人才。1940年9月开学以后至1940年末,陆续录取了一部分不够预科文化程度的学生成立了初中补习班。这批学生包括安塞保育院小学毕业生约35人,大多为烈士子女或敌占区、在国民党后方工作的干部子弟,多为十二三岁的少年,如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李鹏(李勋烈烈士之子)、彭士禄(澎湃烈士之子)等。(12)参见周瑞安《黄墨滨深情回忆延安自然科学院》,《世纪行》2009年第6期。此外,还有一批从部队调来的有工作经验的“红小鬼”,如陆标、刘金福、王一哲等。(13)参见陆标《熔炉——怀念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524页。
可以看出,此前边区由于缺乏科技人才教育机构,无法满足知识青年的学习需求,而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立无疑为这批知识青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深造机会,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组织抽调、学生自愿报考、转校等方式,很快就招收了一批学生。但是由于缺乏稳定的生源和完善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学生来源非常复杂。以初中部二班为例,这个班约有五六十人,其中谢绍明、聂承在、艾政等17人是保小毕业生,李鹏、李润修等7人来自后方的重庆育才学校,黄鲁、伍毅鸿等17人来自敌后和蒋管区,吴锦春、马济元等7人是从工作岗位上抽调而来,邓镇、藩萍2人来自香港。(14)参见艾政《永难忘怀的三年》,《心向延安:延安自然科学院校友足迹点点》,第52页。由于学生来源不同,各班文化程度不齐,差异很大,也为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由于班级同学都勤奋努力,热情无私,通过互相补课的方式来部分弥补。
四、延安自然科学院下属实习工厂的创办与经营
延安自然科学院建立的初衷为培养科技人才,促进边区工农业经济发展,以求缓解和摆脱危机。因此从建院伊始就有明确的发展指向,将教学、科研、工作、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为便于开展教学实践,该院在筹办阶段相继接收、改造、营建了一批直属工厂,使师生通过参加生产、改进技术得到实习和锻炼,也能切实为改善边区经济作出贡献。
1939年5月起,自然科学院的技术人才已初步集结,但当时科学院尚在筹建,除了留下必要的建设人员以外,部分研究人员暂时集中在难民纺织厂、安塞沟槽渠振华纸厂进行生产调研。造纸厂从筹建到原材料开发,自然科学院的筹备人员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华寿俊等人成功地改进了该厂的人工造纸技术,用延安当地遍地丛生的一种高韧性野草——马兰草作原料来造纸,使得该厂月产量提升50%以上。(15)参见《土纸产量增加月出十五万张——振华造纸厂参观记》,《新中华报》1940年8月13日。研究人员与周边群众一起研究纺织、造纸、农具机械的改进方案,改造手工业作坊。经过一年的努力,截止科学院正式开学之前,这些技术人员帮助各个单位把生产指标翻了两番。(16)参见华寿俊《会议李富春同志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565页。
1940年春,科学院接收了当时只有几个工人的油灯厂,该厂当时的主要产品是煤油灯,包括白铁皮焊成的灯座和灯头。接收之后,该厂暂驻学校新建的几孔窑洞中,派李华楫和许明修去领导,因二人都曾念过“高工”机械科,有一定经验。在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的协助下,1940年底该厂正式搬进科学院新建的平房中。随即又从边区工农业生产展览会借调来一部小车床,经过改造和加长,能修配各种零件,生产织布机、轧花机的主轴。其后又陆续增加了铆工、锻工等工种以制造大型设备,还曾派人参加过甘泉铁厂的土法炼铁。在延安自然科学院下属的诸多工厂中,该厂是唯一有固定职工,始终坚持生产的示范性工厂,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为教学和生产都作出了一定贡献。当时学校实验设备、实习工厂中的主要非标准金属设备都由该机械实习厂提供。同时由于当时相对较大的机械厂如军工局各厂主要生产军工产品,无暇顾及延安附近民用小厂如纺织、火柴、肥皂、造纸和医疗器械的设备需要,这部分需求均由该厂承担,充实了边区的机械生产,并收入了一部分加工费用以补助学校。
1940年10月,自然科学院化工实习工厂开工。该厂的前身是桥儿沟新华化学厂,由自然科学院教务处长屈伯川担任厂长,他动员了部分师生参与该厂的建设工程,经过五个多月,新建厂房一幢,其它房屋数间等。随后科学院还建设了小型酒精厂、肥皂、制碱等试验性工场,酒精厂所用的蒸馏塔是由机械实习厂提供并焊接组装的,建厂原料是科学院同学参与搬运的。开学后,学生于此实习,所制肥皂、精盐上市出售,所得又可补助学校。科学院技术人员还配合开办了几处纺织厂、农具厂、皮革厂,由科学院借调过去很多技术人员,厂里的技术员如徐驰、李强等,也被聘为科学院教师。
1941年6月,该院与边区工业局合资开办的玻璃厂竣工,厂长为科学院教员刘咸一。该厂可以制造玻璃管、玻璃瓶、灯罩、瓶子、杯子及各种试验用具,主料均采自边区。(17)参见《玻璃厂开工制造》,《解放日报》1941年7月24日。限于设备不足,烧玻璃的火灶以边区老乡烧瓷用的窑炉改良而成,解决了火力不均匀的问题。(18)参见《科学院玻璃厂制造灯罩、瓶子成功》,《解放日报》1942年5月25日。坩埚则在民间土法的基础上改良,使用瓷泥、石英、砂石、焦炭、石炭渣制造了炭坩埚。
此外,学院还与附近的光华农场、延河上游的边区工业区建立了合作关系,作为院外的实习基地。农作课以光华农场为教学基地,师生与农户结成协作户,以发展棉花等经济作物和高产的“马牙玉米”等粮食作物,使一些新的作物品种在当地落户。工业区集中了纸厂、棉纺厂、被服厂、机械厂等一系列规模较为可观的工厂。虽然设备较为简陋,却是依靠共产党自己的科技人员动手创办起来的骨干工业,学生因此倍受鼓舞。
科学院在教学中时刻重视同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紧密关联,其所兴建的一批工厂均由师生利用有限的设备改良、扩建而成,对旧有技术进行改良,是学院科研、技术实力的直接体现。这些工厂的创办为师生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场所,其所生产的产品能够补助该院的经费,也为边区工业注入了一些新鲜血液。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困难时期党和边区政府自主兴办科技院校的勇敢实践,在各方面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之下,社会各界的积极配合下,边区科技人员通过独立更生、艰苦奋斗,顽强克服了诸多困难,一举打破了开办前党内党外对于兴办科技教育可行性和必要性的种种质疑,为边区注入了科学教育新风和学习科学的动力。它的创办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革命热情,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坚定了党和政府开展科技教育的信心和决心,为该校教学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北联大文学院院长马雅堂先生曾于1942年参观延安自然科学院,对该院所表现出的不同于鲁艺、陕公等校的新气象颇感惊喜,他说:“外面的人以为在延安的人们,总是在开会,做政治斗争。而不知这延安同样也有文化,也还有科学”,“这种仪器和各种标本等等,在大后方各大学里,也是很难得的”,“回去以后当告慰在大后方的科学学界,使他们也能知道延安的真相”。[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