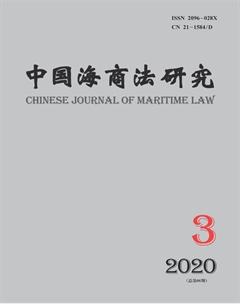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研究
杨巍 杨滢
摘要:对于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点“保险事故发生之日”,域外法多通过主观解释、客观解释等方法对其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4条规定的起算点,学界争议基本也可归纳为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争。在中国现行法及理论框架下,第264条所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之日”作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时效起算点之合理性有待商榷。结合诉讼时效起算的基本原理以及海上保险的特有性质,该起算点应界定为“权利人的救济权可以行使之时”。对于保赔保险这类特殊的海上保险合同,应结合其性质的界定、约定索赔时限、先付条款等因素确定其诉讼时效起算点。
关键词:海上保险;诉讼时效;起算点
中图分类号:D922.28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20)03-0035-07
Research on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time bar concerning the claim for
insurance compensation of marine insurance
YANG Wei,YANG Ying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As for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time bar in marine insurance claims which is the occurrence of the peril insured, foreign jurisdiction always gives the interpretation in favor of the insured through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objective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methods. Various approaches also exis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time bar provision in Article 264 of Maritim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can be either subjective orobjective. In the currentlegal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China, it is still open for discussion touse the date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perils insured as is stated in Article 264, to serve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time bar of the claim for insurance compensation. Combining the basic rules of limitation of a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insurance, the starting point should be defined as the date when the obligees right of relief can be exercised. A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insurance, the starting time can be determined by considering the definition of its nature, the agreed limitation of the claims, the pay-first rule and other factors.
Key words:marine insurance;limitation of action;starting point
海上保险合同诉讼时效是适用于海商法领域的特殊时效,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简称《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是特殊规则与一般规则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第264条规定,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点是“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这既不同于《民法总则》规定的起算标準,也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简称《保险法》)规定的起算标准①。这固然可解释为海商法作为商事单行法的特殊规则,但仅从“保险事故发生之日”之自身涵义来看,也仍存在以下疑问:第一,海上保险事故发生后通常会面临复杂的核损程序,核损程序结束前诉讼
① 参见青岛海事法院(2013)青海法海商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书、宁波海事法院(2011)甬海法商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沪高民四(海)终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并民终字第892号民事判决书等。
② 参见《瑞典海商法》第19章第1条第2款、《意大利航海法典》第547条第2款、《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典》第409条等。
③ 英美法中的limitation通常被翻译为“起诉期限”,大陆法中的verjhruang(德)、prescription extinctive(法)、prescrizione(意)一般被翻译为“消灭时效”。为行文方便,统一表述为诉讼时效。
④ 参见Wetzel v. Lou Ehlers Cadillac Group Long Term Disability Ins. Program,222 F.3d 643 (9th Cir. 2000)。
⑤ 参见Prudential-LMI Commercial Ins. v. Superior Court,798 P.2d 1230(Cal. 1990)。
⑥ 参见《日本商法典》第663条、《日本保险法》第95条。
⑦ 中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126条规定:“关于海上保险,本章无规定者,适用‘保险法之规定。”
⑧ 参见江朝国:《保险法逐条释义》,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619页。
时效是否起算?第二,“保险事故发生之日”在某些情形下不易确定(如国际多式联运中,发生于途中的货损往往抵达目的地时才能发现)。在此情形下,應如何解释“保险事故发生之日”?第三,在保赔保险等特殊海上保险中,保险金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如何确定?对这些问题,学理研究尚未充分展开,而司法实务上已有因此类问题而引发争议的实例①。笔者拟从参酌域外经验、现行法规定之解释、起算规则与其他规则的衔接等角度对其加以阐释。
一、两种解释标准
对于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点,虽然域外法多表述为“保险事故发生之日”②,但对其具体解释存在较大分歧,大致可分为主观解释标准与客观解释标准。
(一)主观解释标准
主观解释标准是指以权利人主观上知道或应知某种事实的时间点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美国、日本等国采取该解释标准。在美国,限制被保险人起诉时间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各州关于诉讼时效③的成文法规定;二是保险合同的约定。只要合同约定的诉讼时效没有延长法定时效,也未将法定时效缩短到不合理的地步,便都具有强制约束力④。在保险实务中,保险单一般将诉讼时效起算点约定为“损失发生”之日。[1]大多数美国法院对此采取传统解释,认为应以被保险人发生损失之时为诉讼时效起算点。但对于持续伤害以及损失不易察觉等情形,美国各州法院又存在以下两项特殊处理规则:一是加州最高法院确立的“延迟发现损失规则”(the delayed discovery rule),即将损失发生的时间定义为“损失相当明显,且被保险人察觉或者应当察觉到这种损失,并且能合理地意识到根据保单规定,自己应当履行通知义务的时点”
⑤。“延迟发现损失规则”类似于《保险法》第26条规定的“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之起算标准。二是其他州法院采取的“衡平展期规则”(equitable tolling of the limitations period),即将诉讼时效起算点确定为“保险人拒赔、被保险人的诉因成熟之时”。[2]而且,在被保险人提交损失证明、保险人对损失进行核算期间,应中止时效的计算。因此,尽管在保险单等书面文件中通常约定以“损失发生之日”作为时效起算点,但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实际适用的是主观解释标准。
2010年《日本保险法》施行之后,商法典中关于保险合同之规定被废止,海上保险合同改为适用《日本保险法》,保险金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由两年改为三年
⑥。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日本商法典》还是《日本保险法》对诉讼时效起算点都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务中保险合同诉讼时效也并未统一采取民法典规定的起算标准(即“权利得以行使时起算”)。对于保险金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日本学界及实务界存在三种意见:一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二是“保险事故发生之日”;三是“保险合同中有关支付保险金的期间结束之日”。其中第一种意见为主观起算标准,而后两种意见为客观起算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保险公司和裁判根据不同案情,实际采取的起算标准也有所不同。[3]
(二)客观解释标准
中国台湾地区“海商法”对海上保险诉讼时效未作规定,故其适用“保险法”相关规定
⑦。“保险法”第65条规定,保险金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点是“权利得为请求之日”。对于该起算点的理解,台湾学界存在三种学说,即主观说、客观说和主客观混合说,其中客观说为现行通说
⑧。客观说认为,诉讼时效自“请求权发生时”起算,在确定起算点时无需考虑请求权人主观上何时知悉其权利可行使、义务人实际上能否进行给付等因素。有学者指出,所谓“得为请求之日”是指权利人得行使请求权的状态而言。例如火灾保险中,一般指发生火灾事实之日。[4]132针对“保险法”第65条,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6年度第16次民事庭会议之决议指出:“所
① 参见中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2年度台上字第1258号民事判决书。
② 亦有学者对《海商法》第264条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该规定违反法理。参见徐猛、茅麟:《论保险合同诉讼时效规定的理解和适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4条的思考》,发表于《中国海商法研究》,2012年第3期,第53页。
③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桂民终425号民事判决书。
④ 参见傅旭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476页;奚晓明:《新保险法热点与疑难问题解答》,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谓请求权可行使时,系指行使请求权在法律上无障碍时而言,请求权人因疾病或其他事实上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者,时效之进行不因此而受影响。权利人主观上不知已可行使权利,为事实上之障碍,非属法律障碍。”例如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主审的一个火灾保险案中,判决书①
认为:“系争火灾保险之标的物既于1996年11月21日因发生火灾而受损害,被上诉人系保险标的物之抵押权人,倘无不能请求之事由,自应认自该标的物发生损害时即得请求保险契约所生之权利。原审法院以该标的物损失金额,于1998年2月3日始经公证公司确定,认为被上诉人之请求权消灭时效,应自该日起算,确有不当。”
综上所述,主观解释标准与客观解释标准虽然存在差异,但均未拘泥于“保险事故发生之日”的字面涵义,而是将起算点界定为保险事故实际发生之后的某一时点。在该时点,必须权利人已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行使权利,两种解释标准对此存在共识。两种解释标准差异的产生原因在于,界定该“相当程度”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主观解释标准将主观上的“可识别性”置于优先因素,故以权利人知道或应知某种事实的时点作为起算点;客观解释标准更加关注行使权利的“客观可能性”,故以行使权利的各项条件客观上具备之时作为起算点。
二、《海商法》第264条的解释路径
《海商法》第264条规定,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点是“保险事故发生之日”。对于该条应如何解释,中国学界和实务界存在极大争议,基本可概括为客观解释标准与主观解释标准之争
②。持客观解释标准的学者认为,對“保险事故发生之日”应采严格文义解释,即将其认定为保险事故客观发生之时点。理由在于:其一,该标准符合海上保险合同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价值取向,其作为一个完全客观的时间点,具有其他时效起算标准所无法比拟的确定性,可以提高商事效益。[5]其二,该标准符合海上保险法历史发展的进程,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包括英国等海上保险大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采“保险事故发生之日”之起算标准。从海上保险实践看,各国海上保险法的差异对海上保险业的发展有着明显的阻碍,不仅会妨碍国际海上保险市场的发展,还会增加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交易成本。[6]其三,就实现条件来说,在通讯与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对掌握保险标的是否遭受实际损害并不存在客观障碍。[5]司法实务中采客观解释标准的实例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市蝶山支公司、梧州市汇祥船务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一案
③
,涉案船舶于2014年8月10日5时30分左右发生触礁沉没事故,法院依据《海商法》第264条认为:“2014年8月10日应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之日,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4年8月11日起算。”该案主审法院采用了纯粹的客观标准,即以保险事故实际发生之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
多数学者对客观解释标准持批评态度,认为该标准损害了权利人的时效利益。为了消除客观解释标准的弊端,他们将各种主观因素不同程度地添加到起算标准中,从而形成主观解释标准。基于对不同主观因素的考量,主观解释标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意见:其一,“保险事故发生之日”应解释为“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而非保险事故实际发生之日
④。对《海商法》第264条不能仅作文义解释,否则对被保险人极为不利,因为被保险人对诉讼时效期间内的相当一部分时间是无法利用的。[7]456反观《保险法》第26条,正是由于“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时日有可能晚于保险事故发生之日,故该条排除了保险事故发生至知道这一段“不知”期间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权利可能造成的不利。[8]因此,对海上保险事故发生之日也应采用知道或应当知道标准。其二,有学者认为,现有时效起算点无法解决发生救助、共同海损理算分摊的情况,故建议将因海上保险合同产生的请求权之时效起算点规定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9]其三,还有学者主张,保险合同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当区分情况(保险人拒赔、保险人同意赔偿后又反悔、保险人超期核定责任等)确定。例如保险人同
意赔偿而事后又不予赔偿的,则诉讼时效应从法
① 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津高民四终字第160号民事判决书。
或约定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10]采主观解释标准的实例如在“百事昌化学公司(Beston Chemical Corporation)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
①中,法院认为:“就本案而言,涉案货物承运船舶于1999年11月6日到达目的港
,次日,警备队登船检查时发现货损,因此,本案保险事故发生日期应认定为1999年11月7日。”该裁判意见即采取“知道货损之日”的主观起算标准。
笔者认为,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为“权利人的救济权可以行使之时”。此处的救济权是指违约责任请求权,即因保险人未依约支付保险金而使被保险人对其享有的请求权。具体而言,该起算标准的适用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被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而保险人拒绝支付,自被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人拒付时起算诉讼时效。二是被保险人与保险人达成赔付协议,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时保险人未依约支付保险金的,此时起算诉讼时效;履行期限届满前保险人表示将不依约支付保险金的,自被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表示时起算诉讼时效。三是虽然保险人同意支付保险金,但双方就支付金额或支付条件未能达成一致,自最后一次协商破裂时起算诉讼时效。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该起算标准符合诉讼时效起算的基本原理。虽然《海商法》属于商事特别法,但其特殊时效规则亦应符合诉讼时效的一般原理。其一,诉讼时效的直接限制对象是救济权,在救济权未产生时不存在诉讼时效起算问题。诉讼时效制度旨在维持法律安全和法律秩序,其只能适用于请求权。[11]在中国现行理论及法律框架下,诉讼时效的直接限制对象是救济权性质的请求权,[12]主要包括侵权请求权和违约请求权。在海上保险领域,诉讼时效的直接限制对象是保险人未依约支付保险金而由被保险人享有的违约请求权,即保险金请求权受到损害而产生的救济权。因此,在保险人尚无违约行为、违约责任其他要件尚不具备的情形下,因救济权尚未产生而不能起算诉讼时效。其二,保险金请求权的履行期限与诉讼时效通常是衔接关系。拉伦茨教授指出:“时效起算不仅要考虑请求权的发生,也要考虑请求权的到期。”[13]中国学界通说亦认为,合同明确约定债务履行期限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债务未被履行,即表明债权人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了侵害。[14]原给付义务(合同债务)受履行期限限制,诉讼时效并不直接发生效力;只有原给付义务被违反而形成次给付义务(违约责任)的情况下,诉讼时效才实际发挥作用并予以起算。[15]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因保险人享有期限利益,其不必现实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其不履行也不构成违约行为,所以此时诉讼时效尚无起算问题。如果履行期限届满时保险人仍未依约支付保险金,被保险人此时取得违约请求权(救济权),而该请求权的行使须受诉讼时效限制,故应起算诉讼时效。质言之,履行期限对诉讼时效起算有直接影响,即履行期限未届满原则上诉讼时效不能起算。[16]其三,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对于支付保险金的不同态度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基于保险合同的射幸性,保险人不同于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确定地负有交付某种货物的义务,而是须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经理赔核算等程序才能确定是否支付保险金以及具体数额。因此,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态度的不同选择直接影响着诉讼时效起算。保险人的态度大致包括:拒绝支付、达成赔付协议后一直拖延支付、达成赔付协议后预期违约、未能达成赔付协议等。在这些情形下,诉讼时效起算点应当分别是:“被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拒付行为时”“履行期限届满时”“被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预期违约行为时”“最后一次协商破裂时”等。因为这些时点在不同情形下使“权利人的救济权可以行使之时”之起算条件得以具备。
第二,保险金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标准中的“权利受到侵害”,不应解释为“保险标的受到侵害”,而应理解为“保险金请求权受到侵害”。其一,“保险标的受到侵害”与“保险金请求权受到侵害”对诉讼时效起算具有不同的意义。有学者认为,保险事故发生侵害了被保险人的权利,因此保险事故发生和被保险人权利受侵害的时间一致。[9]该观点误解了诉讼时效起算标准中“权利受到侵害”的涵义。保险事故发生固然直接给保险标的造成损害,但保险事故发生仅为保险金请求权产生的前提条件,其与权利救济尚无关联,因此,其只是诉讼时效起算的前置事件而非起算条件。当保险人于各种情形下实施违约行为时,其未依约支付保险金的违约行为导致保险金请求权受到侵害,基于限制救济权的目的,诉讼时效起算成为必要。其二,核损程序是
① 参见克里斯蒂安·冯·巴尔、乌里希·德罗布尼希:《欧洲合同法与侵权法及财产法的互动》,吴越等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② 《海商法》第216条第2款规定:“前款所称保险事故,是指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的任何海上事故,包括与海上航行有关的发生于内河或者陆上的事故。”
③ 参见青岛海事法院(2013)青海法海商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四终字第107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桂民四终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等。
④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378-379页。
否完成对判断“权利受到侵害”有直接影响。由于海上保险主要为损失填补保险,即保险人给付的保险金以实际损失为限,故核损程序的重要意义在于辨明损失是否由承保风险造成以及确定保险金的具体数额。保险人在确定须承担保险责任之后,根據被保险人所提供的索赔资料或证物,进一步核对损失清单、核算损失的数额,以决定赔偿的数额。[17]这意味着,判断被保险人是否享有权利以及所享权利的内容均须以核损程序完成为前提。核损程序尚未启动或尚未完成的情形下,因无从判断“权利受到侵害”而不具备起算条件。
第三,《海商法》第264条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一,《海商法》的制定深受《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的影响,[18]该法并未直接规定海上保险诉讼时效,而仍将普通时效规则适用于海上保险。依据《1980年英国诉讼时效法》规定,时效期间从诉因产生之日的第二天起算。[19]在海上保险实务中,法院通常认为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有一个使其免于特定损失的承诺,在损失即保险事故发生时,就推定保险人违反了该使被保险人免于特定损失的首要义务(primary obligation),诉因随即产生,时效开始计算。[20]英美法中“诉因”的意义在于,针对被告的违约行为或侵权行为,原告选择特定的诉讼程序寻求救济
①。因此,“诉因产生时起算时效”与笔者主张的“救济权可以行使之时起算时效”本质上并无不同,因为二者均秉承以时效限制救济权的思路来确定起算点,区别仅在于是否借助英美法诉因理论实现该目的。其二,海上保险的新近立法理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始肇于近代的海上保险制度基于当时航运业风险抵御能力较低的现实,以侧重保护保险人的立法理念进行了相关制度设计。承担海上运输的主体承担着较陆地运输更为频繁的特殊风险, 因而海商法形成一系列分担海上风险的特殊机制。[21]但随着现代航运技术的迅猛发展,海上航运的安全性越来越高,作为近代海上保险制度之基础的航运风险已发生根本改变。这导致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和风险分配在新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下有失公平,因此一般保险中“侧重保护被保险人”的价值取向也逐渐渗透到海上保险领域。[22]如前文所述,各国在未直接修改“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算时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解释路径将起算点认定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时点,即反映了立法理念的这种变化。虽然《海商法》第264条的文义脱胎于近代海上保险的立法理念,但对其解释及适用亦应符合新近立法理念的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海商法》落后于国际海事立法的新发展,国际主流立法和实践已对《海商法》形成了倒逼之势。[23]在《海商法》修改前,对于保险金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采取笔者观点是较为务实的选择。
第四,该起算标准适用于各类海上保险合同。依据《海商法》第216条,海上保险合同包括损失保险合同和责任保险合同,这两类保险合同均应适用该起算标准。其一,海上货物运输保险、船舶保险等损失保险的保险金请求权适用该起算标准不存疑义。这些损失保险是最常见的海上保险类型,是对海上风险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进行补偿的基本方法。[7]415前文如无特别说明,都是以损失保险为前提进行分析,因此该起算标准适用于损失保险的理由不再赘述。其二,责任保险的保险金请求权适用该起算标准也是合理的。由于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故依据《海商法》第264条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之日”确定诉讼时效起算点显然不妥当
②。有学者认为,责任保险的保险事故可分解成两个步骤:一为“发生可能被请求的事实”,即保险事故客观发生之日;二为“发生被请求的事实”,即被保险人的责任确定时。责任保险之被保险人,必须等到第二阶段“被请求的事实”发生,保险事故才算发生,故原则上责任保险之时效起算点应为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责任确定之时。[4]135在司法实务中,有不少法院采取该观点
③。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法释〔2018〕13号)第18条亦采该观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该条的立法理由主要侧重于“保护被保险人合法利益、符合保险原理”等
④。笔者认为,相较于《海商法》第264条而言,司法解释的规定进
① 采此观点的案例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28号民事判决书。
② 参见Cassell v. Lancashire and Yorkshire Accident Co,(1885)1 TLR 495;
TH Adamson & Sons v. Liverpool London and Globe Insurance,(1953)2 Lloyds Rep.355。
③ 参见《民法总则》第197条。
④ 参见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保险法〉有关索赔时限理解问题的批复》(保监复[2000]304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875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民终字第7125号民事判决书。
步明显,但仍未尽合理。因为司法解释仅解决了责任保险中保险事故的特殊认定标准问题,而仍未考虑到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时保险人拒赔、不履行赔付协议、赔付期限未届满等情形對诉讼时效起算的影响。因此,笔者主张的起算标准也应适用于责任保险的保险金请求权。事实上,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对责任保险的保险金履行期限通常设有规定,例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2009)第5条规定,在十日之履行期限未届满之前,虽然赔偿金额已经确定,但因保险人尚未构成违约,此时显然还不能起算诉讼时效。保险实务中的这种做法恰可证明笔者所主张起算标准的合理性。
第五,对于“权利人的救济权可以行使之时”之起算点可能造成权利不确定性的疑虑,笔者给出以下回应:其一,该起算点适用于海上保险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因合同条款对履行期限、索赔程序等已做事先约定,而该起算点主要基于这些因素判断,故并非极不确定。其二,相较于普通民事诉讼,海上保险诉讼当事人一般为保险公司、运输企业等商法人。其具备较强专业知识和资金优势,对理赔、索赔已形成较成熟的行业流程,这也极大降低了权利不确定性的风险。其三,从域外法发展趋势来看,主观起算标准配以短期时效期间已被大多数国家及地区所接受,《民法总则》亦采该模式。“保险事故发生之日”之客观标准虽具有确定性优势,但其诸多弊端已被实践证实。结合中国海上保险仅有二年短期时效期间的现实,以“权利人的救济权可以行使之时”为起算点,更有利于厘清双方的权利义务。
三、保赔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
保赔保险是海商法领域的一类特殊保险。《海商法》和《保险法》对保赔保险均未作规定,但保险实务中保赔保险常有应用。以下对保赔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予以分析。
第一,保赔保险合同的性质对诉讼时效起算的影响。现行保赔保险制度主要是从
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发端而来,尽管保赔协会承保内容大多属于责任风险,但对保赔保险合同的性质是否为责任保险,学界仍存有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保赔保险在理论上被当成是海上责任保险的一种类型,但它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规定,而只能适用合同的一般法律规范。[24]第二种观点认为,保赔保险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海上保险,单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并不能解决保赔保险合同特有的问题,应明确保赔保险作为海上保险合同的性质。[25]实务主流意见采取第一种观点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与南京宏油船务有限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上诉一案有关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的复函》([2003]民四他字第34号)指出: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与会员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不属于商业保险,不适用我国《保险法》规定,应当适用我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但是交通运输部2018年发布的《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态度有所变化,其第14.6条规定互保协会对其会员的补偿责任参照适用海上保险合同的规定。保赔保险合同是否被纳入海上保险合同的范畴,尚有待立法机关的最终决断,但在修法之前其诉讼时效起算仍应适用合同法规则。
第二,“索赔时限条款”对诉讼时效起算的影响。《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保险条款》第8条就索赔时限作出规定,分析该条可得知,
保赔保险合同的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点是“被保险人承担责任之时”。一般认为,该条是借鉴《英国船东协会规则(2006)》的结果。[26]在英美法允许当事人约定时效条款的法律框架下,若保险合同明确约定被保险人提交索赔通知的时限,那么法院在解释时限时则会采取非常严格的态度。如果被保险人未在该约定时限内提交索赔通知,则法院多会支持保险人以被保险人未在通知时限内提交索赔通知而拒赔的理由②。但是在中国现行法框架下,诉讼时效规则采取严格法定主义③,实务中并不认可当事人就时效事项达成协议的效力④。虽然近年来不乏主张允许时效协议的学理意见,[27]但从解释论角度而言,“索赔时限条款”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应无疑义。因此,该条款因与现行法时效规则不具兼容性而不能对诉讼时效起算产生影响。
第三,“先付条款”对诉讼时效起算的影响。在
① 参见《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保险条款》第8条。
保赔保险中,被保险人向船东互保协会行使请求权还须受到“先付条款”的限制①。先付原则是保赔保险补充性的充分体现。保赔保险与一般责任保险的重要区别在于,保赔保险的承保人是具有互助性质的互保协会,而被保险人则是其会员,即每个成员既是投保人又是某种意义上的保险人。因此,先付原则对于维护互保协会的稳定运作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符合互保协会维护会员船东利益的宗旨。[28]再者,因会员船东入会即意味着接受先付条款,基于意思自治原则自应认可先付条款的效力。由于先付条款的存在,被保险人向互保协会请求赔付的时点应为被保险人承担责任之后,其向互保协会提起索赔请求而对方违约之时,诉讼时效起算。
四、结语
《海商法》第264条规定的诉讼时效起算标准是借鉴域外法的结果,但是对于该条的理解与适用,学界似未充分关注各国及地区对“保险事故发生之日”所作的各种变通解释,这些解释使该起算标准的实际适用效果与其字面涵义相去甚远。基于域外法经验和中国的诉讼时效理论,笔者主张以“救济权可以行使之时”作为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点。这既与诉讼时效的一般原理相契合,也有助于保险实务中不同情形下对权利人的救济,且符合保险实务中的某些惯常做法。对于较为特殊的保赔保险,应结合其性质的界定、约定索赔时限、先付条款等因素确定其诉讼时效起算点。
参考文献:
[1]
约翰·F.道宾.美国保险法[M].梁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85.
[2]小罗伯特·H.杰瑞,道格拉斯·R.里士满.美国保险法精解[M].李之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01.
[3]沙银华.日本保险经典判例评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50.
[4]刘宗荣.新保险法:保险契约法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初北平,曹兴国.变革中的海上保险合同诉讼时效再审视[J].法学杂志,2014(11):94.
[6]谷浩.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海上保险立法:变革、协调和特点[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51.
[7]傅廷中.海商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8]奚晓明.新保险法热点与疑难问题解答[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102.
[9]李兆良.海上保险诉讼时效规定的理解和修改[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3,24(2):59.
[10]江必新.保险纠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61.
[11]汉斯·布洛克斯,等.德国民法总论[M].张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295.
[12]杨巍.民法时效制度的理论反思与案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8.
[13]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M].王晓晔,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39.
[14]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780.
[15]崔建远.无履行期限的债务与诉讼时效[N].人民法院报,2003-05-30(3).
[16]武亦文,赵亚宁.《保险法》第26条诉讼时效规范之反思与优化[J].保险研究,2019(7):116.
[17]温世扬.保险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65.
[18]司玉琢.海商法专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435.
[19]OUGHTON D W,LOWRY J P,MERKIN R M.Limitations of actions[M].London:LLP Reference Publishing,1998:43.
[20]BENNETT H.The law of marine insuranc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704-705.
[21]何丽新.论新民商立法视野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修订[J].中国海商法年刊,2011,22(2):53.
[22]司玉琢.国际海事立法趋势及对策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53.
[23]曹兴国,初北平.作为特别法的《海商法》的修改——制度体系、修法时机及规范设计[J].政法论丛,2018(1):84.
[24]张湘兰,张辉.国际海事法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228.
[25]张虹,郭丽君.相互保赔险合同的法律性质分析[J].中国保險,2016(8):7.
[26]郑睿.英国海上保险:法律与实务[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259.
[27]金印.诉讼时效强制性之反思——兼论时效利益自由处分之边界[J].法学,2016(7):136.
[28]刘畅.船东保赔协会之先付原则与第三人直接诉讼——以英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为视角[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