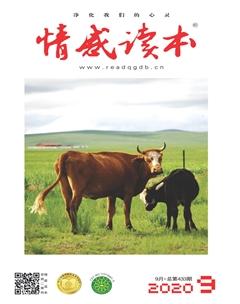父亲的眼泪是我人生的救赎
尹衍梁
父親不赞美我,就是自己在那边哭。我也是百感交集,红着眼眶站在台上想:当时你对我哭,是因为我是不良少年;现在你对我哭,是因为我是博士。
我终于了解,父亲对我的责骂,都是出自真心的期盼。
父亲寡言,但很严肃,在同乡与朋友之间深受尊敬、信任。他有很多想法和别人不太一样,一个就是他喜欢人前教子,在别人面前打骂、教导儿子;第二是相信棒头出孝子,因为我爷爷当年就是用打的,而且打得很严重。
七八岁开始,我每天都挨打。父亲白天工作很忙,晚上才回来吃饭,吃完饭下了桌,就开始问我今天做错什么事。妈妈告状、姐姐告状,他就用皮带抽我,手臂上一条一条的瘀血痕。所以小时候,我一直喜欢穿长袖。
这造成我10岁开始就不平衡,“你打我,我就去打别人。”那时候住在眷区附近,跟里面的孩子去附近打闹,父亲就越打越重。
但是“棒头出孝子”不是每个孩子都适用,如果父亲用疏导的方法,或许我就不会误入歧途了。结果就是,我根本没办法念书,一天到晚打架闹事,初三连英文字母都写不全,数学也不会,小太保哪里会念书嘛!于是念到进德中学(感化院)去了,一共待了两年半。
在进德的头一年,我还是一样跟人家打闹,后来出事了,跟别人打架肚子被划破。过了一周,父亲来看我,我们就坐在花园的石凳上,周边很多人在玩,他却哭起来了。我说:“你干吗哭?不要哭了,不好看。”我没看过他哭,这是第一次。
他流着忏悔的眼泪对我说:“我不是不爱你,我一定要你的未来好。”我也很难过,说:“你一副我就是坏人的样子,你跟我讲这个不是很奇怪吗?”后来我想一想:对,他一定爱我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从那天起,我就不再打架了,开始好好读书。原本我是全校最后一名,在进德的后一年半,我是全校第一。后来,我插班进成功中学夜间部,感化院能插班进公立学校夜间部,以前没有过的。
当兵回来后,他给我一万美元,叫我去环游世界,还给我一张去意大利的机票。我把一万美元的支票贴身藏在内衣裤里,怕被偷走,就这样流浪了半年,坐火车、睡火车站,从欧洲跑到中南美洲,再到美国,回来身上只剩下50美元。很有意思吧?
回来以后,他就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现在你游历了世界,从今天开始劳动。我说:好。于是,就进入润泰纺织,从科长、经理、副总经理一直做到现在。
26岁时,我创办了润华机械厂,这个厂倒闭了;后来又开个染料工厂,这个工厂爆炸了。这两个工厂加起来花了三四千万元(新台币,下同),那时候这是一笔大钱,我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衍梁啊!恭喜你得到可贵的失败经验,你以后比别人更不会犯错了。”恭喜我,没有骂我,所以我后来比别人更相信可以在失败中站起来。
大学毕业那年,爸爸的好朋友郑作恒突然打电话给我,要请我吃饭。他先带我去舞厅跳舞,我那时候不知道有这么漂亮的地方,舞池里那些舞女像热带鱼一样游来游去。
接着带我到五月花酒家,他就换了一叠10元纸钞,放在桌子上,小姐来敬酒,亲一下就给10元,几十位小姐涌上来亲,我在旁边看,目不暇接!
结账后,他对我说了几句话:“衍梁啊,我必须跟你说,今天是你爸爸请求我带你出来的,因为他不方便带你出来,而且你父亲也不来这种场合,所以找我带你来见识见识。总之,要我送你几句话:第一,你永远不要赌博,就算你有亿万家财,到明天也可能一无所有;第二,你有没有看到那些小姐,她们不是真的喜欢你,她们爱的是钱,你如果笨到被女人骗,那是活该。”我父亲是很通情达理的人,但他自己很严谨,一开始就用这种震撼式的洗礼,让我了解人生:原来这么美丽的事情,其实是虚假的。
政大企研所毕业典礼那天,我父母来参加。企研所博士班就我一个毕业,我排在第一个,带领其他班的人领毕业证书。父亲不赞美我,就是自己在那边哭。我也是百感交集,红着眼眶站在台上想:当时你对我哭,是因为我是不良少年;现在你对我哭,是因为我是博士。
父亲有几句话我是永远记得的,他说:“你记住,你爸爸没有欠任何人的钱,只有人欠你爸爸的债。”爸爸走后即使有找到证据,也只有两个字:宽免。
他还告诉我:“商人的招牌就是信誉。小商人贩卖的是货品,大商人贩卖的是信誉。”
我到现在也是和爸爸一样,盖房子不偷工减料,卖东西只卖真东西,这是贩售信用。他叫我把事情做好,不要先想赚钱;把事情做好,钱就会来追你。乍听之下,这个逻辑很奇怪,但这个逻辑是对的。
另外,就是在我不成器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像你这样的孩子,有你不多,没有也不少。”我常常咀嚼这句话,我就想,以后一定要让你不能没有我。
我没有打过我的孩子,因为我是被打坏的。女儿现在34岁,政大会研所毕业,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做事认真负责。儿子28岁,在英国牛津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博士。打骂教育这招,有些人是不吃的。我都和孩子讲道理,虽然他们会回嘴说:“哎哟!老生常谈啊。”我常会跟孩子说:“你做得很正确、很棒,爸爸鼓励你。”因为我以前没有得到认同,父亲从没有夸奖过我,他只说:“还可以更好嘛。”
余娟《人生因爱而完满》(百花洲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