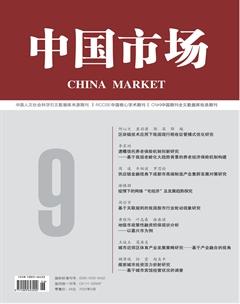纳税人与食税人的关系探究
朱志宇
[摘要]有纳税人便有食税人,但界定两者关系要从纳税根源甚至法哲学去寻找。厘清相关关系及其作用,既符合现代国家宪政的意义,也符合市场机制平价交换的基本原则。因此意义重大。
[关键词]纳税人;食税人;关系;作用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6.
现代国家经济的深入与广泛,在法律的约束下,纳税人的概念是非常清晰的。
“纳税人”的概念一但明确,与之对应的概念“被纳税人”也会随之明确下来,比如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雇主和被雇者、借款人和被借款人等等。但经济学意义上的纳税人似乎与被纳税人是同一个主体。纳税者既是纳税人也是被纳税者。由这一个主体会引申两条法律上的意义:一是被谁纳税,其根源为何?二是既被纳税,谁又享受纳税,作用为何?
以上两点常识,表面看来很简单,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但这种常识中往往包含着法律乃至哲学上的最基本问题。追究到本质层面,就不一定是普通大众所能彻底了解的。因为它涉及到根本性的立法原则和道德哲学问题。
1 先来探讨纳税的根源
纳税古来有自。可能从原始部落,直至国家的建立。而纳税行为又受不同的哲学理念和社会制度影响产生不同的结果。
中国自清朝以前,封建制的国家是“天授君权”。即天下为皇家私有,所谓:“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既然天下为独家私有,那么,人们的生命权、财产权以及国家的公共资产全归皇家独占。老百姓要养活自己,所使用的任何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必须要交纳贡税。如同现在借取别人的资金要偿付利息一样,其逻辑理由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不能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去随意评价当时社会制度的对错,而只能以同情的心态观待当时社会的现实性及其合理性。
那时的税收同样是强制的。纳税人与被纳税人也是同一个主体。税收交入皇家国库,满足皇家和官吏阶层费用开支。我们可将此类人称为食税人。但此时不要忘记,那时天下人的纳税并不完全用于皇家的穷奢极欲,政治清明时税收绝大部分用于保护国家、人民的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兴建工程,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其财政功能与现在社会有一致性。若皇权黑暗、政治腐败,其贡税一定是满足私欲、中饱私囊,结果定是民不聊生。
若从法律意义上说,古代与现代税收皆具有强制性,表象相同。但性质完全不同。
古代法治权不具备对等的价值。因为一个国家中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都归一家私人所有,那种强制是主人对奴隶和臣民的强制,臣民纳税是必尽的义务,不可能发生平民与皇权在立法原则上的平等。法律的制定是居高治下的,臣民只有服从的权利,而完全服从的权利也就谈不上权利了,则纯粹变成了责任和义务,纳税也是这种绝对服从的一种结果。
西方国家的奴隶及封建社会也经历了很长时间。其哲学理念和社会制度与中国大同小异,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曾称赞奴隶制的合理性,那是当时的文化习俗及现实所决定的。
现在国家的宪政与制度,其哲学伦理理念与封建时期完全不同。不要说是个人的生命权利,仅仅是财产权,如果被说成只归哪一家所有,甚至为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所有,那也是非常滑稽可笑的观念。因此,自然法权基础的彻底转换,构成了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不同的评判标准,这些标准涉及到法律、制度和道德。
举英国哲学家洛克在1689年和1690年出版的两部《政府论》为例。洛克首先批判了菲尔麦的“君权神授说”。以前英国国王具有封建君主的绝对权力,由于1688年的英国政变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有菲尔麦起而为绝对君权辩护,说君权为上帝所授,这是中世纪时期神权理论逻辑,由此逻辑必然推导出“王权世袭”的理论。洛克则一针见血指出:“由于没有自然法,也没有上帝的明文法,来确定在任何场合谁是合法继承人,就无从确定继承权。因而也无从确定应该由谁来掌握统治权。”[1]强调在自然法权利下,人人都有维护自己生命的权利,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由。
上述的现代国家的自然法权实际上已经深入人心,不用赘述。而人人为之建立的国家和社会需要保障以上三种基本权利。以此三项基本权利又延伸了许多其他的公权法和私权法。当然,这些法律的建设和执行,必要有相应的财力予以保障与支持,这种财力就是纳税的根源。
显然,此时的纳税本质和充要条件与封建王国截然相反。这是建立在平等权利的意义上的纳税。即为了保障人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所必须要让渡出去的部分财产权利,这种让渡同样是一种等价交换机制,建立在以法律作为约束的平等协商的契约基础上的,否则没有平等的价值,没有平价交换的原则,没有相互信任的法律契约,则强制权力必然会变种到封建王权治下的法律状态
2 纳税人与食税人的关系
理解了纳税根源,还需要厘清纳税作用。要真实理解纳税作用,则必须厘清纳税人与食税人的相互关系。
2018年中国财政收入已达25.88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是15.4万亿。上述两个数字说明:一是国家财政收入绝大多数是靠纳税收入。这样大的税额完全是靠全国劳动者的辛苦努力完成的;二是如此巨大的财政收入,同样是国民财富资源的一部分,也存在如何配置使用更为合理的问题。我们首先撇开财政收入用于公共建设物化的那块资金,仅看专用于中央和地方公务员的费用开支部分。这些经费专用于人员经费,可以将此视为食税人。理解纳税人与食税人的关系,还要回溯一下哲学理念。
洛克坚持劳动价值论。其缘由是,财产是劳动者个人创造的财富,由劳动创造的价值当然是私有财产,这是维护生命权延伸的结果。自由支配自己创造的价值是自然法权的一部分,同样不可剥夺。亚当·斯密也同样坚持劳动价值论。[2]认为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是个人福利和国家财富的唯一根源。财富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才是产业分工和市场交换的前提。无产权边界,无财富自由,则谈不上交换,也就无所谓市场。没有市场,平等交换的机制就会被破坏,则一切不公平、非正义、不道德的现象就会随之发生。后来的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乃至马克思都坚持劳动价值学说,其思想源流是一致的。
阐述这些理论,与纳税与食税人有什么关系呢?其深刻关系有三:一是私有财产是每个人的生命劳动创造的,不能在不公平的角度上随意被剥夺;二是税收是纳税人私有财产的转让,其转让同样遵循着市场平价交换的原则。通过法律中的契约关系来规定纳税人和食税人的相互权利、义务及责任;三是纳税人转让的劳动收入,通过市场机制和平价交换原则购买政府的等价服务。如果市场的等价机制被破坏,则平等交易权利就会被破坏,其平等交易行为也会自然破裂。因此,作为等价交换权力的双方同样具有平等监督乃至用法律手段促使任何一方承担起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公务员的“公”和纳税人及公民的“公”才能相互平等并相互制约,这就是所谓的公平与正义。
根据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和2003年的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以及2017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一系列的市场性的提法,国家财政这一巨大的收入,同样涉及到广大百姓的国民福利,这种巨大的公共资源,又如何让市场的平等交换机制起决定性的作用呢?这无疑是一个更大的经济学及社会学课题。其课题中的重中之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仅从经济学意义上说,财政收入的合理配置和使用,直接关系到纳税人和食税人的行为准则及正义公平。既然强调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那就肯定了纳税人与食税人的平等关系,也同样肯定了纳税人的纳税必将换取食税人等价服务。这就是市场等价交换原则的本质。
许多人或许会问,食税人的服务如何评价?虽然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的确难以评价服务标准,难以寻求服务计价原则。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此,而在于有没有将纳税人与食税人纳入市场等价的机制中來,有没有用平等的价值去审视双方,有没有建立平等服务的道德观念。完成了以上那些条件,才有可能再来讨论计价准则问题。到那时,依据平等交换原则,则评价标准自会水到渠成,应运而生的。
参考文献:
[1]洛克.政府论[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6:3.
[2]亚当·斯密.国富论[M].章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