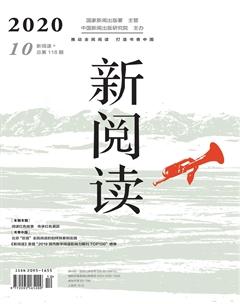萧锋日记,两代情缘
萧南溪
我最佩服父亲萧锋的,是他64年来从未间断地写日记,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天天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在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提笔记述,更不是一件易事。但无论是爬雪山、过草地,无论是在怎样艰难严酷的环境下,萧锋却从未停止过记日记。小休记地名、大休写事件,用五花八门的铅笔、钢笔写在五颜六色的草纸上。
那一夜,读懂父亲
年轻时,我不理解父亲。“我经常劝他,别人打麻将、玩门球、到处去旅游,身体倍儿棒,多好。你成天整理材料,还要自己出钱出书,何苦呢?”又说:“你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就是我们的希望和牵挂!”直到有一天,一个意外的发现,让我真正读懂了父亲。1988年,父亲大概觉得自己时日不多,没白天没黑夜地写。夏天蚊子多,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白色尼龙蚊帐,让他把小桌子搬到蚊帐里来写。
有一个星期天,我在家里一觉醒来,已经是深夜一两点钟了,我发现楼下还亮着灯,就下楼想劝父亲早点休息。一看,他正在改写《血战湘江》的稿子,父亲两腮全是泪,稿纸上全是泪痕。我吓了一跳,忙问他:“爸爸,你哪儿不舒服?”他含着泪对我说:“孩子啊!我成千上万的好战友、好同志的事迹,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他们有的比我有文化,有的比我有能力,有的比我会打仗,但他们都走了,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只要我还有口气,就一定要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写下来,你一定要把它们传下去呀!”
红军妈妈萧曼玉
父亲的日记很少写自己,他更多是写烈士的事,写历史事件,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一个鲜活的父亲。父亲坚持一生写日记的动力有两个:一是烈士的英雄事迹让他不能释怀。父亲曾回忆,过草地时,侦察连的崔明义班长是江西老表,身體很壮实,是我父亲收容队的队员。行军中他一会儿帮这人拿行李、一会儿帮那人背枪。自己带的青稞炒面他也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和战友们分享。有一天,由于天黑看不见,他滑进了泥沼。“我们赶忙趴下用枪递过去救他。他却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呼:‘别过来,一个还不够吗,还要再搭上一个!我们就眼看着他被泥沼吞噬……多好的战士啊!”“我永远也忘不了泥水吞噬时他最后的眼神,好像在对我说:‘总支书记,别忘了告诉我的母亲……”父亲泣不成声地对我说。我觉得父亲的笔不辍,就是要把这些烈士的名字和事迹记下来,传下去。
父亲就是井冈山脚下走出的一个放牛娃、小裁缝,是村里的赤贫,没有读过书。支持父亲一直把日记写下去的力量,还有我的红军妈妈萧曼玉。她是父亲革命的引路人,也是他的识字老师。1927年,我父亲认识了在吉安白鹭中学读书的女学生萧曼玉。曼玉虽是富家女,却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当时萧锋学徒的裁缝铺就在白鹭中学旁边。有一天,曼玉偷偷把萧锋叫出来:“忠渭哥,你怕不怕死?”萧锋回答:“不怕死!”随后,他们一起动员了九栋十八乡42名萧氏子弟参加了泰和紫瑶山游击队。萧锋任一小队小队长,曼玉是游击队文书和士兵委员会的主任。萧锋仗打得好,可是上级要他写战报,这可难坏了他,因为他大字不识一个呀!这时候曼玉就主动提出,由自己担任萧锋的识字老师,还教他用记日记的方法学文化。
1932年,在并肩战斗中心心相印的萧锋和曼玉结婚了。1933年3月,他们在瑞金第一期团校学习马列,我父亲在全校识字考核中拔得头筹,能认得3000个字,曼玉妈妈到瑞金街上买了一本《王氏四角号码字典》。不幸的是,1934年8月,时任公略县(今吉安县)少共书记的曼玉妈妈,遭到敌机轰炸,连同怀抱里吃奶的孩子牺牲在县委机关转移的路上。
母亲贡喜瑞说,日记比生命更重
1981年10月,父亲从原北京军区装甲兵的领导岗位卸任下来后,曾多次说,“日记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历史,它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的历史的一个侧面,我不能带着它去见马克思,一定要把它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他又拿起了笔杆子,整理日记,撰写回忆材料。为此,父亲先后4次自费南下北上,到江西、福建等十几个省、市,重踏长征路,重走历次浴血战场,重访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这方面,我母亲帮助了他很多很多。
我的母亲贡喜瑞是晋中才女,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日工作中,萧锋和贡喜瑞相识相恋,结为夫妻。每次战前,萧锋都要指着背上装日记本的蓝布油包对战友说:“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一定要把这个包交给组织。”而作为萧锋爱人的贡喜瑞,也把日记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
1944年8月,父亲带母亲去延安治疗肺病,同时接受了任务,把为陕甘宁边区教二旅补充的850名新兵带到延安。在经过干涸的乌龙河时,母亲背着父亲装日记的蓝布包,骑着驮着全部家当的枣红大骡子,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突然一阵狂风暴雨,上游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母亲猝不及防,被掀翻到河里。父亲发疯一样向母亲游过去,母亲却全然不顾自己,拼命地将装有日记的油布包递了过去。警卫员把贡喜瑞救上岸时,已经奄奄一息。全部家当都被冲走,所幸日记保存了下来。萧锋赶紧打开日记一看,心疼得不得了,土地革命战争这10年的日记都被打湿了。在延安窑洞里,母亲生下我还没有满月,她就靠在炕上,将父亲这10年的日记,一字一句地誊抄清楚。母亲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说,“日记是你父亲的遗愿,你一定要将它们整理、出版!”
我接过父亲的笔,完成他的愿望
父亲去世后,仍有一屋子的日记和资料静静地躺在家里,我想谁都可能教化学,但整理父亲的日记只有我来完成,我决定提前退休,去完成父亲的遗愿。20多年来,我从一个对电脑一窍不通的人,到能自如地操作基础的编辑软件;我参与策划拍摄了数字电视影片《萧锋血战陈庄》,在中央六台播出百十次;将父亲的10多部半成品书稿整理后编写成《萧锋征战记》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把父亲的大陆最后一战——金门战役,用写春秋的方法写了六十万字的《金门战役的纪实本末》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还有一本“萧锋夫妇画册”,也广受好评。从2010年起的这10年里,我不断修改充实讲稿,不仅是上井冈山,一些党校、学校、社区、厂矿企业和社会公益组织也纷纷邀请我去讲红色党课。
除日记外,父亲传下来的还有良好的家风。他们省吃俭用,资助了30个烈士遗孤和对他们有滴水之恩的亲属的孩子,培养了十五个大学生,研究生。父亲去世那一天,还催着母亲把自己的半个月工资寄给老家南溪村的五保户。
“红色基因”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和魂”,我们应将其融化在血液中、深植在骨髓里,落实在行动上,让子孙后代传下去,永不变色!
作者系萧锋将军之女,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理化教研室原副主任、副教授
萧锋(1916—1991年)原名肖忠渭,字凌川,江西省泰和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万安暴动。1928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国少将,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