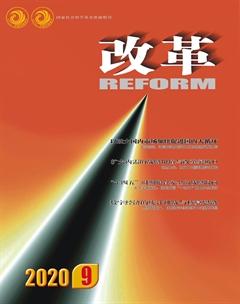贸易、就业与中国农村贫困
陈思宇 陈斌开



摘 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中国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重要方略,产业扶贫则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主要实现手段。在全球化快速扩张背景下,如何有效实施产业扶贫并完成减贫目标,是关乎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系统性梳理全球化和中国农村贫困的典型事实和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研究出口贸易冲击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地区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实证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冲击显著降低了地区贫困发生率。结合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影响机制作进一步检验发现,贸易冲击通过提高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率和增强移民网络效应,来增加家庭人均收入。为彻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一方面要扩大开放程度,充分利用贸易红利促进产业扶贫的实现,另一方面要发展国内市场,以应对全球经济的波动。
关键词:贸易冲击;农村贫困;外出就业;移民网络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0)09-0080-14
精准脱贫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我国基本方略,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目标。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新时期脱贫攻坚的目标,集中到一点,就是到2020年实现“两个确保”: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此后,我国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生态扶贫、教育脱贫等举措,切实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阶段,强效的扶贫机制和持续的脱贫动力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
产业扶贫是脱贫致富的出路之一,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从长期来看,贫困人口从产业发展中受益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产业合作、产业项目建设、创建产业扶贫基金、产业投资等方式,有助于帮扶和刺激产业发展,进而实现优化产业资源配置、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产业效率的目的。
一、相关文献综述
20世纪以来,全球化浪潮推动全球贸易市场加速扩张,贸易对经济发展愈发重要,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产业扶贫能够取得有效的成果,离不开贸易发展。农产品贸易有利于形成农业经济规模效应[1]、促进农业技术进步[2]、扩大农业就业规模[3],推动农业产业发展,有效地帮助农村居民增加收入,是产业扶贫的重要途径。另外,制造业产品贸易对产业创新[4]、企业生产率[5]、就业规模[6]有积极影响,有助于促进当地制造业的发展与产业扶贫实现。通过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是产业扶贫的基本逻辑,以产业为主导的“造血式”扶贫机制往往比以个体为扶贫对象的“输血式”扶贫方式具有更有效的长期减贫效应[7]。产业扶贫通过有效配置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构建多要素协同作用的长效扶贫机制[8],在充分顺应地区资源特点和产业基础的前提下[9],加大产业资本融资和产业资金投入[10],能够取得更大的规模效益,实现更有效的扶贫效果。
自Bhagwati & Srinivasan提出贸易与贫困的联系后[11],经济学领域有大量文献致力于探究贸易对贫困的影响效应。贸易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加速经济增长、增加不熟练工人工资等途径,实现减贫[12]。Vamvakidis & Athanasios利用跨国历史数据追溯贸易与贫困的联系,发现1970年以前贸易对贫困几乎没有影响,甚至1920—1940年呈现负向联系,近年来随着各国贸易开放不断加深,贸易的减贫效应才得以体现[13]。从国际经验看,在减少贫困的过程中,贸易是重要的因素之一。Ahmed利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了国际贸易显著地缓解了贫困[14];董运来等利用印度的经验研究发现贸易可促进农业发展,进而对贫困人口的减少和贫困发生率的降低产生积极影响[15]。
对于中国贸易与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李石新等指出,中国贸易与农村贫困具有倒J型特征,20世纪90年代之后贸易发展有利于农村贫困减少[16];黄季焜等指出,贸易有助于农村地区缓解贫困,但可能会恶化收入分配[17]。而Chen利用GTAP模型分析得出,贸易并不能使农村居民受益,没有减贫效应[18];Han使用1988—2008年中国城市家庭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得出贸易加剧了工资不平等,贫困人口无法从中获益[19]。上述文献均集中于国家层面,并不能解释中国地区间贫困发生率的差异,另一些文献则着重解释了地区贫困率的差异问题。胡海军等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贸易与贫困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性分析,指出沿海地区农村居民是最大受益群体,贸易加剧了地区收入差距[20];郭熙保、罗知从经济增长的角度估计贸易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内陆地区的边际减贫效应高于沿海地区[21];Huang et al. 的研究表明,贸易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产生消极影响,但有利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脱贫[22]。
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主要的贡献和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现有文献大多通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或者收入分组数据计算省级层面贫困发生率,本文则使用《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数据进行检验,使贫困识别更加准确;第二,现有文献关于贸易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金融危機前后,本文则主要研究2010年之后的贸易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能更好地阐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贸易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状况及机制;第三,鲜有文献基于省级数据对贸易影响农村贫困的机制进行研究,本文结合微观数据,基于家户层面数据进行分析,弥补了相关文献的不足。
二、全球化与农村贫困:典型事实
减贫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国一直在为消除贫困而积极努力。根据世界银行设定的贫困标准,国际贫困线为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9美元;针对中低收入国家,贫困线为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于3.2美元;针对中高收入国家,贫困线为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于5.5美元。2016年,中国位于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720万,相较于1990年下降99%;按照中低收入国家标准,中国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7420万,相较于1990年下降93%;按照中低收入国家标准,中国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3.3亿,相较于1990年下降70%,减贫成果显著。图1(下页)展示了世界贫困率与中国贫困率的变化趋势。1990—2016年,中国贫困率从66.2%下降至0.5%,同期世界贫困率从36%下降至10%。2005年,中国贫困率首次低于世界平均贫困率,并在此后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的平均减贫速度。
中国对于贫困人口的认定经历了三次调整,2008年以前中国设定了两个扶贫标准,即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2008年,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一,统一使用1067元作为国家扶贫标准。2009年,国家扶贫标准从1067元上调至1196元,2010年随CPI上涨再上调至1274元。2011年,中国决定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在2019年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追溯了按照不同贫困标准计算的农村贫困人口数和贫困发生率(见图2,下页)。
1978—1985年,中国主要通过促进全面经济增长来减少贫困。按照1986年的贫困标准,即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6元,中国贫困人口由2.5亿减至1.25亿,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至14.8%;按照2010年的贫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由7.7亿减至6.6亿,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至78.3%,大量农村人口实现脱贫。这一阶段,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4%,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6倍,减贫主要依赖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聯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农村居民的收入得以增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大量农业劳动力,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条件。
1985年之后,中国主要是通过实行有计划的开发性扶贫来缓解贫困。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贫困人口呈现地缘性集中的特征。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1986年中国成立了国家级农村扶贫机构——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旨在系统化、制度化地开展全面扶贫工作。在国家扶贫办的统筹下,国家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1994年,中国公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明确提出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到2000年底,国家“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按照1986年的贫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减至3209万,贫困发生率下降至3.5%;按照2010年的贫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减至4.6亿,贫困发生率降至49.8%。在这一时期,户籍制度的放开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其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2001年,中国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明确了未来10年的扶贫目标,即解决3000万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实现6000万低收入人口稳定脱贫。该纲要鼓励开展整村扶贫,把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并确定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给予重点扶持。2010年,扶贫重点县得到的扶贫相关资金规模达到606.2亿元,相较于2002年增加355.9亿元,年均增速达11.7%。在此期间,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2.2%,高于全国农村平均增速11.5%,扶贫政策效果显著。同时,农村户籍劳动力的市场参与度也在上升。2010年,农户中24.5%的劳动力选择外出就业,相较于2003年上升6.2个百分点。在外出人员中,男性占比66.6%,女性占比33.4%;男性以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居民服务业为主,女性以从事制造业、居民服务业、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为主;男性外出务工人均收入为1708元,女性人均收入为1386元。2010年,农户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为41%,相较于2000年上升10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为农村家庭创造更多收入以缓解贫困。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用10年时间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阶段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党和政府把扶贫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014年,我国正式实施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有效地弥补了之前粗放式扶贫方式的不足,取得了卓越成果。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五年扶贫攻坚计划,实现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对扶贫开发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作出进一步部署。
精准扶贫作为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结合多种减贫方式,实现了对贫困人口的精确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精确识别是指针对贫困人口完善建档立卡,剔除识别不准人口,补录漏登贫困人口,加强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机制,确保贫困人口能够享受政策帮扶。精确帮扶是以产业扶贫为主要手段,配合劳务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辅助手段,帮助贫困地区发展产业促进精准脱贫,并且指导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增加贫困户收入,实现脱贫目标。精确管理包括建立考核评估机制、督查巡查机制、约束退出机制、扶贫资金项目监管机制等,确保扶贫政策落实。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9899万人,2013—2019年中国农村减贫人数分别为1650万人、1232万人、1442万人、1240万人、1289万人、1386万人、1109万人,连续7年减贫人数均保持在1000万以上,2019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已经降至551万人。2014年底,国务院扶贫办公布了全国共832个贫困县,2016—2019年分别摘帽28个、125个、283个、340个,截至2019年底已脱贫摘帽776个,贫困县已经减至56个,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决定性成就。
中国一直致力于实现高质量脱贫,依靠产业发展带动贫困人口脱贫是保障长期稳定减贫的重要手段。贸易开放是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通过深化改革促进贸易结构优化、规模增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实行外汇“双轨制”改革,贸易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图3呈现了中国1960—2018年对外贸易情况。中国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167.68亿美元增长至1990年的1112.21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7.67%,远高于世界同期贸易年增长率9.53%①。同时,中国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从1978年开始由负转正,实现大幅上升,从4.56%增长至1990年的13.61%②。在此阶段,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加工贸易,劳动密集型行业得到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23]。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开启了对外贸易市场化进程。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颁布,中国实施汇率并轨,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发展。1992—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1518亿美元上涨至658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6.3%,期间贸易逆差从1994年之后开始逆转。在这一时期,中国关税大幅降低,加权平均关税从1992年的32.17%下降至2001年的14.11%,下降近18个百分点,加速了贸易规模的扩张。同时,大量外资开始涌入中国市场,外资带来大量投资和先进技术,稳固了中国加工贸易的模式。2001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口、出口分别占中国加工贸易进口、出口总额的72%和75%[24]。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此后,中国积极履行开放服务贸易市场、清理完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削减关税等承诺,到2007年中国加权平均关税已经降至5.07%。加入WTO后,中国享受WTO成员国间贸易优惠政策,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对外开放程度。2002—2007年,中國进出口贸易总额从6586亿美元上涨至24 78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8.4%;贸易顺差从374亿美元上涨至308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从22.6%上升至35.4%,实现了贸易体量上的巨大突破。从贸易结构来看,货物贸易是主要的贸易方式,中国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二大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但服务贸易逆差仍然存在。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产生巨大波动。由于外需骤降,200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相较于2008年下降4500亿美元,降幅达到16%。中国通过增加出口信贷规模、调高出口退税率、支持企业出口带动产业升级等激励措施,积极应对冲击。在政策支持下,2008—201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达10.5%。但是,贸易顺差在持续减少,2012年贸易顺差为2318.7亿美元,相较于2008年下降1170亿美元。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追求高质量的贸易发展模式。中国在开放贸易市场、建立贸易伙伴、改善贸易结构等方向上实现突破。2013—201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45 633亿美元上涨至51 42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6%,并于201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与此同时,中国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持续增加,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下降,贸易模式在不断完善。
三、贸易与农村贫困:实证检验
不同地区由于地理特征、经济发展程度、自然禀赋等差异,贸易冲击的效应存在区域性差异。陈怡、王洪亮、姜德波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有正向作用,但是在劳动要素流动性较高的地区,贸易对贫困人口收入的增长效应更大[25];黄季焜等使用CAPSIM模型得出贸易对不同地区的贫困农民会产生差异性影响,西部和北部地区的贫困人口可能会遭受损失[17];郭熙保、罗知使用1996—2005年的省级年度数据,证明了贸易的减贫作用随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而增加,对内陆地区的减贫作用大于沿海地区[21];然而,陈恭军、田维明使用1998—2010年的数据得到贸易开放的减贫效应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更加有效[26]。
图4(下页)呈现了2018年中国省级出口贸易冲击与贫困发生率的情况,其中,我们将省级地区当年与前一年贸易出口额差额的对数定义为贸易冲击,来反映区域性所受贸易增量的影响。2018年,从贸易冲击来看,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和四川存在明显的贸易出口增长,出口增量均高于10万美元,西部地区的贸易增量则总体处于较落后水平。同期,我国有8个省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零,分别是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上海、天津和北京。贫困发生率最高的省份集中在西部地区,甘肃、新疆、西藏、贵州、云南的贫困发生率均高于4.8%,与其他省份存在明显的差距。由图4可以明显看出,地区贸易冲击与贫困发生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贸易冲击越大的地区,贫困发生率越低。另外,我们选取省级地区2010—2018年贸易量占全国贸易量的平均比重用以反映地区相对贸易体量。从图5可以看出,贸易体量越大的地区,贫困发生率越低,可见贸易开放对地区贫困率存在明显负向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利用实证回归来探究地区间贸易冲击的差异是否能解释贫困发生率的高低。我们使用2010—2018年省级数据实证检验贸易冲击与地区贫困发生率的关系。数据使用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省级年度贸易数据和《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的贫困数据。表1报告了实证检验中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具体地,我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Povertyit=α+βtradeshockit+γXi+δi+θt+ε
其中:Povertyit表示i地区t年的贫困发生率;tradeshockit表示地区i在t年的出口贸易冲击;X为一个地区的特征变量,包含了地区生产总值、常住人口、建筑业产值、财政一般支出、外商直接投资5个变量,δi为省份固定效应,θt为年份固定效应。表2报告了回归结果。
从表2列(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贸易出口冲击显著降低了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地区所受贸易出口冲击每上升1%,贫困发生率将降低0.0058%。回归结果展示了贸易冲击与贫困发生率的显著负向关系,与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27-28]。贸易开放能够从经济增长、就业创造等影响途径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同时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29]。接着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使用地区进出口贸易差额对数刻画贸易冲击,在度量中加入进口逆差的影响能够更加全面地衡量地区贸易情况的变化。根据表2列(2)的回归结果,同时考虑进口与出口贸易量的变化,贸易冲击对地区贫困发生率仍然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即进出口贸易冲击每上升1%,贫困发生率将下降0.0047%。另外,贸易依存度能够反映地区参与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各地区贸易开放度的不同是导致其所受贸易冲击大小的重要原因,我们使用贸易依存度进行稳健性检验,表2列(3)报告了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贸易依存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当地农村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0.02个百分点,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然而,基准回归的结果并不能说明贸易对貧困发生率作用的因果效应,内生性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将2009年各地区出口贸易占比与全国贸易冲击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我们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和相关性的要求。一方面,2009年出口贸易占比是固定的比例,不随时间变化,同时全国范围的贸易冲击与省级层面贫困发生率也没有直接关系,两者的交互项满足排他性要求。另一方面,2009年出口贸易占比反映各省份贸易的相对量级,随时间变化较小,因而工具变量与实际省份所受贸易冲击也满足相关性要求。具体地,我们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完成工具变量回归检验:
其中:trade_ratioi2009表示2009年各省份贸易出口占比,tradeshockt表示2010—2018年全国贸易出口冲击,其余变量含义与基准回归一致。表2列(4)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地区所受贸易出口冲击每上升1%,贫困发生率将降低0.0104%,相较于基准回归具有更大的经济影响,说明基准回归低估了贸易的减贫效应。表2列(5)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第一阶段的结果,固定贸易结构模拟的省级贸易冲击与实际所受贸易冲击之间呈现显著正向相关性,且工具变量回归F值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佐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四、贸易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机制
贸易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减贫也是经济发展的一大目标。贸易通过各经济市场和网络传导,其中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重要市场,贸易冲击能够创造就业、提高均衡工资,从而实现贫困人口的收入提升。另外,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是城镇化进程中重要的移民群体,移民网络也是一个重要的传导机制,内陆地区外出务工人员选择经济发展更快的沿海地区务工,能够带动内陆地区贫困人口脱贫。
我们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微观角度来验证贸易冲击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途径。CFPS数据库搜集了个体、家庭和社区层面的数据,从2010年开始每两年公布一次调查数据,已经有5次的面板数据可供使用。我们通过家庭数据限定农村范围,并识别出农村贫困人口,获得家庭工资性收入和外出务工信息,验证贸易冲击的影响途径。
CFPS数据库现有数据覆盖时间与基准回归中所用数据覆盖时间一致,并且中国2010年实行了最新的贫困标准,我们可以在同一贫困标准下探究影响机制,避免了贫困标准变动带来的贫困识别误差。我们仍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Yait表示家户层面的被解释变量,包括外出务工、人均工资性收入等变量;主要解释变量为省级层面的贸易冲击tradeshockit;模型中加入家户层面控制变量Za,包括家庭规模、是否从事农业、农业收入对数、房屋产权和存款数额;地区层面控制变量Xi,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常住人口、建筑业产值、财政一般支出、外商直接投资;模型中加入省份固定效应δi和年份固定效应θt。
(一)外出就业
我国非技术劳动力资源具有比较优势,非技术劳动力也是最有可能从贸易中受益的劳动力群体[30]。农村外出就业人口大多是非技术劳动力,2018年贫困地区仅有22.7%的农村劳动力接受过技能培训,且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在低端行业,从事非技术职业[31]。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提高是摆脱贫困最直接的方法。Maertens et al. 指出,贫困家庭通过贸易受益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而不是产品市场[32]。从供给端来看,贸易冲击会创造大量就业,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增加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从需求端来看,贸易冲击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推动了均衡工资提高,农村外出就业人口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性收入。
首先我们验证贸易冲击是否会减弱贫困发生的概率。我们识别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家户为贫困,即Yait为是否属于贫困,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3列(1)报告了回归结果。根据我们对边际效应的计算,贸易冲击每增加1%,贫困概率减少0.3%,贸易冲击对贫困仍然呈现显著的负向效应,微观数据支持了宏观结果。从供给面来看,贸易冲击吸引更多的人外出就业,我们预期可以观察到受贸易冲击越大的地区,家户更大概率会参与外出务工。我们将通过家户层面数据探究贸易冲击是否增加了家户成员外出务工的概率,即Yait为家庭是否有外出务工人员,我们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分析,表3列(2)报告了回归结果。对回归结果进一步计算,我们得到贸易冲击每增加1%,该地区家户参与外出务工的概率显著上升0.4%。回归结果证明了贸易冲击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意愿,农村富余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增加了家庭的收入来源,从而提高了农村家庭收入。
根据2018年数据,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的41%,是占比最大的收入来源,同时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增收贡献率达42%,也是最大的增收来源①。因此,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侧来看,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均衡工资水平上升,使得农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提高,并且工资性收入占比也有所提升。家中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相较于没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可能获得更高的工资性收入,从而实现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表3列(3)报告了外出务工选择对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相较于没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显著增加4.928%。表3列(4)报告了外出务工对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比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相较于没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比显著增加0.39%。
另外,贸易冲击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使得从事农业人口减少,进而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和人均农业收入提高。在外出务工人员比例越高的地区,人均农业收入会增长得越多。基于CFPS数据库,对家户人均农业收入在省级层面取平均,计算出该地区外出务工人员比例,表3列(5)报告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地区外出务工比例每上升1个百分点,可使当地人均农业收入显著增加0.015%,但农业收入途径的经济效应相较于工资性收入途径的影响是微弱的,外出务工对人均收入的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来实现。
(二)移民网络
农村勞动力选择外出务工,不仅是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而且是务工人员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纽带。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以自发和亲戚朋友介绍为主,其中亲戚朋友介绍外出占30.1%,外出劳动力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从劳动力外出地区选择来看,以省内就业为主,选择省内就业的外出劳动力占比达到65.4%,省外就业占比为34.6%[31]。
我国不同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东部地区大多数省份拥有海上运输的地理优势,贸易开放程度远高于内陆地区,2018年东部省份吸收了73.8%的出口贸易冲击。来自贸易冲击较弱的地区的外出务工人员,在东部地区获得了更高的工资水平,从而能够提高其家庭的人均收入,带动迁出地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说,省外就业的外出务工群体建立了地区间影响的通道。
我们验证贸易冲击是如何影响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地区选择的。首先,我们关注省外务工,即Yait为家中是否有在外省务工的人员,使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表4列(1)报告了回归结果,根据边际效应的计算,结果显示,贸易冲击每下降1%,该地区人员选择到外省务工的概率上升0.5%。其次,我们关注外出务工人员对东部地区的选择,即Yait为家中是否有在东部地区务工的人员,表4列(2)报告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贸易冲击每下降1%,该地区人员选择到东部地区务工的边际概率上升0.46%。这两项结果说明,对于受到贸易冲击较小的地区,外出务工人员更倾向于选择外省区务工,且更倾向于到东部地区务工。受到贸易冲击较小的省份,其贸易开放度也相对较低,该地区外出务工的人员有更大的概率选择贸易开放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务工,因为其预期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性收入。
外出务工人员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会寄回到农村家庭,从而提高家庭的人均收入,帮助家庭脱贫。在东部地区务工的人员,其务工所在地的工资水平往往高于其迁出省份,那么外出务工人员将工资寄回就产生了省份之间的资金流动,实现了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增加收入的效应。首先,我们关注有东部地区务工人员的家庭相较于其他家庭的寄回工资数额和家庭工资性收入水平,表4列(3)和列(4)报告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相较于其他家庭,有东部地区务工人员的家庭收到的务工寄回的工资水平比其他地区高出1.162%,家庭工资性收入高出2.423%。得益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开放,在东部地区务工的人员寄回家庭的工资数额明显更高,因而提升了家庭收入水平,增加了家庭人均收入,从而有助于减贫。进一步地,我们限定样本为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表4列(5)报告了回归结果,相较于在其他省份务工,在东部省份务工的家庭工资性收入高出0.779%,印证了东部地区对其他地区的带动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扶贫减贫,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大规模开发扶贫计划帮助近三亿人脱贫。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14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明确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
在我国减贫事业中,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方略,其中产业扶贫是最重要的手段。《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贫困户更多分享农业全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值收益,产业发展最终受益的是参与其中的农村劳动力。产业扶贫的核心是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就业、增加收入来源,是造血式扶贫。国际贸易对产业扶贫的实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冲击可显著降低地区贫困发生率,能够一定程度解释地区贫困发生率的差异。贸易扩张增加了国内市场需求、创造了大量就业,为农村贫困劳动力提供了外出务工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提高了农村家庭工资性收入,也因为劳动力外出,农村人均土地禀赋增加,人均农业收入实现提升。另外,由于我国地区间差异明显,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发展明显好于其他地区,贸易冲击刺激农村劳动力前往东部地区务工,形成了劳动力流动的移民网络,加强了省份之间的帮扶联系。国际贸易冲击促进了地区产业全面发展,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移民网络,帮助低收入贫困人口增加收入来源、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实现脱贫。
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发展机会,导致财富在国家间再分配,世界不平等程度加剧。在国家内部,资本与劳动报酬出现不平衡增长。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出现反全球化倾向,国家民粹主义情绪高涨。在未来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对外贸易可能经历不可预期的波动。为保证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一方面,中国要扩大开放程度,提高国内经济的贸易开放度,使得各产业部门能够享受贸易带来的红利,刺激产业发展,带动产业扶贫,进一步消除贫困;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强大的国内市场,强劲的国内需求能够有效弥补全球化退潮后的消极外需,是保障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持续发展的根本。内需强劲是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产业发展是产业扶贫的基础,未来稳定的产业扶贫应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
参考文献
[1]马轶群.农产品贸易、农业技术进步与中国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J].国际贸易问题,2018(6):41-53.
[2]王爱民,李子联.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J].经济经纬,2014(4):31-36.
[3]程国强.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结构与贡献[J].管理世界,2004(11):85-96.
[4]林薛栋,魏浩,李飚.进口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的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7(2):97-106.
[5]余淼杰.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J].经济研究,2010(12):97-110.
[6]毛其淋,许家云.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加入WTO的微观证据[J].经济研究,2016(1):69-83.
[7]李志平.“送猪崽”与“折现金”: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分析与政策模拟研究[J].财经研究,2017(4):68-81.
[8]刘世成.扶贫小额信贷的瞄准机制与绩效评估实证分析——基于四川R县数据[J].西南金融,2016(9):12-14.
[9]吕炜,刘畅.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社会性支出与贫困问题研究[J].财贸经济,2008(5):61-69.
[10]徐翔,刘尔思.产业扶贫融资模式创新研究[J].经济纵横,2011(7):85-88.
[11]BHAGWATI J N, SRINIVASAN T N. Foreign trade regim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a[Z]. NBER Books, 1975.
[12]BHAGWATI J N, SRINIVASAN T N. Trade policy and development[Z]. World Bank, 1978.
[13]VAMVAKIDIS A. How robust is the growth-openness connection? Historical evide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2, 7(1): 57-80.
[14]AHMED A D, CHENG E J, MESSINIS G. The role of exports, FDI and imports in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J]. Applied Economics, 2011,43(26): 3719-3731.
[15]董运来,余建斌,刘志雄.农业贸易自由化、贫困和粮食安全:印度的经验[J].華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21-29.
[16]李石新,邹新月,郭新华.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农村贫困的减少[J].中国软科学,2005(10):51-57.
[17]黄季焜,徐志刚,李宁辉,等.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的农业、贫困和公平[J].农业经济问题,2005(7):9-15.
[18]CHEN S H, RAVALLION M. Household welfare impact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Z].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3.
[19]HAN J, LIU R J, ZHANG J S. Globaliz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7(2): 288-297.
[20]胡海军,张卫东,向锦.贸易开放度与我国农村贫困的联系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8):15-21.
[21]郭熙保,罗知.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与减轻贫困——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08(2):15-24.
[22]HUANG J K, et al. Agricultura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overty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7,18(3): 244-265.
[23]王燕飞,蒲勇健.中国对外贸易的劳动就业效应:贸易结构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09(3):10-19.
[24]FEENSTRA R C, WEI S J. Introduction to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1-31.
[25]陈怡,王洪亮,姜德波.贸易自由化劳动要素流动与贫困[J].国际贸易问题,2013(4):27-39.
[26]陈恭军,田维明.扩大贸易开放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2(11):85-90.
[27]HASSAN A F M K. Trade open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Search for a causal relationship[J]. South As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5, 12(4): 38-51.
[28]AGUSALIM L. The dynamic impact of trade openness on pover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donesia's econom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Issues, 2017(7):1.
[29]张茵,万广华.全球化加剧了城市贫困吗?[J].经济学(季刊),2007(1):105-126.
[30]HARRISON A. Globalization and poverty[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6.
[31]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9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32]MAERTENS M, SWINNEN J F M. Trade, standards, and poverty: Evidence from Senegal[J]. World development, 2009, 37(1): 161-178.
(责任编辑:文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