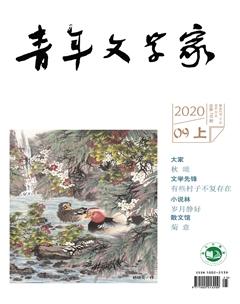尘世的蝉
贺湘君
坐在春寒料峭里,怎生就怀念起蝉鸣?传说六月天会飞雪。那么,三月天也会响起蝉鸣吗?分明又是痴人说梦了。举目窗外长空,春雨仍是没完没了,挥之不去的倒春寒,将心情挤迫得逼仄横起且莫名生恹。
那晚,将看剩的半卷书和凉了水的茶壶收起。新买的《花间十六声》里掉出一张前几日随意夹进去的书签。“吃茶去”,清冽三字入眸来,有济群法师的印章。陌从苏州西园寺里求回来的“西园茶事”。背面写着:问茶、读书、静坐、带心回家。我已端坐两个时辰,看风从鹅黄帘子外吹进来,寂寂寥寥翻动我的书页;也吹过印有牡丹的青花瓷壶,落在素净的桌布上,悄无声息地隐匿。我却忘了起身,去阻止那一刻禅意的惊起。唯有静坐。
三月天里响不起蝉鸣,蝉声是夏日绝句。我们一切的行为举止,包括鬓上颜发,指间算盘,无一不接受自然造化的四季差遣。夏听蝉声,冬看雪。你走了很远的路,于夜里归来,借着旧时月光审度眼前的屋檐窗棂,看见满庭阶的秋霜。蝉音是墨夜唯一的歌者,将你心口的凸起和凹陷,削平填实。蝉声,曾几何时,收藏了儿时温暖的记忆。
我们总会在花朵熙攘的季节怀念冰雪的单纯唯一,也会在寒风凄凛的冬日惦记着春暖花开,做着想去喂马劈柴、浪迹天涯等不切实际的幻想。鸽群收买了天空的纯净,蝉翼垄断了世间的梦想,我们浮尘野马般的人生,亦只是游历在尘间印在壁上的佛眼,等待一个醍醐灌顶的提醒:“若有人于河中掬一瓢饮,当知,已饮阎浮提一切河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或春风得意高朋满座,或历尽沧桑心如止水,或糊糊涂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我想来应该并为后一类的集合里。我们日日啜饮尘烟得以寄身的红尘,溜风潲雨是免不了的烦恼。欢颜少,寡意多,生命自有实践的饱满意义,也填不满幽黑隧道的攀爬挣扎。
东晋陶渊明,少时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鸿鹄大志,当梦想铩羽而归,他便悲壮地折戟沉沙,优雅的转身。归于东篱下,做个自在的采菊人,另辟蹊径,为世人寻来《桃花源记》的慰藉。不为五斗米折腰,仅仅是一个文人输不起的清高吗?我分明看见了陶公生了一炉火,热了一壶酒,悠悠吟唱着:“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
归隐,是古人垦拓的一种精神图腾。今天,仍然有它淡墨轻烟的绝妙风景。它应是一种常人难以抵达的境界,是人人心中甘愿供奉的净地。现代人也思渴归隐,与山野僻壤共存不是归隐的唯一出路。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诚然我们已找不到昔日的南山,我们却可以选择与書本、植物、花朵、月光、清茶等为伴,随时随地于喧嚷尘世里捞起一片旧时月光。
《花间十六声》里第十五记写《金缕衣》,用了大量的笔墨介绍法门寺出土的金缕衣。眼神掠过浓墨重彩明亮亮的词汇字眼时,脑海里浮现一个清峻高雅的人名:李叔同,亦是弘一法师。他曾作《金缕曲》述志:“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
从风华才子到芒鞋布衲、托钵空门、最后圆寂于陋室绳床的一代高僧,承受了世人几多狂澜惊愕?弘一大师病危前手书之偈语:“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他这一生,应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典范,连张爱玲也说过一句:“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的寺院围墙外,我是如此的谦卑。”这是一种高贵的清醒,留待世人做反复的比较、辨知和参悟。
思想自是不可禁锢的浮尘野马。抬眼看去,路边枝头春意在闹,夏天仿佛蹲伏在门口那汪雨水里,跨了门槛就携阳光而来。耳边便隐约响起“知了,知了”的一声声高亢的蝉鸣。
且做尘世的蝉,餐风饮露,亦是一种朴拙圆满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