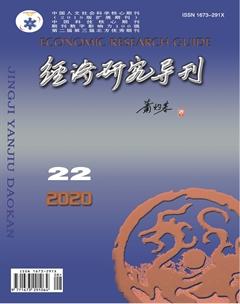资源型城市城镇用地增长边界划定研究
徐宏娟 耿哲 徐岩



摘 要:城镇用地增长边界(UGB)划定对资源型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以徐州市中心城区为例,构建地理加权元胞自动机(GWR-CA)模型,在对该模型进行校准和验证的基础上,考虑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约束条件,设定未来城镇用地需求情景,基于“反规划”理念,对2030年UGB进行划定。结果表明:GWR-CA对2015年城镇用地增长模拟的精度较高,可用于模拟未来城镇用地扩张;两种情景下,2030年分别新增城镇用地106.75km2和273.25km2,前一种情景更为合理,在生态约束下2030年UGB面积为441.02km2,城镇空间主要向东部及东南部紧凑式扩张。研究考虑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环境约束,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引导城市空间有序发展。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GWR-CA模型;城镇用地增长边界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22-0115-06
引言
城镇用地扩张一直是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镇用地不断扩张,但城镇用地无序蔓延给区域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带来了许多问题,如耕地过度非农化、森林砍伐、生态环境破坏等[1]。如何有效引导城市合理扩张,协调城市发展和资源及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2]。特别是在资源型城市,由于矿产资源的开采,资源型城市出现沉降塌陷、液化灾害等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严重制约着城市建设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综合考虑其生态环境约束,引导其城市用地有序增长,成为这类区域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UGB)作为目前控制城市无序扩张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之一,其最早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开展研究和实验[3]。UGB不仅是城市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的分界线,也是城市在某一时期城市扩张的边界线[4]。有效划定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可遏制城市“摊大饼”式无序蔓延,倒逼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城市用地利用效率,从而降低城市增长的资源消耗成本[5]。我国在UGB研究与应用方面相对较晚,2006年《城市规划编制办法》首先提出要进行UGB的划定,同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将刚性边界和弹性边界的概念引入北京市城市边界之中[6]。然而,UGB一开始主要根据研究人员的经验划定,科学性相对不足,后来学者们综合考虑空间因素(如交通、地形),采用基于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CA)的城市用地增长模型[7~8]、CLUE-S[9]、CA-Markov[10]及FLUS[11]等模型划定UGB,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已有研究大多针对非资源型城市开展UGB研究,而对资源型城市UGB划定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在已有模型中,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GWR)能可有效探索空间异质性影响因素[12],因而将其与约束性CA模型进行耦合的GWR-CA城市用地增长模型[13]可更有效地为UGB划定提供依据。
为此,本研究以资源枯竭型城市徐州市的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对其2005—2015年城镇扩张驱动力进行分析,构建GWR-CA城镇用地增长模拟模型对研究区2030年城镇用地扩张进行情景模拟,进而划定其UGB,以求为研究区城镇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一、研究区概况及数据
(一)研究区概况
徐州市位于江苏省西北部,其地处东经116°35′~118°66′,北纬33°71′~34°97′。徐州是中国第二大铁路枢纽,交通发达,区位优势明显,有“五省通衢”之称,也是华东地区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作为资源型城市,徐州市歷史上依资源而兴、靠资源发展,然而,随着矿产资源逐渐枯竭,一系列生态问题陆续凸显,如矿产开采造成的地面塌陷与沉降、水体污染等,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徐州市正处于转型关键时期,并正着力打造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导致近年来徐州市特别是其中心城区(包括贾汪区、泉山区、铜山区、云龙区、鼓楼区6个区)城镇用地快速扩张。因此,徐州在生态环境问题、地理位置、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及土地利用变化等方面均具有典型性,将其作为研究区可为资源型城市城镇用地增长边界划定提供参考。本研究以徐州市中心城区作为研究区(见图1)。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数据包括土地利用数据、DEM数据、城市规划数据、交通区位图及社会经济发展数据等。其中,土地利用数据采用2005年、2015年的Landsat TM遥感数影像图进行解译,土地利用类型分为7类:城镇用地、水域、耕地、草地、林地、其他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影响徐州城镇用地扩张的潜在因素分为地形因素、可达性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其中地形因素包括高程和坡度,主要通过30m分辨率DEM(地理空间数据云)处理而来;可达性因素包括到高速公路的距离、到一般公路的距离、到市政府的距离、到区政府的距离、到乡镇政府的距离、到水域的距离及到景点的距离等,这类因素通过ArcGIS中的欧氏距离工具分析得到;自然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河流、未稳定塌陷区、山林保护区、洪水淹没区、严重液化区、风景名胜区、湿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二级水源保护区等,主要来自《徐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年)》等资料。以上所有因素都统一处理为30m分辨率的栅格数据,城镇用地规模预测中所用的人口数据来源于2005—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徐州统计年鉴》。
二、研究方法
(一)GWR-CA模型
CA模型因具有自组织性、“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和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反映城市发展变化的能力而被认为是模拟复杂城市系统非常有效的模型之一[14],CA中元胞(土地单元)具有两种状态:城镇用地和非城镇用地,每个元胞都在特定步长t下按已设定的转换规则进行转换[15]。元胞i在t+1时刻的状态转换概率Pgi,t受其当前的状态Si,t、空间变量影响下的土地利用转换概率Pdi、周边邻域影响Pni、限制性因素Con和随机因素Sto的综合作用[16]。Pgi,t的表达式为[13]:
采用GWR-CA模型进行分析时,首先计算研究时段需转换的元胞数量num,并设定每次迭代转换数量k,本文在模型验证时主要通过获取研究时段内城镇用地变化数量来求得num,而在未来城镇用地模拟时通过城镇用地需求预测获取num;然后选择具有最大Pgi,t的k个非城市用地元胞进行转换,并更新土地利用图层,重新计算Pgi,t,重复上述迭代过程,直到所转换的元胞数量等于num为止[8]。
(二)模型校准及验证
本文采用2005—2015年数据对GWR-CA模型进行校准。根据研究区实际,选取以下潜在驱动因素:到水域的距离(X1)、到高速公路的距离(X2)、到一般公路的距离(X3)、到镇政府的距离(X4)、到区政府的距离(X5)、到市政府的距离(X6)、到景点的距离(X7)、高程(X8)和坡度(X9)。同时,作为资源型城市,研究区城镇用地扩张的绝对限制因素包括未稳定塌陷区、山林保护区、洪水淹没区、严重液化区、风景区、湿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二级水源保护区、湖泊、河流、水库以及坡度大于25度的土地单元,对于这些绝对限制性因素,将其Con值设置为0,其他区域设置为1。
为获取模型各变量的参数,本文分别提取1 250个发生城镇用地转换的元胞(Y=1)和1 250个未发生城镇用地转化的元胞(Y=0)共2 500个样本点用于GWR模型分析。首先,基于SPSS软件对各因素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并以方差膨胀因子VIF<10为标准剔除具有显著共线性的潜在因素,再将保留的因素纳入GWR4.0软件中进行GWR回归分析,并采用ROC检验(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回归分析结果,ROC越接近1,模型有效性越高。在此基础上通过克里金空间插值法对各驱动因素回归系数进行空间插值,从而获取各驱动因素在各个栅格处的作用系数。
模拟模型精度验证主要采用总体精度、Kappa系数、FOM指数(Figure Of Merit)等方法[19],其中,总体精度介于0~100%之间,Kappa系数、FOM都介于0—1之间,以上指标值均越大越好。对于Kappa系数,当其大于等于0.75时,模型具有较好的准确性,0.5 (三)资源型城市城镇用地增长边界划定思路 “反规划”理念认为,城市规划应先将城市生态基础保护起来,从而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20]。基于“反规划”思想,本文通过参考《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2005年)和《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第224号)初步划定生态控制线,主要包括山林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二级水源保护区,再结合徐州资源枯竭型城市和自然环境的特点,将未稳定塌陷区、洪水淹没区、严重液化区、湖泊、水库、河流以及坡度大于25度的区域也纳入控制线范围,在此基础上对城镇用地进行布局。本文目标年城镇用地扩张边界划定具体思路为:首先,根据上述过程划定生态控制区并将其作为GWR-CA模型的绝对限制因素;其次,结合历史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预测目标年的城镇用地需求量;最后,在采用历史数据对GWR-CA模型进行校准和精度验证后,将生态控制区作为绝对限制性图层,采用GWR-CA模型对未来城镇用地扩张进行情景模拟,并选择合适的情景划定城镇用地边界[11]。 本文设定两种未来发展情景:情景一,基于综合增长率的城镇人口及城镇用地预测,情景二,基于马尔科夫模型的城镇用地预测。其中,情景一主要是考虑近年来研究区城镇人口年均综合增长速度,进而预测2030年城镇人口数量,并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确定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标准,进而预测2030年城镇用地規模。情景二采用广泛用于土地利用数量变化预测的马尔科夫模型[21]对城镇用地规模进行预测。分析时,本文以2005年为基期年,2015年为验证年,土地利用类型的转移概率公式为[22]: 三、结果分析 (一)模型校准与验证结果 首先,在GWR分析前对自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9个潜在变量均不存在显著共线性,进而将其全部带入GWR进行分析。结果表明,GWR模型的赤池信息准则(AICc)为1 163.182,而全局Logistic回归的AICc为1 412.293,GWR的AICc结果小于全局回归模型,表明采用GWR模型可获得最优带宽。对模型进行ROC检验,结果表明,GWR和全局Logistic模型的ROC分别为0.968和0.902,表明两者的拟合效果均很好,但GWR模型拟合效果更优,因此研究区城镇用地扩张驱动力应考虑空间异质性特征。 从回归模型结果来看(见下表),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到高速公路距离(X2)、高程(X8)、坡度(X9)对研究区城镇扩张影响均为正向,回归系数分别在0.146~0.402、0.013~0.085、0.013~0.059之间,到一般公路距离(X3)、到镇政府距离(X4)、到区政府距离(X5)对城镇扩张影响均为负向,回归系数分别在-3.392~-0.972、-0.706~-0.076、-1.037~-0.326之间,而其余因素的影响既有正向也有负向,这表明各变量在不同区位对城镇用地扩张有着不同的影响效果。进而,采用克里金空间插值法对以上各变量回归系数进行空间插值,从而得到各元胞各变量对城镇用地扩张的影响系数。 将以上空间插值得到的结果带入式(2)和式(3)求得各变量作用下非城镇用地城镇化的概率图层,进而基于2005—2015年数据采用GWR-CA模型进行模拟,并将2015年模拟结果与实际土地利用现状进行对比,采用前述精度验证指标进行分析,结果(见图2)表明,GWR-CA模型的总体精度为96.52%,Kappa系数为0.82,FOM为0.58,Kappa和FOM值分别大于0.75和0.5,且FOM大于已有研究中的FOM值[23~26],说明校准后的GWR-CA模型能较好地反映研究区城镇用地扩张过程,该模型可信度较高,可用于对研究区未来城镇用地扩张的模拟。 (二)目標年城镇用地增长边界划定 本文根据前述两种情景进行未来城市用地扩张模拟:情景一,基于综合增长率的城镇人口及城镇用地预测,预测出2030年研究区城镇人口为383.38万人,按人均建设用地115m2/人计算,可得2030年城镇用地面积为441.02km2,比2015年增长106.75km2;情景二,基于马尔科夫模型的城镇用地预测,将2005年与2015年作为预测基期年,利用不同地类之间面积数量或比例关系进行概率转换[22],预测出2030年研究区新增城镇面积273.25km2。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政策与规划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对城市建设用地实行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坚持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27]。因此,未来城镇扩张速度与以前相比会有所减缓。2018年徐州荣获联合国人居环境奖,成为宜居城市中的翘楚,自2015年以来,徐州一直致力于旧城改造工作,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战略位置,打造生态宜居的样板城市,这就要求徐州节约集约用地,遏制城镇的粗放扩张,加快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故此徐州2015—2030年主城区的城镇扩张面积不宜过大。因此,本研究中马尔科夫模型在未来城市用地扩张模拟方面可行性不强,而情景一预测结果更符合未来发展情况,故将情景一作为城镇用地增长边界划定的依据,故需转换的城镇用地栅格数为118 469个,进而确定城镇用地增长边界(见图3)。 从情景一下城镇用地增长边界模拟图来看(见图3),新增城镇用地主要分布在铜山区、云龙区和鼓楼区,而贾汪区、泉山区相对较少,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城镇用地扩张要求地势平坦,连霍高速与淮徐高速的交汇加速了附近城镇的发展,徐州经济开发区与铜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带来的经济增长促进了开发区附近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用地增长边界划定结果表明,2015—2030年新增城镇用地约106.75km2,城市空间出现向东部和东南部的扩张趋势,同时生态约束控制使城镇用地增长更为紧凑,有利于倒逼已有城镇用地的集约高效利用,保护耕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同时,由于在城镇用地扩张模拟过程中综合考虑了采矿塌陷地等生态敏感区域对城市建设的影响,划定的城镇用地增长边界更有利于协调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因此,以上结果不仅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也遵循了城镇用地扩张的客观历史规律。 四、结论与讨论 针对已有研究较少对资源型城市城镇用地增长边界进行研究的问题,本文以徐州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在“反规划”理念下运用GWR-CA模型来划定2030年其城镇用地增长边界。研究表明:首先,GWR-CA模型模拟结果的总体精度、Kappa系数、FOM分别为96.52%、0.82和0.58,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可用于对未来城镇用地扩张进行模拟。其次,基于综合增长率的城镇人口及城镇用地预测结果更符合研究区发展实际,在“反规划”理念下划定2030年徐州市中心城区的城镇用地增长边界,新增城镇用地面积为106.75km2,城市空间有向东部和东南部扩张趋势,城镇用地集约水平将会提高。 限于数据可获取性,本文在驱动因素选择方面不够全面,如缺少基本农田这一重要的限制性因素。同时,本文采用遥感解译数据进行研究,在用地规模上可能与实际城镇用地会有一定差异。因此,未来需综合考虑以上问题,进一步提升研究区城镇用地增长边界划定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1] 丛佃敏,赵书河,于涛,等.综合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城市扩张模拟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以天水市规划区(2015—2030年)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18,(1):14-26. [2] Xia C.,Zhang A.,Wang H.,et al..Predicting the expansion of urban boundary using space syntax and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J].Habitat International,2019,(86):126-134. [3] 张韶月,刘小平,闫士忠,等.基于“双评价”与FLUS-UGB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以长春市为例[J].热带地理,2019,(3):377-386. [4] 刘伟玲,张育庆,杨俊.不规则邻域CA的城市增长边界研究——以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J].测绘通报,2018,(8):93-96. [5] Liang X.,Liu X.,Li X.,et al..Delineating multi-scenario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with a CA-based FLUS model and morphological method[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8,(177):47-63. [6] 张振广,张尚武.空间结构导向下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理念与方法探索——基于杭州市的案例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3,(4):33-41. [7] 龙瀛,韩昊英,毛其智.利用约束性CA制定城市增长边界[J].地理学报,2009,(8):999-1008. [8] 舒帮荣,刘友兆,张鸿辉,等.集成变权与约束性模糊CA的城镇用地扩张情景模拟[J].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13,(4):498-504. [9] Huang J.,Liu T.,Huang D.Delimiting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using the CLUE-S model with village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J].Land Use Policy,2019,(82):422-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