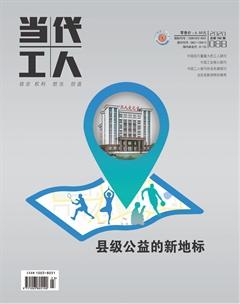到世界最高点寻找什么
三水

4月30日,中国移动在海拔6500米的珠峰前进营地开通5G基站,5G信号覆盖珠峰峰顶及珠峰北坡登山线路。
5月27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8名队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开展我国第七次峰顶测量工作。
今年的春夏之交,“珠峰热潮”让公众把视野重新聚焦在这座世界最高峰。
环球旅行探险家汝志刚,也选择在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60周年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沿着祖国境内的北坡路线一路攀登,再次亲吻“珠峰母亲”的额头。
第二次登顶
5月28日8时56分,在世界的最高峰,一场生命的考验刚刚结束。8844.43米,终究没有拦住一个热血沸腾的攀登者。汝志刚费力地摘下氧气面罩,长出了一口气。地球上,已经没有新高度可供他挑战了。
“汝志刚”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大众视线范围内,是在一年前,他第一次登顶珠峰。
尼泊尔时间2019年5月22日7点26分,汝志刚沿南坡路线成功登顶珠峰,返回大本营后,他上传了一条记录“希拉里台阶大堵车”的视频。
“希拉里台阶”是位于珠穆朗玛峰峰顶周围高约12米、长约50米~80米几乎垂直的裸露山体岩石断面,海拔8790米,距离8844.43米只有一步之遥。 在汝志刚看来,珠峰像一把汤勺,希拉里台阶就是勺把。
当天清晨5点前后,他和队友抵达希拉里台阶底部,上行和下撤的人正好撞上了,五六十人形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拥堵。
一侧是冰壁,另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悬崖,登山者只能贴着山脊线前行。汝志刚每隔一两分钟就要紧贴着冰壁,给对面的人让出空间,方便他们摘掉或者挂上安全锁。一摘一挂间,稍有不慎就会跌落万丈深渊。
两个多小时后,汝志刚终于艰难登顶,他“扑通”一声跪在群山之巅,手里的五星红旗和着风唰唰作响。那段摇摇晃晃的视频也最终轰动世界,被载入史册。
2019年12月底,汝志刚前往云南丽江、四川四姑娘山等地开始了他的“北坡攀登训练计划”。
以往,为了训练,住在嵩山脚下的汝志刚,一周内攀登6次嵩山,每次海拔上升1500米,来回近16公里山路,有的时候还一天来回攀登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他不得不调整训练计划。那段时间,他只能在小区内跑步。
4月10日,汝志刚抵达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正式开始珠峰北坡之旅。在5月8日之前的28天里,汝志剛和队友们会进行周期性的“拉练”,有时从大本营出发,沿着冲顶路线,在3号营地与1号营地之间折返;有时则会选择附近较低的山峰,进行登顶训练后,返回大本营。
5月16日,汝志刚与队友在珠峰一侧的向东峰边拉练,边等待窗口期。因为珠峰天气多变,精准的峰顶天气预报只能看到一周内的天气。为了尽量保障安全,登山者一般都会在窗口期冲顶。
5天后,汝志刚一行从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出发,行至海拔5800米的“过渡营地”。那一夜,营地被大雪袭击,汝志刚早上醒来时,发现帐篷已经有大半埋在雪中。
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5月23日,经过6小时的艰难跋涉,汝志刚与队友抵达6500米的前进营地。
前进营地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东面是海拔7016米的向东峰,南面是珠峰北坳,西面是海拔7530米的章子峰,仅仅在北面有一个S型的出入口。因此,整个山谷进入的氧气非常稀少,即使是夏尔巴向导(夏尔巴是一个民族,他们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大部分以“高山向导”为职业)都会有高反不适。
那天深夜,一直斗志昂扬的汝志刚,终于在队友拍摄的视频中露出疲态,他摩挲着标志性的大胡子,大喊一声:“加油!”
5月28日凌晨2点,汝志刚和队友开始向珠峰发起最后的冲击。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中,风声盖过了喘息声,汝志刚将自己扣在路绳的安全扣上,四肢紧贴冰壁,顶着风挺进。
8点56分,经历49天的攀登,他终于完成“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极限挑战。亘古耸立的巍巍珠峰,因为他们的到来,生出片刻生动。
转行理工男
登顶珠峰第一次成为汝志刚的目标,是在2015年。那年,他在朋友圈发西藏阿里的风景照时,为了凑够9张图,加上了一张珠峰的照片。当时的他就职于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还不具备挑战珠峰的能力。
很多人难以想象,学习通信工程专业的汝志刚是如何与珠峰结下不解之缘的。实际上,大学时期的汝志刚不仅有着扎实的计算机基础,还一直对中华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可能在旁人看来,我前后做的工作并没有任何关联,但对于有着异于常人的耐力和毅力的我而言,转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汝志刚说。
前期的工作经历为他后来世界环旅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2015年,汝志刚辞去软件工程师职务,放弃了朝9晚5的稳定生活,开启了探险生涯。他曾到世界73个国家旅行,徒步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前往罗布泊寻觅楼兰古城、登上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每次提起大自然,他从来不会用“征服”二字,而是“感谢接纳”。
在旅途中,汝志刚深刻感受到世界各地风土人情的文化意义,他开始创建自己的自媒体平台,用文字记录旅途故事。比如,他喜欢拍短视频介绍珠峰的一切,从帐篷、睡袋、垃圾桶,到碎石、冰雪、太阳。珠峰上的吃播,可能是一碗很快就放凉了的白粥,也可能是因为饮用水被牦牛污染,一道牦牛尿味的炖菜。“我做这些的目的其实就是想把中华文化宣传出去,”他说道,“随着去的地方越来越多,旅途也变得越来越深刻,我开始了解很多现有资料都没法查到的信息。我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些。”
在完成此次珠峰北坡攀登活动后,他还计划将于今年完成南极、南美洲的旅行探险,以及世界第二高峰K2——乔戈里峰的攀登活动。
他们的故事
在珠峰,几乎每一个登山者都见到过遗体,他们管这些叫作“路标”。海拔8000米往上,有超过200具登山者遗体,“那就像一个突然的警钟。”汝志刚说。
一年前,从南坡登顶后下撤至海拔8700米位置时,汝志刚遇到一位因体力透支而精神恍惚的印度姑娘。
匆匆一撇,不久之后便是一声惊呼,他迅速转头,只见“一块黑色巨石”向他滚来,他下意识躲开,还是被绳子的张力带倒。
缓过神后,他才发现自己的羽绒服已经被冰爪(套在鞋底增加冰上摩擦力的鞋钉)划破几个大洞,羽绒都飞了出来,而抓破他羽绒服的正是刚才的印度姑娘。
那一瞬间,他的心也曾跟着那道滑落的黑影一起下坠。
他看见夏尔巴向导双手拖拽着女孩的左臂,但无法阻止她的身体不受控制地下滑,双腿和右手无力地在世界之巅留下来过的痕迹,很快就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和雪崩掩盖。
返回营地后,汝志刚得知女孩最终遇难,他在日记中写下:被梦想碰撞的生命才是伟大的,你做到了!我会一辈子记住你最后时刻挣扎的画面,虽然至今仍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样的故事,但你追求梦想的精神会永远鼓励着我。
汝志刚回到大本营后的第二天,峰顶再次传来消息,又有3人死亡。汝志刚落泪了:“那一瞬间,时间仿佛是凝固的,直到远处马儿奔跑来的铃铛声打破了这一切,我才意识到我也是登山者,我也在为我的梦想而战。”
苍茫的珠穆朗玛峰,对于留下的人是永远的黑,而对于离开的人则是短暂的红,红与黑之间,是对山顶的信仰。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高度似乎有种与生俱来的崇拜感,抬头见到的大树、高楼、飞机、白云,都能让人勾勒出对美好的向往。
登山,自然也是这样的过程。
汝志刚喜欢带着憧憬和期待迎头而上,他认为,攀登过程中的不可预知,正是登山最大的魅力,登顶后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成就感更是难以言喻。
虽然有强烈的紫外线、剧烈的山风、突然的雪崩,但也有夜晚看似伸手就能抓到星星的璀璨夜空,以及在雪白巍峨的山体映衬下,金色的阳光辉映着珠峰之巅。沉醉在这样的景色里,汝志刚脑海里仿佛回响着海明威对高山上生灵的提问——“这头豹子到这样的高山上寻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