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评析
程 鑫
[提要]
公司虽在清算期间通过登报的方式向债权人进行清算公告,并按照行政主管机关的要求办理注销登记,但该程序并不具有证明公司股东对公司存续期间债权债务不再负责的绝对效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债权人能够证明对公司存在债务,且在公司注销前未得到通知的,其仍有权在公司注销后向公司的股东主张债权。
委托方向货代企业多给付的海运费、运杂费,同货代企业为委托方垫付的滞箱费,属于同种类债权,可以相互抵销。
[案情]
2016年1月1日,A公司与大连上城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城公司)签订《货运代理协议书》,其上记载:A公司委托上城公司办理大连及其他口岸进出口货物的订舱、报关、报检、提箱、提单签发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货运代理业务。由于A公司的过失导致委托货物无法及时出运,由此造成的损失及费用由A公司承担。A公司同意向上城公司支付运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具体数额上城公司应当向A公司出具结算清单。A公司按上城公司出具的费用结算清单支付运费及相关费用,应每周出具运费确认函并盖章确认,未及时确认又未对运费等相关费用提出异议的视为对费用的确认。A公司向上城公司提供了一份空白转账支票,其上有A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与法定代表人范某印章,收条上记载,此支票支付以下费用:1.进出口滞箱费;2.集装箱残损修理费。2016年5月3日,A公司委托上城公司海运出口订舱2×20GP,船舶名称LTENBURG,航次1619E,提单号QYHA公司6190316与QTHA公司6190251,集装箱号TEMU3249369 与MIIU0001880。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A公司法定代表人涉嫌刑事犯罪,货物无法正常报关装船出口,一直积压在港内。
2016年10月28日,A公司与上城公司签订协议,其上记载:A公司于2016年5月3日在上城公司(诺扬公司大连总代理)海运出口订舱2×20GP,编号为TEMU3249369 与MIIU0001880的两个集装箱已于5月6日正常入港,但由于A公司被海关缉私局调查,业务中断,导致货物无法正常报关装船出口,一直积压在港内。经协商,上城公司同意A公司指定代理人董某收取这两个20尺集装箱共计人民币50 000元以冲抵A公司欠费,货物由董某提走,两箱于2016年10月28日从大窑湾一期码头提走,预计于2016年11月2日返还大运场地。其后,上城公司收取了董某给付的50 000元现金。
2017年1月24日,大连海事法院对上城公司与A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6)辽72民初第6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A公司向上城公司支付2016年3月至5月货运代理相关费用人民币380 492元;支付人民币137 794元自2016年4月25日、人民币171 296元自2016年5月25日、人民币71 402元自2016年6月25日至实际支付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130%计算的违约金;支付诉讼相关费用人民币5 600元;驳回上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上城公司向大连海事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截至2019年3月19日,A公司履行了上述判决的全部给付义务。
自2015年始,上城公司与诺扬公司签订《代理协议书》,约定上城公司为诺扬公司在大连地区总代理,负责大连至日本港口集装箱班轮航线上的营运船舶在大连港的船舶代理与货运代理业务。
2017年5月24日,上城公司的业务往来邮件记载“应付金额为336 381美元”。2017年6月9日,诺扬公司为上城公司出具了金额为8 820美元(兑换人民币为60 858元)的发票。2017年6月26日,上城公司汇款336 381美元。上城公司原始的记账凭证上记载,“付A公司2016年11月滞箱费为8 820美元;汇总数额为336 381美元”,
上城公司成立于2006年9月27日,投资者2人,分别为B(投资比例90%)和C(投资比例10%)。2018年11月5日,上城公司股东会决议成立清算组依法清算,注销公司。2018年12月21日,上城公司清算组出具《清算报告》,该报告记载,已于2018年11月7日通知全体债权人,并于2018年11月7日在《大连晚报》第12版刊登了注销声明;剩余财产人民币2 418 531.8元按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公司注销后如有债权债务由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公司注销后,公司的账册、文件等交由C保管,期间2年。2018年12月27日,上城公司因决议解散被注销。
[争议]
一、被告B、C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二、原告A公司的起诉是否经过诉讼时效。
三、双方是否互负债务以及能否抵销。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B、C诉讼主体资格适格,A公司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双方互负债务能够抵销,故A公司诉请本院判令B、C连带返还A公司50 000元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的诉讼争议焦点为:一、被告B、C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A公司的起诉是否经过诉讼时效;三、双方是否互负债务以及能否抵销。
(一)被告B、C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公司清算组在清算期间应通知、公告债权人,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清理债权债务。B、C已证明上城公司在清算期间通过登报的方式向债权人进行了公告,但未证明其向已知债权人A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二款“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上城公司未完成清算义务,B、C在登记机关办理注销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对A公司有效。上城公司注销后,A公司以B、C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本院对B、C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
(二)A公司的起诉是否经过诉讼时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签订协议时间虽为2016年10月28日,但彼时A公司只是根据协议约定履行了支付50 000元费用的义务,尚无法知晓其权利会受到侵害,故本院对B、C主张以2016年10月28日作为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大连海事法院作出(2016)辽72民初第647号民事判决的时间为2017年1月24日,该案审理中并未抵销A公司委托董某支付的50 000元款项,A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对上述判决全部履行完毕,而在本案中的起诉日期为2019年11月6日,距离A公司知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不满三年,故A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三)双方是否互负债务以及能否抵销
关于A公司主张对B、董某的债权,A公司认为依据协议支付的50 000元费用既包括海运费、运杂费,也包括滞箱费等双方之间一切可能产生的费用。本院认为,大连海事法院(2016)辽72民初第647号案件审理中并未抵销A公司委托董某支付的50000元款项,A公司已于2019年3月19日对(2016)辽72民初第647号案件判决中确定的债务全部履行完毕,故有权向上城公司非依法注销后的股东即本案被告B、C主张50 000元债权。
关于B、董某主张对A公司的债权,其包括案涉集装箱的滞箱费、清洗维修费等。对于滞箱费,B、C主张的用箱日期为2016年5月3日至11月8日,依据协议,两箱于2016年5月6日正常入港,10月28日从大窑湾一期码头提走,预计于2016年11月2日返还大运场地。考虑到集装箱入港前必然存在至场地的取箱与装货环节,返场前存在洗箱环节,B、C主张的用箱日期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A公司向上城公司出具了给付进出口滞箱费与集装箱残损修理费的空白转账支票,表明双方对滞箱费与集装箱残损修理费的支付合意,故B、C有权向A公司主张滞箱费。具体数额方面,B、C提供了上城公司原始的记账凭证、业务往来邮件、银行汇款凭证与发票,原始记账凭证上记载的“付东方超捷2016年11月滞箱费为8 820美元;汇总数额为336 381美元”,2017年5月24日的业务往来邮件记载“应付金额为336 381美元”,2017年6月9日诺扬公司为上城公司出具的发票金额记载为8 820美元(兑换人民币为60 858元),2017年6月26日的上城公司的银行汇款记录显示其支付金额为336 381美元。据此,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上城公司已代A公司支付了滞箱费8 820美元,兑换人民币为60 858元的事实,故B、C亦有权利向A公司主张上述债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本案中,B、C负有返还A公司50 000元的到期债务,A公司负有返还B、C 60 858元的到期债务。B、C在庭审中主张抵销欠付A公司的50 000元到期债务,于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
[案例注解]
清算是公司注销的法定程序,在清算程序中,清算组负有清理公司存续期间债权、债务的法定义务。实践中,清算组的构成人员均为公司的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清算后资产的分配具有直接利益。公司法为防止清算组故意不通知债权人,设置了清算公告程序,但该公告仅仅具有公司注销的程序性合法效力,不能绝对免除公司存续期间的所负债务。基于实践的复杂性,债权人在公司清算公告期间可能基于各种原因无法及时申报债权。正如本案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清算期间因其他原因入狱导致无法申报债权,应认定为善意的债权人。对于该种情况,清算公告无法起到通知债权人的实际效果,故当然不具有免除双方之间债权债务的效力。公司虽经依法注销,但注销后的股东仍需要对公司存续期间的债权人承担债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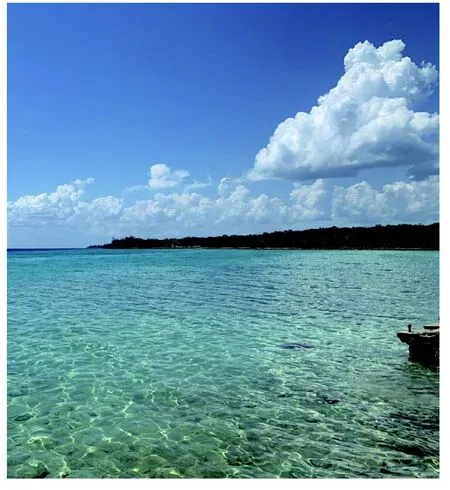
——以法定抵销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