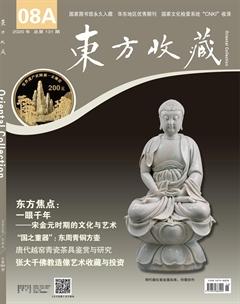“找回”诗筒
张静波



晚明、清代以降,笔筒自创式之始,即为文房之宝收藏的热门,而竹、木笔筒最为称雅。彼时,文人士大夫乃至江南巨贾豪门,竞相购藏,以为雅奢;及至清初,康雍乾三帝,更是堪称“粉丝”和“发烧友”,下诏延揽嘉定竹刻名匠,入值皇家造办处,助推竹刻一脉“火”遍宇内,其艺或工,穷乎神技,登峰及巅,五百年后,余脉未绝。
笔者入藏竹木笔筒几十数,其中有部分规格尺寸明显偏小,仅堪掌中把玩,或只能置放当下的圆珠笔(图1至图6)。
两年前入藏的一枚,更为袖珍、夸张(图7),竹筒矮三足,高13.5厘米,口径仅为4.5厘米,包浆润厚老熟,镌刻刀口深峻,呈枣皮红色,小巧而挺秀,古玩店家称为“小笔筒”。一眼看过去,放入一支毛笔,即有倾倒之虞,与常识不相符合;聯想舍下庋藏的同类们,疑窦丛生;再想到国内知名博物馆,大多也藏有此类“迷你”型“小笔筒”,遂查阅权威图书、图录,解惑求证。仅抄几例——《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竹木牙角器全集(1)竹刻器》图22、29,分别标名“明末清初,竹雕刘海戏金蟾笔筒,高11、口径4.9厘米”“清,竹雕留青山水楼阁笔筒,高10.3、口径5.9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竹雕溪山行旅图笔筒,清早期,‘石鹿山人李希乔制款,高11、口径5.2厘米”“清中期,黄杨木雕知音图笔筒,高10.7、口径5.7厘米”;还有,苏州博物馆藏品,“朱三松竹刻桐荫玩月笔筒,款镌‘丙午秋月,三松,高10.4、口径5.1厘米”。得到的结论,三家众口一词,均标名为笔筒……
再翻书。扬之水有《笔筒、诗筒与香筒》一文,说:“作为插笔之用的笔筒,蔚成风气在明清,它似与竹刻的发达密切相关,虽然兴盛之后便有了各种质料的作品,竹刻独领风骚之外,又有木雕、牙雕、漆雕、瓷器等。如果探寻其源,那么竹笔筒的前身可以说是诗筒。”扬先生旁征博引:“诗筒故事初见于白居易《醉封诗筒寄微之》及《秋寄微之十二韵》。”(按:微之,元稹字)由白居易与元稹“每以筒竹盛诗来往”唱和,开创中唐新乐府诗运动的一段佳话,及至宋代林和靖、宋石介,“直到明代中叶竹刻竟成为一项专门艺术,方始遥承唐宋遗韵。高濂《遵生八笺》卷八《起居安乐笺·下》列举出游携带的各式雅具,其中有‘诗筒葵笺。”再到《红楼梦》二十二回中出现的诗筒等,引征甚详。“关于竹诗筒的制作,王世襄《竹刻小言》引褚松窗《竹刻脞语》云:‘截竹为筒,圆径一寸或七八分,高三寸余,置之案头或花下,分题斋中咏物零星诗稿,置之是中,谓之诗筒,明末清初最多。”
其实,还要稍稍补充扬先生的博征,“诗筒”这一称谓还有前身、前世,系由“书筒”演化、“诗化”而来。早于白居易半个多世纪的李白,《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诗云:“桃竹书筒绮绣文,良工巧妙称绝群。灵心圆映三月江,彩质叠成五色云。中藏宝诀峨眉去,千里提携长忆君。”诗中虽谓曰“书筒”,可是,相信浪漫如诗仙,不单单用于纳书,亦纳胸中随时涌出的诗情、随手挥就的诗稿;再有,稍晚于李白的钱起,《裴侍郎湘川回以青竹筒相遗因而赠之》:“楚竹青玉润,从来湘水阴。缄书取节直,君子知虚心。入用随宪筒,积文不受金。体将丹凤直,色映秋霜深。宁肯假伶伦,谬为龙凤吟……”此中的“青竹筒”,直可“诗筒”之谓也。
回到明末清初,竹刻的发源地。《嘉定竹刻》载:“诗筒——文人雅集的产物……诗筒以竹刻成,是当时嘉定竹刻中的重要品种。诗筒有两种,一种形似香熏,一般高三四寸,径二寸许,置放于外书房案头或花下,将书斋中咏物零星诗稿放入筒中,长期保存;另一种形似笔筒而稍小,高三四寸,径三寸许,专用于文人雅集。诗筒以嘉定所产的护居竹制成……明清竹人中,侯崤曾、王梅邻为刻诗筒高手。”已故文学家、古籍收藏家黄裳,藏有海内孤本《明月诗筒》一卷,康熙年间侯崤曾后人刊刻,载录康熙九年(1670)中秋之际,侯氏后人举办诗会,邀请著名学者、名流十四余人,于故宅苣园“明月堂”举办“明月诗会”,诗会上使用的诗筒,即为侯崤曾之手泽。“侯崤曾所刻的诗筒目前尚未发现,但清代乾隆时期,刻诗筒依然较为普遍,王梅邻就是一位佼佼者。王梅邻所刻的‘翠筠逸兴诗筒,是一件地道的诗筒,现收藏于嘉定竹刻博物馆。”
除了竹、木制诗筒,作为陶瓷创制母国,独领风骚两千多年的陶瓷之国,瓷制诗筒在晚明也已出现,2005年“十七世纪景德镇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就出现了一个当时疑惑、现在看来有解的“问题”——著名青花瓷研究学者张浦生先生告诉苏富比亚洲区主席朱汤生,比例较为细长的小型“笔筒”,应该是“香筒”。马来西亚的庄良有女士进一步解释说,在庙里进香时,买了香后用香筒盛着去香炉那儿烧。朱汤生敏锐地质疑道,那么这些小型细长“笔筒”上常有的同文人书斋有关的款识和纹饰,明显同进香无关,又怎么解释呢?
如上所述,竹木笔筒、诗筒乃至其他材质诗筒,虽然历经劫难,世间还是留下了遗存,而其中有许多就静静立在博物馆展柜里,惜官藏、私藏不察,将此风雅之物“冒名”笔筒,“相见不相识”。
再回到图7这枚诗筒,上镌北宋米芾《苕溪诗》一首,并附刻者跋:“松竹留因夏,溪山去为秋。久赓白雪咏,更度采菱讴。缕会玉鲈堆案,团金橘满洲。水宫无限景,载与谢公游。香光喜临米海岳此诗帖,坟自运时亦多止之。阮元大人大雅教正,胡长龄。”并镌方章篆书款,印文:印渚(标点为笔者所加)。
诗筒是胡长龄赠予阮元的。胡长龄(1758—1814),字西庚,号印渚,江南通州(今江苏南通)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侍讲学士,乾隆六十年(1795)任国子监祭酒,嘉庆十八年(1813)官至礼部尚书,次年病故,时年五十七岁。这位状元虽官至尚书(从一品),正史却载录寥寥,查《清代职官年表》《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简略记载称其:才名卓绝,过目成诵,与山阳(今江苏淮安)汪廷珍齐名,时称“汪经胡史”,著述《三余堂集》遗世。又查野史笔记《清稗类钞》,一段记载很有意思,曰:“殿试时胡长龄以名得大魁。胡印渚,名长龄,乾隆朝,大魁天下。殿试时,胡卷本在进呈十本之末,时高宗春秋高(乾隆时年79岁),睹胡名,笑曰:‘胡人乃长龄耶?遂置第一……”而这位状元郎很有个性,入官后,因不愿攀附权倾当朝的和珅,长期不得重用升迁,直到嘉庆四年(1799),仁宗查办赐死和珅,胡长龄方才时来运转,“由是胡为仁宗所重,累迁至礼部尚书”。
诗筒的主人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与胡长龄同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翰林院毕业考试)第一,授编修。逾年大考,高宗亲擢第一,超擢少詹事。召对,上喜曰:‘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值南书房、懋勤殿,迁詹事。”阮元二十五岁中进士,三十岁位至三品詹事,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晋太傅,谥号文达。阮元不仅官运亨通,政声卓著,位及人臣,同时更是思想家、著作家、刊刻家,在经史、编纂、金石、校勘、书法等方面都有高深造诣。《清史稿》载:“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道光帝祭文中称其“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当代学者评价他:“在清代以赞助、奖掖学者而享誉后世的学者型官员中,阮元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位。嘉道时期已经到了对百余年来汉学研究进行全面清理、总结时期。而当时能够担此重任的,非阮元莫属。”其文化影响力,播布后世汉学甚深。
这枚胡长龄赠阮元“大雅教正”的诗筒,解读其中传递的信息,颇有意味。看看他们有着怎样的关系:一、同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同榜进士。这层关系,在古代科举史上有一个专有名词,谓曰“同年”,类同于当下博士、研究生同班同学。清代官场上的潜规则,“同年”为天然的政治盟友,一般都会相互关照、提携甚至庇护;二、均为江苏(苏中)同乡;三、同事、同僚(翰林院)。关键是这层同事关系,几年之间,二人的名分、地位跌宕、落差之大,超乎想象。这期间,两人的工作范畴高度重叠,应该交流、交往频密,他们之间的人性、学识也经受了考验,不禁教人联想、感叹。单从官阶来说,胡氏高中状元即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阮氏殿试为二甲第三名,赐进士,朝考第九,授翰林院庶吉士,官阶约为八品,同时入翰林院供奉,进入乾隆帝的秘书班子。短短三年后,散馆,阮元品学兼优,得高宗恩宠,“超擢少詹事”,奉旨南书房行走(从三品);第五年,阮氏三十岁官至詹事府詹事(正三品);而胡氏因不附权相和珅,和珅虽不敢奈何乾隆爷钦点的这位“吉祥物”,但心中的不快可想而知,由是,胡氏仕途只能蹭蹬,幾乎原地踏步。阮元在五年之内,“超常规”提拔迁任詹事府,虽然与翰林院没有相互隶属关系,为“专备翰林院迁转之资”,但有些职掌院、府是互兼的,詹事府詹事、少詹事例得充任副总裁官,均参加“侍班”,或皇帝集议,而身在翰林院的胡状元,也要在詹事府的司经局充任修撰。此时,小胡长龄六岁的“同年”“小老乡”阮元,成了状元郎老兄的领导、长官!嘉庆四年(1799)正月,胡、阮科举得功名后的第十年,阮元兼兵部左侍郎,三月调户部左侍郎,七月兼礼部左侍郎奉署浙江巡抚(正二品),位列“封疆大吏”,时年三十六;而胡氏,仅在乾隆当政的最后一年(1795),才官任国子监祭酒(从四品,类似今天的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兼高教司司长)。是时,和珅把持朝政,气焰熏天,更借科举大肆敛财徇私,容不得他人插手,这个“祭酒”,听着唬人,很美,却不过一杯残冷剩酒而已。
这十年间,阮、胡几乎都在宫廷大内,一定会有很多的交集,而私下交谊呢?目前能查到的,胡长龄十四年后有诗为证:“癸亥三月(嘉庆八年,1803)薄游西湖,时阮芸台(阮元字)开府杭州,那绎堂尚书(那彦成,1763—1833,满洲正白旗人,字绎堂,号韶九、东甫,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时任刑部尚书,从一品,谥号文毅)亦以谳事驻浙,皆己酉同年也,却寄以诗。”“其一:不曾黟涉径呼门,定胜平津阁内宾。五相一渔浑间事,不招明月恰三人”“其二,曾辱先公褒一字,而今谁念次公狂。惟应鲁国奇男子,肯说江东老孝章”“其三,我本江东一步兵,多君千里致莼羹。湖楼小住听春雨,不为秋风作此行”。这一年,胡氏已在外放奉天府丞兼学政任上(正四品),南下杭州出差。诗文不用详解,胡诗里面传达的,是三位“同年”、曾经的“同事”,虽然身份、地位早已悬殊,不期于杭州阮元任上相聚,“不招明月恰三人”,偕游西湖的那份愉悦之情。
再来解读这枚诗筒。胡长龄镌于其上的,原为北宋大书法家米芾《苕溪诗卷》其中的一首,且有真迹遗世,名为《苕溪诗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阮元任乾隆内府少詹事时,奉旨主编《石渠宝笈续编》,应该十分熟悉此诗、此帖;而胡氏刻在诗筒上的字迹,却是明末大书法家董其昌临摹米帖之帖、胡状元再传摹的董体,其中奥旨,恐怕只有他俩方能神会。
有清一代,康熙帝推崇汉文化,书法尤喜董其昌字迹,董帖几乎不离左右,晨夕观赏、临摹不辍,几近痴迷。清三代帝王、大臣、士子,于是乎人人苦练“董体”。董其昌(1555—1636),江苏松江华亭人,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明末后期大臣,书画大家,《明史·文苑》有传,说书法至董其昌,集古法之大成,“六体”与“八法”无所不精,“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自康熙朝,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写得一笔好董体,甚至成为人臣士子追逐功名的捷径(康熙朝布衣高士奇,以“董体”入仕、近侍,成为宠臣,以三品之身入清史,并有谥号,所谓青史留名,即为一例)。这枚诗筒临的是有“董家自己面貌”的“米帖”,胡长龄“再临”镌刻之上,一定有其思量,为其一;其二,此诗为米芾《苕溪诗卷》之一首,而苕溪是浙江八大水系之一,也应阮元时署浙江之景;其三,诗中最后一句“水宫无限景,载与谢公游”,“谢公”二字,胡氏其实延伸了“谢安”之喻,借指、暗喻阮元几年前去世的恩师、谢安后裔谢墉(1719—1795,字昆城,号金圃,晚号西髯,曾任皇子永琰师父,文学家、乾隆朝六部侍郎)。阮元于浙江巡抚任上,为恩师作有《吏部左侍郎谢公墓志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续碑传外集补》传稿)。诗筒的临诗帖正文之后,胡长龄耐人寻味的,用同样大小的字体镌跋:“香光喜临米海岳此诗帖,坟自运时亦多止之。”(坟,大防,释其大意:我在临“董”时,十分防止、注意行气运笔,看似外放而内敛)。胡氏也应熟知董其昌书法之论:“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八字箴言,无上之咒也。”从这枚诗筒的表面看,胡氏说的是“临书”体味,蕴藏其背后的,则有为官、为人的提示、提醒。作为相知、相交甚恰的“同年”“同乡”、前“同事”,胡长龄之赠,诗筒小小,深意拳拳。
再说一题外的话,日前在网上浏览,偶然看到一幅胡长龄的字,与本藏诗筒诗文一般无二,唯独落款为“阮元仁兄教正,弟胡长龄”,下有两枚方章篆书款印,一方“臣胡长龄”,另一方模糊不可辨,其笔画、间架结构,与清代几乎个个都是书法家的状元字迹,有云壤之别;尤其是落款称阮元为“仁兄”,再加钤印称“臣”,实在荒唐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