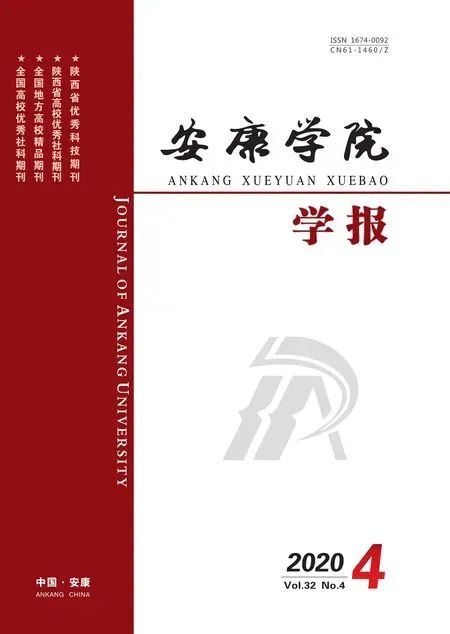从“语言”到“语言行动”:超语行动的兴起及理论机制研究
郑丽钦
(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一、前言
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21世纪,人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频流动已成为社会常态,催生了多语社区和多元文化现象的出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同时受后现代、后殖民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学界针对多语情境下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的问题,创新发展了“超语行动”(translanguaging)概念。作为新理念和新范式,超语行动近几年发展强劲,从威尔士走向全球,从课堂教学策略演进为多语情境下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的理念和范式,引发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我国学界对超语行动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袁妮亚和周恩梳理了“超语言技能”的缘起、概念特征和该领域的研究主题,重点研究超语行动的语言观和语言习得观[1]7-13。王平则从认识视角、研究范式、研究对象、研究幅度对超语和语码转换两个概念进行差异性和相似性的比较并提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2]56-62。本文在简要介绍超语行动的兴起、内涵和特征后,运用历时性研究,详细梳理语言理论和双语理论发展的历程,重点分析超语行动立基的语言行动观和动态双语理论。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超语行动所蕴含的发展和整体思维、平等和全纳思想以及自然和生态理念对我国的外语和双语教育具有启发意义。
二、超语行动的兴起
超语行动一词来源于威尔士语trawsieithu(translanguaging)。自80年代开始,得益于学界关于双语与认知和双语之间的关系的全新认识,威尔士地区扬英语抑威尔士语的现象得到缓解,英语和威尔士语由割裂和冲突走向共存和融合。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帮助威尔士语学生习得英语,任职于威尔士一所高中学校的教育家威廉姆斯(C.Williams)尝试在教学中鼓励学生交替使用输入和输出语言,例如,学生先用英语阅读材料,之后用威尔士语进行口语或书面语交流。这一过程看起来平常,但要求参与者超越某种具体语言的限制来思考需要解决的问题,极其训练和挑战学生的认知、思维和语言能力[3]18。超语行动在威尔士高中非语言课目教学中试用后取得了巨大成功,“学生不仅成为英语和威尔士双语者,同时对学科内容知识有更深的理解和运用”[4]280。威廉姆斯创造性运用超语行动教学策略一举成功并成为威尔士地区双语教育的特色,引发官方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威尔士地区政府甚至立法保障超语行动在该地区学校教育中的合法化[5]642。
随后,学界研究发现,威廉姆斯将超语行动限制在“双语者必须充分掌握两门语言之后才能正确、成功运用超语行动,超语行动不适用于二语初学者”的假设具有局限性。双语或多语者不管是在家里、学校或社会交际情境中,都在随时随地、有意识无意识使用超语行动。因此,超语行动是双语或多语者的本能,并非局限于有计划的课堂情境。在双语或多语社区的街头巷尾,超语行动标识牌、超语现象随处可见。Gar cí a认为,在像纽约这样的多语地区,离开超语行动,人们根本无法生活和交流[6]308。此后,学界将后多语主义下的不同英语变体,如新中式英语主义(new Chinglish)、新加坡英语(Singlish)等也归属于超语行动的范畴[3]18。
李嵬认为,超语行动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将语言使用和思维、认知以及社会文化环境联系在一起。学界因此将超语行动从课堂策略延伸为囊括任何超越语言界限讨论和解决问题(包括民族和社会问题)的行动和实践[3]18。
三、超语行动的内涵和特征
目前,学界关于超语行动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不同时期,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超语行动进行阐释。超语行动提出之初,学界所持的观点是双语者拥有两套独立的语言系统。基于此,创始人威廉姆斯将超语行动定义为“以一种语言输入信息,然后再运用另一种语言输出,即学习者必须先完全理解输入语言所传递的信息,然后才能用另一种语言成功输出信息”[4]280。之后,C.Baker及其同事G.Lewis和B.Jones从语言功能角度阐释超语行动为“通过使用两种语言建构意义、组织经验、实现理解和获得知识的过程”。随后,他们又从社会文化角度进一步定义超语行动为“动态使用两种语言,通过整合方式发挥两种语言在组织和协调心智过程的功能,包括理解、说话、识字和学习。超语行动关注语言的交际和认知功能以及语言的产出”[5]643。C.Baker等学者虽然超越语言的形式和结构定义超语行动,然而他们仍未能突破限制在两门语言之间的欧洲传统[7]21。Gar cí a在吸收动态系统理论基础上,从更广泛的视角将超语行动定义为是双语或多语者调用语言经验库的资源,为建构不同语言表征的不同世界意义而进行多重语言实践的能力,是涌现于不同语言实践交互融合的全新整体(one new whole)[7]21。此外,Pennycook和 Jrgensen等学者也从不同视角关注超语现象并提出不同的阐释。尽管定义和视角不同,但是学界对超语行动的基本特征却是有共识的。超语行动的主要特征是“超越”“转换”和“整合”。首先,“超越”不仅包括超越语言的结构和形式,语言不仅仅是静态的语音、词汇、句法和语法规则的符号系统,更是在使用过程中生成意义、表达思想、铸造经验、获得理解和知识的一系列行为和实践;还包括超越不同语言的界限,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语言结构虽然存在差异,但任何语言所发挥的功能是一致的,因此不同语言的界限可以被打破。其次,在超越的基础上,语言具有转换和整合的性质,语言的结构和功能转换为语言经验库。这个经验库整合了个人历史、经验、环境、态度、信念、身份、意识形态、认知活动和身体活动等各种资源。在这个经验库中,上述各因素互相协调并转化成能够建构意义的行为后以过往经验(lived experience)的形式存在[8]1223。
值得一提的是,translanguaging在我国学界也尚未形成一致翻译。袁妮娅、周恩将其译成“超语技能”[1]7-13、王平译成“超语”[2]56-62。笔者认为这两个翻译版本都未能突出双语和多语动态的特征和功能,即无法体现语言的“行动”性和“实践”性,故本文将其译成“超语行动”①笔者曾与李嵬教授通信,请教translanguaging的中文翻译问题,李教授建议使用“超语实践”或“超语行动”。。
四、超语行动的理论机制
由上可见,超语行动的内涵和外延是动态发展的,学界对超语行动所立基的语言理论和双语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直接驱动超语行动的动态发展和完善。
(一)从语言到语言行动的语言理论
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创建的结构语言学视语言为一套由音素、词素、词语、句法和语法规则组成的非模态抽象符号,割裂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的关系;之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观认为所有语言背后都存在统一的规则,语言是一套由规则组成的、表征世界的抽象符号,转换生成语法观同样注重提取和生成普遍语法规则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忽略语言的使用(performance)。传统的结构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观受笛卡尔“身心二元论”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词义和句义作为表征外在世界的抽象符号,蕴含于语言形式中,语言习得和使用是大脑加工处理信息的心智过程,是“脱离”身体、环境和社会文化情境而独立存在的“离身”认知,不同语言体系和语码之间存在音素、词素、句法和语法规则等语言形式的差异,因而是独立、离散和互相干扰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期,借助神经科学和医学技术的进步,人们通过仪器观察人脑如何加工处理语言,深入认识认知的机制——认知并非是独立于身体和外界环境的内在心智过程,而是与身体和环境动态耦合的过程,认知不是“离身”存在的,而是“具身”“体验”和“扎根于情境”的。语言是高级认知。语言并非简单的结构系统和抽象符号,语言的音素、词素、词语、句法和语法等语言形式都镶嵌于社会历史文化中并扎根于情境中。语言使用者的知觉、运动、社会、情感以及他们从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中组织的经验参与语言理解和使用,即个体从输入的语言中组织和构建经验,然后利用经验产出有意义的语言。
基于此,智利生物学家H.R.Maturana和F.J.Varela提出语言行动(languaging)的概念。从名词语言(language)到动词语言行动 (languaging),旨在强调语言不是静止的系统、形式和符号,而是正在发生的状态,是语言使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系列行动和实践。Maturana和Varela认为,正是通过行为调节之下的语言行动,我们才得以识知(knowing)和建构世界。我们的生活和语言是一个相互耦合的过程(mutual linguistic coupling),我们与他人无时无刻不在使用语言建构着包括自己在内的存在,而绝不是简单地用语言表达自己[1]8。Varela强调,所有的行动(doing)都是识知(knowing),所有的识知都是行动,语言行动就是识知[1]8。因此,语言是语言使用者行动和实践出来的,是其参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产物,是其社会和文化经验中的一个物质组成部分[9]2。语言行动观超越语言结构和语言形式谈语言,不同的语码和语系在语言结构和形式上存在差异,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在发挥沟通交流、组织经验和认知理解等功能上是一致的。因此,不同语言体系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共生协作,共同构成语言使用者可移植的流动资源并储存在语言经验库中(lingustic repertoire)。
受认知、经验和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每个个体的语言经验库存在差异性。Garc í a将这种个性化、独特的语言称作个体语言(idiolect)。个体语言是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沟通交际时涌现的语言,是个体的心智语法(mental grammar)。个体语言具有动态性和情境性,这是因为个体选择和使用的语言总是根据说话的对象和情境而不断调整以促进意义的协商并实现交际目的。个体在持续使用语言过程中丰富其语言经验库。相较于单语(monolingual),双语和多语者在习得和使用语言过程中积累了更多语言特征和语言所承载的复杂社会文化特征,因此双语者和多语者的语言经验库更丰富。虽然个体语言在词汇和结构上存在差异(即使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家庭成员的个体语言也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却不妨碍沟通,因此语言使用者常常无法察觉自己的个体语言,然而个体语言是真实存在的,是超语行动时所使用的语言[10]290。
(二)动态双语理论
学界关于双语之间、双语和认知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互相干扰到增益,到依存,再到动态关系的过程。
1.双语之间、双语和认知是互相干扰的关系
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视语言为结构和符号,不同语系和语码是独立和离散的语言系统。受此影响,自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学界一直秉持双语者持有的两种语言之间是互相干扰的关系和双语对认知产生负面有害影响的观点。威尔士学者Saer以单一的“智商”为指标,对威尔士语—英语双语者和来自威尔士乡村的英语单语者进行智力测验,结果发现英语单语者的智力水平更具优势。Saer总结道:“测验结果显示双语者和单语者的智力差异一直持续到大学生涯,双语对学生智力的负面影响深远。”[11]357同一时期,来自瑞士的学者Izhac Epstein对多语者的心智表征(包括内在言语、心智翻译和计算等)实验结果显示,多语者的大脑需要同时处理不同语言的任务,此过程对多语者智力产生干扰,多语者的思维反应因此比单语者更缓慢。Izhac Epstein据此得出“多语是社会弊病”的结论[11]357。
2.二语之间、双语和认知增益的关系
1962年,加拿大学者Peal和Lambert的研究克服了Saer和Epstein实验中存在的指标单一和方法缺陷的问题。他们的研究证明,双语者的认知能力较单语者更高一筹。这一突破性研究扭转了学界对双语之间和双语对认知产生负面干扰影响的观点。在同一时代,Susan Ervin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证实双语能够优化学习者语言和思维的关系[11]358。尽管后来的研究批判Peal和Lambert在研究方法和受试遴选方面存在问题,但他们的研究仍是学界肯定双语之间、双语和认知是增益(additive)关系的开始。Lauren等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多语可以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和元语言意识[12]655。
3.二语之间、双语和认知依存的关系
J.Cummins在支持Lambert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深层共享能力(Common Underlying Proficiency,CUP)概念。Cummins的研究表明,尽管两种语言表层结构上存在差异,但在认知方面,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双语者具备的一语和二语能力可以互相转化。随后,Cummins又提出双语之间、双语和认知是依存关系的假说(Interdependence Hypothesis):双语者第二语言能力部分地取决于第一语言能力的水平。如果双语者第一语言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其第二语言学术能力往往也更强;第一语言不仅可以提高双语者的认知能力和学术能力,也可以正面影响双语者的第二语言能力发展。相反,如果双语者的第一语言能力未达到一定熟练程度,一语不仅无法正面影响第二语言能力的发展,学习第二语言也会对第一语言产生负面的影响[13]222-251。
4.动态双语理论
近代神经科学和认知研究发现,双语者习得的一语和二语并非以两套独立的语言体系存在,二者以整合和统一的方式存在于学习者和使用者的语言经验库中。语言使用者在使用语言时,两种语言不是处于此消彼长的转化状态,而是一种语言被激活的同时另一种语言也一样保持活跃、处于供随时调用的状态。基于此,Gar cí a在Cummins依存假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超语行动的理论机制——动态双语理论,为日益多语化社会中双语和多语的习得和使用提供了指引。动态双语理论中的“动态”主要体现在双语之间的动态关系和超语行动中语言习得和使用的动态关系。
传统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视双语为具有特征差异和界限明显的独立关系,依存假说固然拉近双语之间的关系,但双语之间仍然处于界限明显的离散状态(如图1、2所示)。动态双语理论重新定义了双语者双语之间的关系,消解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和界限,拒绝以二元观区别不同语言的特征以及标记不同语言之间的界限。由于界限和差异性已消弭,无论多种语言都可以融合一体并活跃共存于双语者的语言经验库中,等候语言使用者最优调配合运用(如图3所示)。

图1 传统结构主义语言观下的双语关系[7]14

图2 卡明斯依存假说中的双语关系[7]14

图3 动态双语理论下的双语关系[7]14
在语言习得和使用方面,动态双语理论立足于动态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认为语言习得过程是个体认知因素和社会情境因素非线性、动态、耦合互动的复杂自适应过程。超语行动植根于“软组装”(soft assemble)原则[7]14,即双语者充分调用语言经验库中储存的符号资源(semiotic resources),这些符号资源来自双语者过往的语言实践,有些可能来自一语语言实践,有些可能来自二语乃至多语的语言实践;有些可能来自家庭语言实践,有些可能来自学校和社会的语言实践。超语行动者将根据交际情境重新组装这些实践,使之契合当下的交际情境和任务。此外,超语行动者从当下的交际情境和任务中发展新的语言实践,新旧语言实践在互动中构建和整合成一个语言经验库。因此,超语行动超越传统二语习得理论“输入—加工—输出”直线性语言习得路径,而是以涌现的交际情境和任务为驱动,通过语言实践的自我重组形成宏观有序的整体资源,是一个动态、线性的复杂过程。与传统二语习得理论强调二语和外语学习达到“母语者”同等流利的目标不同,超语行动侧重“多语能力”(multilingual competency)的培养。“多语能力”并非指每种语言独自发挥作用,而是指在同一个语言经验库中的不同语言共同协作实现有效交际目的的能力。基于此,超语行动关注的是学习者语言资源库的建立,而不是每种语言或所有语言需要达到的程度[14]3。
五、思考和启示
随着全球化时代步伐的加快,多语和多元文化社区的语言习得和使用已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超语行动融合多学科研究成果,其所蕴含的整体发展思维,平等和全纳思想以及自然生态理念对外语和双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启示。
(一)发展和整体的思维
纵观超语行动的发展历程,其内涵和外延随着交叉学科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和拓展。超语行动的发展如同语言使用者语言经验库的成长。个体通过语言认识和改造世界,在此过程中,不断构建、更新和丰富个人语言经验库。同时,通过不断丰富语言经验库,个人的认知、创造性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因而得以提升。超语行动超越语言是结构和形式的静态语言观,从更宽广和动态的视角将语言视为行动、实践和经历,将语言使用和习得视为构建语言经验库的动态发展过程。传统结构语言学以语言的结构和形式为视角,关注焦点是语言学习者和使用者语言的准确性和流利性,以静态结果为导向;由于语言经验库的建设是一个不断持续和发展的过程,语言行动观以构建语言经验库为视角,关注的焦点是语言学习者和使用者在复杂社会网络中(真实和虚拟网络)流动(fluid)的语言实践,关涉语言使用者语言、思维、认知和情感的整体发展,以动态过程为导向。相较于单语者,双语和多语者有更丰富的语言习得和使用经历,他们构建的语言经验库也因此更丰富。研究表明,超语行动对学习者在知识建构、文化意识建构,以及创造性、多元任务处理能力的开发都有益处[3]18。
超语行动的发展和整体思维对我国外语和双语教育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外语和双语教育应当为学习者的多语和多文化体验和经历创造条件和情境,丰富并充分调动学习者的语言经验库,建立多维度评价体系,构建发展“全人”的外语和双语教育机制。
(二)平等和全纳的思想
社会语言学家Pennycook指出,语言概念是由控制政治权力的国家和政府所构造的[15]205。这一情况在殖民主义时代尤为突出。殖民主义时代的“中心主义”“西方中心论”刻意为某些语种和语言贴上政治和权力标签,在语言上烙下身份和特权的印记,语言标准化、语言同化和语言统一加剧了语言不平等所反映的社会不平等,导致一些少数族语走向濒临灭绝的境地。超语行动从“超”的宏观视角出发,认为语言是个体的社会实践过程,以流动资源的方式存储于学习者的整体资源库。超语行动超越具有身份特权和政治权力印记的民族和国家语言,其所关注的是语言使用者的个体语言、个体语言实践和个体语言经验库的构建。任何个体的语言实践都是独一无二的、平等的、值得被珍惜和尊重的宝贵资源。超语行动倡导和鼓励语言使用者平等对待每一种语言,调用所有的语言经历,旨在为每个双语和多语者争取平等话语权的理念,为消解传统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等级观念以及语言后殖民主义而努力。
当前,我国外语和双语教育仍然以学习者外语是否达到目标语言的“本族语”标准为重,轻视学习者语言实践经历和个体独特语言。外语和双语教育应当借鉴超语行动平等和兼容的思想,消除民族中心主义、民族虚无主义,超越语言和语种好坏和优劣的二元对立,尊重学习者独特的个体语言和语言经历,培养学习者的多语能力。
(三)自然和生态理念
超语行动立基于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语言是具身化社会实践的产物,即语言使用者参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产物,是语言使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系列具体实践。例如,生长在双语家庭的儿童,从小沉浸在双语自然环境中,在具体情境中反复实践,他们熟练精通的双语能力是“做”出来的,这些语言经历是可再移植的流动资源,构成语言经验库。在语言使用方面,超语行动认为语言使用者能够根据具体的交际情境,自然、非预设涌现(emerge)出与情境相符合的语言(可能来自不同语言体系)以便实现交际目的。语言使用者从这些自然情境中习得真实和实用的语言,丰富了他们的语言经验库。M ühlh usler的生态语言理论将这种现象称为“平衡原理”(equilibrium),即语言能够自动调整并适应环境,在使用过程中自我丰富。语言使用者本能具备这种平衡能力[6]17。
此外,超语行动从学校课堂情境延伸到家庭、社区和社会,说明语言学习并非局限在学校课堂,人们所经历的每一个场景都是语言习得的场所。语言教学应善于利用现实的场景,在真实场景中引导学习者体验、思考和运用语言,丰富学习者的语言经验库,这对开展体验式教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六、结语
超语行动作为指导双语和多语习得和使用的新理念和新范式,引发了学界各领域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超语行动超越语言结构和形式、超越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界限,从更宽广的宏观视角将语言视为行动和实践,将不同语言体系整合成统一的语言经验库。超语行动蕴含的发展和整体思维、平等和民主思想以及自然生态教育理念对外语和双语教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然而,超语行动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其理论框架尚未完善和成熟。目前关于超语行动的研究也大都停留在理论层面,有关其在教育和社会情境中运用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此外,研究超语行动的范式和方法也比较单一。有关超语行动可探索的研究空间极其广阔,期待超语行动在我国教育和社会情境中的落地和实践,期待学界进一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超语行动研究理论和实践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