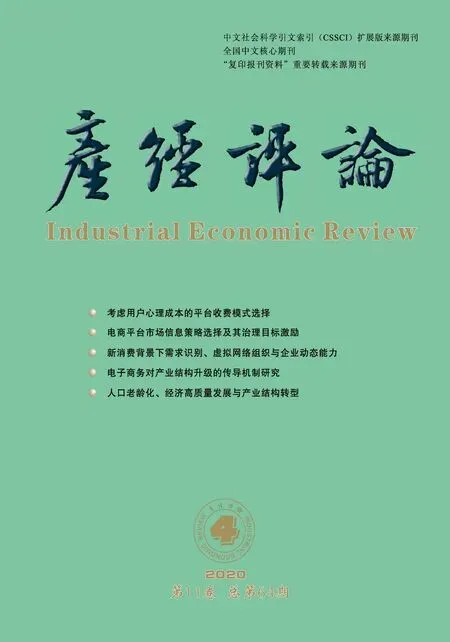电商平台市场信息策略选择及其治理目标激励
——基于苏宁易购十类第三方商品数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邹 佳 马 敏
一 引 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网购已经成为众多消费者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我国网购人数达到6.1亿,网络零售总额达到9.01万亿元,占据零售总额的23.6%,而电子商务总额更是达到了31.63万亿元。然而,与平台企业规模快速增长相矛盾的是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例如,淘宝等平台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大量假冒伪劣产品;美团外卖被曝光其大量卖家并不符合食品卫生规范。尽管平台企业设置了声誉评级、顾客评论和图片展示等功能,但与之相伴而生的过度宣传、虚假评论以及“刷单炒信”等现象反而制造出无数的“噪音”,使消费者更加迷惑。2018年马蜂窝旅游网涉嫌抄袭用户点评信息就一度成为热点新闻。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cca.org.cn),2019年经营性互联网服务和远程购物服务分别占据服务类项目投诉排行榜的第1、3位,两类投诉总量超过71000次。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100ec.cn)《2019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诉监测报告》数据也显示,2019年全年共计受理980家主流电商平台用户投诉,其中零售电商有466家,零售电商类投诉占全部投诉67.27%,退款问题、发货问题、商品质量依旧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网购问题,位列热点投诉问题前三,商品质量投诉同比上升17.45%,从同期的第三大热点投诉问题上升为第二。
区别于传统信息不对称问题,电商平台市场的信息问题是市场多方参与者策略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平台可以看作一种共享经济所驱动的网络中介,平台企业将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的买卖双方(或多方)连接起来,并将外部性内部化为自身收益(Caillaud和Jullien,2003[1];Armstrong,2006[2];Rochet和Tirole,2006[3];Weyl,2010[4]),买卖双方通过平台企业进行直接交易,同时平台企业有能力对双方实施控制(Hagiu和Wright,2015[5],2019[6]),所以从平台企业、消费者和供应商三方参与者的微观行为因素出发能够更有效地厘清电商平台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形成机理。
在电商平台市场中,平台企业不仅是市场的参与者,也兼具市场治理者的角色。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治理能力以及治理目标激励等方面的原因,平台企业的治理效果并不如愿。而探究平台企业的策略行为,不仅可以解释电商平台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形成,而且能够发现平台企业自我治理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加有效的治理体系。
本文从买方预期的视角出发,通过平台企业的信息策略选择解释电商平台市场质量信息不对称的产生,并探究其治理困境的形成原因,进而讨论平台企业和政府共同参与的多方治理路径。主要内容为:首先在消费者有限理性条件下研究平台企业信息策略的最优选择;然后用不同治理目标情境下平台企业治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激励及冲突来分析治理不足的原因,并探讨如何针对平台企业的治理不足而构建“平台企业-政府”合作的治理路径;接着通过与消费者完全理性预期的情况进行对比考察消费者理性预期形式的影响;最后根据商品交易量与用户评价之间关系,运用从苏宁易购上收集的十类第三方商品信息数据,实证检验用户预期的有限理性特征,从而验证基本假设的现实性。
二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平台市场的预期研究和平台市场的治理研究。
1.平台市场预期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从预期的视角探究平台市场中信息接收一方用户在信息完全性程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Katz和Shapiro(1986)[7]根据网络市场用户是否拥有完全信息而将预期分为积极预期(Responsive Expectation)和消极预期(Passive Expectation)两类,前者指能够完全响应价格的变动,使预期需求变化与实际需求变化总是保持一致,后者指对市场需求形成一个固定的预期而不随价格发生变化;Economides(1996)[8]使用这两种预期形式分析了网络产业的需求与规模决定问题,考察了正网络外部性对网络产业的影响,并指出垄断的网络能够通过控制用户预期维持高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Gabszewicz和Wauthy(2014)[9]首次将消极预期用于双边市场,研究了用户缺乏信息的条件下垄断市场和具有纵向差异的双寡头市场的产出,并与用户完全信息,即形成积极预期的情况进行了比较;Hagiu和Haaburda(2014)[10]使用该预期模型系统地研究了用户信息水平对垄断市场、具有横向差异的竞争瓶颈市场和双寡头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利润的影响。该研究除了对纯粹的积极预期和消极预期模式进行比较之外,还比较了二者的混合模式,并引入了谨慎性预期(Wary Expectation)的概念,即假定用户在缺乏信息的条件下通过观察本边价格而预测平台在另一边的最优价格及最优需求;邹佳和郭立宏(2017)[11]使用该预期模型研究了在不同市场结构中,双边平台对两边用户进入次序的选择问题,发现预期和市场结构都会对次序选择产生影响;Belleflamme和Peitz(2019)[1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在竞争瓶颈平台市场,当一边的用户因为外生原因拥有充分信息条件下,平台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向另一边开放信息还取决于交叉网络外部性和横向差异的大小;曲创和刘重阳(2019)[13]使用该预期模型分析了搜索引擎平台企业在不同市场结构中的信息传递策略选择,在两种预期混合模式中进一步加入了差异化竞争和垄断的混合。
上述研究的共同点在于,无论是在完全信息还是在缺乏信息的条件下,都假定用户是完全理性的,即用户的预期可以完全实现。在此假定下,研究结果都发现在垄断条件下,平台的最优信息策略是使用户达到完全信息,而平台间的竞争(双寡头结构)则会使其更加倾向使用户缺乏信息的策略。但现实情况是,消费者往往无法实现完全理性。因此,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将放宽完全理性的假定,从有限理性的视角去探究和解释平台市场信息传递策略及信息完全程度的形成。
2.平台市场治理研究
由于负外部性或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平台企业需要通过监管行为来保证自身利润最大化,而且源于信息和所有权优势,平台企业的管控相对于社会管控会更为有效(Evans,2012)[14]。在此基础上,汪旭晖和张其林(2016)[15]提出了平台型电商企业管理兼具“治理”与“管理”双重特征以及社会公允价值和平台战略导向双重目标的“温室”管理模式;阳镇(2018)[16]认为平台型企业通过对平台内用户的社会责任管理实现了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的创新;李广乾和陶涛(2018)[17]研究发现平台企业“第四类”法人的主体地位,并提出在区分“大平台”和“小平台”的基础上建立治理政策。但是,王勇和冯骅(2017)[18]发现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会导致平台企业的私人激励往往不符合社会激励;肖红军和李平(2019)[19]针对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问题,从运营主体、商业运作和社会资源配置三个层次界定了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正是由于平台企业和政府的监管各有利弊,所以才需要二者的相互配合。汪旭晖和张其林(2015[20],2017[21])以阿里巴巴集团为例,系统阐释了“平台-政府”双元管理范式下的平台资源配置、平台定价、税务征管、外部监管和内部管理,以及平台对“柠檬问题”的治理;王勇和冯骅(2017)[18]提出了“政府-平台-企业”的三层委托-代理监管模型。
现有研究发现平台企业自身具有作为治理者的激励,尽管治理手段较政府具有一定优势,但私人目标往往与社会目标并不一致,从而形成激励不足,因此提倡政府与平台企业相配合进行治理。但缺乏对平台企业治理激励不足的原因以及合作治理作用机制、路径构建方面的深入分析。
综上,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其中颜色填充部分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图1 理论框架与研究内容
三 基本模型
平台商业模式的特征在于控制权的归属(Hagiu和Wright,2015)[5],例如在自营型平台企业模式中,定价权和剩余索取权属于平台企业,而在平台型平台企业模式中则属于供应商企业。现实中,除了定价权和剩余索取权之外,还存在许多其他类型的控制权(Hagiu和Wright,2019)[6],例如商品质量、宣传、营销、售后、信息反馈等等。本文研究涉及到定价、剩余索取、质量选择和信息传递四种权力,在平台型平台企业模式中,前三种权力归属于供应商。由于平台企业具有建立信息沟通渠道、设置评论与声誉机制、规定售后服务规范等权限,并能够强制供应商遵守规定,因此可以认为平台企业有能力控制,至少是部分控制商品买卖中的信息传递,因此信息传递权归属于平台企业。
假定只有一个供应商和一个平台企业,供应商通过平台企业出售商品,自行制定价格、决定商品质量并获取剩余,平台企业控制了供应商对消费者的信息传递。博弈的参与者为平台企业、供应商和消费者。在博弈过程中,平台企业和供应商可以掌握大量信息且具有很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因此假定它们总是完全理性的,但消费者并不一定具有这能力,因此对消费者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两种情况分别进行分析。
n=a+bS[λS+(1-λ)Se]-bpp
(1)
其中S代表实际的商品质量(质量溢价),Se代表消费者根据私人信息做出的预期。λ表示消费者在预测商品质量时两部分信息来源的比例,0≤λ≤1,代表了平台企业的信息策略是向消费者传递更少信息还是更多信息,λ越接近0表示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信息越缺乏,反之则越充足,λ=0可以看作平台企业采用了缺乏信息的策略,λ=1则是完全信息的策略。
设平台型平台企业向供应商收取的费用为r≥0,也就是供应商通过平台企业出售商品所缴纳的中间费,平台型平台企业的利润为πr=nr,代表其按照销量进行收费。供应商利润为πw=n(p-r-cS2),其中cS2代表提高质量所需的成本,假定是边际递增的,c>0。
在给定质量、质量预期以及信息水平等变量时,供应商制定的价格应位于利润最大化的边界上(1)相当于Hagiu和Haaburda(2014)[10]所提出的谨慎性预期。,因此有由此得出以及:
(2)
(3)
四 平台企业信息策略
当平台企业拥有向消费者传递质量信息的控制权时,由于平台企业会预先规定与消费者沟通的渠道或机制,因此平台企业、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决策顺序为:第一步,平台型平台企业规定对消费者传递质量信息的水平;第二步,供应商观察到平台型平台企业所规定的质量信息水平后,决定商品质量,同时消费者形成质量预期。
完全理性要求在利益最大化目标下具有无限的信息处理与计算能力,而现实情况却是,消费者与此要求相去甚远。与完全理性不同,有限理性更加接近生物行为,假定行为者通过经验、直觉或模仿等方式进行决策,常见的有限理性行为包括复制动态学习、强化学习、信念学习、老练学习、贝叶斯学习以及经验加权学习等(王先甲等,2011)[23]。
在电商平台市场中,当消费者因缺乏信息而无法做到完全理性时,通常会从两个渠道获取所缺乏的信息以调整信念:第一个渠道是以往的经验,也就是观察以往预期和真实情况之间的差距;第二个渠道是外部信息,例如其他消费者的分享、卖家声誉、商品评价或其他公开信息等。因此,消费者会综合两个渠道的信息,通过强化学习不断调整信念。


(4)

其中,U代表了稳定状态下外部信息对消费者预期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决定了稳定状态下平台企业会减少还是增加消费者的信息完全程度。这是因为当外部信息对消费者预期产生负向影响时,平台企业会希望向消费者传递更多信息从而减弱外部信息的影响;当外部信息对消费者预期产生正向影响时则正好相反。
五 治理激励与路径构建
由于平台企业兼具市场治理者的角色,因此其信息策略的私人最优选择会影响到实现治理目标的激励,而且在委托代理关系影响下,治理目标的实现还会受到供应商信息策略的约束。因此,本文从平台企业对实现治理目标的激励,以及平台企业与供应商在激励上的冲突出发,解释了平台企业治理不足的原因,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合作治理路径。
(一)完全信息目标激励
下面在提高消费者完全信息程度的治理目标下,探讨平台企业对于实现目标的激励,以及与供应商在目标激励上是否存在冲突。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以提高消费者完全信息程度为目标的治理活动中,平台企业治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需要改变供应商有可能出现的“负面”信息策略,还有自身也会出现的由私人目标与社会目标不一致所导致的激励不足问题。
(二)社会福利目标激励
下面在提高社会福利的治理目标下,探讨平台企业对于实现目标的激励,以及与供应商在目标激励上是否存在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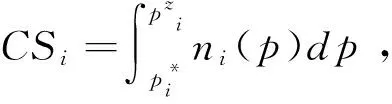
(5)
社会福利等于:
(6)
设ΔW=W1-W0,根据“哈伯格三角”,ΔW代表了消费者缺乏信息相对于完全信息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由于质量和需求函数都不变,因此ΔW仅来源于信息策略选择导致的均衡价格变动,结合命题2的证明过程计算上述二式可以得出:
(7)
根据式(7)可以得到结论3。

(三)治理不足与目标冲突
结合完全信息目标激励和社会福利目标激励的分析,在均衡状态下,平台企业、供应商的私人选择以及治理目标对于完全信息程度的要求如表1所示。

表1 有限理性预期条件下治理目标的激励与冲突
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消费者有限理性预期条件下电商平台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平台治理会出现两类问题,第一个是治理不足,第二个是目标冲突。
1.治理不足问题。表1将治理不足问题的原因分为两种:第一种来自于供应商的激励相容约束,第二种来自于平台企业的激励不足。具体如下:

(2)平台企业激励不足问题。如果外部信息对消费者预期的影响从负转向正(表1最后一行),就会形成平台企业在治理问题上自身的激励不足。此时供应商和平台企业没有冲突但都会选择缺乏信息的策略,因此仅仅约束供应商或平台企业都是不够的,最合理的合作治理路径应该是既约束平台企业又约束供应商,“双管齐下”地提升激励效果,从而避免由于二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合作治理达不到理想效果。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出,在外部信息对消费者预期的影响为负时(表1中第2列1-4行),平台企业提升其收费水平会使供应商从完全信息的策略转向缺乏信息的策略,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近年来电商平台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愈演愈烈。

(四)合作治理路径构建
由于政府相对于平台企业在手段和信息等方面处于劣势,但在治理目标上却处于优势,因此合作治理模式是大多数学者所提倡的(阳镇,2018[16];李广乾和陶涛,2018[17];王勇和冯骅,2017[18];肖红军和李平,2019[19];汪旭晖和张其林,2015[20],2017[21])。但政府与平台企业的合作治理路径应该取决于平台企业单独治理的不足及其原因。
上文在消费者不同预期条件下,通过分析平台企业和供应商对于实现不同治理目标的激励,以及治理目标之间的冲突,将平台企业治理不足的原因分成了两类,下面将以此为基础构建“平台企业-政府”合作治理路径。

图2 电商平台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治理路径构建
第一步,分析预期条件。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预期的有限理性是造成治理激励不足与目标冲突的原因,因此首先需要确定消费者预期是否完全理性,然后再进一步确定影响平台企业和供应商激励的其他原因,例如外部信息的影响以及平台企业的收费水平等。
第二步,确定治理目标。通过社会福利目标激励下的分析,完全信息和社会福利这两个目标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冲突,如果冲突出现的条件满足,就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选择其中一个。
第三步,治理路径构建。根据平台企业和供应商在实现治理目标上的激励,将治理激励区分为“平台充足-供应商充足”、“平台不足-供应商充足”、“平台不足-供应商不足”和“平台充足-供应商不足”四类。当平台企业有足够的激励去增加消费者信息,而供应商没有,说明平台企业没有能力解决供应商的激励相容问题,那么政府就应当以供应商为监管对象去协助平台企业一同治理,例如在政策、法规或数据等方面提供支持;相反,如果平台企业没有足够激励去增加消费者信息,而供应商有,那么政府就应当以平台企业作为监管对象,通过政策法规等手段去督促平台企业采用更加有效的治理手段;如果平台企业和供应商都没有足够的激励,那么政府应当同时使用上述两种路径;最后,如果平台企业和供应商都有充足的激励,政府无需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因此,四类情况对应的合作治理路径为:第一类,平台企业单独治理;第二类,政府治理平台企业,平台企业治理供应商;第三类,政府既直接治理平台企业又与平台企业一起治理供应商;第四类,政府与平台企业共同治理供应商。具体如图2所示。
第四步,选择治理路径。根据激励不足类型的识别来选择路径,分别判断均衡状态下平台企业和供应商信息策略选择的私人最优与社会最优是否一致,如果两者都一致就识别为第一类,前者不一致后者一致识别为第二类,两者都不一致识别为第三类,前者一致后者不一致识别为第四类。
六 消费者完全理性预期的情况
本部分在相同的条件下,从平台企业信息策略以及平台企业在实现治理目标的激励两个方面,比较消费者完全理性预期时与有限理性预期时的不同,从而考察消费者预期形式对电商平台市场信息策略以及治理的影响。
(一)平台企业信息策略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供应商的商品质量正比于平台企业所规定的信息水平,当消费者完全理性时,会通过观察平台企业的信息水平而确定自己的预期,而预期越高,平台企业及供应商的获利能力就越高,因此最优选择是传递给消费者完全信息。
但是,该结果依赖于平台企业合理的收费水平,因为当平台企业收费过高时,供应商会发现提高质量的收益不足以抵消其成本,将质量降至最低是最优选择,但由于消费者是理性的,降低质量会使需求下降,最终使供应商因亏损而退出电商平台市场。
(二)完全信息治理目标激励
(三)社会福利治理目标激励


(8)
(四)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比较
由上述分析发现,在均衡状态下,如果消费者完全理性,那么平台企业和供应商的最优信息策略是向消费者传递完全信息,且该策略恰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表明在既定条件下,电商平台市场的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于消费者的有限理性。当消费者完全理性时,即使是垄断市场同样也可以在信息缺乏问题上发挥效率,因此使消费者的预期变得理性是减弱及消除信息缺乏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七 实证检验
由于消费者的理性预期形式是本文的研究基础,下文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对消费者的理性预期形式进行检验,从而验证理论结果的现实性。
(一)研究假设
根据式(1)有n=a+bSSe-bSλ(Se-S)-bpp,其中Se-S代表了实际质量与预期质量之间的差距。当消费者有限理性且至少被部分隐藏了商品信息(0<λ<1)时,在Se固定不变的条件下,Se-S会负向影响需求;当消费者完全信息(λ=1)时,n=a+bSS-bpp,Se-S不会对需求产生影响;同样,当消费者完全理性时,Se=S,Se-S也不会对需求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在消费者有限理性预期的条件下,实际质量与预期质量之间的差距是显著存在的,因此会对需求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在消费者完全信息或缺乏信息且有限理性的条件下,由于预期一定会实现,预期质量与实际质量之间的偏差是随机偏误,因此不会对需求产生显著影响。
由于现实中消费者很难做到完全理性,因此本文主要针对有限理性这一假设进行检验,即当实际质量与消费者预期质量之间的差距负向影响需求时,消费者的预期是有限理性的。基于以上思路,提出假设:消费者的预期质量与实际质量越接近,商品需求就越大。
(二)样本与变量
本文以苏宁易购商品作为样本,检验上文提出的假设。原因在于:一是苏宁易购的第三方店铺都是品牌专营店,因此每个店铺商品的质量是由一家供应商单独决策的,且消费者的预期也只会影响到一家供应商的决策;二是苏宁易购的自营商品相对较少,而本文仅考虑第三方商品的情况。相比较而言,在较大的平台型电商中,由于淘宝和天猫品牌专营店的比例较低,而京东自营商品的比例又很高,所以选择苏宁易购作为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关键词搜索,在苏宁易购上搜集了男装、女装、运动器材、箱包、家纺、汽车用品、化妆品、内衣、家居用品和鞋这十类商品中综合排序前120位的商品,逐个采集商品信息。选择这十类商品的原因是这些产品的品牌繁多、质量差异较大,因此消费者在购买前不容易判断商品的质量,从而较容易因缺乏信息而形成有限理性预期。
采集变量包括:(1)商品的用户评价数量(num)。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了商品需求。由于苏宁易购并不显示售出数量,但每个购买者都会产生评价,因此评价数量与售出数量高度相关(2)购买商品后即使不评论在一定时间后也会产生默认评价,因此评价数量与实际需求量之间存在一个滞后期,对于截面数据来说,这个滞后期并不会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2)店铺评分中的用户评价(eva)。作为解释变量,代表了该品牌供应商产品总体质量的现实情况与消费者总体预期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小,评分越高,因此根据假设该变量应正向影响被解释变量。由于在一定时期内,消费者预期不会发生明显变化,但缘于样本的多样性,可以认为实际质量发生了变化,因此用户评价作为代理变量可以在预期质量不变的条件下反映实际质量与预期质量之间的差距,即Se-S。之所以使用店铺评价而非商品评价是因为店铺评价能够反映消费者对该品牌供应商所有产品质量的总体评价,相对于单独的商品评价,信息量更大,随机性降低,也符合本文理论模型中供应商能够对质量进行调整的假定;(3)商品种类(kind,虚拟变量)、搜索排序(seq)、价格(price)、是否旗舰店(flag,虚拟变量)、店铺评分中的物流时效(logis)、店铺评分中的售后服务(after)和商品的用户好评率(goodrate)为控制变量。价格变量中有些商品不同型号的价格会有所不同,因此价格是一个区间,对于这类样本取价格区间上下限的算术平均数作为价格,同时设置p_section这一虚拟变量代表价格是固定值还是区间值。
综上,本文的实证模型设置如下:
lnnumi=α+βevai+γcontrol-μi
其中lnnum代表被解释变量的对数形式,control代表上述8个控制变量,其中价格也为对数形式(lnprice),μi代表误差项。
本文使用爬虫程序按上述规则自动爬取1038个样本,通过数据筛选剔除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和自营商品的样本,由于自营商品背后的决策逻辑并非本文的研究范围,且自营商品的数据结构与第三方商品差异较大,故而将其剔除。筛选后的有效样本780个,各样本的搜索排序(seq)还按照原有序号并未改变,这是因为搜索排序对销量的影响是相对的,只要能够体现样本之间的相对关系即可。之所以并未对有效样本在数量上进行补充是因为本文所需的被解释变量即评价数量(num)随着搜索排序的下降而产生非常明显的减少,综合排序120位之后的商品评价数量为1甚至0的比例很高,因此可以认为作为解释变量的用户评价(eva)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如果继续扩大搜索范围则会由于变量本身的特点反而对模型产生不良影响。各变量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店铺评分中的用户评价对商品评价数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成立,说明消费者对质量的预期中存在有限理性的部分。

表3 回归结果

(续上表)
设表3中模型(1)、 (2)和(3)的误差项分别为e1、e2和e3,将其对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于商品的预期质量这一变量无法观察,而回归模型的误差项可能会包含该变量的影响。根据第五部分的推导,当供应商完全理性时,最优质量决策与消费者的预期无关。因此,消费者预期质量与实际质量的差距对误差项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供应商的完全理性。同时,表4结果也表明了误差项与解释变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因此模型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四)稳健性检验
1.相对评价。将店铺评分中的用户评价、物流时效和售后服务变为该三项得分低于或高于同行的百分比,低于为负,高于为正,变量名称分别设为:eva_rela、logis_rela和after_rela,采用与上文相同的方法进行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只是用户评价的显著性稍有降低,但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仍然在5%水平上显著(具体报告见附录的表A1)。
与表4的误差分析相同,用相对评价对三个模型的误差项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显著性水平相比较使用绝对评价时均有所升高,但除模型(1)外,剩余两个模型仍然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具体报告见附录的表A2),所以仍然验证了供应商完全理性的假设以及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2.面板数据。由于在样本中很多商品来源于同一家商铺,因此可以将同商铺的不同商品设置为时间进行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从而可以控制住商铺之间的个体差异。转化为面板数据后显示商铺总量为418个,豪斯曼检验无法拒绝原假设,因此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与表3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具体报告见附录的表A3)。将店铺评分的三类绝对评分改为相对评分,再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也基本一致(具体报告见附录的表A4)
八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从消费者有限理性预期的视角出发,研究在垄断市场的情境下电商平台市场商品质量信息不对称及其治理方面的五个问题:(1)平台企业信息策略的选择;(2)平台企业在实现治理目标上的激励与冲突;(3)电商平台市场治理路径的构建;(4)消费者预期形式的影响;(5)对消费者预期形式的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1.在消费者有限理性预期的条件下,预期质量与实际质量的差异决定了平台企业选择使消费者完全信息还是缺乏信息的策略。
2.在消费者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平台企业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治理会出现激励不足、激励相容约束以及目标冲突三类问题,而这三类问题的产生取决于消费者预期质量与实际质量之间的差距以及平台企业收费水平这两个因素。具体来说:激励不足源于社会目标与平台企业私人最优策略选择的差异;当预期质量低于实际质量且较小时,如果平台企业收费较高,平台企业和供应商在提高消费者完全信息程度这一目标上的激励是相反的,平台企业偏好完全信息而供应商偏好缺乏信息,由此产生了激励相容约束;平台企业和供应商中一个或二者都有可能对提升社会福利这一目标激励不足,但源于完全信息在维持垄断价格方面的作用,提升消费者信息完全程度并不一定总是能够提升社会福利,因此会产生治理目标的冲突。
3.治理路径构建,应首先以消费者预期作为约束条件,然后明确治理的社会目标,权衡目标冲突,最后根据平台企业与供应商在实现治理目标上是否激励不足来选择。
4.使消费者预期变得理性是治理电商平台市场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市场化手段。通过对比消费者完全理性预期与有限理性预期的情况,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完全理性预期时并不会出现平台企业对信息不对称问题治理的激励不足、激励相容约束以及目标冲突三类问题。
5.消费者预期检验。基于苏宁易购十类第三方商品的数据,通过检验电商商品实际质量与消费者预期之间的差距这一变量和商品销量之间的关系,验证了电商平台市场消费者预期的有限理性特征。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从消费者有限理性预期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垄断市场中平台存在使消费者缺乏信息的动机,相比较以往在消费者完全理性假定下认为垄断市场中平台具有传递完全信息激励的研究结果,本文在有限理性假定下的研究结果以及对该假定的实证检验,可以对电商平台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产生及其治理困境进行更加有力的解释;二是通过比较平台企业私人目标、供应商私人目标和社会福利目标之间的差异,发现平台企业治理信息不对称过程所产生的激励不足、激励相容约束以及目标冲突三类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从平台企业、供应商和消费者三方的微观行为出发,更加深入地解释了治理行为的作用机理,为构建合作治理路径提供坚实基础。
本文得到的启示为,对电商平台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进行治理时需要考虑三方面问题:一是考虑消费者预期特征的影响,判断平台企业自身的治理是否存在激励不足,这是构建政府参与的合作治理路径的前提条件;二是判断治理是否会提升社会福利,当治理目标在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提高社会福利两方面存在冲突时,需要进行权衡;三是识别平台企业和供应商在实现治理目标的激励上是否存在差异,作为构建和选择政府与平台合作治理路径的基础。
需进一步说明的一点,本文最主要的局限是没有考虑竞争的影响。与普通市场的竞争结构不同,由于电商平台市场的信息完全性水平是平台企业和供应商二者策略性行为的共同作用,所以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和平台企业内部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关系都会对信息策略及其均衡产生影响,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将引入这种“双层竞争结构”的情境。除此之外,本文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当平台企业与供应商的激励不同时,平台企业如何通过激励相容约束实现目标;二是考虑除信息完全程度外更加多元化的信息传递策略,例如是否会传递虚假信息等;三是考虑消费者预期和平台市场信息策略的协同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