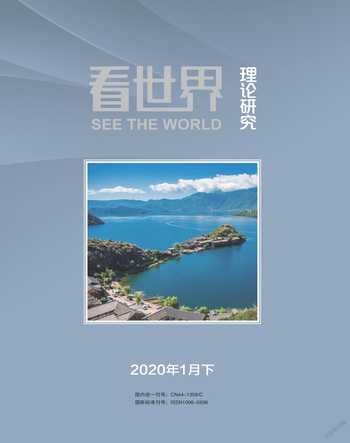分析《人面桃花》中秀米的抗争性
梁瑜
摘要:以秀米探尋父亲陆侃发疯出走的原因为开端,秀米遇到了张季元,辗转花家舍,为了实现混杂着“桃花源”和“大同世界”的革命梦想,她对同时期女性进行抗争,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抗争,对自我追寻的不断抗争。
关键词:秀米;抗争;困惑
前言
《人面桃花》是格非的一次先锋尝试,在90年代初,文本形式和叙述角度遭遇困境,作家们在“怎么写”方面有所创新,但与“写什么”结合在一起时,就不是那么可观。但这部作品很好的将两者结合到一起。格非谈到:“我曾经只重视小说的哲学内涵,现在我觉得人物和故事是小说的血肉。这部小说中我第一次考虑到塑造人物和讲好故事。”《人面桃花》塑造了秋瑾般女革命者秀米,以秀米、老虎、喜鹊三个不同视角讲述了秀米从女儿到女人到校长再到禁语人的人生经历。
一、秀米对同时期女性的抗争
秀米是困惑的,面对周围各型各色的女性,与张季元暧昧不清的母亲,一辈子都在渴望嫁给属猪男人的翠莲,一直干着家务事二十四岁认字、作诗的喜鹊,她在看了周围女性的遭遇以后,她开始逐步追寻自己,认清了自己所求——革命。作品中描述道“秀米觉得身外的世界虽然藏着无数的奥秘,却始终对她保持缄默。她宛若置身于一处黑漆漆的封闭的屋子里,只能凭借暗弱的光线,辨别屋子的轮廓”,她开始慢慢打开束缚她的高墙,击碎他人的给予女性期望的束缚,同样也带给了一些女性的改变,如喜鹊后半生的醉心诗词,终身不嫁。
《人面桃花》以秀米父亲陆侃忽然出走为开端,秀米想弄清父亲发疯的原因,是她抗争之初,她询问身边的可以问的人,但是这些人都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母亲“当即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拍得桌上的四只碗同时跳了起来”;她又去问翠莲,翠莲蛮有把握地说:“不为别的,都是韩昌黎的那张狗屁桃源图惹出来的事。”这个解释也后来也被不攻自破;而喜鹊的回答是“就这么疯了呗”。
三个人不同的描述,但是中心目的却是让秀米不在乎有这么好奇的好奇心让秀米继续像他们一样被禁锢在其中,但是秀米“她的好奇心就像一匹小马驹,已经被喂得膘肥体壮,不由她作主,就会撒蹄狂奔。”秀米周围亲近的人,母亲对父亲发疯的封建迷信做法,不理解父亲发疯的原因,翠莲的一辈子仿佛被那算命先生钉住,最后以乞丐身份走远。
二、秀米对当时社会的抗争
《人面桃花》一开始就显示了秀米寻找自己、寻找外部世界的动机的渴望,透露出困惑。张季元死后,重回普济的革命显得更为茫然,忘却目的,忘却为谁而革命,在她出狱又陷入了新的迷惘,只能在新的迷惘中寻找出路。这种无根似的漂泊感、生命的痛苦体验以及乌托邦幻灭之后精神上的无所皈依让人物最终陷入了无可奈何的宿命绝境之中。秀米的对社会抗争主要体现在革命上,虽有命运的因素,但是内在驱动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内在驱动是一种乌托邦主义激情。在文中有两种体现, 一种是王观澄所创建的以花家舍为载体的古典形态的江湖乌托邦,一种是秀米所创建的以普济学堂为代表的现代形态的革命乌托邦。结合秀米的时代背景中国的知识份子渴求着一条探寻光明的出路,构建一个新的社会。陆侃的乌托邦冲动给了秀米一个冲击,革命党人张季元的到来更是带来了现代的乌托邦冲动,但是在花家舍惨遭蹂躏、九死一生的经历使她最终放弃了父亲陆侃的古典乌托邦理想,而走上了张季元致力于反清抗暴,建构现代革命乌托邦的道路。但是现代乌托邦也存在着危机,秀米领导成立了普济地方自治会,在一间寺庙里设立了育婴堂、书籍室、疗病所和养老院,然而一切如同虚设力图通过教育的方式改良国民的劣根性,进而建立新的乌托邦社会 。自治会计划受挫后,秀米又办起了普济学堂,自任校长,直接致力于反清革命活动。在介入社会秩序的乌托邦进程中,秀米沉迷暴力性质的革命,忽略了亲情的伦理,直接间接造成自己母亲和儿子的死亡。革命者们在建设乌托邦世界的时候只考虑自己的欲望却很容易忽略了当时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张季元有一次表示到:“男女不需婚嫁,只要喜欢就住在一起”,表达了平等的观念,但是随后说到“要是不同意,就杀掉她父母。”表明这种只为自己的革命观是忽略人的基本权利的。格非认为:“描述那些尚处于暗中,未被理性的光线所照亮的事物,那些活跃的、易变的、甚是脆弱的事物”是作家的要职责之一。在秀米的迷茫、困惑心理状态上践行了这一点,特别是秀米在死后接触到张季元日记的内容,看到了更广阔、未知的世界,但是她的束缚和压抑感就越来越明显,她找不到发泄口,陷入了忧郁,在浑浑噩噩许久之后,她通过自残来假装证明自己的清醒,用门框反复夹自己的小拇指,直到手指变形鲜血流出,看似清醒了,实则还在困惑,她开始不再在乎嫁给谁,觉得自己的身子随别人糟蹋罢了,反正不是自己的。
三、秀米对自我的不断抗争
秀米的对自我抗争,离不开种种象征物,如金蝉、瓦釜、阁楼,这些物件伴随着她的对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入。金蝉、瓦釜成为故事线索并贯穿故事始终。金蝉是小说中革命党人之间传递的信物,出自李商隐《无题》中:“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椽少,毖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诗暗示了秀米的种种经历,金蝉是金蟾一字之差,金蟾是闺房中熏香之物,蟾锁春心,如同秀米和她周围的男男女女,蝉蜕变幻。春心比喻张季元的到来,诱发秀米母女“春心”,而“革命”是历史的春心,在经历社会的重重变故之后,“杏花春雨江南,灯灰冬雪夜长”。只留下相思和火焰的灰烬。
金蝉夜可以说寓意着宿命。第一次在出现是在张季元前路凶险把金蝉交给秀米,传递给秀米革命信息,第二次出现在花家舍时,韩六赠予秀米金蝉,暗示秀米进行乌托邦革命。第三次是小驴子给革命失败禁语的秀米,但是秀米拒绝他的来访,这意味着革命乌托邦冲动在她的内心深处已寂灭。丧失了革命乌托邦意义的金蝉不过是一个无用的空壳而已。作品中出现金蝉还有暗访花家舍时,秀米小儿子死亡的雪地上,陆侃笔记中关于“金蝉”和“金蟾”的区别。金蝉还有金蝉脱壳的意思,隐喻了秀米追逐乌托邦的迷幻人生,终为空壳。
四、总结:
格非将他的作品取名《人面桃花》,就会联想到那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选取人面和桃花两个意象。“桃花”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大同理想寓意,传达了国家梦思想在中国的历史里就像桃花一样绚烂却难以为真。秀米回忆自己一生感概“年复一年,春去秋来,有绚丽盛开也有花败花落之日”,表达了时间不断前进。人面不知何处去是秀米人生之路的映照。秀米因为困惑,得不到答案,进行了许许多多的抗争,对同期女性的抗争,对当时社会的抗争,对自我的不断抗争,但秀米追寻乌托邦未果。格非他反思批判乌托邦实践给人类带来 的毁灭性灾难 , 如花家舍的毁灭,但又对乌托邦不断执著追求,乌托邦实践虽然被证明是一场灾难 , 它注定只能存活于人类的梦想幻境中,但可激发个体求新求变及向善向美的动力,可就是格非希望在这篇小说中表达自己的家国情怀,希望有人为这个美好梦想不断实践。
参考文献:
[1] 姚晓雷,格非《人面桃花》等三部曲中乌托邦之殇,文艺研究14年第4期
[2] 王旭,论格非《人面桃花》中梦境叙事空间的构筑,黑龙江业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3] 耿传明,格非的《人面桃花》与历史乌托邦,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4] 张学听,格非《人面桃花》的诗,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
[5] 黄惟群,神神乎乎的悬念和突变——格非的《人面桃花》解读,小说作家作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