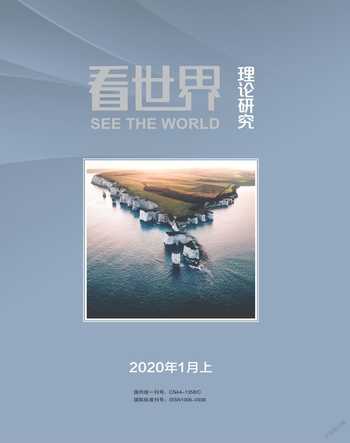场馆类科普教育基地的科普教育研究设想
姚灵芝
摘要:科学普及教育在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从1999年中国科协开展了创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的工作以来,科普教育基地就对推动素质教育、加快科学技术普及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四川省是我国主要的科技创新地之一。作为全国科普创作中心之一(北京、上海、成都),四川省在建设和创新科普教育方面有一定基础。另一方面,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开始推广全民科普教育,1951年日本《博物馆法》颁布之后就将博物馆的科普教育现代化发展推上日程。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分析四川省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东京国立科学博物馆在科普教育的展览内容策划、科普教育人才培养、环境设置等几个方面的构建,发现两者的异同点,探讨场馆类科普教育基地未来的发展方向,为科普场馆教育的建立、发展提供建议。
关键词:科普教育基地;博物馆;熊猫基地;东京科学博物馆
根据中国科协2009年制定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认定办法(试行)》中的定义,科普教育基地主要是指依托教学、科研。生产和服务等机构,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具有特定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功能的场馆、设施或场所。其中,科技博物馆、动物园等场馆作为城市主要科普基础设施之一,是城市科普服务和科技传播的中心,规模相对比较大,拥有大量科普展教资源,是科普工作的主要阵地。科普场馆作为非正规教育职能的社会教育机构,应发挥教育内容、方式多样化的特点,满足不同层次公众学习、了解科技的需求,成为其接受终身教育的场所[1]。
当前我国的科普教育基地已具备较强的科普综合服务能力,能够满足公众的部分科普需求,对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和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我国科普教育基地的科普能力建设还面临着比如缺乏总体布局的发展规划;运营管理上,一些场馆存在着重展览轻教的现象;教育展示的理念和形式缺乏创新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制约着科普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一、国外科普场馆教育发展回顾
当代欧美科普场馆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场馆的教育功能愈发显著,尤其是博物馆的科普教育发展。18~19世纪在欧洲成立的近代博物馆,与前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博物馆设施开始关注公众的需求。19~20世纪初欧洲各国的博物馆面临着深化面向大众的教育机能的诉求,英国企业家卡耐基强调博物馆是拥有教育功能的公共机构。在美国的科普教育机构,其向来重视教育功能,博物馆表现出第二教育机构甚至是独立教育系统的趋势[2]。1969年向公众开放的旧金山探索馆将世界科普场馆的发展从注重展览展示推向以教育为目的的发展阶段;1990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的核心要素归类为“教育”与“为公众服务”。
日本的近代博物館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已效仿欧美诞生,但具有现代科普教育功能的博物馆的出现是在1951年《博物馆法》的颁布之后。确定博物馆公众教育机构的地位,重视社会需求的娱乐和研究成为博物馆应达到的目标[3]。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日本博物馆的建设已形成种类丰富、内容完善的格局,对社会发展、推动公众科普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东京的国立科学博物馆为例,东京科博拥有丰富的微古生物标本、资料、数据,下设产业技术史资料信息中心,专门提供与产业技术相关的资料的调查、信息的收集、评价保存、科普资料的研发工作,科普教育资源丰富。在馆校合作方面,东京科博与东京大学、筑波大学等高校合作,共同培育分类学等自然史科学的研究人员。针对想要从事博物馆工作的大学生,开放体验标本资料收集、保管的学习支援活动;开办“科学交流养成实践讲座”,对通过SC1、SC2课程的学员授予“国立科学博物馆认定科学交流者”名称。除了大学,东京科博也针对小学、中学的学生,通过科学体验学习项目的教育普教委员会来开发教育项目。
二、四川省科普教育基地建设与现状
目前,全国教育科普基地共计1080家,四川省在2015-2019年度被认定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有23家。以成都市为例,科普基地可大致分为5类:科技、教育类场馆,如四川科技馆、四川省图书馆;具有科普展教功能的自然、历史、旅游等社会公共场所,如四川省博物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科研机构和大学面向公众开放的实验室、陈列室或科研中心,包括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等;工业企业面向公众开放的生产设施;现代农业类科普场馆[4]。其中,个别科普场所的科普教育能力较为突出,比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成都市动物园等。这些场馆发展时间较长,具有丰富的科普教育经验。如熊猫基地在2000年就已成立保护教育部门,专门从事开发基地的科普教育项目的工作,拥有一支年轻、专业的科普志愿者队伍;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动物、环境保护方面的科普教育能力在国内均属前沿,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总的来说,通过与国外的科普教育发展的比较来看,我国的科普场馆教育虽然已取得一定成绩,但可以发现总体而言依然处于一种粗放式的起步阶段,发展模式较为单一,尚未形成系统的多元化发展模式。目前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展陈设计与活动策划能力较弱。场馆的教学设备不够先进,缺乏革新,展教方式是单向的,观众往往难以获得深刻认识
(二)缺少专业科普教育工作者,专业性有待提高
(三)科普活动较少,未能充分利用科普基地设施
三、案例考察分析
(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熊猫科学探秘馆”
“熊猫科学探秘馆”以“熊猫研究基地概览”、“神秘的大熊猫”、“熊猫的恋爱与婚配”、“熊猫的遗传探秘”、“生命的摇篮”、“熊猫和它的伙伴们”六个方面为展示主题,展示了熊猫基地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成果。其教育目标是向观众展示人类对大熊猫的认识研究、保护拯救主题,展示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鼓励关注生物多样性状况;根据现代社会大人和孩子少有亲近大自然的机会这一现状,强调接触、互动和实践,帮助建立人与大自然的情感联系,从而达到理解和乐于环保行动的效果。
在展览内容策划方面,“熊猫科学探秘馆”根据大熊猫的分布、成长轨迹、生命周期及生物多样性主题来区分规划,分别展示了熊猫的数量分布、身体结构特征、交配繁殖、人工授精、产仔育幼以及其他濒危物种的信息。与一般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常设的标本、模型展览有所区别,科学探秘馆旨在激发观众“探秘”的好奇心,展览多以图片、声音、文字、视频的形式,让观众在互动中探寻熊猫的奥秘,诸如电子沙盘互动查询系统、模拟人工喂养大熊猫体感机、熊猫婚配游戏、3D影院小剧场。导览媒介有触摸式电脑、LED电子图文显示屏、展览折页、看板、互动展品。展区可视信息随处可见,被安置于馆内的各处。采用中、英、日三种语言,呈现形式多样。说明信息多与图片一同阐释式展现,以大熊猫的生命轨迹(发情-交配-产仔-育幼)设计安排参观路线。
在环境设置方面,熊猫科学探秘馆与2017年重新装修向公众开放,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展区没有实物展品,多为文字图片等的科普信息展示。内容围绕大熊猫、以及生物保护的主题展开,展示方法引入了国际最新的展示设计理念和高科技展示方式,采取以多媒体展示为主、大幅展板导视为辅的方式,用40个触摸屏,向游客分别介绍了大熊猫繁殖、遗传、营养、内分泌等知识。科学探秘馆基本色调为绿、蓝、黄、白,其中以绿色、蓝色为主调,以轻快明亮的颜色烘托了展示自然、环境的氛围。馆内采用人工照明,灯光柔和不强烈,白炽灯多安装在天花板上,电子大屏幕起到了辅助环境灯光的效果。墙面多装饰以大熊猫的大幅摄影作品,突出了“大熊猫”的主题。大熊猫憨态可掬、生动可爱的样子更加拉近了游客,使游客一进入馆内就能感受到轻松、愉悦的现场气氛。
在科普教育人才培养方面,熊猫基地在2000年便率先引入了国外先进的保护教育理念和方式,成立了科普教育部,目前已配备了专业和专职的教育工作者共23人,从事教材编写、项目研究、活动开展和杂志编辑等工作。另外,熊猫基地还拥有一支100余人的科普志愿者队伍,从2015年开始通过“招聘—培训—实习—考核—上岗”的模式,5年的时间里已培养出11期优秀的志愿者。每年2次的志愿者招聘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线上的招聘面向社会大众,线下的招聘与成都市各大高校合作,走进校园开展志愿者招聘讲座,集结出一批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志愿者。他们在基地的各个讲解点,通过模型、图片等手段向游客们展示、讲解大熊猫及其伴生动物的生物知识。除了长期的志愿者项目,基地还定期开展“小小志愿者”活动,与成都市的中小学校合作,让青少年也拥有体验志愿者的机会,使其在志愿服务中对自己所讲解的内容形成更深的印象,加深了对青少年儿童的科普教育效果。
(二)东京国立科学博物馆“地球上多种的生物”
东京国立科学博物馆分为日本馆和地球馆,分别展示日本列岛的自然、与自然相关的历史以及地球的环境变动、生物的诞生和灭绝。其中,以自然生物为主题的“地球上多种的生物”展区是我们的主要考察对象。展览有“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陆上生物的多样性”、“多样性的由来”、“系统广场”、“在大自然生存的各种办法”、“保护生物多样性”6个版块,介绍了在进化的过程中被分成不同种类的动植物是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生存、形成自己特有的形态以及生活方式。通过多种展览手段模拟生物的生活实景,展出动物标本,仿真复原植物,再加以视效、声效的模拟,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冲击。
在展览内容策划方面,“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展出了大量海洋生物的真实标本和原尺寸复原的模型,解答了海洋的光合生态系统、化学合成生态系统等诸多问题;“陆上生物的多样性”模拟了陆上的红树林、沙漠、湿地等自然环境,展示了在各个环境中生活的形态各异的动植物;“多樣性的由来”、“系统广场”将抽象问题具象化,来馆者能在此了解到生命结构细胞的构成、根据设计图,合成蛋白质等知识;“在大自然生存的各种办法”、“保护生物多样性”使来馆者通过真实的标本了解到大自然生态系统的构成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依据由浅入深、由表到里的规律策划展览结构。采用裸展和橱窗式展示结合的方式,易于受损的动植物标本被置于玻璃橱窗;被独立出来的中心展区展示生物石膏化石模型。大量使用可互动式展品,鼓励游客动手触摸。展示手段多样变化多端。设有触屏式电脑,大型场景复原:海洋环境和热带雨林环境。“海洋生物的多样性”版块入口处环绕大型球幕,展现海洋环境,全景画展示海洋远景;展品组合多样:“化石标本+说明牌”组合,“复原模型+图片+阐述式说明”组合,“多媒体声像资料+说明牌”组合。
在环境设置方面,展区根据主题的不同设置不同的主题色,“海洋生物的多样性”以蓝色为主色调;“陆上生物的多样性”以绿色为主色调。整个展厅采用明快、活跃的原色色彩,全部使用人工照明。展区内大量设置的大型LED电子屏除了有展示、模拟背景的功能,也起到了环境照明的作用。穹顶安装具有聚光功能的射灯,“多样性的由来”版块刻意降低照明度,烘托出神秘的气氛。
在科普教育人才培养方面,东京科博的教育工作者本身就是有实力承担各种科学研究的科技人员,他们拥有专业的知识,经常前往世界各地考察研究,同时也会接待国外的学者进行交流活动。另外,早在1986年东京科博便引入了志愿者制度,其志愿者队伍的则主要以退休后的高龄者为主,从事科普讲解、楼层导览、辅助体验学习等工作。“地球上多种的生物”展区的志愿者科普讲解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在特定的讲解区域进行一次。志愿者在科普道具小推车后通过动物化石、模型向游客讲解与恐龙相关的知识。
四、小结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考察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优秀的科普教育场馆的几个特点
1、 极具特色的展览选题。以大熊猫为主题的展览在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科技馆中较为罕见,而熊猫基地的科学探秘馆正是这其中独一无二的存在。而东京科博则按照其自然科学的展览主题,由浅到深、由表至里的设置了展览版块,最后引导游客了解生物多样性的重要。
2、 并列式的展览结构。展区内各区块以不同主题划分,属于并列关系。熊猫基地各区块的内容相互联系,按照熊猫的交配、育幼、成长的顺序串联起熊猫的整个生命,令人印象深刻。
3、丰富的信息负载手段。作为科普教育场馆的博物馆,重点在于教育而非展览,因此两馆皆抛却常见的橱窗式陈列,采用多媒体技术设置多种可参与操作互动的展览设备,设有看板、LED电子图文显示屏、折页、触屏式电脑、3D小影院以及互动展品。展示手段多种多样,图文并茂全面深入的展示了教育项目。但白璧微瑕的是,熊猫基地馆内最常见的触屏式电脑展览方式,基本采用阐述式文字说明,主体皆采用陈述式句式,含有大量专业术语,对于没有专业背景的观众,尤其是未成年观众来说稍显乏味沉闷,难以引起强烈的兴趣。
4、自然的展场氛围。东京科博各展区依据不同的展览主题选定不同的主题色,照明以墙壁射灯为主,辅以大版面的照片,烘托出自然、和谐的氛圍。而悬挂在墙壁四周的科普展板、电子显示屏营造的环境灯光则强调了科普教育展场“科学探索”的神秘氛围。
5、专业的科普教育志愿者。无论是熊猫基地还是东京科博,其志愿者都经过专业的培训,能够结合展览内容,从专业的角度对游客进行科普。遗憾的是东京科博的志愿者年龄构成稍显单一,科普讲解方式难以引起低龄游客的兴趣。其科普教育主要依托于场馆展览本身,没有最大化的发挥科普讲解志愿者的作用。
五、促进科普教育基地发展的建议
科普场馆最核心、最重要的功能是开展教育科普活动,向参与者传递科普知识。[5]场馆类科普教育基地作为重要的科普教育场所,在馆内开展的教育活动需要结合其拥有的科普教育资源,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建设能够激发来馆者科学探索兴趣的、专业的科普教育项目。从本次的考察结果来看,我们初步讨论了以下建议:
1、 加强对科普基地的展览内容策划和管理,做好科普的基础建设。要想发挥科普教育基地的科普教育功能,场馆的基础展览内容建设是最必不可少的重点。场馆可以借鉴和参照国内外优秀的科普教育案例,从布局、教育目标、展览手段、场馆硬件设置等方面进行升级,探索适合自己的科普教育模式。
2、 培养专业科普教育人才。首先要确立科普教育人才在科普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和大学、中学、小学等教育机构合作进行科普学、科技传播、博物馆学等学科的建设交流。规范培养、管理科普志愿者的方式,丰富志愿者的年龄构成,适当扩大高校志愿者的比例,用他们自身扎实的理论知识和独特的讲解风格为基础,提高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定期举办志愿者的交流活动。
3、科普基地自身要加强自身营运管理。建设工作要突出特色,各基地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结合场馆特有的科普资源,以满足社会公众的科学需求为目的,开展特色鲜明、有实效的科普活动。进一步确立和完善科普基地建设的教育目标、布局规划、展览重点、资金运用,保证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孙莹.科普场馆教育功能的类型及其实现机制[J].理论导刊,2012,(2).
[2]周婧景.博物馆儿童教育:儿童展览与教育项目的双重视角[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3]大堀哲.博物館概論.東京:学文社,2005
[4]贾英杰.科普理论与政策研究初探[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5]蔡黎明.场馆非正式学习中的科普教育活动——以上海自然博物馆为例[J].科协论坛,2018,(4)
本项目来源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支持(项目编号:S201910656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