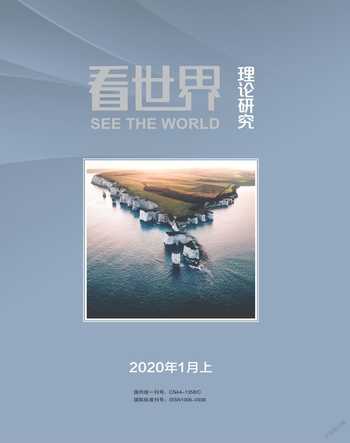重温《美丽人生》:黑色喜剧的叙事策略分析
李伊玮
摘要:时隔23年,意大利经典电影《美丽人生》中国观众再次见面。在这部温和的黑色喜剧中导演贝尼尼运用高超的叙事策略,在主题选择、故事架构、人物设定与叙事手法上都下足了功夫,开创性地用黑色喜剧的方式表达了深刻的主题,讲述出残酷战争中热烈的爱情与温厚的亲情,赞扬人性之美,构建了影片独特的叙事风格。
关键词:美丽人生;黑色喜剧;叙事分析
意大利经典电影《美丽人生》于1997年上映,横扫当时各大国际电影节,被誉为影史经典。时隔23年,4k 修复版的《美丽人生》于2020年1月3日与中国观众再次见面。在这部温和的黑色喜剧中,导演贝尼尼运用高超的叙事策略,营造了乐观诙谐乃至荒诞的影片基调,让炽热浓厚的爱情与亲情以及积极热忱的人生信念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之下显得尤为温暖与可贵。
一、主题选择与叙事风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段严肃沉重的历史,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悉数世界电影经典,反映二战题材的影片不在少数。传统的二战影片多通过描述残忍血腥的战争场面以及刻画人物的细腻情感来传递战争的残酷与悲情。就像正面描写真实的战争场面的《拯救大兵瑞恩》、描写魂断情长的乱世爱情故事的《魂断蓝桥》以及以集中营为背景来表现纳粹残酷的《辛德勒的名单》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天性乐观的意大利艺术家贝尼尼另辟蹊径,秉承其擅长的乐观积极、热情洋溢的叙事风格,采用独特的悲喜剧的叙事方式反映二战背景下犹太人的悲惨遭遇,将笔触聚焦于一个小人物如何在种族屠杀的阴影之下保护自己家庭的故事,讲述出残酷战争中热烈的爱情与温厚的亲情,使得这样一部悲喜交加的作品给观众带来视听与精神层面的多种程度的冲击。
从二战后新现实主义兴起之时,意大利电影就一直秉承着贴近现实与人道主义的传统关怀。罗伯托·贝尼尼作为意大利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并未传承新现实主义风格传统的表现路径,而是对固有主题进行新颖独特的另类阐释与演绎,这正是《美丽人生》这部影片在意大利电影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犹如贝尼尼在讲述影片创作思路所提到的“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将我自己、我的喜剧主人公置于一个极端的环境之中,这种最为极端的环境就是集中营,它几乎是那个残酷时代的象征,消极面的象征。我用一种喜剧的方式描述一个有血有泪的故事,因为我并不想让观众在我的影片中寻找现实主义。”因此他试图通过一个充满智慧与坚强的父亲的精巧设置将战争的残酷与苦难消解,以轻松乐观的人生态度向观众表达这样一个主题:即使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人們依旧要保持尊严、热忱与信念,这才是创造美丽人生的真谛。
影片的叙事结构分为两个序列。前半部分讲述了小人物圭多浪漫滑稽的爱情故事,在犹太青年圭多对光彩亮丽的贵族小姐多拉的求爱过程中,通过一次次的化险为夷与“机缘巧合”制造浪漫与笑点,消解了在当时意大利社会背景之下的紧张感与凝重感,又为其后战争爆发与人性摧残的悲剧埋下层层伏笔。同时贝尼尼利用其自身夸张的喜剧化表演风格,饱满地塑造了圭多这样一位乐观坚强、机智勇敢、充满热忱的犹太青年形象,深深地感染着观众。而影片的后半部分转变了基调,悲情随着喜剧画面逐渐递升。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中,圭多默默消化着纳粹对于犹太人肉体与精神上的摧残,为儿子编造了“成为赢家就可以得到坦克作为大奖”的游戏,伟大的父亲通过一次次的编造谎言与庇佑保全,让天真的儿子沉浸在这样的反常的游戏中并成为“最终的赢家”。荒诞的童话牵动着观众悲喜交加的神经,构建了影片独特的叙事风格。
二、叙事结构与细节叙事
“结构是对人物生活故事中一系列时间的选择,这种选择将事件组合成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序列,以激发特定而具体的情感,并表达一种特定而具体的人生观。”[1]《美丽人生》的叙事结构分为两个部分。
影片的前半部分,在1939年阴云笼罩的意大利小镇上,圭多在求爱过程中的智慧与幽默处处消解着战争爆发前夕社会的压迫感与历史的沉重感。从圭多与伙伴驾着松散失修的小轿车闯入村庄滑稽的出场方式开始,一段段闹剧似的情节就推进着叙事轻松发展。特别是在向多拉示爱的过程中,圭多的种种机智又离谱的浪漫举动,又令观众忍俊不禁。而在这轻松欢乐的表象下,现实生活的压力与对当下时局的无奈也暗潮涌动。圭多因犹太身份申请书店重重受阻;圭多叔叔的饭店遭到“野蛮人”的打砸、白马被涂满带有侮辱性的标语与颜色;小学校长大力宣扬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进行军国主义教育……这些强烈的对比穿插在影片叙事之中,将看似荒诞和反差的情节串联起来。
后半部分的影片基调一改之前的明媚靓丽,沉重阴暗的灰白色调暗示着集中营的暗无天日。圭多为了保护儿子的心灵不受重创,将之编造为一场有趣的旅行,让祖舒华带着“最终的胜利者就会赢得坦克作为大奖”的信念沉浸在“游戏空间”里。天真烂漫的祖舒华与冰冷的囚室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而圭多为儿子所作的表演又不断消解着这真实图景里的残忍与冷血。他将冷酷德国军官所介绍的营中规矩翻译为有趣的游戏规则,鼓励祖舒华挣得更多的游戏积分。一家人坚定着对生命以及生活的希望,例如父子俩在做工间隙偷偷用广播对多拉说“早上好,我的公主!”,在德国军官聚餐的夜晚将唱片机的传声筒伸向窗外播放咏叹调等等。导演巧妙地将丰富的细节铺垫在故事序列当中,呈现出喜中带悲、悲中有喜的感情基调。使得影片的整体结构气脉相通。
电影情节展示故事,而细节则有揭示作用。“关于电影形式的真正问题是:电影创作者是否利用背景中的细节来取代大部分的结构。”[2]而这部影片之所以结构紧凑,叙事流畅,就在于导演采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作为铺垫。例如从影片一开始,做酒店部长的圭多叔叔时便便遭到打砸,叔叔只是简单解释“他们只是野蛮人,无声胜有声。”这一情节转瞬即逝,而从叔叔如此平静淡定的反映就可以了解到这样的事情应该发生不止了一次,看似安定和的社会背后早秩序破败,冲突重重。再有,圭多冒充罗马督学来到多拉所在的学校视察,宣讲的核心内容便是日耳曼族是普天之下最优越的种族,可见墨索里尼政府对全社会进行的思想统治。社会对犹太族的歧视越演越烈,多拉的订婚宴上,叔叔的白马被涂上了滑稽的颜料和“小心:犹太马”的字样。而后与圭多因猜谜交好的德国医生突然接到急电返回柏林,预示着战争即将爆发,也正是这位医生在集中营中救了圭多一命。两人的儿子祖舒华为了逃避洗澡和换衣服躲进小柜子里,看似是小孩子调皮捣蛋的惯用伎俩,这一细节也让祖舒华在之后的集中营中因为不爱洗澡躲过了毒气室的残害,并在故事结尾被父亲藏在信箱柜中躲过屠杀,最终得以幸存。如果没有这些细节叙事,影片的整体性就会被打破。《美丽人生》运用巧妙的细节叙事技巧,让整部影片的结构更加紧凑和顺畅,同时也为伟大父亲所编造的荒诞童话提供了更多的逻辑与可能。
三、人物设定与表演
贝尼尼夸张的戏剧式演绎让主人公圭多从影片一出场就自带搞笑气质。他自诩为“圭多王子”,勇敢追求自己的“公主”,为多拉制造了众多的惊喜。在面对现实生活的艰难困苦时也总能乐观面对,轻松化解,他总能让鸡蛋机缘巧合地砸在官员的头上从而被称为“鸡蛋衰人”,化身罗马督学恶搞权威科学家发表的种族宣言,从头到脚地讽刺了“世上最优越的种族”。圭多是乐观机智的犹太青年,也是幽默浪漫的丈夫,更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他向儿子解释“犹太人和狗不得进入”的招牌,是因为人各有喜恶,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书店竖个牌子写上生番和蜘蛛不得入内。用这样轻松调侃又符合孩童思想世界的说谎方式化解了儿子的疑虑,也让圭多在残酷的集中营中为儿子编造做游戏的谎言这一举动有了合理的解释。大屠杀之夜,当圭多将儿子藏进信箱中以争取机会营救妻子,却不幸被德国士兵抓获实行枪决的路上,他仍然坚持表演,迈着夸张搞笑的步伐,像小丑一般佯装出得意的表情,却付出生命的代价让祖舒华享受与赢得这场“游戏”。
多拉是一位出身高贵学教师,拥有着美丽善良、勇敢坚韧的美好品质。她讨厌贵族之间无聊的社交礼仪,厌恶将非人道主义思想传输给孩童。在经历了一系列与圭多的奇遇后,她大胆地与这个犹太青年相爱,冲破传统观念的桎梏,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婚姻自由,过上了简单幸福的家庭生活。随着故事的推进,当丈夫和儿子被纳粹带走,没有犹太血统的多拉义无反顾地选择追随丈夫与儿子,甘愿被关押进集中营中。这时的多拉俨然成长为深爱丈夫与儿子的妻子和母亲,在女牢中听闻老人和孩子会被送进毒气室,多拉失魂落魄地挑拣死人的衣服,虽无言,但妮可丽塔·布拉斯奇将失魂落魄的神态表演得细致入微,直到听到丈夫和儿子通过广播的报安,多拉终于露出宽慰的笑容,一位柔软却坚韧的女性形象跃然于荧幕之上。
除此之外,圭多的叔叔虽然出现的镜头不多,但成功塑造了一位睿智温和、品味高雅具有绅士风度的犹太人形象。影片开头圭多来投靠身为酒店部长且热爱收藏的叔叔,面对“野蛮人”的野蛮行为总是默默忍受,并不看在眼里;向做侍者的圭多讲述“侍者不是下人,服务需要高度艺术”的道理;当德国女官跌倒在面前下意识搀扶并关心询问有没有跌伤。这一形象是导演对犹太人的映射,他们智慧且博雅,在一切事情面前保持尊严与人道主义,即便在种族迫害之下仍秉承着这些优秀的品质。而集中营中的德国女军官则是纳粹残暴的战争机器的化身。她凶狠地呵斥着不守规矩的犹太人甚至是军官的孩子,受到圭多叔叔好心的搀扶与关心时没有任何表情地径直离开。作为德国军人,她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与个人行为,是被法西斯驯化的可悲的战争机器。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有其自身的作用。通过对人物的性格与细节刻画,影片为观众描述了二战时期法西斯社会的现实语境,赞扬了人性的光辉,也对人性的黑暗和法西斯的残酷进行了深刻的讽刺与鞭挞。
四、叙事节奏与张力
叙事节奏是一部影片的灵魂,直接影响叙事效果,牵动观众的情感与情绪。《美丽人生》中,主人公圭多的语速轻松畅快、行动敏捷夸张,加之干净利落的轉场与细节的深入刻画,使得整体的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叙事技巧上,导演有意淡化情节中的戏剧冲突,加强喜剧元素。例如圭多数次与多拉的未婚夫鲁道夫发生多次冲突,却总是以圭多机智幽默的恶搞化解,观众的紧张情绪也随着一幕幕搞笑的场景转变为轻松的笑声。而在假扮总督先生来到多拉所在的学校里,圭多作为犹太人受命宣扬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这是似乎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而圭多手舞足蹈地将这种族主义的宣言瓦解,被发现后从窗户落荒而逃。主人公如此张狂的欺骗方式与荒诞的行为表现被抓现行,本应产生极大的冲突甚至受到惩罚,却以圭多滑稽逃跑而化解。还有在集中营中,祖舒华因为听到其他小朋友说出“纳粹会用人制造纽扣和肥皂”的真相而开始对父亲编造的游戏谎言产生怀疑,执意要离开,再次激起观众的担忧与焦虑情绪,而后又被圭多用欲擒故纵不断诱惑的方法化解了这一危机。影片通过这些情节不断制造矛盾又弱化冲突,用幽默的举动化解矛盾,用轻松的方式缓解紧张情绪,收放自如,时刻牵动着观众的心情。
影片的高潮部分发生在法西战败前夕的大屠杀之夜。圭多为营救妻子多拉将儿子藏在信箱柜中,在寻找多拉的惊险过程中,圭多最终还是被德国士兵抓获。而在被士兵押送去实行枪决的路上,圭多故意迈着浮夸搞笑的步伐从儿子眼前走过,祖舒华惊喜地目送父亲走远。 镜头跟随着圭多走向无人的隐蔽之处,他一路自信的神情甚至让观众沉浸在主人公一定会再次化险为夷的想象与期待中,此时枪响了,固定镜头中那位端着枪的士兵匆匆离开,此处的留白并没有给观众展示圭多被枪击的惨状,给观众留下意味深长的想象空间。天亮之后,游戏结束,真正的坦克驶向祖舒华的面前,他赢得了这场游戏,观众的紧张情绪也得到了有效地释放。这场荒诞的童话最终落幕,祖舒华在人群中找到了妈妈,并与妈妈在阳光下紧紧拥抱,正如故事讲述者在片尾说道:“这是我的经历,这是我的父亲所作的牺牲,这是我父亲赐我的恩典。”让观众在多维度的欣赏感受中体会到亲情与人性的伟大,更进一步体会到这部影片的叙事艺术价值。
爱情与亲情的联结、悲与喜的交合、童话式的叙事表现,构建了这部伟大动人的黑色喜剧。导演贝尼尼在主题选择、故事架构、人物设定与叙事手法上都下足了功夫,在一幕幕生机盎然且感人肺腑的情节中,开创性地用黑色喜剧的方式表达了深刻的主题,成为影史的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周铁东译.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2]齐宇译.电影的观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