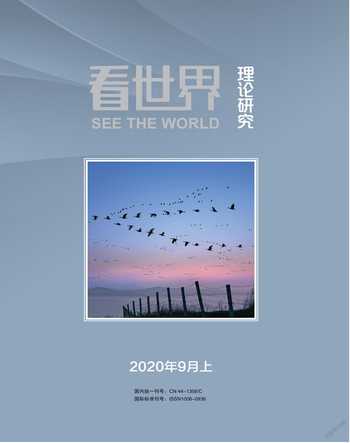以《烂柯山·痴梦》为例浅析昆曲正旦表演
邹美玲
摘要:《烂柯山·痴梦》是传承至今的昆曲经典折子戏,凝聚着数代昆曲艺术家的心血,是正旦行当极具代表性的剧目,也是笔者个人研习正旦以来,极为钟爱的剧目之一,在多年的学演过程中,每每被此剧打动。本文拟以该折剧目为例,试论心得,并浅析昆曲正旦的表演艺术。
关键词:《烂柯山·痴梦》;昆曲;正旦表演
一、经典剧目传承与典型人物形象塑造
在2009年的全国昆曲演员学习班中,笔者有幸得江苏省昆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继青亲炙,学习了《痴梦》一折戏,并在上海兰心大剧院汇报此剧后半折,开始了笔者昆曲学习、尤其是正旦学习的新阶段。张继青老师于20世纪60年代,经由徐子权先生建议,向“传字辈”艺术家沈传芷先生学习了《痴梦》。可以说,这是一出具有鲜明的“沈家做”风格的剧目。
《烂柯山》的女主人公崔氏并不算“正面形象”,是一个有缺点的女性。她结婚二十年未能盼得丈夫朱买臣发迹做官,难以继续忍受清贫的生活,逼迫朱买臣休妻,改嫁张木匠,却依然没有得到向往的生活。《痴梦》一折,她偶然得知前夫朱买臣高中的消息,百感交集,一方面她对自己的势力选择感到懊悔,另一方面,却仍对朱买臣怀有期待,希望他回头接受自己,昏沉之际入梦,梦见凤冠霞帔加身,喜近癫狂,醒后徒留失落悲凉。《痴梦》的表演极具张力,甚至有一些带有丑态的表演,与其他正旦应工的人物形象有着明显反差。
但正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形象,经过历代昆曲艺术家们的艺术加工,活色生香地立于昆曲舞台之上,历经时间的考验,依旧广受观众的欢迎。
在昆曲舞台上,正旦通常扮演有一定年龄、分量的角色,诸如《跃鲤记》中的庞氏、《琵琶记》中的赵五娘一类,都是典型的“大正旦”,她们生于封建社会底层,生活经历坎坷曲折却依然恪守礼教,端庄、本分。而崔氏则是一个带有浓郁市井气质的妇女形象,她的性格更是张扬、世俗,于大喜大悲之间切换,风格外露夸张,是典型的“雌大花面”。
崔氏的造型装扮,同样有异于其他正旦角色,虽身着正旦常用的银泡子和青褶子,却不加水袖,而是采用“翘袖”,腰间扎一条腰巾,这样的装扮,既有助于表演,也更能体现出她泼辣、外放的性格。
二、表演层次的递进
细窥《痴梦》结构,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即从人物出场开始,至偶遇差官得知朱买臣高中的消息止,她独自咀嚼、思考这件事,情绪难以平静;第二段为昏沉入梦,梦见朱买臣的从人们携凤冠霞帔前来,迎接自己回去“做夫人”,欣喜若狂,直至梦中张木匠持斧头来劈,美梦破碎;第三段则是从入梦后至梦醒结束,徒留满目凄凉。崔氏的心情在《痴梦》中无疑是大起大落的,故而每个段落中她的精神状态、情绪波动都是不同的,要求演员在表演层次上有所递进。
《痴梦》中的崔氏是很典型的带戏上场,前情往事的纠缠、自己对生活的选择,都时刻提醒着她。她的眼神是发直的,两耳时刻辨别着声音,在得知朱买臣高中之际,她有慌乱、但迅速掩盖的一瞬间。
这一段落中崔氏演唱了本折戏的第一支曲牌【锁南枝】,昆曲的唱腔和表演不仅仅是程式,而是要为人物服务,其中崔氏夹白“一夜夫妻百夜恩”处,运用了较为夸张的笑,这个笑要有一定的生活化,尽量体现出崔氏肉麻的、充满幻想的情绪。而后,戏落下来,崔氏回忆起更早前的事情,在出嫁时父母的嘱咐。此处是第一段和第二段戏的衔接,必须把握好音量、节奏的控制,不能让表演断裂。在学父母说话、与崔氏此刻自我的表达中,既要自如转换,又要充分发挥戏曲跳进跳出的表演模式。
第二段梦境的表演,是《痴梦》一折最核心、最精华之处,入梦后的崔氏,进入到自己营造出的虚拟世界。因此,入梦后的表演,要营造出一定虚幻的、远离现实的感觉,但同时,梦境的发生原本就是依托于现实的,因此也不能与现实完全背道而驰,个中分寸,拿捏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渔灯儿】是《痴梦》最为核心的主曲,是一段极具特色的梦中之唱。连用四个“为什么”的排比句,表现崔氏在梦中听见朱买臣从人们叩门声时的情景。这一段唱,将崔氏“醒来”的动作放慢、放大,把她故作疑惑却实则急切的心情、与似梦非梦的情境非常细腻地营造出来,尽显痴态。
当年,张继青老师带《痴梦》一剧进京演出,对入梦之后的表演进行了处理,通过运用龙套出场压低音量、运用古筝进行配乐等手段,营造出梦幻的感觉;同时崔氏的情绪和表演,也是与之呼应的。比如,在第四个“为甚么”处,有几步像“踩棉花”一样的脚步,为了表现出慢镜头之感;在家院念“夫人开门”后,崔氏有一个与前面的笑不同的狂笑,十分得意,转而“寻不出爷爷”时,情绪又有一丝的疑惑和低迷。在龙套们逐班相见时,面对院公、衙婆、皂隶们时,崔氏的情绪也都是不同的,这些细微处的转变,都要配合相应的表演,来展现崔氏在梦中所见所感。
在崔氏看到凤冠霞帔后,是全场情绪的最高潮,这里的笑也是最为开心、癫狂的,充分体现“雌大花面”的特色,声音全部放出来,念“我好喜也”时,台步调度的幅度也是较大的。随后崔氏唱【锦中拍】,穿戴凤冠霞帔,这一段要.将戏做到极致,通过服装造型、表情神态以及台步等方式,表现崔氏此时此刻的飘飘欲仙;紧接着张木匠持斧到来,崔氏情绪转变,唱腔与张木匠的念白掺在一起,气氛紧张,迅速脱掉凤冠霞帔,回到桌子里,结束一个完整的夢。
第三段戏开始,崔氏召唤着从人送回凤冠霞帔、一边从梦中醒来,“原来是一场大梦”,从梦中高度紧张的状态中松弛下来,语调也“冷”下来。【尾声】的演唱中,崔氏从梦境中逐渐抽离,回归到对生活的无奈感慨,其中最后一句“只有破壁残灯零碎月”作为全剧的收束,对景伤情,她先后关注到“破壁”、“残灯”,从灯影过渡至地上漏进的月光、再过渡至天上的月亮,通过台步、眼神、三个半云手及最后一“指”的运用,配合造型亮相,将悲凉的情绪推向高峰。在几声冰冷的小锣伴奏下,充满思索回味,悔恨地哭泣下场,全剧结束。
三、正旦表演的“破”与“立”
《痴梦》是一出有些“另类”的正旦戏,因此在表演上一定是有“破”有“立”的,与常规正旦表演同中有异。
首先,在音色上崔氏要有正旦的厚重感,与闺门旦、六旦音色有明显区分,同时,又要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更为外放甚至刺耳的处理,比如剧中几声大笑,一些诸如“啊呷呷”的口头感叹语,都要体现这个角色狂放市井的一面。
在念白节奏上,也不能与其他正旦角色一样从容缓和,或具有一定身份,而是要更为接近日常口语的节奏,生活化比重更高。在演唱上也与其他正旦角色的平稳、端庄不同,在许多字声的处理上,也适当运用了一些夸张、怪诞的方式。比如在开门后从人们行礼,当皂隶们进来时,崔氏十分害怕,在问“啊?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哪”时,声线是颤抖的,音调也有较大起伏,是非常典型的通过声音的造型来塑造人物的例子。
在形体方面,崔氏的动作比其他正旦形象更为日常,她的许多指法、台步都有一定的“破格”,比如最后“破壁残灯零碎月”的亮相,指向月亮的手臂完全伸直,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通常昆曲表演、尤其是正旦表演所讲究的圆融含蓄,正是这些“出格”的形体动作,才让崔氏这个角色有着与众不同的质感。
学习《痴梦》至今已有十余载,2018年剧院传承《痴梦》时,又跟随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徐云秀老师学习了此戏,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舞台经验的逐渐丰富,对这个戏也有着越来越深的感悟,也领悟了崔氏这个“不安分”的女性形象如此受观众欢迎的道理所在。正是因为有像崔氏这样体现世态冷暖、人性复杂多面的形象,昆曲正旦的表演才是丰富立体、充满魅力的,吸引着我们不断求索,一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