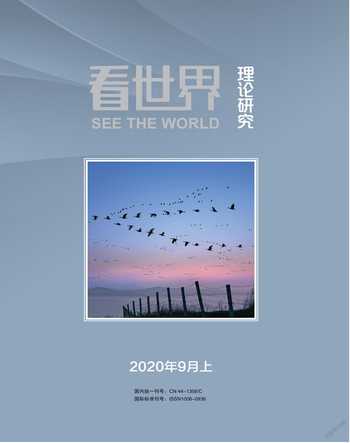试论话剧《推拿》中的群像性探索
杨露
摘要:话剧《推拿》把目光聚焦在盲人推拿师这一特殊群体上,对被社会边缘化的盲人推拿师的生存境况、生命尊严、人生理想和爱情追求等主题的进行了一个探索。本文从“盲人化的叙述视角、人物群像的象征性和极致化的话剧结构三个角度出发来进行论述,以期对话剧《推拿》中的群像性探索有一个更全面的解读。
关键词:《推拿》;群像性;叙述方式;盲人视角;边缘人物
毕飞宇的小说《推拿》在拿到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后,先后被搬到电视剧和电影的荧幕上。而娄烨导演的电影版《推拿》更是斩获第51届金马奖七项大奖和国际上的众多具有超高含金量的奖项。话剧版的《推拿》在2013年也终于被搬上了话剧舞台。话剧版的《推拿》在遵从原著的情况下,对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做了一个极致化的处理,以便在表达盲人推拿师这个群体特征时,还能对个人的个性化进行塑造。
一、盲人化的叙述视角
特殊的叙述视角一直都是文艺创作上热衷去探讨的一个点,例如萧红《呼兰河传》和迟子建《北极村童话》中的“儿童视角”、方方《风景》中的“亡人视角”、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视角”、王安忆《长恨歌》中的“鸽子视角”等特殊创作角度,而毕飞宇的《推拿》则选取了“盲人”的叙述视角,小说《推拿》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以要即将要着重讲述的对象来命名,话剧版的《推拿》延续了小说盲人化的叙述视角,让每一个盲人主人公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采用“罗生门式”的结构方式去讲述自己的故事。例如剧中的金嫣,在舞台上热情、张扬、勇敢的表现自己对张宗琪的爱,金嫣在向张宗琪和“沙宗琪”推拿店里其他同事表述自己从大连追到南京的原因时,观众可以从金嫣的视角去感受到这一人物敢爱敢恨的鲜明性格,以及金嫣和张宗琪的情感建置;再如都红,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在原小说的基础上,更是被无限放大。她渴望得到平常人的尊严,讨厌被人怜悯和保护,为了逃离众人的“保护”,她誓死不愿再弹钢琴,甚至不惜掰断自己的大拇指。采用这种“盲人化”的叙述视角,可以使现场的观众能够对盲人的黑暗世界更加感同身受,从而削弱掉普通受众视角上的某种优越感。《推拿》作为一部“群像性”的话剧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个体主人公情感的表达难度。人物一多,主线就很容易变乱,导演和编剧要是拿捏不好这个度,整个剧作就会像一盘散沙。“群戏效应”很难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去凸显每一个个体的情感特点。但编剧喻荣军从每一个人物的“盲史”出发,去探寻其内部的情感结构。例如小马,他九岁因为一场车祸失明,作为见过光明而后失明的盲人,是要比先天性失明的盲人在情感上更为痛苦和难以接受的。在经过自杀未遂后,他才终于接受自己失明的事实。沙复明作为先天性失明的盲人,他不知道“美”是什么,所以他四处去寻找“美”。他经常听到来做推拿的顾客夸赞都红美,所以他把都红当做美的化身,沙复明在剧中一再对都红说道:“美是什么?美就是你啊。”去追求和保护她,而都红却对小马一往情深,沙复明的痛苦来自于他的“爱而不得”和对“美”的困惑与追寻。剧中的每个人物都从自己的情感需求中,去探求个体的情感价值。话剧版的《推拿》从个体情感作为一个叙述点,探讨了盲人与常人一样的爱恨、纠葛与生命困境。这也是话剧版《推拿》力求想做到的一个点,即:让盲人感受常人的世界,让常人了解盲人的世界,从而盲人和常人能站在同一个端点去对话。
二、人物群像的象征性
电影、话剧作为一个符号化的文本创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人物作为话剧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往往被创造者赋予特殊的象征意蕴,从而达到创造者揭示其话剧主题的重要目的。话剧《推拿》塑造了系列人物形象,而这些人物形象也被导演郭小男和编剧喻荣军加持了特殊的象征意义。
小说《推拿》中的盲人和妓女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中的边缘人物。盲人因为生理上的残缺,与主流社会有一层无形的隔膜;而妓女是直接被主流社会文化所排斥的。在话剧版的《推拿》中,妓女小蛮一角被导演和编剧删除掉,留下了更多的空间来表现盲人的残缺世界以及盲人渴望寻找属于自身的社会认同。例如剧中冷艳而又绝望的都红,被一群冠以“慈善”的人当做“变异物种”来看,从而陷入到自我感动、自我友善的情绪里。剧中的主持人和慈善家们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同情”都红,把都红的尊严践踏在脚下,却还以为自己在做慈善,陷入自我感动的伪情绪里。都红为了反抗这种被迫“关爱”,不惜再也不演奏自己所喜愛的钢琴,而宁愿去当一个推拿师。都红在剧中一再强烈的表达自己想法“我不会再弹钢琴了”“我要去大街卖唱,二胡带起来方便”,盲人在生理上的缺失和常人的自我“友善”使得两个群体之间产生一条巨大的交流鸿沟。话剧《推拿》从盲人这种被边缘化的心里感受,去呼吁主流社会群体:对盲人最好的尊重,是把他当做一个与自身无异的常人,收起你自以为是的“关爱”,平等对话,尊重彼此,或许是两个群体能更加相融的一个最好方式。
三、极致化的话剧架构
《推拿》的小说原著有18万字的篇幅,且又拿过茅盾文学奖,算得上是一个头部内容的作品。要将一个18万字的小说浓缩到只有两个小时的话剧舞台上,对导演和编剧而言,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再者,小说原著是采用多条叙事线索进行推进,人物众多,人物命运和困境也相对分散。话剧版的《推拿》针对这些改变问题,对话剧的结构进行了一个极致化的改编。
话剧版的《推拿》为适应舞台的特殊性,将小说多条叙事的线索改编成了相对集中的单线叙事,其他的线索则被旁敲侧击的杂在整个话剧的内容里,不会留下太重的痕迹,但隐隐约约又能感受其存在,与“草蛇灰线”的叙事形态有异曲同工之妙。剧作以拆穿危机贯穿全场,给整个推拿中心的盲人推拿师们设置一条巨大的压力线,并在其间穿插推拿中心的老板沙复明对都红的守护与追求;金嫣不远万里从大连来到南京,只为嫁给自己的挚爱张宗琪;王大夫与小孔享受爱情的甜蜜,却因各种现实原因而无法结婚;小马对性的萌动和好奇;都红自我毁灭式的渴求尊严等,大危机套上人物小困境的戏剧结构,使得整个剧作呈现出一种紧张的节奏感。观众在为主人公捏把汗的同时,又能够有效的突出话剧的主题,即:盲人因各自的生理缺陷而带来的心灵创伤,使得他们在爱情、事业甚至是命运面前,或痛苦或努力或主动或被动的挣扎着,以求得生而为人的尊严和快乐。
此外,编剧喻荣军对人物的性格定位做了一个极致化的处理。
编剧喻荣军把小说《推拿》往“小说话剧化”的方向靠拢,从剧本的叙事结构、人物群像的塑造方式和故事的叙事线索三个方面来改编剧本,基本完成了编剧的职责。话剧版的《推拿》没有成为爆款,除了从剧作上去寻找原因,似乎还要考虑到“盲人群戏”的方式,是否真的适合剧场呈现和剧场叙事?这是我的一个思考和疑问。希望话剧版的《推拿》在经过再次改良后,能够重回大众视野,让盲人与常人平等对话。
参考文献:
[1]向荣.看似专注,实则盲目 话剧《推拿》[J].上海戏剧,2013(11):34-35.
[2]徐健.用情过度带来的叙事偏移——评话剧《推拿》[J].艺术评论,2013(10):125-129.
[3]乔宗玉. 话剧《推拿》不成功,弊在概念化[N]. 中国艺术报,2013-09-13(004).
[4]魏平. 眼盲了,心却更亮[N]. 中国艺术报,2013-08-2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