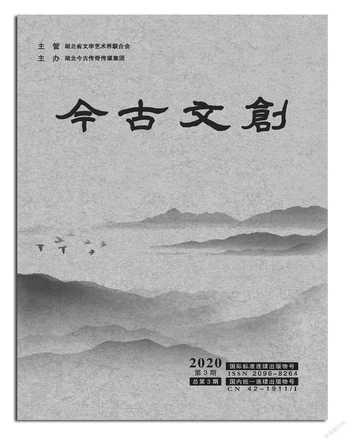论纪弦诗歌中抒情主人公形象
龚晓旭
摘 要: 纪弦(1913-2013),覃子豪与钟鼎文被誉为台湾诗坛的三大元老,在台湾诗坛享有极高的声誉。在这三人当中,纪弦的创作更加引人注目。这位人瑞作家在世的一百年间创作了一千多首诗,在现代诗创作的理论上颇有建树。他延续了现代派诗歌创作的薪火,将现代诗的创作推向了又一高度。由于纪弦有美术学习的基础,所以他的诗歌不仅在风格上比较明快热情,而且色彩搭配得宜,用独特的眼光和笔触构造了一个奇特的艺术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当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尤为特殊。笔者以纪弦三个时期的创作为例,分析一下他的诗歌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关键词: 创作分段;意象;抒情主人公;创作风格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3-0023-05
纪弦生于1913年,于2013年去世,是文学史上少有的人瑞诗人。他自1929年开始写诗,存世的一千多首诗当中,绝大部分都是佳作。在漫长的写诗过程当中,纪弦的写诗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929年—1948年,这一时期是纪弦创作的初期,文学史上习惯称之为扬州时代。这一时期纪弦的詩作虽然不够成熟,但是跳跃着少年追梦的火花,诗作风格明快艳丽,处处彰显着追梦人的理想和信念,代表作品如《四行小唱》《理想》《归思》《舷边吟》等;第二个时期为1948年—1976年,这也是他创作的高潮时期——台湾时代。这一时期的创作一反之前诗歌创作当中田园牧歌式的浪漫,而是以一种冷静和客观的眼光去反思工业社会文明外衣下的生活现实和城市精神。代表作有《诗的复活》 《光明的追求者》《命运交响乐》《阿富罗底之死》等。这一时期的创作彰显着诗人的创作主张和创作理念,抒情主人公形象由一个追梦的孤独青年成长为一个现实的反叛者,工业社会的适应者以及城市精神的探寻者。第三时期的创作从1976年-2013年,由于诗人1976年离台赴美,所以第三时期的创作也被称之为“美西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受诗人生活环境所影响,表现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气的意境。在宁静和相对隔绝的生活当中,向往着外星球的生活,这是纪弦诗歌生涯的一个尾声。代表作有《活着便是宣言》《时间的相对论》《年老的大象》《重返色彩的世界》等。
一、光脚吟唱孤独的流浪者(扬州时代)
纪弦在初期的创作大部分(1929年-1948年)都围绕一个字眼展开—— “孤独”。而这种孤独在某种意义上拥有着双重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身心上的孤独,诗人为求学离开自己的故乡,常年的奔波和知己难寻使得诗人感觉自己像一个流浪者。而孤独的状态使得诗人的自我和真我完整的展露出来。如作品《脱袜吟》,“何其臭的袜子,何其臭的脚,这是流浪人的袜子,是流浪人的脚”,诗作虽然短小,但是流浪者的形象跃然纸上。诗作并未对流浪者的形象作具体的描述,但是通过袜子和脚可见流浪者的惨象。而后两句“没有家,也没有亲人,家呀,亲人呀,何其生疏的东西呀”,又以平淡的口吻写出了流浪者的自述,也顺带点明了诗的主题。整首诗看似语言比较凌乱,但是逻辑十分清晰,由于在外流浪许久,所以亲人和家都变成了生疏的东西,由于亲人都不在身边,所以才会有何其臭的袜子和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将这首诗看作是诗人青年时期的写照——涉世未深,四处奔波,心中有期许,理想实现遥遥无期。整首诗并未提及“孤独”二字,但是流浪者的形象足以证明这种孤独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而孤独还有着第二层含义。在诗作《理想》当中,“你要我和你耕瘦瘠的田,我却有未开采的金银矿;你的理想是条美丽的小蛇,而我的理想好比凛然的龙”,诗人将理想和现实分别比喻成瘦瘠的田和金银矿,一条龙和一条蛇,这样的比喻不仅表明了作者的理想和现实背道而驰,进一步阐明了作者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以及在追求理想的过程当中与世界的疏离。而这种与世界的疏离必定会产生孤独,不可否认的是对理想信念的执念所造就的孤独,也是成就诗人的一剂良药。生存环境的变化势必会影响诗人的创作倾向,在《独行者》当中,诗人用朴素的话语将整个生存环境细致地描绘了出来。“忍受着一切风的吹袭和一切雨的淋打,赤着双足,艰辛地迈步,在一条以无数针尖密密排成的,到圣地去的道途上,我是一个虔敬的独行者”。这样的描述未必是诗人真实的生存环境,而仅仅是一种艺术加工,艺术真实比现实更能触动情肠。1937年是日军侵华的开始,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诗人,自然对眼前的生存状态感到无奈和心酸,但是诗人甘愿忍受着风的吹袭和雨的淋打,尽管赤着双足,但依旧朝着以针尖密密排成圣地的道途上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诗人不仅要克服敌人枪炮的恐惧,更要克服恶劣生活环境所带来的孤独。尽管是一个人前行,但是前进的脚步绝不会偏移方向,因为诗人是一个虔敬的独行者。在孤独且恶劣的环境中,诗人有着清醒的认知,他以梦为马,书写着青春年华。
长诗《面具》赤裸裸地剖析自己的精神,向读者呈现出了一个真实的纪弦。这种敢于自我剖析的精神正是现代人所缺乏的。诗人直言活着是痛苦的,因为他可以辨别善恶,判断真伪,由此可见,当时是小丑和烈士行走在同一道路上的时代。在诗作的描述当中,看到了时代的缩影。当时国内外的环境都比较复杂,中国处于内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政治立场就显得格外重要,纪弦戴着面具行走在道路上,也是因为政治环境所迫。表里不一的行为让诗人感到痛苦,也让诗人感觉自己的人格是二重的。尽管在外界,诗人无法正视一个虚伪的自己,但是回到自己的陋室当中,关上了门窗与外界隔绝,在没有人的情况下,诗人可以把自己的面具摘下,这个时候诗人的灵魂便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人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我的存在才是真实的,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我的行为是纯粹的,只有在自己的天地里,我有自由的意志。”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在陋室当中,许多人也许都和诗人一样,是一个演员,也是唯一的观众,是上帝,也是唯一的选民,崇拜着自己,也赐福给自己。只有在这里真实的自我才会表现出来,尽管这样真实的自我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是谁都没有理由去剥夺这样的存在。
纪弦初期的创作,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始终是一个孤独的流浪者,他渴望温暖,渴望回归,但是现实总是和理想背道而驰。尽管通往理想的道路上布满荆棘,充斥着矛盾和孤独,但是作者依旧赤足,昂首挺胸,大步向前。初期的创作虽然没有绕开孤独的字眼,但并不让人感觉到凄凉,相反让人们看到一个追梦青年坚定的步伐和不灭的理想。现实纵然可以一次次把诗人击倒,可以剥夺诗人“穿鞋”的权利,但是无法毁灭诗人追梦的信心,他依旧可以光脚吟唱着孤独,以一种洒脱的方式流浪到梦想的彼岸。纪弦初期的诗作以孤独为底色,以青年理想为支柱,再辅以明媚的色彩,诗作虽略显青涩,但是却呈现出田园牧歌式的浪漫,回味隽永。
二、反浪漫的工业社会适应者(台湾时代)
1948年-1976年是纪弦创作的高潮期,褪去了年少的青涩和轻狂,纪弦开始在创作上寻求新的突破。时代在不停地发展,工业在不停地进步,快节奏的生活也打破了诗坛的某种平衡,各种快餐类文学充斥着整个市场,有些人开始担心现代诗的发展会走向一个极端。
面对这种困境诗人纪弦开始在工业社会当中寻求新的定位,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来适应快节奏的工业社会。和初期的创作相比,这一时期的创作在风格上显得更加成熟和稳重,摆脱了前期创作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以敏锐的眼光来探寻工业社会的生活现实和城市精神。
在《诗的复活》当中,诗人痛心疾首地写道:“被工厂以及火车,轮船的煤烟熏黑了的月亮不是属于李白的……或是被地球的庞大的阴影偶然而短暂地掩蔽了的月亮也不是属于李白的。李白死了,月亮也死了,所以我们来了”。诗人以一种客观冷静甚至于有些乐观的态度看待工业文明的发展。尽管月亮死了,李白死了,但是可以鸣着工厂的汽笛,庄严的,肯定的,有信仰的宣告诗的复活,“所以我们来了”。工业社会的到来对于大部分来说是一种恐慌,这种恐慌包含着对未来生活的质疑以及对自身终将被时代所淘汰的无奈。
在工业社会大背景下的诗人却显得尤为冷静,面临着被煤熏黑的月亮和死去的李白,诗人不是一味的诅咒和谴责,而是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来应对种种改变,甚至还宣告着诗的复活。李白时代的风,花,雪,月已经被工业社会的煤烟,望远镜,汽笛,大提琴所取代,李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属于我们的时代才刚刚到来。纪弦在对未来的认知上表现出超乎常人的理智和客观,这不仅表现出诗人在认知上与时俱进,更在创作上表现出和时代高度的一致性,认同性。
这一时期的纪弦在创作的时候,极力遏制着过去的浪漫激情,而更多地追求在冷静的意象当中,表现出他对工业社会的独特洞悉。如诗作《阿富罗底之死》中,诗人写道:“把希腊女神Aphrodite塞进一具杀牛机器里去,切成块状。把那些“美”的要素抽出来制成标本,然后一小瓶一小瓶分门别类地陈列在古物博览会里,以供民众观赏,并且接受一种教育。这就是二十世纪,我们的。”诗人在诗作中表现出了忧虑和思考,以沉重的口吻说出了自己观察到的结果,希望以此来启发更多的民智,也担负起了一个诗人该尽的责任。
文学是时代变化的风向标,保持文学才智不枯竭的唯一方法就是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进行探索,并以文学的方式反馈给大众,以此来启发民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审美,而20世纪的审美有些抽象,这种抽象来源于工业社会的进步对于慢节奏生活的破坏。诗人无法再放慢脚步去欣赏那些曾经浪漫的风花雪月,也无法驻足欣赏身边留存的风景。因为一旦停下了腳步,就会被这个时代狠狠地甩在后面。
所以,20世纪的审美是把美的东西切成块,把美的要素抽出来制成标本,放在博物馆里供民众来欣赏,并且受到一种教育。这样的教育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诗人敏感地捕捉到工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整个社会教育有着割裂的作用。在诗作的最后,诗人并未对这种现象作出悲观的评价,这样的留白有利于读者进行更加深层次地思考和再创造。
工业时代的到来,分离也便成了常事,而现代人最应该学会的本领之一就是习惯分离。诗人在1948年离沪去台,远离故土,使得诗人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格外的留恋,也在很多诗作当中表现了出来。如诗作《法海寺》《五亭桥》《云和月》。
离开大陆之后,法海寺、五亭桥、扬子江、大屯山、长安,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作者的梦中,作者对故土的留恋可见一斑。写于1969年的诗作《法海寺》将思乡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法海寺的夕照,葫芦形的白塔,倒影在我小时候玩过的湖面上,绿杨深处宁静里带几分神秘。天下美中之美景,世界名画中之名画,还能让我再看你一眼吗?白塔啊,今生今世……”
诗人的青年时代都是在扬州度过的,法海寺是扬州瘦西湖上的名胜之一,而诗人年少的时候常去写生,自然对它异常的熟悉。离开故土之后这些家乡的名胜风景时常会出现在他的梦中,勾起他的思乡之情。整首诗虽然并未出现思乡二字,但是诗人对法海寺的高度褒扬也体现了故乡名胜风景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诗作以省略号和问号结尾,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也为读者的二次创作提供了一个契机。以问号和省略号结尾的诗作还有写于1954年的《一片槐树叶》,诗人看见夹在书本里的一片发黄的槐树叶,生发出来的思乡之情显得格外沉重,触动情肠。“蝉翼般轻轻滑落的槐树叶,细看时,还沾着些故国的泥土哪。故国哟,啊啊,要到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让我再回到你的怀抱里,去享受一个世界上最愉快的,飘着淡淡的槐花香的季节……”
诗人用短短三节诗抒发了思念故乡、思念故国的情感,且将两种情感调和得刚刚好,既不显得沉重,又不会让读者感到悲凉,相反表达出来的是一种真挚的向往,实在是思乡诗作中的佳作。每个诗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都应当把握情感的浓度,诗歌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它不仅仅承载着诗人最初创作时赋予它的激情,还囊括着读者的再次创造。如果诗人在创作之时就已经将情感全部倾泄其中,那么读者很难在再创造的时候找到合适的“缺口”来盛放自己的情绪,读者的情感会显得无处安放,在阅读诗作的时候也会感觉诗作所表达的情感浓烈得化不开。
纪弦用问号和省略结尾的方式,刚好解决了这一难题,既恰到好处地流露出自己的思乡、眷恋故土的情感,又留出足够的空间来给读者尽情地创造。诗人说要去享受一个飘着槐花香的季节,那读者从诗中嗅到花香的时候,也会自然联想到这个季节其他的产物,这样一来诗作的情感显得更加丰润,诗作也拥有更长远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在1948年—1976年的创作当中,纪弦的创作风格比起前期有所改变,对现实理智客观地认知也对其诗歌的创作有所影响。在本时期的创作当中,诗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逐渐变为一个工业社会生活的适应者,尽管工业时代的到来,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但是诗人仍然相信这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他也在这个大时代当中找准了自己的定位。诗人的创作也给那些在迷茫的诗人指出了一些方向,诗歌并没有死亡,诗歌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在台湾时代,诗人在诗歌、文学和绘画上都创作颇丰,算是创作当中的高潮期。
三、仰望星空的耄耋者(美西时代)
1976年年底,纪弦离开台湾,移居美国,正式开始了他的美西时代。虽然生活的环境不断地转换,但是诗人并未放弃诗歌的创作,一直以一己之力延续着现代派诗歌的薪火。年岁的增长,生活环境的改变使得作者在诗歌创作风格方面也发生了转变。如果说诗人的创作高潮期改变了以往的田园牧歌式的浪漫的话,在诗人的美西时代,他又重拾了这种浪漫。青年时期的浪漫是对未来天马行空的想象,行至暮年的浪漫就是对外太空的切实可行的向往。纪弦在美西时代的创作,有着对外太空的生活有着向往,也将思乡这个主题贯穿到底,除此之外,一部分诗作还闪耀着哲学的光辉。
在诗人2002年创作的长诗《重返色彩的世界》当中,诗人写道“于是到了2013年,我满一百岁,那就必须乘坐一艘超光速太空船前往月球,那没有水也没有风,寸草不生十分荒凉,咱们唯一的卫星以庆生,以祝祷……”可以看得出来是诗人在年老的时候对外太空的生活充满着向往,他还梦想着自己到一百岁的时候可以乘着超光速太空船到月球上,用自己的画笔去记录那一个没有水没有风寸草不生的星球上的风景,重返那个充满色彩的世界。
远离了故国,诗人思乡的情感更加沉重。从古至今不论政见立场如何,思乡的情感都能冲破偏见直达每个读者的内心世界,触动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在作者众多思乡的诗篇当中,《致终南山》尤为引人注意,从诗人的作品当中,可以了解到作者从未真正到过终南山,但是但凡读过这个作品的人,都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终南山的山形和走势以及其特有的风景,终南山的一草一木都深刻地印刻在脑海中。“我从未见到你的身姿与山容,但是我可以想象你的山色和其苍翠,我就青一块,绿一块,紫一块在我的画布上涂抹就涂抹……”诗作色彩绚丽,可见作者的美术功底也为诗作添色不少。
诗人移居美国的时候已经六十高龄,这一时期的创作自然也闪耀着诗人的智慧和哲思。创作于1999年的《月光曲》是美西时代不可多得的佳作。全诗为:“升起于键盘上的月亮,做了暗室里的灯。”全诗不过十六字,但是内容含量却非常丰富。意象的组合异常的奇特,将天上的月亮和暗室的灯做了对比,二者都可以带给人们光明。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的月亮是键盘上升起的,这属于诗歌的艺术加工,是虚写的部分;而暗室的灯是实写的部分,虚实的高度结合也彰显了作者不俗的文学功底和奇异的想象力。这首诗作于1999年,虽然意境优美,却是一首悼亡诗,属于两个人的合作,作者在后记当中提及此诗是在好友姚应才关灯弹奏《月光曲》的时候,曲终诗成。当时是一首长诗,金句只有两句,却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安放,最终没有成诗。后因好友和哥哥一同阵亡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所以作者终身不再听《月光曲》,以这首残诗来纪念好友,也算是了却了一个心愿。好友虽然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他的精神就好似在暗室当中的月亮,虽说发出的光芒不是很强烈,但是可以照亮每一个角落,也可以鼓舞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勇敢地朝着前进的方向进军。正如他升起于键盘上的月光,会在那些黑暗无光的岁月里作指引人们前行的灯火。
在《年老的大象》当中,诗人以一只年迈的大象自比,“年老的大象,无论走了多远,一旦病重,自知活不久了,就会马上回头,回到他小時候喝水的地方,躺下来静静地死去。”在诗作当中可以揣测出,诗人在这一时期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但是心中还挂念着自己的故乡,“我在地球上散步,从一个洲到一个洲,从一个国到一个国,从一个城到一个城,看山,看水,看花,看树,看那些动物,看那些女子,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好玩的了,就想回到扬州去看瘦西湖的风景”。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的心境很平和,面对病痛,生死,他异常冷静。他把丰富的人生阅历看作是在球上的散步,从一个洲到一个洲,从一个城到一个城,可是奔波半生,他还是想回到最初的瘦西湖。
落叶归根是每个中国人特有的情结,行至暮年,纪弦唯一的愿望就是可以回到自己的故乡。故乡也是纪弦一生的牵挂,不管是青年时期创作还是中年时期的创作,都没有绕开思乡这一主题。青年时期的思乡之情,显示出“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涩;中年时期的思乡之情,像一杯经过时间发酵的烈酒,酒入愁肠,化作了无限的感慨和悲怆,显得沉重和浓烈;而晚年的思乡之情趋于平和,褪去了青年时思乡的青涩和中年思乡的苦闷,显得平稳和恬淡。
美西时代的创作有着不同于少年时代的浪漫气息,虽然纪弦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思维却异常的活跃,他时常仰望星空,渴望着外太空的生活。所以笔者将这一时期他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概括为仰望星空的耄耋者。比起前两个时期的创作,在创作尾声纪弦的诗歌不管是在数量上或者质量上都远远大不如前。但比起前两个时期的创作,第三时期的创作在风格上更加沉稳,思维也更加多变,表现领域也更加宽泛。
纪弦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扬州时代,台湾时代和美西时代。从诗歌的质量和数量上而言,台湾时代是创作的高峰期,留下了不少佳作。而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也随时代的变迁和生存环境的改变,由刚开始的光脚吟唱孤独的流浪者,成长为反浪漫的工业社会适应者,最后成为仰望星空的耄耋者。在创作风格上由最初的青涩朦胧到成熟稳健最后转变为随性自由。
参考文献:
[1]纪弦.纪弦诗选集[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10).
[2]纪弦.纪弦回忆录[M].联合大学出版社,2001.
[3]张志忠.中国当代文学60年[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5):284-286.
[4]胡旭梅.语到极致是平常——论纪弦诗歌《傍晚的家》[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04).
[5]黄承基.纪弦“现代诗之我观”[J].科教文汇旬刊,2012,(01).
[6]罗晓莉.论纪弦现代诗艺中的修辞、体验与审美感受[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05).
[7]刘纪新.论纪弦的“身体诗”[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
[8]奚密.我有我的歌——纪弦早期作品浅析[J].现代诗复刊21期,1994,(02).
[9]刘登翰.晚景论纪弦[J].载诗探索,
199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