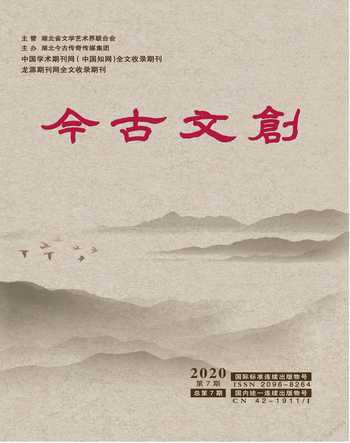《半轮黄日》中的二元互补与平衡
丰慧
【摘要】 《半轮黄日》是尼日利亚作家阿迪契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在当代非洲文学、族裔文学、后殖民主义及女性主义等领域都具备颇高的研究价值。在非洲部落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交汇、冲撞中,二元哲学贯穿始终。这与西方二元论所研究的事物两极不同,伊博二元主义更强调一对概念的互补、共生,从而实现调和,化解冲突。笔者通过发掘传统部落体系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个体与集体中的二元互补、分析多重文化、心理要素的内在相互作用,对深入解读世界文学中的“非洲性”这一主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有利于拓宽非洲当代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
【关键词】 阿迪契;二元互补;非洲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7-0011-02
一、引言
《半轮黄日》是尼日利亚作家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1977— )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讲述了20世纪六十年代年尼日利亚内战前后十年间,几位主人公的个人命运于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时,各自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轨迹。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笔调精致刻画、巧妙叙事,打破了世界文坛对非洲故事叙事方式和内容的固化思维形式。本书中,后殖民时代尼日利亚中产阶级面临的個体困境与国家发展、多元文化背景下本土伊博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社会变迁尤其是比亚法拉战争带给本土人民的创伤,均成为其描摹的对象。
二、二元主义哲学的研究背景
“现代非洲小说之父”钦努阿·阿契贝在论文集《创造日前的黎明》中曾这样阐述伊博思想哲学,说它是“互补的二元对立”。(Achebe,1976)需注意此处伊博文明中的二元对立主义并不等同于西方哲学中“对立的两极”。
二律背反理论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哲学基本概念。它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一种对称性关系。如德里达所指的“分裂世界为不可调和的两极,然后选择其中一个,摒弃另一个” (Petrović, 2014)。
伊博二元论基于这一对概念不断相互作用以达到的平衡之上。西方哲学的二元论强调两股力量之间的对抗,而后者则把两个极点看作是一种互补形式。
本文研究重点就是这种互补共生的平衡,而非两个孤立极端的相对主义。通过探索本书中本土伊博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内在作用力,旨在呈现一个观点:互补二元论及其所带来的叙事技巧已巧妙融入非洲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表述及呈现战争这一“非洲性”不可或缺的题材时,这种二元平衡起到根本性作用,推动了世界文坛“非洲民族性”这一概念的构建。
三、部落制与现代文明的二元互补
在《半轮黄日》中,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自然与超自然理论、传统与变革,逐渐演化出了非洲与西方世界的二元对立。比亚法拉战争对阿迪契而言,是一场伴随冲突的自我身份塑造。约翰·霍利利认为这是一种必要——之前对战争残酷性的渲染与描写需要融入人文情怀(Hawley, 2008)。
而作为新生代作家,阿迪契对与这一段历史具有必要的时间间隔,能够更清晰地反思、抽炼,将其加工,使之成为艺术。尽管奥兰娜与奥登尼博崇尚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但在阿迪契现实主义叙事中,他们同时呈现出维护集体主义思想的一面。
在阿皮亚看来,二人代表“受过西式教育并西化了的小部分人群,以作家、知识分子为主,在本民族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交流中起到调和作用”。诚然,在《半轮黄日》中,阶级与身份,以及最终的世界观,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西式教育的水平。奥兰娜和奥登尼博代表着“新派”观点,仆人乌古则代表着“老式”观点。他来自一个小村落,信巫术,用传统意识形态看待这个新世界。但一个人的群体身份有别于社会阶级,部落身份也一样。
正如一些观点认为,民族分裂与社会分裂,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殖民传统和自治政府冲突的结果,如同霍利所写,“在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内,殖民政府所偏向的族群所带来的不公正,会在随后的时日内减少稳定的几率,并会在一个新的殖民世界得以复原”。
在本书中,阿迪契并没有深入殖民主义如何造成阶级民族分裂,只是通过一些人物事例,通过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描绘了社会局面的复杂。
本书中,集体的概念很大程度上与部落联系在了一起。在战争开始的几年前,作者借主人公奥登尼博之口阐明了部落身份的积极一面:
但我认为非洲人唯一的真实身份是部落。我之所以是尼日利亚人,是因为白人创立了尼日利亚,给了我这个身份。我之所以是黑人,是因为白人把”黑人”建构得尽可能与“白人”不同,但在白人到来之前,我是伊博族人。
由此,尽管本书中与部落有关的暴行——从奥兰娜家族遭遇的屠杀到对政府军对饥饿难民的空袭,阿迪契展现了部落主义的积极一面。在社会单元中,阿迪契有意识地运用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平衡,再一次调和了个体叙事与经典叙事之间的内在关系。换言之,通过对特定情节的描写,她将这些元素(如部落主义、口述文学)插入典型的非洲性背景下,打破了读者对这片“黑暗大陆”的刻板印象。
四、个人意志与集体意识的二元平衡
在其个体性描绘中,阿迪契涉及暴力、战争这一艰难的主题。战争是“非洲主题”不幸却又不能略过的一笔。海伦·哈比拉曾说,此类场面的描写实为博人眼球,同时助长了读者对非洲贫困、战乱的刻板印象(Habila,2013)。哈比拉这一观点醒了非洲作家,这一刻板印象在文学构建中的存在。
阿迪契坚持将二元平衡融入战争书写,实为冒险之举,容易把事物推向非黑即白的极端。为了维系融合,避免极端评价,阿迪契发掘了个体良知与集体善恶观的内在作用。她将战争的恐怖残酷通过个体描绘出来。乌古在酒吧参与轮奸这一事件中,作者对集体恶行与个体恶的区分探讨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场性侵与乌古之前参与的杀戮相比,被视作更为严重的战争犯罪,很大程度上由于这并不是发生在战场,而是针对一名平民,一名手无寸铁、女性。这一犯罪映射出个人身份在集体身份中消失了。
“最后他看了一眼女孩。她也在瞪着他,目光平静,充满仇恨。”
战争结束后,这一形象一直另乌古无法释怀,比任何场面都根深蒂固,讽刺的是,这常犯罪演化成了乌古内心深处的精神创伤:
“他醒过来,憎恨梦中的形象,憎恨他自己,他将给自己时间,弥补他所犯的过错;“他想指导如果凯内内得知酒吧女招待的遭遇,会对他说什么、做什么,对他的感觉有什么变化,她将憎恶他。奥兰娜也会如此。艾伯莱奇也会如此。”
这场犯罪逼迫乌古从他者视角去看待自己。当他回到故乡,发现自己的妹妹也被尼日利亚士兵轮奸后,这一视角得到深化。乌古没有在这种邪恶面前屈从,他通过悔改,保持了人性的完好。乌古的举行强调了善恶的构建和在集体力量下个体的“恶”的匿名化。
因为无名的尼日利亚士兵在邪恶的刻板形象面前非常容易被归类;然而烏古,出于一时间的软弱做出了强奸这种罪行,在一个战争背景下,展现了实际行为中的“罪”,在构建中,是匿名性的(乌古对于女招待如同尼日利亚士兵之于他的妹妹)。
同样,屠杀奥兰娜家族的暴民,向比亚法拉城镇投炸弹的飞行员,也不该因为自己参与集体暴行而受责罚。他们所在的部落,如伊博族,不能被是做强奸犯。该责备谁这个问题是开放性的,也许矛头应对准无意识和无知。
阿迪契将对将谴责对象从传统的暴徒形象转化为寻求一种集体与个人的平衡。这暗示着,社会已被战争所改变,平衡是战后重建必须完成的课题。阿迪契关于谁应收到谴责这一问题的讨论,是为了走向调和、平衡。
五、 结语
阿迪契聚焦伊博族社会,集中刻画了战争暴行背后的人文情愫,在不可逆的创伤后维系了社会当中的文化身份。部落作为一个社会单元,在解释个体身份上是足够的,然而集体意识也对其中的成员具有显而易见的影响。
本书通过将二者融汇调和,达到了战争的悲剧在物质形态上最大展现效果。与此同时,开放式结尾让作品更加贴近现实,可以在保有完整性的同时唤起读者的道德认同和悲悯情怀。本书自2006年发表以来获得巨大反响,阿迪契继承非洲文学传统,开创了世界文坛关于“非洲性”这一主题新的书写历史。
参考文献:
[1]Achebe, Chinua.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C]. New York City: Anchor Books, 1976.
[2]Petrović, Lena. Remembering and Dismembering: Derrida’s Reading of Levi-Strauss[J].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2004 ,3 (1): 87–96.
[3]Hawley, J. C. Biafra as Heritage and Symbol: Adichie, Mbachu, and Iweala[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2008 ,39 (2): 15–27.
[4]Eliot, T. S. Critical Essays. [C].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2.
[5]Habila, H. We Need New Names by Noviolet Bulawayo—Review[N]. Guardian, 2013-6-20.
[6]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半轮黄日[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7]周春.美国黑人文学评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