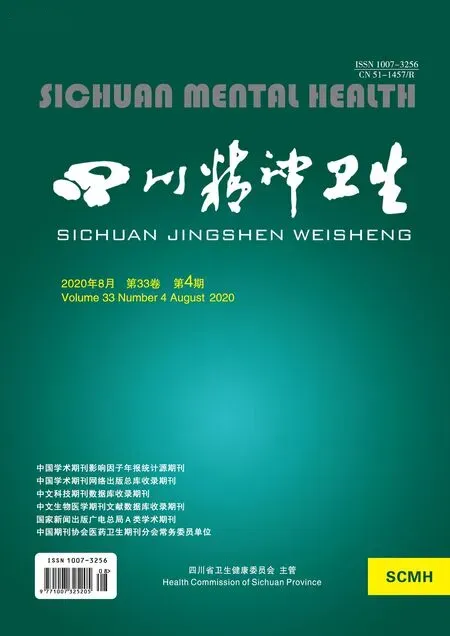伴自伤行为的女性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家庭功能与童年创伤经历的相关性
李雪瑞,张 玲,胡潇予,黄 杰,夏兴文,胡 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 400016*通信作者:胡 华,E-mail:huhuateam@126.com)
抑郁障碍是一类以持续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点的心境障碍,可伴有自伤自杀行为和不同程度的认知改变[1]。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抑郁障碍已经成为全球疾病的主要负担之一[2]。女性抑郁障碍发病率约为男性的2~3倍[3]。目前青少年抑郁障碍及自伤自杀行为已成为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大公共精神卫生问题,抑郁障碍女性青少年有更强的自杀倾向与更频繁的自伤行为[4-5]。童年创伤是指个体在18岁以下的童年及青少年期所经历的单一或多重虐待[6]。既往研究表明,童年创伤是影响抑郁障碍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7],有童年创伤经历的个体更倾向于对各种人际关系做敌意的归因,造成信息偏差[8]。家庭功能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沟通、联系和维持关系以及做出决定解决问题的方式[9]。抑郁障碍患者看待问题的态度倾向于悲观消极,他们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对家庭功能的看法存在差异[10]。患者的预后受其感知的家庭功能的影响,有童年创伤经历的抑郁障碍患者报告更差的家庭功能[11-12]。但目前关于伴自伤行为的女性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家庭功能及与其童年创伤经历的关系并不完全清楚。故本研究通过了解伴自伤行为的女性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所感知的家庭功能特点及其童年创伤经历,并探索其相关性,以期为对患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干预、缓解其抑郁情绪和减少自伤行为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9年3月-9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门诊或住院治疗的、有自伤行为的女性抑郁障碍患者为研究组。入组标准:①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tenth edition,ICD-10)抑郁障碍诊断标准,由两位主治以上职称精神科医师确诊;②女性,年龄13~25岁;③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中自伤行为总频率≥1。排除标准:①患有严重躯体疾病及脑器质性疾病者;②患有其他精神疾病者;③难以完成评估者。符合入组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50例。同期在重庆市区学校及社区招募健康青少年女生作为对照组。入组标准:①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II)评分<14分;②女性,年龄13~25岁。排除标准:①患有严重躯体疾病及脑器质性疾病者;②患有精神疾病者;③难以完成评估者。符合入组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42例。本研究通过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被试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评定工具
采用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筛选出伴自伤行为的抑郁障碍青少年女生,该问卷包括掐伤、抓伤、割伤等12个自我伤害的条目。调查受试对象在过去一年内相关行为发生的频率,累计各种行为的发生频率为总频率,总频率≥1即认为具有自伤行为,该问卷Cronbach'sα系数为0.921[13]。
采用BDI-II评定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抑郁程度。BDI-II共21个条目,采用0~3分4级评分。各条目评分之和为BDI-II总评分,评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严重[14]。该量表 Cronbach'sα系数为0.930[15]。
采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FAD)评定个体对家庭功能的感知。FAD共60个条目,包括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总体功能7个分量表[16-17]。该量表采用4级评分,某一维度评分越高表明该维度的家庭功能越差。中文版FAD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10,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60~0.85[18]。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91。
采用 Bernstein等[19]编制的童年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简化版测量个体的童年创伤经历。赵幸福等[20]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CTQ共28个项目,包括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5个因子。采用5级评分,总评分越高表明受虐待程度越严重。该量表中文版Cronbach'sα系数为0.730,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21]。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37。
1.3 评定方法
由重庆医科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调查前均进行一致性培训。首先由两名精神科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者对患者进行诊断,其诊断一致性达到要求。调查员向受试者介绍本研究的目的和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在不受干扰的独立房间进行量表评定,平均耗时约20 min,问卷当场填写,作答完成后当场收回。调查结束后调查员及时检查问卷,发现遗漏、误填等要求填写者纠正。所有资料由另一调查员审核整理。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3.0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主要采用频率和百分比描述,并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计量资料之间的相关性。以FAD总体功能评分为因变量,以CTQ各因子评分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双侧检验。
2 结 果
2.1 两组一般人口学资料
研究组共50例,年龄(16.90±2.26)岁,核心家庭36人(72.00%),非核心家庭14人(28.00%);对照组共42例,年龄(17.43±3.82)岁,核心家庭35人(83.33%),非核心家庭7人(16.67%)。两组年龄(t=-0.788,P=0.433)及家庭结构(χ2=1.664,P=0.197)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FAD、CTQ及BDI-Ⅱ评分比较
研究组与对照组FDA中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问题解决、总体功能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行为控制分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CTQ中的躯体忽视、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躯体虐待、性虐待、总评分及BDI-Ⅱ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见表1。
表1 两组FAD、CTQ及BDI-Ⅱ评分比较(±s,分)

表1 两组FAD、CTQ及BDI-Ⅱ评分比较(±s,分)
注:FAD,家庭功能评定量表;CTQ,童年创伤问卷;BDI-II,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
组 别FAD评分研究组(n=50)对照组(n=42)t P角色2.47±0.44 2.09±0.42 4.219<0.010情感反应2.81±0.49 2.31±0.48 4.954<0.010情感介入2.58±0.58 2.18±0.53 3.429 0.001问题解决2.48±0.42 2.12±0.44 4.015<0.010行为控制2.39±0.38 2.24±0.42 1.823 0.072总体功能2.48±0.37 2.08±0.38 5.205<0.010组 别BDI-Ⅱ评分34.76±11.08 7.60±4.16 16.039<0.010研究组(n=50)对照组(n=42)t P沟通2.70±0.44 2.21±0.37 5.676<0.010 CTQ评分躯体忽视9.48±3.68 7.10±2.12 3.880<0.010情感虐待9.48±3.68 7.10±2.12 3.880<0.010情感忽视14.30±5.34 10.40±4.63 3.702<0.010躯体虐待9.20±3.83 5.64±1.12 6.258<0.010性虐待6.20±2.61 5.38±0.88 2.081 0.042总评分51.42±15.41 37.52±9.67 5.262<0.010
2.3 研究组CTQ评分与FAD评分相关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研究组FAD的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总体功能评分与CTQ中躯体忽视、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评分均呈正相关(r=0.285~0.677,P<0.05或0.01);FAD的问题解决、沟通、角色、行为控制、总体功能评分与CTQ中躯体虐待和性虐待评分均呈正相关(r=0.232~0.470,P<0.05或0.01)。见表2。
2.4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以FAD的总体功能评分为因变量、CTQ各因子评分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仅情感忽视进入回归方程(β=0.318,t=2.566,P<0.05)。见表3。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FAD的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问题解决、总体功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与杜娜等[22]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发病时,家属往往因患者的情绪状态与自伤行为而处于紧张状态,家庭中信息沟通往往含糊,家庭交流较差,角色任务分工不清与角色任务完成差、对刺激的情感反应过度、相互情感关注程度少、难以相互理解[22],故容易导致患者感知到家庭功能是不健康的。本研究中,研究组和对照组FAD的行为控制维度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杨光远等[23]研究结果一致。患者家庭的行为控制与普通家庭无差异。事实上,即使在无精神障碍患者家庭中,家庭功能在行为控制方面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强调外部权威和服从规则有关[24],家庭难以建立自己的内部权力结构。另外,处于青春期的孩子遇到问题时更倾向于寻求同伴的鼓励与支持,家庭内部沟通频率与质量较低[25],通常难以达成一致的行为规范来应对问题,使家庭呈现忽视而非控制的行为模式。

表2 研究组CTQ评分与FAD评分的相关性(r)

表3 研究组CTQ对家庭总体功能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CTQ各因子评分均较高,说明伴自伤行为的女性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较正常女生在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躯体虐待、躯体忽视和性虐待五个方面均有更明显问题。研究表明,童年创伤可引起更严重的抑郁及更早的抑郁发作,各种形式的高水平童年虐待都与自伤行为的增加有关,且高水平的童年期性虐待、情感忽视与女生自伤行为的关联强度高于男生[26-28]。
相关分析显示,研究组FAD各因子评分与躯体忽视、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评分均呈正相关,问题解决、沟通、角色、行为控制、总体功能评分与躯体虐待、性虐待评分呈正相关。表明伴自伤行为的女性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感知到的家庭功能与其童年创伤经历密切相关,这与Dorrington等[29]研究结果一致。童年创伤经历会影响大脑发育与认知功能[30-31],导致个体对外界信息的感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对各种人际关系更易做出敌意的归因,在生活中更倾向于对自己及周围环境进行消极的评价和解释[8]。家庭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有童年创伤经历的个体对家庭关系互动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家庭环境缺乏凝聚力[32-33]。陈青等[10]研究显示,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与其他家庭成员对家庭功能的看法存在差异,可能是因为其童年创伤经历影响了他们与亲属之间的人际互动,在负性情绪的影响下,感知到的家庭功能更差。
回归分析显示,伴自伤行为的女性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情感忽视评分可以正向预测家庭总体功能评分。研究表明,长期的情感忽视不利于儿童的情感表达,在生活中消极情感评价越高,生活满意度越低[19,34]。本研究中伴自伤行为的女性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由于童年期存在被照料者情感忽视的经历,对正性情感感知较低,感知到的家庭功能健康状况更差,在面对外界压力时,不会主动寻求家庭的支持,更容易产生负性情绪,长此以往出现抑郁情绪和自伤行为。
综上所述,伴自伤行为的女性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存在明显的、多维度的家庭功能损害和多形式的童年创伤,且二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情感忽视可以预测伴自伤行为的女性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感知的家庭总体功能。本研究局限性在于:①只是将伴自伤行为的女性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和健康对照组进行了对比,未与不伴自伤行为的抑郁障碍患者进行比较;②研究样本量较小;③数据均来源于被试的自我报告。未来可优化研究设计,扩大样本量,结合客观研究指标,进一步探讨童年创伤与家庭功能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