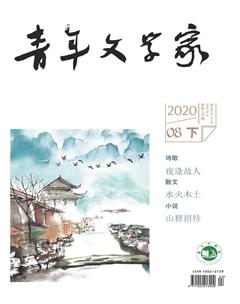《印度合伙人》折射的印度美学意识
摘 要:现实主义题材的宝莱坞电影《印度合伙人》讲述了一位实力宠妻的普通工厂工人力破千难万阻,帮助全印度妇女摆脱经期安全隐患、实现人格独立的励志故事。电影文学与美学一脉相承。影片在题材选择、场景布局、情节规划、叙事手法、人物塑造等方面流露出的思想意识,无形中与印度传统美学相契合。
关键词:印度美学;电影文学;印度合伙人
作者简介:胡倩(1996-),女,汉族,湖北宜昌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文艺学专业文艺学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2
引言:
美学家托马斯·门罗指出:“印度美学史是印度哲学与宗教史中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着力于研究印度美学,就必然绕不开印度宗教哲学。分析影片《印度合伙人》在题材设置、情节规划、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安排,能够发掘由此折射的印度美学意识。
一、题材设置与场景布局
(一)“符号真实”——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
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上,印度古典美学家一致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艺术美是现实美的再现。泰戈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学事业是创作主体“把内心感受幻化为外部图景,把情绪感触孵化为语言符号,把短暂事物化为永恒记忆,以及把自己的心灵真实变成人类的真实感受”的产物。总而言之,印度美学将艺术形象视为生活中实体形象的替代品,由此呈现出的真实仅仅属于虚假的真实。影片以印度卫生巾之父阿鲁纳恰拉姆为原型,所反映的印度女性生理期卫生状况,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贫富差距、性别歧视等问题,印证当下印度社会现实。但影片中印度卫生巾之父变成拉克希米,并非阿鲁纳恰拉姆本人,原有遭遇也因电影所需艺术化表达而掺入大量虚构成分,成为真实人物的“影子”。艺术形象“以假乱真”多归结于艺术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主客体双方因默契化体验而形成的固有思维习惯,但究其本质,它只是对现实的模仿,而绝非现实本身。
(二)去工业化——对自然的依恋与敬畏
原始社会受生产力水平所限,横生的自然灾害得不到合理化解释,人们对自然不由产生神秘和敬畏之情,在神话中赋予自然以神的形象,由此形成早期自然崇拜。此外,印度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遭到自然环境的规约,人们有意识地保护自然生态。公元4-5世纪,印度就出台了相关法律条文:“不必要的损坏种植的或者野生的植物者,必须牧一天母牛,吃牛奶斋。”受原始思维与社会形态的双重影响,人与自然应当始终保持亲近和谐关系的观念在印度人民头脑中不断积淀,形成相对稳定的民族意识形态。印度艺术与美学多借助自然元素,显现出崇尚自然的独特品格。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农村,场景布局较少显露现代高科技的痕迹,呈现出“去工业化”特质。移动电话没有普及,报纸是连接村庄与外部世界的重要媒介,自行车是出行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加之传统的印度民居、悠闲的生活方式、如画的自然景观,构成和谐的田园牧歌式生活。
(三)装饰用色——“庄严”为美
“庄严”意为装饰或修辞,目的在于美化客观对象,是印度古典美学家在装饰主义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提出的一种美的艺术形式,而后成为印度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印度古代一批学者因重文辞、尚庄严的创作理念共性形成“庄严论”派,其中创作以檀丁的《诗境》、婆摩诃的《庄严论》最具代表性。随后,“庄严”理论不仅作用于印度诗歌,在诸多艺术形式都有鲜明体现,现代电影文学也不例外。影片在人物服装的配色、节日欢庆场面的刻画上呈现出“庄严”美特征。由人物显现的“庄严”主要体现在女性角色上,剧中女性服装大多艳丽且色彩繁多,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除服饰外,妇女还佩戴琳琅满目的装饰物,诸如耳饰、鼻饰、项圈、手镯、腰带、脚钏,种类丰富、制作精细。通过以上装扮,女性形象更加美丽夺目,耀眼迷人。在节日欢庆场面,如女孩成人礼片段,运用色彩叠加,在人群纵情欢乐、载歌载舞的过程中,烘托出喜庆气氛,“庄严”之美应运而生。
二、叙事手法与情节规划
(一)弱化剧烈冲突——消解严格意义上的悲剧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首创悲剧概念,指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陶冶。”后世学者大多在此基础上延展。受悲剧理论影响,希腊悲剧与近代西方悲剧往往表现为斗争双方因不可磨灭的矛盾冲突,致使一方或双方遭受失败或毁灭,由此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刺激。就悲剧冲突的美学性质而言,它不应当是矛盾的调和,而印度悲剧卻惯于在激烈的冲突过后安排大团圆结局,呈现出反悲剧性特征。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中,《持斧罗摩》和《那罗和达摩衍蒂》等故事充分体现出印度民族悲剧精神。在此后的文艺作品中,真正的悲剧也多让位于单纯的苦难故事或将结局美化为矛盾调和后的和谐幸福生活。影片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展现出双重悲剧美学意蕴,集中表现为拉克希米的觉醒意识与全村人愚昧思想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帕里爱而不得的情感悲剧。拉克希米担忧妻子经期健康,萌发制作廉价卫生巾的想法,却被小镇村民视为异类。当试验在小镇广场失败,双方的矛盾冲突达到顶峰,后因拉克希米出走随之中道而止,由此淡化悲剧色彩。此外,拉克希米与合伙人帕丽在创业过程中互生情愫,但“帕拉恋”自始就暗示着不完整的悲剧结局,这场爱情悲剧最终因帕丽的主动退出得到消解,而使得故事更具浪漫主义色彩。
(二)宗教崇拜——神猴哈奴曼揭示印度崇高美
影片在叙述中有意安排了一个情节:集会上,一尊名为哈奴曼的神猴塑像被视为力量之神,人们争相捐款祈求庇佑。印度神猴崇拜由来已久,直至当今印度街头,乃至寻常百姓人家都普遍供有哈奴曼的塑像或画像。哈奴曼形象最早可追溯至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神猴哈奴曼为风神之子,相貌乖张,力大无穷,能腾云驾雾、随意变身,帮助阿逾陀国王子罗摩征服楞枷城十头魔王罗波那,获得战争的胜利,并救出被劫走的罗摩之妻悉多。文学现象与美学、宗教意识形态联系密切,印度人民将哈奴曼尊奉为地方神,反映出民众思想信仰和道德教义,也显露出民众对美的认知,即“把那种超常的、有巨大能量的、永恒不变的东西看作美”。这种崇高的审美观源于古代印度人民从太阳、火、狂风、暴雨等自然现象中所感知到的无限性。
三、形象塑造与精神超脱
(一)外在形象——人体“美”的标准
《奥义书》提出“梵”的概念,并指出“梵”通过思维、意念创造万物。美由万物派生,层次上分为本体之美与现象界之美。本体之美即梵之美,在这一层次美丑无差别。现象界之美,体现为分有或显现梵性的生命之美和引起感官刺激而使人愉悅的物欲之美,因主观意识介入而具美、丑之分。人体美属于现象界之美,审美主体差异性导致审美评价和判断千差万别。民族内部因血统与生存空间的相似性,审美心理又呈现出趋同性与相对稳定性。文学创作暗含人体美丑判断标准,女性人体美如《罗摩衍那》中对悉多的描绘:“她面如满月眉毛美,乳房娇嫩又丰满……”男性人体美如罗摩“胸膛像狮子,胳膊长,两只眼睛像荷花瓣一样,非常优雅,品质高尚……”印度民族显现出“以形式上的匀称、适度,即符合比例为美;以合人体美规律的青春健康和性感的肉体为美;以光亮的眼睛和亮泽的皮肤为美;以女性优雅的风度和内心的善良为美”的人体审美观。影片中拉克希米的饰演者阿克谢·库马尔体格匀称,肤色亮泽,不仅拥有俊俏面孔和健硕身型,同时具备迷人微笑和深邃眼神,加之其雄厚的表演功底,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流量明星”。此外在盖特丽、帕丽等角色的演员选取上,同样符合印度民族所推崇的人体形式美规律。
(二)他者同情——“情味”论的逻辑起点
受原始思维影响,印度人认为“众生有情”,将人与万物同归于“有生类”,并通过“以己度物”的方式赋予外物以人的感知能力,人、兽、物三者的界限逐渐趋于模糊。此思想被概括为“万物有情论”,对印度文学惯于把一切有情物作为艺术表现对象来渲染情感的做法产生重要影响,为古典主义“情味论”奠定基础。“情味论”旨在探讨审美情感效应,艺术中的情感被归结为八种常情和三十三种不定情。常情衍生出“味”,类似于“共鸣”,是接受主体被唤起的人类共同的审美情感效应。拥有共同的审美心理结构,有情众生都能“感同身受”。影片从日常小事引入,巧妙通过男性视角阐释女性问题,显现出“他者同情”。运用艺术手段,在揭露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男女地位差异和民族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激发出接受主体处于潜伏状态的“常情”,观众和欣赏者通过观影体验,与角色产生情感互通。
(三)人格理想——抒发个体性灵美
《奥义书》在论及美的形态时,将美划分为优美、崇高美、精神美与境界美,其中所涉及的精神美是主体由于心灵的纤尘不染,不受情欲纠缠而显现出的性灵美,表现为人格力量的伟大超常,如仁慈豁达的胸怀、追求正义的信念、舍身奉献的精神、锲而不舍的态度、超乎常人的毅力……印度美学中关于人格理想的阐述在此基础上得以建构。思维决定存在,艺术作品在塑造人物时,少不了对个体性灵美的揭露。影片中拉克希米受巴沙坎先生一席演讲鼓舞,立志于为全印度消费不起护垫的五亿妇女提供廉价卫生巾,实现“小我”向“大我”的转变。推广中,他还意识到女性应摆脱贫困、获得独立人格与价值。至此,原有目标升级为帮助妇女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作为“小人物”,拉克希米遭受诋毁与谩骂、忍受贫困与孤独,却始终不忘初心,在一次次自我寻找与确证过程中实现人性的升华,彰显出崇高的人格魅力。
《印度合伙人》在题材选择、情节安排、人物塑造等方面,既体现独特个性,又揭露印度电影文学的共性特征。由故事内容、人物内涵、民俗风情所呈现的印度式表达,折射出印度传统美学意蕴,在文化身份与民族精神的认知中,印度美学内涵得到充分彰显。
参考文献:
[1]托马斯·门罗著,欧建平译.东方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2]泰戈尔著,倪培耕等译.泰戈尔文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蒋忠新译.摩奴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邱紫华、王文戈.东方美学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印)蚁蛭著、季羡林译.罗摩衍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摘 要:现实主义题材的宝莱坞电影《印度合伙人》讲述了一位实力宠妻的普通工厂工人力破千难万阻,帮助全印度妇女摆脱经期安全隐患、实现人格独立的励志故事。电影文学与美学一脉相承。影片在题材选择、场景布局、情节规划、叙事手法、人物塑造等方面流露出的思想意识,无形中与印度传统美学相契合。
关键词:印度美学;电影文学;印度合伙人
作者简介:胡倩(1996-),女,汉族,湖北宜昌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文艺学专业文艺学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2
引言:
美学家托马斯·门罗指出:“印度美学史是印度哲学与宗教史中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着力于研究印度美学,就必然绕不开印度宗教哲学。分析影片《印度合伙人》在题材设置、情节规划、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安排,能够发掘由此折射的印度美学意识。
一、题材设置与场景布局
(一)“符号真实”——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
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上,印度古典美学家一致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艺术美是现实美的再现。泰戈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学事业是创作主体“把内心感受幻化为外部图景,把情绪感触孵化为语言符号,把短暂事物化为永恒记忆,以及把自己的心灵真实变成人类的真实感受”的产物。总而言之,印度美学将艺术形象视为生活中实体形象的替代品,由此呈现出的真实仅仅属于虚假的真实。影片以印度卫生巾之父阿鲁纳恰拉姆为原型,所反映的印度女性生理期卫生状况,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贫富差距、性别歧视等问题,印证当下印度社会现实。但影片中印度卫生巾之父变成拉克希米,并非阿鲁纳恰拉姆本人,原有遭遇也因电影所需艺术化表达而掺入大量虚构成分,成为真实人物的“影子”。艺术形象“以假乱真”多归结于艺术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主客体双方因默契化体验而形成的固有思维习惯,但究其本质,它只是对现实的模仿,而绝非现实本身。
(二)去工业化——对自然的依恋与敬畏
原始社会受生产力水平所限,横生的自然灾害得不到合理化解释,人们对自然不由產生神秘和敬畏之情,在神话中赋予自然以神的形象,由此形成早期自然崇拜。此外,印度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遭到自然环境的规约,人们有意识地保护自然生态。公元4-5世纪,印度就出台了相关法律条文:“不必要的损坏种植的或者野生的植物者,必须牧一天母牛,吃牛奶斋。”受原始思维与社会形态的双重影响,人与自然应当始终保持亲近和谐关系的观念在印度人民头脑中不断积淀,形成相对稳定的民族意识形态。印度艺术与美学多借助自然元素,显现出崇尚自然的独特品格。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农村,场景布局较少显露现代高科技的痕迹,呈现出“去工业化”特质。移动电话没有普及,报纸是连接村庄与外部世界的重要媒介,自行车是出行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加之传统的印度民居、悠闲的生活方式、如画的自然景观,构成和谐的田园牧歌式生活。
(三)装饰用色——“庄严”为美
“庄严”意为装饰或修辞,目的在于美化客观对象,是印度古典美学家在装饰主义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提出的一种美的艺术形式,而后成为印度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印度古代一批学者因重文辞、尚庄严的创作理念共性形成“庄严论”派,其中创作以檀丁的《诗境》、婆摩诃的《庄严论》最具代表性。随后,“庄严”理论不仅作用于印度诗歌,在诸多艺术形式都有鲜明体现,现代电影文学也不例外。影片在人物服装的配色、节日欢庆场面的刻画上呈现出“庄严”美特征。由人物显现的“庄严”主要体现在女性角色上,剧中女性服装大多艳丽且色彩繁多,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除服饰外,妇女还佩戴琳琅满目的装饰物,诸如耳饰、鼻饰、项圈、手镯、腰带、脚钏,种类丰富、制作精细。通过以上装扮,女性形象更加美丽夺目,耀眼迷人。在节日欢庆场面,如女孩成人礼片段,运用色彩叠加,在人群纵情欢乐、载歌载舞的过程中,烘托出喜庆气氛,“庄严”之美应运而生。
二、叙事手法与情节规划
(一)弱化剧烈冲突——消解严格意义上的悲剧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首创悲剧概念,指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陶冶。”后世学者大多在此基础上延展。受悲剧理论影响,希腊悲剧与近代西方悲剧往往表现为斗争双方因不可磨灭的矛盾冲突,致使一方或双方遭受失败或毁灭,由此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刺激。就悲剧冲突的美学性质而言,它不应当是矛盾的调和,而印度悲剧却惯于在激烈的冲突过后安排大团圆结局,呈现出反悲剧性特征。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中,《持斧罗摩》和《那罗和达摩衍蒂》等故事充分体现出印度民族悲剧精神。在此后的文艺作品中,真正的悲剧也多让位于单纯的苦难故事或将结局美化为矛盾调和后的和谐幸福生活。影片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展现出双重悲剧美学意蕴,集中表现为拉克希米的觉醒意识与全村人愚昧思想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帕里爱而不得的情感悲剧。拉克希米担忧妻子经期健康,萌发制作廉价卫生巾的想法,却被小镇村民视为异类。当试验在小镇广场失败,双方的矛盾冲突达到顶峰,后因拉克希米出走随之中道而止,由此淡化悲剧色彩。此外,拉克希米与合伙人帕丽在创业过程中互生情愫,但“帕拉恋”自始就暗示着不完整的悲剧结局,这场爱情悲剧最终因帕丽的主动退出得到消解,而使得故事更具浪漫主义色彩。
(二)宗教崇拜——神猴哈奴曼揭示印度崇高美
影片在叙述中有意安排了一个情节:集会上,一尊名为哈奴曼的神猴塑像被视为力量之神,人们争相捐款祈求庇佑。印度神猴崇拜由来已久,直至当今印度街头,乃至寻常百姓人家都普遍供有哈奴曼的塑像或画像。哈奴曼形象最早可追溯至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神猴哈奴曼为风神之子,相貌乖张,力大无穷,能腾云驾雾、随意变身,帮助阿逾陀国王子罗摩征服楞枷城十头魔王罗波那,获得战争的胜利,并救出被劫走的罗摩之妻悉多。文学现象与美学、宗教意识形态联系密切,印度人民将哈奴曼尊奉为地方神,反映出民众思想信仰和道德教义,也显露出民众对美的认知,即“把那种超常的、有巨大能量的、永恒不变的东西看作美”。这种崇高的审美观源于古代印度人民从太阳、火、狂风、暴雨等自然现象中所感知到的无限性。
三、形象塑造与精神超脱
(一)外在形象——人体“美”的标准
《奥义书》提出“梵”的概念,并指出“梵”通过思维、意念创造万物。美由万物派生,层次上分为本体之美与现象界之美。本体之美即梵之美,在这一层次美丑无差别。现象界之美,体现为分有或显现梵性的生命之美和引起感官刺激而使人愉悦的物欲之美,因主观意识介入而具美、丑之分。人体美属于现象界之美,审美主体差异性导致审美评价和判断千差万别。民族内部因血统与生存空间的相似性,审美心理又呈现出趋同性与相对稳定性。文学创作暗含人体美丑判断标准,女性人体美如《罗摩衍那》中对悉多的描绘:“她面如满月眉毛美,乳房娇嫩又丰满……”男性人体美如罗摩“胸膛像狮子,胳膊长,两只眼睛像荷花瓣一样,非常优雅,品質高尚……”印度民族显现出“以形式上的匀称、适度,即符合比例为美;以合人体美规律的青春健康和性感的肉体为美;以光亮的眼睛和亮泽的皮肤为美;以女性优雅的风度和内心的善良为美”的人体审美观。影片中拉克希米的饰演者阿克谢·库马尔体格匀称,肤色亮泽,不仅拥有俊俏面孔和健硕身型,同时具备迷人微笑和深邃眼神,加之其雄厚的表演功底,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流量明星”。此外在盖特丽、帕丽等角色的演员选取上,同样符合印度民族所推崇的人体形式美规律。
(二)他者同情——“情味”论的逻辑起点
受原始思维影响,印度人认为“众生有情”,将人与万物同归于“有生类”,并通过“以己度物”的方式赋予外物以人的感知能力,人、兽、物三者的界限逐渐趋于模糊。此思想被概括为“万物有情论”,对印度文学惯于把一切有情物作为艺术表现对象来渲染情感的做法产生重要影响,为古典主义“情味论”奠定基础。“情味论”旨在探讨审美情感效应,艺术中的情感被归结为八种常情和三十三种不定情。常情衍生出“味”,类似于“共鸣”,是接受主体被唤起的人类共同的审美情感效应。拥有共同的审美心理结构,有情众生都能“感同身受”。影片从日常小事引入,巧妙通过男性视角阐释女性问题,显现出“他者同情”。运用艺术手段,在揭露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男女地位差异和民族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激发出接受主体处于潜伏状态的“常情”,观众和欣赏者通过观影体验,与角色产生情感互通。
(三)人格理想——抒发个体性灵美
《奥义书》在论及美的形态时,将美划分为优美、崇高美、精神美与境界美,其中所涉及的精神美是主体由于心灵的纤尘不染,不受情欲纠缠而显现出的性灵美,表现为人格力量的伟大超常,如仁慈豁达的胸怀、追求正义的信念、舍身奉献的精神、锲而不舍的态度、超乎常人的毅力……印度美学中关于人格理想的阐述在此基础上得以建构。思维决定存在,艺术作品在塑造人物时,少不了对个体性灵美的揭露。影片中拉克希米受巴沙坎先生一席演讲鼓舞,立志于为全印度消费不起护垫的五亿妇女提供廉价卫生巾,实现“小我”向“大我”的转变。推广中,他还意识到女性应摆脱贫困、获得独立人格与价值。至此,原有目标升级为帮助妇女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作为“小人物”,拉克希米遭受诋毁与谩骂、忍受贫困与孤独,却始终不忘初心,在一次次自我寻找与确证过程中实现人性的升华,彰显出崇高的人格魅力。
《印度合伙人》在题材选择、情节安排、人物塑造等方面,既体现独特个性,又揭露印度电影文学的共性特征。由故事内容、人物内涵、民俗风情所呈现的印度式表达,折射出印度传统美学意蕴,在文化身份与民族精神的认知中,印度美学内涵得到充分彰显。
参考文献:
[1]托马斯·门罗著,欧建平译.东方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2]泰戈尔著,倪培耕等译.泰戈尔文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蒋忠新译.摩奴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邱紫华、王文戈.东方美学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印)蚁蛭著、季羡林译.罗摩衍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