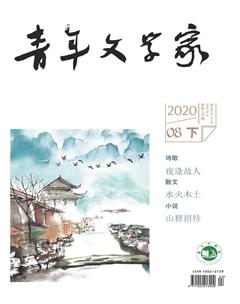废名“诗的内容”新诗创作观新探
摘 要:废名的诗学理论中“诗的内容”内含十分丰富,在“当下性”与“完全性”的基础上,废名对于诗人的创作精神要求自由大胆、不拘一格,突显新诗应有的生命意志和自由精神;在想象上,诗人应从质朴的生活中写出自我的真性情;同时在内容与情感上兼具旧诗所具有的“普遍性”与新诗“個性化”的因素,实现诗情的自然流动与诗意世界的创造。这种新诗观念不仅对于早期的新诗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并且对当下诗歌的健康发展同样有着可贵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废名;新诗;诗的内容;创作;想象
作者简介:李佳铭(1996.6-),女,陕西西安人,硕士,武汉大学文学院2018级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04
废名的诗论专著《谈新诗》的价值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自九十年代起至今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批评家们对废名的诗歌创作理论从多个角度出发进行了探讨。九十年代,如王泽龙从“禅”理的角度理解废名诗歌的风格与蕴含[1];孙玉石从废名新诗观与古典诗学的关联进行了阐释[2]等等;进入二十世纪,张洁宇认为废名在打破新诗传统与现代间隔离的关系上有重要作用[3],陈建军则从废名与胡适新诗理论的对比中看其对后者的超越性[4]。评论界对废名的诗与诗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与剖析,在“诗的内容”与“散文的文字”这一框架之下从各个角度发掘其独特的诗学内涵。
然而以往的评论家在对 “诗的内容”进行阐释时,多是从“当下性”与“完全性”的角度出发,因而尽管对这二者展开了多层次的分析与较深入的挖掘,但仍给后来的读者与创作者一种虽有合理性,但却空泛、矛盾、无法运用其理论进行具体实践之感,这是因为在“诗的内容”这一概念中除了“当下性”与“完全性”之外,废名对诗人的创作精神、想象与质朴的关系、普遍与个性的关系也有不同程度的要求。本文中,笔者将围绕这些为以往评论家所忽略的部分展开,对废名“诗的内容”进行补充阐释。
一、诗人的创作精神
在《新诗应是自由诗》一章中,废名说到“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诗一定要表现着一个诗的内容,有了这个诗的内容,然后‘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5]废名在这里谈到的“自由诗”是针对西洋的“散文诗”而言的,表面上是指包含“诗的内容”,用“散文的文字”进行创作的诗歌,即从形式上来说包含了与现代格律诗相区别的自由体诗以及四行诗、十四行诗等有规律体的诗歌。但笔者认为废名在这里所讲的“自由诗”除了形式上自由之外,更多的是从一种创作者的精神,即创作意识、创作姿态上所进行的评判。
这一点从废名对冰心、郭沫若二人诗歌创作的评价上也可以看出。废名把冰心、郭沫若的诗归入“新诗的第二期”[6],他认为,以胡适为代表的初期新诗尽管有一个“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要怎样做就怎么样做”的自由作诗的理念,但对于诗歌在形式上、字词上的要求过多,即如废名所说“然而在这个‘自由里头无形中有一个但是——但不得做旧诗”[7],初期的新诗是把用文言文写成、强调格律形式的“旧诗”当作死敌的。
到了新诗的第二期,新诗反而与曾经的“敌人”有了“交情”,因此变得更加的自由。“他们的面前是他们自己的‘诗,在诗之国里岂有敌人,古今中外的诗人都可以旦暮遇之,新诗的诗的生命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起点,因其诗情泛滥,乃有诗文字之不中绳墨,——试问诗情泛滥是一件容易事吗?恐怕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8]废名在此所讲的“自己的诗”“诗情泛滥”建立在其一以贯之的“诗的内容”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但不同在于,这里更多强调的是对于诗歌创作一种全然投入、不受拘束的精神状态。黄遵宪曾提出“以我手写我口”的诗歌理念,也被认为是早期白话新诗观念的滥觞,但到二三十年代的诗坛,诗人的诗歌创作在废名看来却渐渐偏离了应有的轨道,这点从废名指斥新月派在形式上大做文章,流于铺排,大闹格律勾当[9]的弊病中可以看出。因而,冰心与郭沫若的诗歌创作给废名带来一种眼前一亮之感,“他们做诗已经离开了新旧诗斗争的阶级,他们自己的诗空气吹动起来了,他们简直有了一个诗情的泛滥。”[10]
郭沫若与冰心在诗歌创作中的这种表现与废名格外推崇的温庭筠词、李商隐诗中近乎“乱写”的“自由表现”有种高度契合,废名十分钟情温李在诗词中天马横空式的“乱写”,这固然是由于其诗词里有可供新诗汲取的“营养”,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乱写”所饱含的自由开阔的气度值得新诗创作者学习借鉴。从诗歌精神的自由度来说,温李这些“当初新文学运动者所排斥的古典派”的创作精神,“倒有我们今日新诗的趋势”[11]了。
在废名看来,判断一首诗歌好坏的首要标准就是其情感是否饱满,同时是否具有偶然性——非刻意为之的造作。废名对郭沫若无名小诗《夕暮》做出这样的评价:“是新诗的杰作,如果中国的新诗只准我选一首,我只好选它,因为它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12];而在废名给出较高评价的其他诗歌的评语中也可常常见到如下词汇:新鲜、质朴、自然、生气……这些特质归结起来,即是诗人的诗情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解放,真正实现了当下情绪的自然流动,获得了自由。因此,当废名说,温李“这一派的诗词存在的根据或者正有我们今日白话诗发展的根据”[13]时,他所期待的并不仅是新诗简单地从意象、意境和情调等方面回到古典中去,而是学习和领悟温李在进行诗歌创造时所有的某种自由而大胆的精神。“我说自由,是说他们做诗的态度,他们真是无所为而为的做诗了,他们又真是诗要怎么做便怎么做了。”[14],而用林庚的话来说,“‘自由非形式之自由,而是表现之自由。[15]”。废名在“诗的内容”理论下进一步提出的“自由诗”的概念不只是在外在诗体形式上的自由,更多是从创作精神层面对新诗现代品格提出的一种诉求。
二、想象与质朴的关系
新诗初期,大多诗人只注意到文学革命中新诗语言的革新,结果只顾关注一首诗歌是否是用白话创作的,而忘记了诗缘何成诗的本质,因而偏离了创作的轨道,为人所诟病。而废名则从对温李诗词的推崇中力图纠正这一问题,他说“温李的诗在盛唐诗高度发展之后,能夠‘于唐人中别开一境,这主要表现,是他们的诗突破了旧诗情生文文生情的局限,而能够充分驰骋他们的幻想和想象,在他们所创造的‘超乎一般旧诗的表现的诗的世界里,极大地增强了诗的素质和内容。”[16]废名深受西方现代派诗风的影响,崇尚意象的跳跃和诗意的蕴藉,同时,深厚的国学底蕴又使他自然地承传了中国传统诗歌追求意境要朦胧含蓄的诗学主张,所以废名的新诗观兼有中西诗学之长,认为新诗是诗人想象的结果,诗人不受约束的自由想象促成诗歌的含蓄和朦胧美。
废名在《十四行集》一章中说到:“新诗不同旧诗一样谁都可以做诗了……因为旧诗有形式,有谱子,谁都可以照填的,它只有作文的工巧,没有离开散文的情调,将散文的内容谱成诗便是诗的情调了。不懂得新诗与旧诗的性质,徒徒雷同做新诗,以为新诗也总有形式。”[17]废名批判了那些以为新诗创作毫无门槛的言论,他认为好的新诗比之旧诗而言更有写作的难度,要想将新诗做的自然,便要在新诗之中张弛想象,同时具备形象美与意境美,给读者留下能解读的余地与可解读的空间。“古典派是以典故以辞藻驰骋想象”[18],“今日的新诗也无非是有想象罢了。今日新诗的生命便是诗人想象的跳动,感觉的灵敏,凡属现实都是它的材料……”[19]。废名将旧诗中温李一派的想象性特点移植到新诗上,既是看到了想象对于诗意的重要性,也是为了借此弘扬新诗的“自由表现”。[20]废名以为,新诗是诗人想象的结果,在其评价标准中,具有想象性的诗歌才可称为真正的新诗,诗人不受约束的自由想象促成诗歌的含蓄和朦胧美,这是今天新诗所必要的,而也正是因为新诗中有诗人充满自由的丰富的想象,才得以与以往的旧诗区别开来,是旧诗中所“装不下的”[21],这也与废名对于诗歌应“自由”的观念是一致的。
如上文笔者所说,废名的诗歌理论主张写诗要符合诗人主观情感的真实,将感受到的“诗意”如实地表达出来,不伪装,不造作。在评价卞之琳《航海》一诗时,他说到:“我是喜欢写实的,童话也是写实,故我喜欢。童话而是写实者,如瓦特之弄开水壶是也。卞之琳的诗即是如此,他的幻想好像是思想家,不,他诗人了。他能像打糖锣的一样,令我像一个小孩子给他吸引去了。”[22]在评价卞之琳《倦》一诗时,他亦有“我前说唯其写实乃有神秘者,因为你看见的东西我不一定看见,我看见的东西你不一定看见,写出来每每不在意中也,故神秘的很。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们说他写得自然,其实神秘的很。”[23]的观点。
废名在此即是说想象并非是用过于难懂而艰涩的意象为读者的解读设置人为的障碍,相反却是从日常生活里介入想象,从最质朴的事物中找到创作的灵感,而并非将想象束之高阁。读者无法解读的想象便是繁琐意象的堆叠与铺陈,这样的诗歌写作看似有难度实则毫无意义,而好的新诗,其想象应当在接近生活的基础上有所抽离,新鲜得难以模仿。作者将情感与思绪凝聚在诗歌所选取的意象之中,本身就具有一种含蓄美,同时也为读者在进行解读时提供了开放与自由的空间,正是这种开放的空间使不同的读者在接触诗歌时得以产生不同的联想。在废名关于“想象”的诗歌理念中本身就包含“质朴”的因素,后者更多指的是诗人的创作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情感,因此其与“想象”并非矛盾对立的,彼此并不冲突,并且,一首新诗要写得成功,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
以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为例,废名对这首诗的评价是“这首诗很不容易写。……心想这首诗倒要读他一遍,一读却一口气把他读完了。我说一口气把他读完了,正是我称赞这首诗的意思,正是这首诗的真实,令人心悦诚服。现在我因为读了《扬鞭集》之后,又觉得这首诗写得真实,是当然的。诗人刘半农原是很结实的人物。”[24]且不管这首诗歌里的“她”到底是指某位女性还是祖国,笔者认为废名在评价此诗时所用的“真实”并非是与虚假对应的那重含义,而是指刘半农在完成“思念”这样一个颇为俗气的题材时,其传递的情感是真挚的,没有流于大众化的、表面的情爱字眼,而是采用一种与读者心意相通,走入读者内心的表达方式娓娓道来。刘半农的这首诗并非没有想象,并非只是用平铺直叙的直白口吻写成的,相反,里面频繁地运用比喻、排比、反问、象征等手法来渲染氛围。“这首诗运用了传统歌谣的复迭手法,他在构思技巧上虽继承了传统的反复与比兴手法,但在语言运用上却是生动活泼的,在意境上是新鲜别致的,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且余意不尽,余韵悠然。”[25]即也是在说虽然在语言形式上作者采用了铺排的形式,但这种铺排是建立在感情之上的,前者只是抒情的工具与手段,而并非目的,诗歌本质的特点仍是质朴。
同样的评价还见于废名评价刘半农的《小诗》中,“像这首《小诗》,很不容易写好,作者却写得恰好,甚不易得。这正是作者的性情好,故能将一个难得表现合式的感情很朴质的表现着了。这种情感原是很平常的,人人可有的,要表现着平常生活的情感却最见性情,见学问。”[26]运用艰涩难懂的意象进行铺排的想象看似有难度,实则只是词语的堆砌,形式上的难度可以通过学习技巧来实现,而真正好的新诗要做到的则是借想象写出自我真性情,蕴含在诗中的感情敦厚饱满,且这种感情虽是最平常最质朴的,但仍种下一粒新生的种子,并非浮于表面,而是结实地生长在诗人自身与每位读者的心里。
三、普遍性与个性化的关系
废名在《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一章中说到:“新诗能够使读者读之觉得好,然后普遍与个性二事俱全,才是白话新诗的成功。普遍与个性二事俱全,本来是一切文学的条件,白话新诗又何能独有优待条件。”即认为一首新诗要获得成功,应当实现“普遍”与“个性”间的平衡[27],这代表他的新诗理论往更深的层面进行了推进。
废名在评价冰心的《春水》第一六四首时说到“冰心女士的新诗太是散文的写法,虽然写着那么的近乎旧诗的句子。……像这样‘将离别的情绪,如果变幻一下,应该就是中国古代诗人创造诗的过程,然而新诗的生命自然是一个直接的书写。这一点正是冰心女士的新诗在新诗历史上的意义,它表现新诗的个性,缺乏诗的普遍性,——如果意识到这个普遍性,冰心女士新诗的生命应是旧诗的题材了。”[28]从这里可以看出,废名认为普遍性是对无论旧诗或新诗皆有的要求,但对旧诗而言满足普遍性是其成功的基础,而新诗虽也要求普遍性,但一定程度的缺乏却也是新诗的独特之处,是区别于旧诗的标志之一。
然而,在谈到郭沫若的《偶成》时废名却认为作者不应当在末尾加上“儿在怀中睡着了”,“这首诗的情景恐怕很好,但诗却写得不成功,因为第四句一件偶然的事情,不足以构成诗的普遍性。”[29]即是认为以此句作结与前面“月在我头上舒波/海在我脚下喧腾/我站在海上的危崖”三句诗所体现的浑然的意境与一致的场景相比,后边是独立于普遍情境之外的偶然事件,这句诗的出现使得诗歌营造的意境氛围与创造的整体形象遭到了破坏。不过,废名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即“所以诗有时还是要‘做出来的,不只是写出来的。”侯桂新认为废名之所以提出这一方法,乃是因为“‘表现个性‘当下关物与‘普遍性的要求之间,便产生了一点隐含的矛盾。”[30]
废名还举出刘半农的《母亲》,将其与《偶成》“黄昏时孩子们倦着睡着了/后院月光下,静静的水声/是母亲替他们在洗衣裳”进行对比,他说到“这首诗所写的情景,读者自然不问是描写当时实在的情景或者不是的,即因为这首诗有诗的普遍性。这首诗不能不说是‘做出来的。郭沫若的《偶成》确是写出来的。”[31]倦睡的孩子,皎洁的月光,静静的母亲的洗衣裳,所有的内容包含在这个情境中是如此和谐,这就是一个整一的形象。
废名在这里所谈到的“普遍性”实际涉及到新诗创作取材与整合的问题,在“《冰心诗集》”一章中他说到“我们从新诗人的诗的创造性又可以知道古代诗人的创造性,旧诗到后来失掉了生命徒有躯壳的存在,而这个诗的生命反而在新诗里发见,这些关系都是无形中起来的,理会得这个关系乃见出新诗发展的意义。”[32]新诗相比旧诗,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所变化,而最重要的还是内容上的变化。废名虽不提倡以“新诗是旧诗的进步”的观点来看新诗,但关键是他围绕“进步”这一命题谈到的“这是诗的内容的变化,这变化是一定的,這正是时代的精神”[33]。新诗比之旧诗虽然从形式上、口语化上、用典上为当时采取保守态度的学者所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真正的新诗在精神内容上确与旧诗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
“旧诗人拿着典故尚且应用无穷,何况新诗是以新鲜的世界为材料呢?”[34]比之旧诗,新诗当然可以沿袭其“一以贯之”的创作方法,在诗歌中力图去呈现一个浑然完整的世界,但这样便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模仿与接续,而并非一种全新的创造,也自然不会把新诗引到一条健康而自然发展的道路上去。新诗比之旧诗若只是在语言与形式上做到了什么革新,在意象的使用上比旧诗有什么突破的地方,那并不足为新,新诗之“新”更在于其传递出的一种全新的创作理念,全新的思想。这也便回到了新文化运动本身的意义——借文学的革新启蒙大众。既然为新诗,以前那些封建的、顽固的、守旧的思想自然不能出现在新诗中,否则只是“旧瓶装新酒”,并无什么实质的意义与价值。同时,新思想要借新诗来展现,达到传播的目的当然要在内容上与旧诗有所区别,笔者认为这也是废名所提出的新诗“诗的内容”区别于旧诗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而真正好的新诗并不只是在传统与现代间做一种简单的加减法,绝不是从两个方面的语言、意象、形式等各选取一些因素融化在一首作品中,也不是局部地寻找一些可用的材料强行将二者弥合,而是基于认真且开放地去考察旧诗所具有的“普遍性”的基础上,同时带着现代人独具“个性化”的眼光和思考去完成一首诗歌的创造,体现在作品中也许只是结尾那一句“儿在怀中睡着了”,但背后所包含的却是从“以新鲜的世界为材料”出发的,对于新诗普遍性与个性化问题的平衡,这也便是废名在书中所说的“新诗发展的意义”所在。
四、小结
废名的诗学理论中“诗的内容”内含十分丰富,在“当下性”与“完全性”的基础上,废名对于诗人的创作精神要求自由大胆、不拘一格,突显新诗应有的生命意志和自由精神;在想象上,诗人应从质朴的生活中写出自我的真性情;同时在内容与情感上兼具旧诗所具有的“普遍性”与新诗“个性化”的因素,实现诗情的自然流动与诗意世界的创造。
总体而言,废名“诗的内容”的新诗观仍是从对“温李”诗词的全面考察中出发的,而这种“内容”也正是旧诗传统中极有价值的部分,同时又表现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最有力地保证了新诗的现代性质,而这种在平衡基础上的突破正是新诗全力追求的价值所在,是现代诗人需要从传统中承继的东西。废名的诗歌主张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新诗理论对当时中国新诗有着积极的建构作用,对当时中国新诗走向规范化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对当下诗歌的健康发展同样有着可贵的启示意义。
注释:
[1]王泽龙:《废名的现代禅诗》,载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第172-182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孙玉石:《呼唤传统:新诗现代性的寻求——废名诗观及30年代现代派“晚唐诗热阐释”》,载《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第131-14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3]张洁宇:《论废名诗歌观念的传统与现代》,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48-154页,2008年1月,第1期。
[4]陈建军:《废名对胡适新诗理论的反拨与超越》,载《长江学术》第57-63页,2009年4月。
[5]废名:《谈新诗》第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6]废名:《谈新诗》第1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7]废名:《谈新诗》第1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8]废名:《谈新诗》第1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9]参见废名:《谈新诗》第150页:“后来新月一派诗人当道,大闹其格律勾当,乃是新诗的曲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
[10]废名:《谈新诗》第1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1]废名:《谈新诗》第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2]废名:《谈新诗》第2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3]废名:《谈新诗》第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4]废名:《谈新诗》第1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5]林庚:《<无题之秋>序》,《无题之秋》,朱英诞著,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版。
[16]废名:《谈新诗》第1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7]废名:《谈新诗》第2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8]废名:《谈新诗》第2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9]废名:《谈新诗》第2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0]侯桂新:《廢名对新诗审美标准的追求——以<谈新诗>为中心》,载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22卷,第95页。
[21]废名在本书《尝试集》一章中说到:“在这一刻以前,他是没有料到他要写这一首诗的,等到他觉得他有一首要写,这首诗便不写亦已成功了,因为这个诗的情绪已自己完成,这样便是我所谓诗的内容,新诗所装得下的正是这个内容。若旧诗则不然,旧诗不但装不下这个诗的内容,昔日的诗人也很少有人有这个诗的内容”。见废名:《谈新诗》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2]废名:《谈新诗》第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3]废名:《谈新诗》第20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4]废名:《谈新诗》第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5]吴奔星:《应是游子拳拳意 并非浪子靡靡音——读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载于《名作欣赏》,1983年05期,第14-16页。
[26]废名:《谈新诗》第8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7]废名:《谈新诗》第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8]废名:《谈新诗》第1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9]废名:《谈新诗》第1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30]侯桂新:《废名对新诗审美标准的追求——以<谈新诗>为中心》,载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22卷,第95页。
[31]废名:《谈新诗》第19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32]废名:《谈新诗》第1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33]废名:《谈新诗》第2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34]废名:《谈新诗》第2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摘 要:废名的诗学理论中“诗的内容”内含十分丰富,在“当下性”与“完全性”的基础上,废名对于诗人的创作精神要求自由大胆、不拘一格,突显新诗应有的生命意志和自由精神;在想象上,诗人应从质朴的生活中写出自我的真性情;同时在内容与情感上兼具旧诗所具有的“普遍性”与新诗“个性化”的因素,实现诗情的自然流动与诗意世界的创造。这种新诗观念不仅对于早期的新诗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并且对当下诗歌的健康发展同样有着可贵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废名;新诗;诗的内容;创作;想象
作者简介:李佳铭(1996.6-),女,陕西西安人,硕士,武汉大学文学院2018级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04
废名的诗论专著《谈新诗》的价值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自九十年代起至今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批评家们对废名的诗歌创作理论从多个角度出发进行了探讨。九十年代,如王泽龙从“禅”理的角度理解废名诗歌的风格与蕴含[1];孙玉石从废名新诗观与古典诗学的关联进行了阐释[2]等等;进入二十世纪,张洁宇认为废名在打破新诗传统与现代间隔离的关系上有重要作用[3],陈建军则从废名与胡适新诗理论的对比中看其对后者的超越性[4]。评论界对废名的诗与诗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与剖析,在“诗的内容”与“散文的文字”这一框架之下从各个角度发掘其独特的诗学内涵。
然而以往的评论家在对 “诗的内容”进行阐释时,多是从“当下性”与“完全性”的角度出发,因而尽管对这二者展开了多层次的分析与较深入的挖掘,但仍给后来的读者与创作者一种虽有合理性,但却空泛、矛盾、无法运用其理论进行具体实践之感,这是因为在“诗的内容”这一概念中除了“当下性”与“完全性”之外,废名对诗人的创作精神、想象与质朴的关系、普遍与个性的关系也有不同程度的要求。本文中,笔者将围绕这些为以往评论家所忽略的部分展开,对废名“诗的内容”进行补充阐释。
一、诗人的创作精神
在《新诗应是自由诗》一章中,废名说到“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诗一定要表现着一个诗的内容,有了这个诗的内容,然后‘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5]废名在这里谈到的“自由诗”是针对西洋的“散文诗”而言的,表面上是指包含“诗的内容”,用“散文的文字”进行创作的诗歌,即从形式上来说包含了与现代格律诗相区别的自由体诗以及四行诗、十四行诗等有规律体的诗歌。但笔者认为废名在这里所讲的“自由诗”除了形式上自由之外,更多的是从一种创作者的精神,即创作意识、创作姿态上所进行的评判。
这一点从废名对冰心、郭沫若二人诗歌创作的评价上也可以看出。废名把冰心、郭沫若的诗归入“新诗的第二期”[6],他认为,以胡适为代表的初期新诗尽管有一个“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要怎样做就怎么样做”的自由作诗的理念,但对于诗歌在形式上、字词上的要求过多,即如废名所说“然而在这个‘自由里头无形中有一个但是——但不得做旧诗”[7],初期的新诗是把用文言文写成、强调格律形式的“旧诗”当作死敌的。
到了新诗的第二期,新诗反而与曾经的“敌人”有了“交情”,因此变得更加的自由。“他们的面前是他们自己的‘诗,在诗之国里岂有敌人,古今中外的诗人都可以旦暮遇之,新诗的诗的生命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起点,因其诗情泛滥,乃有诗文字之不中绳墨,——试问诗情泛滥是一件容易事吗?恐怕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8]废名在此所讲的“自己的诗”“诗情泛滥”建立在其一以贯之的“诗的内容”的理论基礎之上的,但不同在于,这里更多强调的是对于诗歌创作一种全然投入、不受拘束的精神状态。黄遵宪曾提出“以我手写我口”的诗歌理念,也被认为是早期白话新诗观念的滥觞,但到二三十年代的诗坛,诗人的诗歌创作在废名看来却渐渐偏离了应有的轨道,这点从废名指斥新月派在形式上大做文章,流于铺排,大闹格律勾当[9]的弊病中可以看出。因而,冰心与郭沫若的诗歌创作给废名带来一种眼前一亮之感,“他们做诗已经离开了新旧诗斗争的阶级,他们自己的诗空气吹动起来了,他们简直有了一个诗情的泛滥。”[10]
郭沫若与冰心在诗歌创作中的这种表现与废名格外推崇的温庭筠词、李商隐诗中近乎“乱写”的“自由表现”有种高度契合,废名十分钟情温李在诗词中天马横空式的“乱写”,这固然是由于其诗词里有可供新诗汲取的“营养”,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乱写”所饱含的自由开阔的气度值得新诗创作者学习借鉴。从诗歌精神的自由度来说,温李这些“当初新文学运动者所排斥的古典派”的创作精神,“倒有我们今日新诗的趋势”[11]了。
在废名看来,判断一首诗歌好坏的首要标准就是其情感是否饱满,同时是否具有偶然性——非刻意为之的造作。废名对郭沫若无名小诗《夕暮》做出这样的评价:“是新诗的杰作,如果中国的新诗只准我选一首,我只好选它,因为它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12];而在废名给出较高评价的其他诗歌的评语中也可常常见到如下词汇:新鲜、质朴、自然、生气……这些特质归结起来,即是诗人的诗情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解放,真正实现了当下情绪的自然流动,获得了自由。因此,当废名说,温李“这一派的诗词存在的根据或者正有我们今日白话诗发展的根据”[13]时,他所期待的并不仅是新诗简单地从意象、意境和情调等方面回到古典中去,而是学习和领悟温李在进行诗歌创造时所有的某种自由而大胆的精神。“我说自由,是说他们做诗的态度,他们真是无所为而为的做诗了,他们又真是诗要怎么做便怎么做了。”[14],而用林庚的话来说,“‘自由非形式之自由,而是表现之自由。[15]”。废名在“诗的内容”理论下进一步提出的“自由诗”的概念不只是在外在诗体形式上的自由,更多是从创作精神层面对新诗现代品格提出的一种诉求。
二、想象与质朴的关系
新诗初期,大多诗人只注意到文学革命中新诗语言的革新,结果只顾关注一首诗歌是否是用白话创作的,而忘记了诗缘何成诗的本质,因而偏离了创作的轨道,为人所诟病。而废名则从对温李诗词的推崇中力图纠正这一问题,他说“温李的诗在盛唐诗高度发展之后,能够‘于唐人中别开一境,这主要表现,是他们的诗突破了旧诗情生文文生情的局限,而能够充分驰骋他们的幻想和想象,在他们所创造的‘超乎一般旧诗的表现的诗的世界里,极大地增强了诗的素质和内容。”[16]废名深受西方现代派诗风的影响,崇尚意象的跳跃和诗意的蕴藉,同时,深厚的国学底蕴又使他自然地承传了中国传统诗歌追求意境要朦胧含蓄的诗学主张,所以废名的新诗观兼有中西诗学之长,认为新诗是诗人想象的结果,诗人不受约束的自由想象促成诗歌的含蓄和朦胧美。
废名在《十四行集》一章中说到:“新诗不同旧诗一样谁都可以做诗了……因为旧诗有形式,有谱子,谁都可以照填的,它只有作文的工巧,没有离开散文的情调,将散文的内容谱成诗便是诗的情调了。不懂得新诗与旧诗的性质,徒徒雷同做新诗,以为新诗也总有形式。”[17]废名批判了那些以为新诗创作毫无门槛的言论,他认为好的新诗比之旧诗而言更有写作的难度,要想将新诗做的自然,便要在新诗之中张弛想象,同时具备形象美与意境美,给读者留下能解读的余地与可解读的空间。“古典派是以典故以辞藻驰骋想象”[18],“今日的新诗也无非是有想象罢了。今日新诗的生命便是诗人想象的跳动,感觉的灵敏,凡属现实都是它的材料……”[19]。废名将旧诗中温李一派的想象性特点移植到新诗上,既是看到了想象对于诗意的重要性,也是为了借此弘扬新诗的“自由表现”。[20]废名以为,新诗是诗人想象的结果,在其评价标准中,具有想象性的诗歌才可称为真正的新诗,诗人不受约束的自由想象促成诗歌的含蓄和朦胧美,这是今天新诗所必要的,而也正是因为新诗中有诗人充满自由的丰富的想象,才得以与以往的旧诗区别开来,是旧诗中所“装不下的”[21],这也与废名对于诗歌应“自由”的观念是一致的。
如上文笔者所说,废名的诗歌理论主张写诗要符合诗人主观情感的真实,将感受到的“诗意”如实地表达出来,不伪装,不造作。在评价卞之琳《航海》一诗时,他说到:“我是喜欢写实的,童话也是写实,故我喜欢。童话而是写实者,如瓦特之弄开水壶是也。卞之琳的诗即是如此,他的幻想好像是思想家,不,他诗人了。他能像打糖锣的一样,令我像一个小孩子给他吸引去了。”[22]在评价卞之琳《倦》一诗时,他亦有“我前说唯其写实乃有神秘者,因为你看见的东西我不一定看见,我看见的东西你不一定看见,写出来每每不在意中也,故神秘的很。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们说他写得自然,其实神秘的很。”[23]的观点。
废名在此即是说想象并非是用过于难懂而艰涩的意象为读者的解读设置人为的障碍,相反却是从日常生活里介入想象,从最质朴的事物中找到创作的灵感,而并非将想象束之高阁。读者无法解读的想象便是繁琐意象的堆叠与铺陈,这样的诗歌写作看似有难度实则毫无意义,而好的新诗,其想象应当在接近生活的基础上有所抽离,新鲜得难以模仿。作者将情感与思绪凝聚在诗歌所选取的意象之中,本身就具有一种含蓄美,同时也为读者在进行解读时提供了开放与自由的空间,正是这种开放的空间使不同的读者在接触诗歌时得以产生不同的联想。在废名关于“想象”的诗歌理念中本身就包含“质朴”的因素,后者更多指的是诗人的创作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情感,因此其与“想象”并非矛盾对立的,彼此并不冲突,并且,一首新诗要写得成功,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
以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为例,废名对这首诗的评价是“这首诗很不容易写。……心想這首诗倒要读他一遍,一读却一口气把他读完了。我说一口气把他读完了,正是我称赞这首诗的意思,正是这首诗的真实,令人心悦诚服。现在我因为读了《扬鞭集》之后,又觉得这首诗写得真实,是当然的。诗人刘半农原是很结实的人物。”[24]且不管这首诗歌里的“她”到底是指某位女性还是祖国,笔者认为废名在评价此诗时所用的“真实”并非是与虚假对应的那重含义,而是指刘半农在完成“思念”这样一个颇为俗气的题材时,其传递的情感是真挚的,没有流于大众化的、表面的情爱字眼,而是采用一种与读者心意相通,走入读者内心的表达方式娓娓道来。刘半农的这首诗并非没有想象,并非只是用平铺直叙的直白口吻写成的,相反,里面频繁地运用比喻、排比、反问、象征等手法来渲染氛围。“这首诗运用了传统歌谣的复迭手法,他在构思技巧上虽继承了传统的反复与比兴手法,但在语言运用上却是生动活泼的,在意境上是新鲜别致的,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且余意不尽,余韵悠然。”[25]即也是在说虽然在语言形式上作者采用了铺排的形式,但这种铺排是建立在感情之上的,前者只是抒情的工具与手段,而并非目的,诗歌本质的特点仍是质朴。
同样的评价还见于废名评价刘半农的《小诗》中,“像这首《小诗》,很不容易写好,作者却写得恰好,甚不易得。这正是作者的性情好,故能将一个难得表现合式的感情很朴质的表现着了。这种情感原是很平常的,人人可有的,要表现着平常生活的情感却最见性情,见学问。”[26]运用艰涩难懂的意象进行铺排的想象看似有难度,实则只是词语的堆砌,形式上的难度可以通过学习技巧来实现,而真正好的新诗要做到的则是借想象写出自我真性情,蕴含在诗中的感情敦厚饱满,且这种感情虽是最平常最质朴的,但仍种下一粒新生的种子,并非浮于表面,而是结实地生长在诗人自身与每位读者的心里。
三、普遍性与个性化的关系
废名在《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一章中说到:“新诗能够使读者读之觉得好,然后普遍与个性二事俱全,才是白话新诗的成功。普遍与个性二事俱全,本来是一切文学的条件,白话新诗又何能独有优待条件。”即认为一首新诗要获得成功,应当实现“普遍”与“个性”间的平衡[27],这代表他的新诗理论往更深的层面进行了推进。
废名在评价冰心的《春水》第一六四首时说到“冰心女士的新诗太是散文的写法,虽然写着那么的近乎旧诗的句子。……像这样‘将离别的情绪,如果变幻一下,应该就是中国古代诗人创造诗的过程,然而新诗的生命自然是一个直接的书写。这一点正是冰心女士的新诗在新诗历史上的意义,它表现新诗的个性,缺乏诗的普遍性,——如果意识到这个普遍性,冰心女士新诗的生命应是旧诗的题材了。”[28]从这里可以看出,废名认为普遍性是对无论旧诗或新诗皆有的要求,但对旧诗而言满足普遍性是其成功的基础,而新诗虽也要求普遍性,但一定程度的缺乏却也是新诗的独特之处,是区别于旧诗的标志之一。
然而,在谈到郭沫若的《偶成》时废名却认为作者不应当在末尾加上“儿在怀中睡着了”,“这首诗的情景恐怕很好,但诗却写得不成功,因为第四句一件偶然的事情,不足以构成诗的普遍性。”[29]即是认为以此句作结与前面“月在我头上舒波/海在我脚下喧腾/我站在海上的危崖”三句诗所体现的浑然的意境与一致的场景相比,后边是独立于普遍情境之外的偶然事件,这句诗的出现使得诗歌营造的意境氛围与创造的整体形象遭到了破坏。不过,废名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即“所以诗有时还是要‘做出来的,不只是写出来的。”侯桂新认为废名之所以提出这一方法,乃是因为“‘表现个性‘当下关物与‘普遍性的要求之间,便产生了一点隐含的矛盾。”[30]
废名还举出刘半农的《母亲》,将其与《偶成》“黄昏时孩子们倦着睡着了/后院月光下,静静的水声/是母亲替他们在洗衣裳”进行对比,他说到“这首诗所写的情景,读者自然不问是描写当时实在的情景或者不是的,即因为这首诗有诗的普遍性。这首诗不能不说是‘做出来的。郭沫若的《偶成》确是写出来的。”[31]倦睡的孩子,皎洁的月光,静静的母亲的洗衣裳,所有的内容包含在这个情境中是如此和谐,这就是一个整一的形象。
废名在这里所谈到的“普遍性”实际涉及到新诗创作取材与整合的问题,在“《冰心诗集》”一章中他说到“我们从新诗人的诗的创造性又可以知道古代诗人的创造性,旧诗到后来失掉了生命徒有躯壳的存在,而这个诗的生命反而在新诗里发见,这些关系都是无形中起来的,理会得这个关系乃见出新诗发展的意义。”[32]新诗相比旧诗,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所变化,而最重要的还是内容上的变化。废名虽不提倡以“新诗是旧诗的进步”的观点来看新诗,但关键是他围绕“进步”这一命题谈到的“这是诗的内容的变化,这变化是一定的,这正是时代的精神”[33]。新诗比之旧诗虽然从形式上、口语化上、用典上为当时采取保守态度的学者所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真正的新诗在精神内容上确与旧诗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
“旧诗人拿着典故尚且应用无穷,何况新诗是以新鲜的世界為材料呢?”[34]比之旧诗,新诗当然可以沿袭其“一以贯之”的创作方法,在诗歌中力图去呈现一个浑然完整的世界,但这样便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模仿与接续,而并非一种全新的创造,也自然不会把新诗引到一条健康而自然发展的道路上去。新诗比之旧诗若只是在语言与形式上做到了什么革新,在意象的使用上比旧诗有什么突破的地方,那并不足为新,新诗之“新”更在于其传递出的一种全新的创作理念,全新的思想。这也便回到了新文化运动本身的意义——借文学的革新启蒙大众。既然为新诗,以前那些封建的、顽固的、守旧的思想自然不能出现在新诗中,否则只是“旧瓶装新酒”,并无什么实质的意义与价值。同时,新思想要借新诗来展现,达到传播的目的当然要在内容上与旧诗有所区别,笔者认为这也是废名所提出的新诗“诗的内容”区别于旧诗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而真正好的新诗并不只是在传统与现代间做一种简单的加减法,绝不是从两个方面的语言、意象、形式等各选取一些因素融化在一首作品中,也不是局部地寻找一些可用的材料强行将二者弥合,而是基于认真且开放地去考察旧诗所具有的“普遍性”的基础上,同时带着现代人独具“个性化”的眼光和思考去完成一首诗歌的创造,体现在作品中也许只是结尾那一句“儿在怀中睡着了”,但背后所包含的却是从“以新鲜的世界为材料”出发的,对于新诗普遍性与个性化问题的平衡,这也便是废名在书中所说的“新诗发展的意义”所在。
四、小结
废名的诗学理论中“诗的内容”内含十分丰富,在“当下性”与“完全性”的基础上,废名对于诗人的创作精神要求自由大胆、不拘一格,突显新诗应有的生命意志和自由精神;在想象上,诗人应从质朴的生活中写出自我的真性情;同时在内容与情感上兼具旧诗所具有的“普遍性”与新诗“个性化”的因素,实现诗情的自然流动与诗意世界的创造。
总体而言,废名“诗的内容”的新诗观仍是从对“温李”诗词的全面考察中出发的,而这种“内容”也正是旧诗传统中极有价值的部分,同时又表现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最有力地保证了新诗的现代性质,而这种在平衡基础上的突破正是新诗全力追求的价值所在,是现代诗人需要从传统中承继的东西。废名的诗歌主张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新诗理论对当时中国新诗有着积极的建构作用,对当时中国新诗走向规范化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对当下诗歌的健康发展同样有着可贵的启示意义。
注释:
[1]王泽龙:《废名的现代禅诗》,载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第172-182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孙玉石:《呼唤传统:新诗现代性的寻求——废名诗观及30年代现代派“晚唐诗热阐释”》,载《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第131-14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3]张洁宇:《论废名诗歌观念的传统与现代》,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48-154页,2008年1月,第1期。
[4]陈建军:《废名对胡适新诗理论的反拨与超越》,载《长江学术》第57-63页,2009年4月。
[5]废名:《谈新诗》第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6]废名:《谈新诗》第1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7]废名:《谈新诗》第1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8]废名:《谈新诗》第1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9]参见废名:《谈新诗》第150页:“后来新月一派诗人当道,大闹其格律勾当,乃是新诗的曲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
[10]废名:《谈新诗》第1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1]废名:《谈新诗》第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2]废名:《谈新诗》第2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3]废名:《谈新诗》第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4]废名:《谈新诗》第1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5]林庚:《<无题之秋>序》,《无题之秋》,朱英诞著,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版。
[16]废名:《谈新诗》第1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7]废名:《谈新诗》第2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8]废名:《谈新诗》第2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9]废名:《谈新诗》第2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0]侯桂新:《废名对新诗审美标准的追求——以<谈新诗>为中心》,载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22卷,第95頁。
[21]废名在本书《尝试集》一章中说到:“在这一刻以前,他是没有料到他要写这一首诗的,等到他觉得他有一首要写,这首诗便不写亦已成功了,因为这个诗的情绪已自己完成,这样便是我所谓诗的内容,新诗所装得下的正是这个内容。若旧诗则不然,旧诗不但装不下这个诗的内容,昔日的诗人也很少有人有这个诗的内容”。见废名:《谈新诗》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2]废名:《谈新诗》第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3]废名:《谈新诗》第20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4]废名:《谈新诗》第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5]吴奔星:《应是游子拳拳意 并非浪子靡靡音——读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载于《名作欣赏》,1983年05期,第14-16页。
[26]废名:《谈新诗》第8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7]废名:《谈新诗》第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8]废名:《谈新诗》第1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9]废名:《谈新诗》第1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30]侯桂新:《废名对新诗审美标准的追求——以<谈新诗>为中心》,载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22卷,第95页。
[31]废名:《谈新诗》第19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32]废名:《谈新诗》第1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33]废名:《谈新诗》第2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34]废名:《谈新诗》第2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