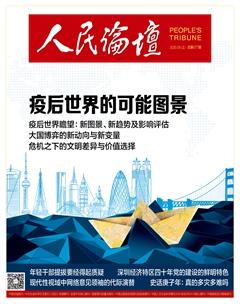当代青年的“恐育”心理和生育观
穆光宗

【关键词】生育观 人口 “恐育”心理
【中图分类号】C913.15 【文献标识码】A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出生率为10.48‰,跌至1949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从人口学角度看,出生率的降低、出生人口的減少一方面与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有关,另一方面与已婚人口的生育意愿改变、弱化有关。
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人口时代
人口少子化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和持续低迷,导致0—14岁少儿人口逐渐下降的现象和过程。具体而言,人口少子化具有两重含义:
一是指0—14岁少儿人口的比重和人数不断下降。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少儿人口占比为36.3%,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为40.4%,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为33.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为27.8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22.89%,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为16.6%。近几年由于“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放开,我国的少儿人口占比有所上升,2019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78%。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达到了883万人。2017年二孩的出生数量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也超过了一半,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显然,在“全面二孩”政策效果显现的同时,“一孩”的出生数量却有较多下降。2017年我国“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
总体上看,人口少子化态势难以阻挡。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数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人。也就是说,“90后”比“80后”少了3100万人,“00后”又比“90后”少了4100万人。
二是指全国育龄女性非生育率下降且低迷,出生人口不断减少。数据显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已经快速转型为“低出生、低生育”社会,其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TFR)已经在1.65以下,略高于政策生育率(大约1.47)。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之时,低生育现象更为稳定,TFR降至1.22;到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1.18。2015年全国1%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其中“一孩”生育率仅为0.556,低得出乎意料。多项数据显示,中国早已掉入低生育陷阱,TFR不仅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2左右,而且从世纪之交开始持续低于1.5甚至1.3。
不争的事实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新人口问题已然不是生育率过高问题,而是生育率过低问题,是如何走出低生育陷阱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解决,伴随而来的是人口问题的转型。
2019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03万人,占总人口的12.6%。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未来中国老龄化会加快发展,“十四五”期间预计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030年之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或超过20%,届时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最大问题是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未备先老”,养老保障体系负担加重,养老金短缺将成为政府面临的棘手难题。老无所养、老无所依、老无所医、老无所护是正在被放大的社会风险,而少子化则是来自源头的根本挑战。
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存在着弱持续发展甚至不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趋势,最终会制约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没有人口的发展,社会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低生育率问题早已出现,今后养老金压力大、劳动力人口不足等问题会更加严峻。2018年以来,许多城市竞相推出吸引人才落户的政策,“抢人大战”频频上演,这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宣示着人口低生育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人口时代,人口负增长为期不远。
低生育陷阱:事实抑或假说
生育政策调整之后的二孩生育效应被一再高估的原因是,一些人没有看到人口表象背后的文化根源;也就是说,我国的婚育文化在改革开放的洪流冲击下已经被彻底改变。2011年,笔者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提到,中国已掉入“超低生育陷阱”。这一判断是基于多年的观察,我国已经出现的超低生育率不仅仅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而且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是晚婚少生文化背景下生成的意愿性、选择性、内生性、稳定性、持续性和内卷性的低生育率现象。意愿性、选择性和内生性的概括旨在说明生育观念根本转变、生育决策的自主性强化和生育动力严重弱化的事实,稳定性、持续性和内卷性则旨在说明低生育的三个特性,即低生育已经形成反弹力几乎丧失殆尽、持续走低的惯性和机制。中国遭遇的低生育现状所隐含的人口萎缩风险将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之后一一呈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小幅减少63万,但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多79万人,是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这是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短期得以释放之故。各方曾预测,“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我国将在2016年至2018年间出现一个生育堆积集中释放的高峰,预想增加的人口数量从几百万到上千万不等。但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全面二孩”第一年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预想中增加数百万出生人口的情景并没有出现。
其实,我国人口的婚育模式已经表现出极晚婚、极晚育、极少育的趋势,这进一步降低了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初婚初育年龄已经大大推后,这一点在发达城市表现突出。譬如,根据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幸福婚姻家庭调查报告——2015年十城市抽样调查》,全国平均结婚年龄26岁,但根据统计,2012年,江苏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9.6岁,2015年为32.4岁,到了2017年,则为34.2岁,其中女性34.3岁,男性34.1岁。可以说,在大中小城市,年轻人“三十而婚”极为普遍,在这种婚姻状况的约束下,新家庭的低生育现象可想而知。
而且,现阶段不同背景下国人的生育模式有趋同的特点,就是趋向“被动性晚婚晚育”“选择性独生优生”的模式,同质性增强,差别性缩小。如果说2016年前,所见多是政策性、强制性的独生子女;那么2016年之后,意愿性亦是被动选择的独生子女就显著增加了。2013年11月出台的“单独二孩”政策和2016年1月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普遍遇冷,就是重要的信号,许多适龄年轻夫妇想生二孩而根本不敢生,“只生一个就够了”已成为主流主导的生育文化。
“不育”可谓是当代中国青年“恐育”心理的一个极端表现。“丁克”(Double income but no kids)一族有一些是不想生,有一部分人可能因為各种原因想生却生不了,由此催生了“代孕”等现象。“代孕”处于灰色地带,有市场需求,但伦理上显然不可取,将生育产业化、子宫市场化和生母工具化,会破坏正常的人伦关系、两性关系和社会秩序。概言之,不要希望什么都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问题,市场会走偏、会失灵、会事与愿违。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需要坚实的伦理基础,需要道德人文的指引。
“恐育”现象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现在有不少年轻人恐婚恐育,甚至有中国“单身社会”到来的说法。日本已经进入“低欲望社会”,低生育社会是低欲望社会的一个反映。“生育恐惧症”是因房价、消费高涨,不少年轻人当上了“房奴”“车奴”,年龄渐长,生儿育女日益成为困扰“80后”“90后”生活方式的共性话题。现在已婚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孩奴”又成了一个让新生代父母普遍发愁的事情,看到现在生养孩子需要承担巨大花销、巨大责任和巨大压力后,心理上普遍患有“生育恐惧症”。
生育率的下降是发达世界的一个必然趋势。从经济学角度看,生育成本—孩子效用的比较可以提供经典的解释。从社会学角度看,则比较复杂,从生育文化、代际关系、生育责任等方面可以给出诠释。
首先,生育是有成本的。社会转型导致生养成本急剧升高、“压力山大”,让年轻夫妇望而却步。随着生育理性的觉醒和高涨,中国人的生育早已经进入成本约束型的阶段。生育直接的抚育成本(如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容易被人们直观感知,生育间接的抚养成本,如时间付出等生命成本、精力和疲惫等健康成本、操心等心理成本、丧失个人自由和成就机会等间接成本纷至沓来,也让不少追求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年轻人产生了“恐育”心理。
其实,多数年轻人不是不想结婚生育,而是因为城市生活成本太高,无奈中选择晚婚晚育。年轻人结婚年龄普遍推后,极晚婚现象挤压了“婚内生育空间”,结果必然是极晚育和极少生。年龄在35岁以上的高龄孕妇所占比例逐年攀升。显然,高房价抑制了生育意愿,生育焦虑指数非常之高,“房奴”“孩奴”成为事实,有人测算过从孩子出生到成家需要数百万之巨,高房价、高生养成本已经如此普遍,很少有家庭可以摆脱高成本约束的生养模式。虽然理想子女数平均接近2,但条件生育率却不到1,高房价、高抚育成本和缺乏带孩子的人手及不确定的巨大机会成本,都成了很多家庭想生而不敢生的障碍因素。
这表面看是人口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人口再生产的成本飙升打击了绝大多数家庭生育的积极性。中国社会的转型已然形成了超低生育文化,印证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这样的命题。时至今日,没有国家和社会的帮助,大多数家庭难以走出只生一个乃至于不生不育的被动选择的低生育困境。如果说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风险社会。因此,通过鼓励生育来提振生育率是重建人口的重大历史前提。
其次,在客观上,生育也可能是没有收益甚至是负收益的。生育得不偿失的观念日渐普遍。从积极的愿景和正收益来看,生育的结果——孩子,是有预期效用(如养儿防老)和即期效用(如天伦之乐)的。传统的生育文化具有工具性价值,即积谷防饥、养儿防老,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以及人口流迁背景下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以养老为主要驱动力的生育文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价值,但实际作用已被严重削弱。
目前,多元混合的社会化养老比较适合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渐渐弱化的中国,其主体应该是社区居家养老(主要面向生活可以自理的老人),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以及包括安养、养护和临终关怀在内的机构养老,重点是发展需要长期照料的带有一定福利补贴的护理型养老机构(主要面对失能甚至失智的老人)。空巢老人可以选择独居养老,但需要社区养老服务的支持,也可以尝试和子女近距离居住,或者抱团养老,或者选择养老院,等等。
最后,计划生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它重塑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育观念。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传播了现代“少生快富”“少生优育”“少生幸福”的生育理念。但错误的地方是在于将“独生”理解为“少生”,甚至当作是“少生”的理想状态。须知,一旦形成内生性生育率,生育率就会低迷不振。例如,深陷低生育泥潭的日、韩、西欧等国家在鼓励生育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收效甚微。原因是多方面的,也不尽相同,主要原因恐怕是生育意愿低迷、生育机会成本太高、生育效用降低、生育缺乏热情之故。
取消生育限制的时机早已成熟。理由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生育意愿就已经达到较低水平,平均低于更替水平。如果取消生育限制,可能带来生育限制时代出生者与生育自主时代出生者的代际矛盾,但有可能创造社会的和谐与契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人口结构。取消生育限制对极高收入群体和极低收入群体可能都有影响,前者是不惧生育成本预期约束,后者是不知生育成本看不见的约束。在生育率持续低迷阶段,取消生育限制的利要远远大于弊。取消生育限制,估计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下的人口结构问题,仅仅是“亡羊补牢”而已,区别在于100只羊到底跑丢了多少只羊,“剩余羊”就是“机遇期”。
综上所述,为维护和促进我国人口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遏制人口少子化态势,必须改变人口与生育的负向观念。国家需降低年轻家庭的生养负担,从各个方面促进生养成本的社会化,保护生育能力,提高生育热情,打造生育—儿童—老人—家庭四友好的社会新时代。
【参考文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年2月28日。
责编/赵橙涔 美编/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