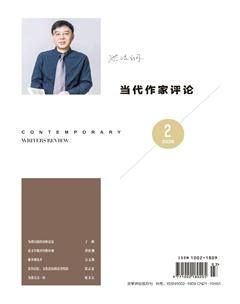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彷徨与秘语
大概是巴渝悠久、古朴、深厚的文化底蕴浸润了诗人的才情,出生于涪陵工作于成都的李永才,大概又沐浴了天府蜀地自古传继至今的诗情与灵性,他一直以来深爱着巴山蜀水,深爱着山水之间的人情世事,并把所有的情感寄托于斯,寄寓于诗。刚年过50的李永才仍然诗情满怀,笔耕不辍。自1987年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第一首诗《冬天印象》,数十年来,先后公开出版《故乡的方向》《城市器物》《空白的色彩》《教堂的手》《灵魂的牧场》等多部诗集(不含1992年第一部自印诗集《深秋的玫瑰》),近年又推出新作《南方的太阳鸟》,李永才:《南方的太阳鸟》,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7。可谓收获颇丰。
李永才满溢儒雅之气,大学时学英语,后又学管理,在政府部门工作20多年,他的诗人身份倒有些特殊,不像个“职业”诗人。其实也不特殊,诗人从来就不是一种职业,“诗”最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向度。他只是不改初衷,从来都是怀抱一颗诗心行走人生。20世纪80年代他还在四川师范大学做学生时,即参与大学生诗歌运动和第三代诗歌运动,早早就埋下了一颗诗的种子,也开启了对诗的一种责任与坚守。他的生活是丰富的,视野是开阔的,诗心是纯正的,加上他对诗的挚爱,使他在创作上稳步上升。学外语,让他熟悉了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典故,也使他能够在中西方文化之间任性游走;他出生乡野,使他深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隐秘关系;他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使他能够充分汲取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意象之美;他熟悉中国新诗的历史,李永才:《新诗百年:贡献、问题及展望》,《当代文坛》2016年第6期。使他的诗歌创作能够在新诗版图上找到自己的坐标,不至于迷失写作方向,也能够从容地在新诗的长河里不断翻腾起浪花。
2016年,适值李永才知天命之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灵魂的牧场》,产生了较大反响。综合考察李永才的诗歌创作,1993年至1998年间他创作了大量乡土诗歌,2000年至2005年又以城市题材的诗歌创作为主,近几年的创作则摇摆、彷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诗评家李犁在评析《灵魂的牧场》时说,其主题“大多是写故乡和童年”,是近年“李永才写作的方向”,并就李永才的诗提出“故乡和童年就是安放灵魂的牧场”李犁:《挽留与挣脱》,李永才:《灵魂的牧场》序言,第1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的结论。我认可这一结论。不仅如此,李永才时隔一年后出版的诗集《南方的太阳鸟》,同样是这一主题的延伸与深化。为什么在都市生活了几十年的李永才近年却在不断开掘乡土这一主题呢?我认为,中年心态使之然,同时也是李永才诗风进一步稳定和结出硕果的体现。当然,李永才笔下的乡土并非狭义的乡土,谓之“乡情”或“乡愁”似更准确,而且其视野更为开阔,内蕴更为深厚,抒情更为隐忍。“乡愁”几乎成为这个时代每个诗人难以解开的心结,年龄愈长,其情愈浓,足以成为当下诗歌的主潮。李永才的诗亦如一道清澈的溪流,汇入到了这一主潮之中。
南方,乡音,以及城市与乡村,就成为《南方的太阳鸟》的内在抒情大结构。何谓太阳鸟?太阳鸟被誉为“东方蜂鸟”“月下老人”,又与凤凰关联。光彩夺目的太阳鸟,传言生于巴山一带,李永才生于巴地,乡情寄予可见。太阳鸟在古老传说中又为折翼之太阳不能飞升天上,只能借助他力重回天空并给人间带来光明,故又含希望之意。联想到李永才的诗,他似欲借助诗之力量,让人性的光辉重悬心空,给人性和世道带来明净的飞翔。当然,李永才人过中年,诗中除了浓浓乡情和对家乡往事、爱情的深切缅怀之外,也含有精神“涅槃”之意,这是人生境界的一种升华。这大概也是李永才近几年诗歌创作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最明显的精神向度。
但凡写诗写久之人,其道行修炼必成一定气候。其作品一经面世,多多少少都会给读者制造一些阅读障碍,这与无难度写作的轻佻口语之风迥异。诗人或许有冒险之为,但读者却在文字的迷宫中经历一番周折或几度灵魂的历险后,终能窥探诗人内心的此许秘密。如此相向的碰撞,是诗人与读者之间的交锋,更是对话。李永才的《灵魂的牧场》,初读如坠云雾之中,不明就里,再读则其形可辨,其心可鉴,欣欣然似已把住其行中之脉,诗中之血。
比如,《荒芜,流水的野心》《昏鸦》《靴子落地》《虚构一场春天的凌乱》《宽窄巷》《藏北高原》……严格讲,这些诗并非同一主题之作,但从其中又似可牵扯出一以贯之的线索。每首诗,都有可能是一座山头、一条河流、一片森林、一抹斜阳,或一种思考、一种认识、一声怨叹……然而过目再三,猛然发现李永才写诗或许真有始终如一的精神内核。
简而言之,从手法上讲,诗人惯用较为生涩的词语(或典故)和跳跃的思维,将视觉色彩和听觉律动并行交织,将诸多能表达颓败情绪的意象叠加,从而抒发如下情思:以荒凉、孤独、废败、没落、灵魂无依的恐惧感作为表象,来建构诗思框架,由此延伸诗意旨归——对现实的无奈感可由诗意来曲折倾诉,并寻求或顺势长出一片灵魂的牧场。从而,诗人在文字轻灵或浊重的抒发里,在意象交织和对抗的张力中,在文字诗意的草原上放牧精神,以求心灵得以喘息和抚慰。
说李永才的诗表达了某种颓败没落的情绪,这得从他诗中的词语和意象来求证。请允许我打开这组诗词语的集中营,用一些篇幅来集中展示和释放诗人的心绪,而這是不需要过多阐释的。荒芜、晚钟、敲碎的黄昏、枯萎、带刺、坏天气、背道而驰、流亡、飘零、错乱、遗忘、昏鸦、吞没、枯藤、逃离、残雪、落难、战栗、哇凉、苍蝇、厄运、凌乱、零落、陷落、折落、旧船、贫困、乡愁、寒霜、旷野、黄昏、伤痛、冷漠、支离破碎、闪烁不定、苦难、沉默、落寞、歧途、惨烈、嘶叫、空洞、死亡、污秽、孤独、烦恼、无聊、白纸、剥落、悲伤、凛冽、流浪、乱世、苦难、乱草、流浪、影子、竹篮打水……再明显不过,这是漫天飞舞的“恶之花”纷纷扬扬地扑面而来,读来寒冷刺骨,如同让心灵蒙上一场大雪。这就形成了李永才诗歌某种整体意义上的意象建构,如果具体到每首诗中,这种整体性只是那种寒冷和恐惧感在不同侧面折射的再聚光而已。
铺天盖地的雪原上,雪下掩藏的又是什么?自然是一颗挣扎的灵魂,是一炬对温暖渴求的目光。这需要阳光!如此才能融化诗人心里雪藏的冷。于是,诗人的这组诗中,不时冒现阳光的意象。阳光是想象的、理想的、能给人温暖的翅膀,是能化解现实矛盾和困惑的光芒,只是诗人诗中飘飞的阳光是折翼的、残缺的。
让这条快要枯萎的河流/分享尘世的祝福/让那些快乐的鱼群,代替我回到故乡/那里有带刺的阳光
荒芜的,一缕阳光/一个被阳光照过的村庄/荒芜之美,就像秋后的哲学/并不源于人类
——《荒芜,流水的野心》
故乡是一切美好的源头,当然这个“故乡”并非实指,它可能只是诗人心灵的某个始发地,或者是对过往岁月的种种缅怀。怀念是“带刺”的,是令人痛苦的。时光之河已经枯竭,这是对时光不能倒流的哀叹,还是对现实的严重不满?过去的美好尤如阳光掠过,只是人的逐渐衰老长成一片岁月逝去的荒芜。诗人面临的是生命“秋”后的阳光,恍惚之间,如此哲学层面的悟知应该符合这世间的万物规律,而并非渺小无助的人类。
诗人的阳光折翼之感在他的这本集子中是随处可见的,可谓一种弥漫不散的气氛。“昏鸦……/抱紧一枚落难的太阳”(《昏鸦》),与人相较,昏鸦是“幸福”的,它能抱紧太阳,尽管是“落难”的,却被现实中身无所寄的流浪汉的火炉所替代。“阳光,像受伤的骑士”(《光芒,樱花内心的独白》),古典、豪情的骑士精神难免落入惨烈、孤单的境地,而理想的火焰正如受伤的骑士,终将面临落荒而逃的命运。这不仅仅是诗人个人的悲哀,或许还是一个时代所共同面临的悲哀。“我的眼睛,陷入玻璃一样的阳光”(《生活的片断》),诗人个人拥有和面对的或许是“一条街的繁华”,然而终是“端坐孤独”,这种生命孤单的痛感是彻骨的。所以,诗人更为向往流水的白纸、跳河而去的浪花。然而,诗人却无法寻找身边的美好,无法寄放精神,只是在种养一些苦难,正如目光所及,虽有阳光,却如玻璃般易碎而难得。这些才是寄存在诗人语言形式之下真正要表达的灵魂的颤栗感,也是最需要读者与诗人一道去体悟和承担的。
他集子中的主体意象是颓败的,然而诗人却在利用阳光这一理念性的意象进行尝试性的补救。其中的挣扎感十分明显,在这纠缠、挣扎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其中存在的某种张力。为了实现和助推其中的张力,诗人采用了视听并行、交织和碰撞的手法。比如:
阳光,像受伤的骑士
惨烈而浩瀚
嘶叫着,扑向孤单的旷野
路边的日子,樱花自由地开放
深处有淡淡的红
像一只泛红的蜻蜓
沿着空洞的篱笆,缓缓地向上爬
——《光芒,樱花内心的独白》
该段前三行是表现听觉的,给人的声音感觉是急迫、哀伤、孤独而广阔无边,是一种动态的漫延;后四行是表现视觉的,给人的颜色体验是舒缓、静窄、温馨、淡雅而诗意,是一种静态的定格。无论动静,都能呈现出两幅鲜明而不同的画面,巨大的对比式落差无形中产生了某种审美的张力。诗人对现实甚至是对历史的矛盾、彷徨、孤独的无力感,和对理想化的美好、诗意生活的憧憬,就如此虚幻地交织碰撞在了一起。这种手法和感觉在诗人其他诗中比比皆是,又如:
桃花涂抹西窗
乌云未及躲闪 红了一半
黎明的尖叫在深水区沉浮,旋转
用松针刺探阳光的隐私
——《边缘与别处》
十分明显,前两行是视觉的,后两行是听觉的。其中所欲表达的,又何曾不是某种矛盾、挣扎的心态呢?
至此,已无需多言,诗人心灵的窗口实际上已然洞开。其中内涵的复杂性,曾经悄悄地隐藏在显得生涩的意象和跳跃性很强的诗行中,但是,只要找到一个有效切入口,诗人所有心灵的暗角都能得到读者目光的照耀。我们除了感叹诗人对折翼阳光的隐晦抒怀之外,是否还能够与诗人颤栗的灵魂一道产生共振?
与《灵魂的牧场》相比,《南方的太阳鸟》似温暖得多。这是一种知天命后的淡泊与释然,还是历经岁月淘洗后,思乡更切的另一种温情表达?这本集子一共分为8辑,除1、2辑分别为11首之外,其他辑均为10首,如果不考虑其中组诗的数量,结构、形式可谓均衡、整饬与完美。这个集子中,自然也有“落日”“暮色”“孤岛”“黄昏”“秋风”“他乡”“流水”等一类颓败、枯涩的意象建构,也有“无言”“雪落他乡”“死亡”“恍惚”“叶落”“送别”“忧伤”“流亡”“失眠”一类的形容或动作的表述,但整体上却比《灵魂的牧场》温暖而有“希望”。“轻如棉花”“鸽子”“温暖的说辞”“柿子熟透秋天”“南方的太阳鸟”“万家灯火”“生长”“复活”“民谣如夜色”“南山若梦”“古镇”“明媚”“颂”“春雨”“永恒”“梦枕江南”“金沙岁月”“诗人的芬芳”“种养故乡”“鸟鸣桃花潭”“抱阳而立”“麦子熟了”“山冈上的茉莉花”……我们无法扫去其中隐含的忧伤,但我们更应感受到其中温暖的力量。他在《落日颂》中如此写道:
落日。你知道,沉默是为情怀
东升西落,一抹苍凉的光
破碎,是为辜负
再次遭遇的对手,比黃羊更灵活
不要试图疏远
这卑微的忧伤。凭着最后的辉煌
抵抗逼近的黄昏
——《落日颂》
不过,从李永才时隐时现的温暖中,我们又能感受到他中年之后对岁月流逝、青春难再的无奈苍凉感。或者,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理解,乡村生活和记忆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也正如青春一般渐行渐远,我们在感受落日余晖温暖的同时,更多的是灵魂岛屿的拱升,从而最终只能依赖开辟“灵魂的牧场”以自救。一个孤寂的人,常将香烟作为交流的工具;而一个常常思考人生、社会,回望故乡的忧伤者,诗歌能够成为抵达宁静的最佳通途。这或许就是一种绝望中的温暖和希望,唯有诗歌能做到。
那些山水,绿林,诗意的码头和鸟声
在自然而苦涩的行走中
退隐于荒芜的岁月
而你经历了这么多远古的孤独
却听不见自己嘶哑的疼痛
——《南方的太阳鸟》
没有谁能够真正说清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到底是什么,真正的时代精神或许只是潜行在绝大多数人的心底,与喧嚣无关,与更表面的新物质形态无关,它更多与一个社会形态的整体变迁相关,与我们数千年的乡村文明的渐次褪色相关,而我们(包括敏感的诗人)却正处于这个当口。诗人笔下流淌的无边忧愁或许恰恰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而非被人误读的个人小情调。诗人彷徨于城市与乡村之际,隐秘地接受和说出这个时代潜隐的秘语,以一个诗人独有的姿态行走在那些最后的村落间,且吟且唱。诗歌,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最后要抱守的希望?
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一书中论及西方文明“已经衰落和随时会崩溃”, ② 〔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第137、140页,黄灿然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继而谈到诗歌中的某种颓废状态,他没有完全否定这一诗潮,而是说:“颓废派写的悲观诗歌也许就是被编成密码并被昏暗地看到的未来。”②这些话颇具启发性。李永才的诗歌创作自然不能被简单地列入颓废派写作,但他诗歌中大量的悲观和荒芜感却是有迹可循的。但我在此想说的是李永才詩歌中的“希望”或“未来”,这么说,才能更为清晰地认识他诗歌的价值。李永才在大量诗歌中歌颂和迷恋乡村,实际上是在哀悼某种“静止的文明”的消逝,他许多童年和青年生活的回忆,其实也一道同质化为“静止的文明”的合体。不过,我想在此借用米沃什的话来肯定李永才诗歌创作的价值:“在人类将寻找净化的现实、寻找‘永恒的颜色这个意义上,换言之,也就是寻找美这个意义上,人类也将探索自身。”〔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第158页,黄灿然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不错,反观李永才大部分诗作,他都在(很多时候在记忆中)寻找着净化的现实、永恒的颜色,或者美。这种对自身的探索是我们无法否定的。
不仅如此,这种探索式的“净化”不无治疗的功能。很多时候,李永才在表达“忧伤”的时候,紧接着就是“治疗”,这种情形不仅是内在的,字面上也是如此。通过整体考察,李永才在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大概就是“忧伤”“悲伤”“感伤”“暗伤”“伤痕”等类似的词语,从而“忧伤”成为他诗歌的基调。伤痕累累的诗人,只有靠诗来治疗。文学与治疗早就是一个老话题了,只是在李永才的诗歌中得到了再次的验证。按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讲,他这是现实中愿望未能得到满足的另类补偿。具体点说,诗人的精神在城市越感受到压迫,就越需要用乡村的一切来治疗。从这点上看来,我们又似乎可以掐捏住李永才很多诗歌的创作动机。对故乡、乡情的回望,也就成为了李永才诗歌创作的一种宗教,实际上具体到了对一个又一个名词的诗意阐释上。于是,一个全新的精神故乡在诗人的脑海里渐渐显影并清晰起来,诗人从中获得治疗与新生。这种治疗的效果,首先是幸福感的生发:
门开了,那是我童年的木房子
有小船一样的怀念
上旧世界对话,是幸福的
——《秋风吹过南湖》
这种幸福感往往定格为一些画面,场景、心情、旧迹、古镇、家乡的人和事、花草、山川河流……都在诗意的画面中纷纷扬扬,如梦境中的碎片,在李永才的诗中逐一拼贴,如此再造了一个精神上的故乡和心灵的栖息地,由是,诗人或许在现实的破败和不堪中流亡之后,有了去处,精神上的伤痕终有了治愈的良方。
如果写诗仅仅是完成一个工匠的工作,那最多只是诗匠,一个注重诗歌技巧的诗匠;如果仅仅是为了表达思想,那还不如做一个纯粹的社会学家或思想家、哲学家。诗人,应该是以上几个身份的结合,诗人的表达方式终究是诗性的,如此才可做到诗意地栖居。所以,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李永才的诗是充满诗性的,在某种层面上说,是写得很俏皮的、灵动的,我们每每读到那些闪光的诗句,不由得感叹李永才的才情与汉语的神性。
他的才情首先表现在一些妙句的采撷上。“依然闪烁的,是过去的事物:那些苍白的,颠沛的,被反复推敲的浪花”(《恍惚富春江》),这是诗人写水的优美诗句。一句“反复推敲的浪花”,令人大为惊讶,这是真正的陌生化创造。“黄昏缚于鸟翅,拍打几次/就成了碎玻璃”(《缓慢的沙河》),尽情地去意会吧,简直绝了。这样的句子,怎样的解析都将成为一种破坏。再来看,“那些腐朽的琉璃瓦当/像皇上牙齿,从城墙上脱落”(《圆明园断想·7》),我们无法想象当时诗人是如何“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地获得如此诗句的。妙语连珠的诗句,在李永才的诗中不断涌现,令人叹为观止。我不忍将其肢解来进行一些无谓的、多余的解读,关键是,这些简单至极却精妙万分的诗句,又恰如其分而精确地包蕴了当时的景、形、势、思、情,可谓将各种因素与技巧融为一体而又不留痕迹。
他的才情其次还表现在对历史与对中西方典故的娴熟运用上。他写古镇、民谣、庙宇,他写重庆的城门、苏堤白堤、白鹤梁,他写李白、包公,写圆明园、乌江渡、百丈关……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同时又将思绪无限地延伸开去。李永才的诗,可谓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历史与地域,时间和空间,往往打破了界限而任由诗人拼贴组合。正如他的一首诗里所写:“如果酒杯是山河,我就是旷世英雄/气吞山河之后,我也有儿女情长”(《高原颂》),诗人的豪气与柔情就如双峰并峙般相映成趣,令人仰望成痴。在写历史的时候,他善用典故,这种典故往往是化用古典诗歌中的意象,使其诗更添新色与内蕴。他诗中的典故还表现在诗中用到大量的外国人名与名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诗人用了点小思,故意设置下一些阅读的障碍。如果读者明白其中典故,自然会意会到诗人所指;如果你不熟悉其中奥妙,不妨顺手查阅相关资料,待你明白就里,自然会豁然开朗起来。我们不否认,诗歌有时也是一种知识,无论是具象的还是抽象意义上的。总的来看,李永才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与西方文化中的典故巧妙地结合起来,这在无形中取得了鲜明的互文性效果,从而也就丰富了他诗歌的诗性内涵。
最后,作为诗歌的核心建构,意象是必不可少的。在意象的捕捉与营构上,李永才也充分表现出独到的一面。上文提到一系列的意象,已充分说明了这点。但是,他在诗歌中有時更注重一些核心性意象的营造,比如乌鸦与火车。乌鸦在他以前的诗中频频出现,不过,他的乌鸦是变化着的乌鸦,是情景与情绪变幻的载体。乌鸦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时常出没,这个意象,李永才算是旧题新做,其“新”有可能体现在将中国和西方诗歌中的这一意象打通与融汇了。囿于篇幅,恕我在此不多列实例并作解读。我想强调的是,在《南方的太阳鸟》这部集子里,李永才连续对火车这一意象进行了建构。如此集中于一个意象的打磨,这在他之前的诗歌写作中是少见的。在《火车修辞与礼仪》一诗里,他似乎为我们揭开了谜底:“而一列火车的意义/或许在于:把空间变成时间”。火车不仅是现代社会工业化的一个符号,在李永才的诗中,更是他对时间与空间这一对元概念的深切感知。尽管火车意象在中外诗歌中并不新鲜,尤其是美国诗人赖特对火车的诗性书写,充分呈现了人在现代工业文明面前的无力感,但在李永才的诗歌中又杂糅了中国挽歌式的体验。我们不得不说,他的火车系列又丰富了这一现代意象的内蕴。
不错,李永才是个有才情有理想的诗人。他一直以来身居都市,在感受这个时代变迁的时候,更在深切地怀念和回顾来路,其对社会的省思与浓浓乡愁,让人看到他诗中一条较为稳定的心路和轨迹。对故乡的眷恋与歌颂,对人生的执着与热爱,对诗歌与哲理的追求,这些将成为他个人在诗歌创作中的最终目标。正如有论者言道:“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始终存在的目标,那么他的每一种心理倾向都带着某种强迫性去追随这个目标,就好像存在着一种他必须遵守的自然法则一样。”〔奥地利〕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理解人性》,第21-22页,陈太胜、陈文颖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我相信李永才的诗歌创作是有目标和法则的,这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和认真体悟他的诗。不过,我也有某种担心,即在这种目标和法则之下可能带来的自我重复。但愿李永才在今后的诗歌路途上,有新的发现与新的创造。
〔本文系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乌江流域诗人群研究”(18XJA751
001)、2016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期以来重庆乌江流域诗人群研究”(2016YBWX07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红,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李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