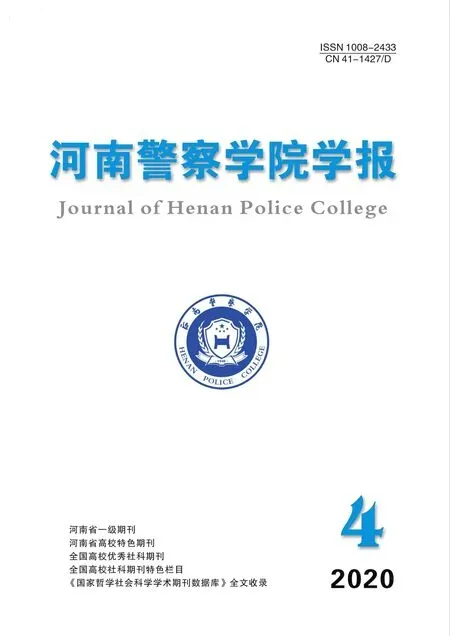参与传销的女性:来自中国女民工罪犯的声音
沈安琪(著), 高梓桐(译)
一、概述
尽管有组织犯罪的准确定义仍存在争议,但它已经引起学术界、执法机构、政策制定者、记者以及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2)Wright, A. (2006). Organised crime. Cullompton: Willan.。人们做了大量工作来调查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犯罪集团和犯罪网络,因为跨国有组织犯罪似乎和现代化、全球化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3)Allum, F., & Gilmour, S. (Eds.). (2012).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有组织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犯罪产业和犯罪市场上(4)Antonopoulos, G. A. (Ed.). (2016). Illegal entrepreneurship, organised crime and social control: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Dick Hobbs. Switzerland: Springer.Hobbs, D. (1988). Doing the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 detectives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East End of Lond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现有的文献表明,有组织犯罪的范围很广,而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有组织犯罪是多样化、多面性和快速变化的,它既包括传统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如收取保护费、敲诈勒索和放高利贷,也包括现代化的犯罪企业。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有组织犯罪,都需要罪犯之间进行一定程度的组织和协调,并且从事资金与服务的交易。
在过去的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女性犯罪者经常被忽略,尽管她们在策划犯罪活动及伙同他人共同实施恶性犯罪中的作用不可忽视(5)Brownstein, H. H., Spunt, B. J., Crimmins, S. M., & Langley, S. C. (1995). Women who kill in drug market situations. Justice Quarterly, 12(3), 473-498.Miller, J. (1998). Up it up: gender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street robbery. Criminology, 36(1), 37-66.。有组织犯罪的研究对女性的忽视并不奇怪,因为犯罪学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男性为中心”的(6)Chesney-Lind, M. (1989). Girls’ crime and women’s place: toward a feminist model of female delinquency.Crime & Delinquency, 35, 5-29.,男性罪犯占研究的主导地位,女性罪犯则被视而不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女性作为犯罪者,顺应这一趋势,学术研究也开始关注犯罪集团和有组织犯罪活动中的女性,重点聚焦于女性在青少年帮派(7)Aldridge, J., & Medina, J. (2008). Youth gains in an English city: social exclusions, drugs and violence. ESRC end of award report. Swindon: ESRC.Batchelor, S. (2009). Girls, gangs and violence: assessing the evidence. Probation Journal, 56, 399-414.Chesney-Lind, M. (1993). Girls, gangs and violence: anatomy of a backlash. Humanity and Society, 17(3), 321- 344.Miller, J. (2001). One of the guys: girls, gangs and gender.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黑手党(8)Dino, A. (2012). Women and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 the ambiguous case of the Italian Mafias. In F. Allum & S. Gilmour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Fiandaca, G. (Ed.). (2007). Women and the Mafia: female roles in organised crime. New York: Springer-Verlag.和跨国有组织犯罪(9)2014年出版了《有组织犯罪趋势中跨国有组织犯罪中的女性》特刊。中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大家都认为,有组织犯罪的研究往往基于北半球女性的经验,而南半球女性的研究代表性不足。2000年曾有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想摸清过去20年女性在全球有组织犯罪中的作用(10)Fiandaca, G. (Ed.). (2007). Women and the Mafia: female roles in organised crime. New York: Springer-Verlag.,报告最后公布了一些参与国的研究结果,但这份“图鉴”(11)Pizzini-Gambetta, V. (2008). Women and the mafia: a methodology minefield. Global Crime, 9(4), 348-353.存在“漏洞”,即内容并不包括中国。关于中国女性参与有组织犯罪的英文文献寥寥无几。在国外的研究中,过去的研究集中在从中国到美国的人口贩卖犯罪中的女性,包括人贩子和“被贩卖的受害者”(12)Chin, K.-L., & Finckenauer, J. O. (2012). Selling sex overseas: Chinese women and the realities of prostitution and global sex trafficking.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Zhang, S. X., Chin, K. L., & Miller, J. (2007b).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Chinese transnational human smuggling: a gendered market perspective. Criminology, 45(3), 699-733.。至于中国大陆,以前的研究主要将性行业的女性流动人口视为性工作者(13)Liu, M. (2012). Chinese migrant women in the sex industry: exploring their paths to prostitution. Feminist Criminology, 7(4), 327-349.Zheng, T. (2009). Red lights: the lives of sex work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将女性视为国内人口拐卖的受害者(14)Chu, C. Y.-Y. (2011). Human trafficking and smuggling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68), 39- 52.Zheng, T. (2014). Prostitution and human trafficking in China. In L. Cao, I. Y. Sun, & B. Hebento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criminology. Oxon: Routledge.。最近的研究(15)Shen, A. (2015). Offending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gender and pathways into crime. Basingstoke: Palgrave.则开始关注中国女性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性产业和国内儿童拐卖中的犯罪行为,这些研究突出了女性在有组织犯罪中的参与度。有人指出,由于社会经济条件限制(尤其是资源不足),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女性往往尤为容易受到越轨和犯罪的影响(16)Liu, Q., & Peng, J. (2012). The report on cases involving female offenders. Legal System and Society, 7, 167- 168.,但关于女性参与有组织犯罪的研究相当有限,因此我们需要更细致和深入的分析。希望本研究能对这一领域的文献工作做出贡献。
中国女性在传销犯罪中出现的概率与日俱增(17)Shen, A. (2017). Women judg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gender, judging and living. London: Palgrave.,本文将通过传销这个个案来研究中国女性的犯罪参与。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础,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女性参与犯罪集团的实证研究结果。其次,介绍了研究方法和数据。接着就案例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详细论述:一是传销的性质和中国有关非法经营的法律规制,二是女性流动人口参与传销的状况及动机,三是女性在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四是探讨了女性参与犯罪活动的得失,最后是文章通过实证证据得出的结论,并提出了研究带来的几点启示。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展示女性参与犯罪集团的情况,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有组织犯罪中的性别动态的中国案例研究。在更微观的层面,它探讨了社会排斥、阶级和性别不平等对女民工的影响。由于有组织犯罪和人口流动的全球性,本研究所处的区域背景也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
我们稍后将看到,这项研究的参与者是为了其他的研究项目而被找到的,她们都是已经被定罪的罪犯。因此,我在接下来会提供一些背景资料,以解释女民工的社会身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调查结果。
二、国内人口迁移、不平等与中国女民工:若干背景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运动。在这个时代,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变迁,数以百万计的人,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天都在从农村转移到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18)Miller, T. (2012). China’s urban billion: the story behind the biggest migration in human history. London andNew York: Zed Books.。据《中国劳动报》(2018年)报道,截至2017年底,中国有28.65万余名农民工居住在城市,但他们的户籍仍然属于农村。国内人口大规模迁移对城市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两点与越轨和犯罪有关:第一,导致社会排斥和歧视农民工的公共政策;第二,使处于不利社会经济群体中的个人易受违法行为影响的结构性因素。
在应对国际流动人口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等法律规制,而为了应对国内潜在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户口制度作为一种流动人口控制模式被引入。户口制度在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造成了相当大的差异,城市居民享有国家资助的福利和各项特权,而农村居民却与这些福利特权无缘(19)Rofel, L. (2007).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农民工在城市受到多方面的排斥(20)Xu, J. (2014). Urbanisation and inevitable migration: crime and migrant workers. In L. Cao, I. Y. Sun, & B. Hebento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criminology. Oxon: Routledge.,这显然是造成城乡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同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被认为是造成中国城市压力巨大的原因,特别是在引发社会动荡和犯罪率上升方面(21)Li, C. (1996). Surplus rural labourers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Asian Survey, 36(11), 1122-1145.Zhang, L. (2001). Contesting crime, order, and migrant spaces in Beijing. In N. N. Chen, C. D. Clark, S. Z. Gottschang, & L. Jeffery (Eds.), China urban: ethn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与国际流动人口一样(22)Pratt, A., & Valverde, M. (2002). From deserving victims to “Masters of Confusion”: redefining refugees in the 1990s.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7(2), 135-161.,中国的流动人口常常被描述为犯罪分子和安全威胁,因而成为犯罪预防战略的规制对象。流动人口问题至今仍是“一个热点问题”(23)Davin, D. (1999). Internal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Basingstoke: Palgrave.。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群体,在制度上处于弱势地位。
市场经济一方面使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成为一个不断两极分化的社会(24)Yan, Y. (2009). The individualis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Oxford: Berg.。传统的城乡不平等已经转化为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25)Wang, H. (2003). China’s new order: soci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 Huter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上层是少数超级富豪,底层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农村居民,其中一部分仍然处于贫困状态(26)Naughton, R. J. (2007).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Hong Kong: SNP Best-set Typesetter Ltd.。农民工犯罪可能是当今新自由主义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外在表现。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国家鼓励个人从事各种创业活动以创造财富,人们被越来越多地动员起来,但社会资源却分配不均(27)Bakken, B. (2018). Introduction. In B. Bakken (Ed.), Crime and the Chinese drea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农民工所属的下层阶级在赚钱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被他们的城市同胞抛在后面。当机会之门在合法世界被关闭时,犯罪之门就会很容易打开(28)Shen, A., & Antonopoulos, G. A. (2016). Women in criminal market activities: findings from a study in China. In G. A. Antonopoulos (Ed.), Illegal entrepreneurship, organised crime and social control. Switzerland: Springer.,事实上,这并非是新现象,默顿将其称之为“越轨创新”(29)Merton, R. K. (1938).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 672-682.(deviance innovation),即社会弱势群体试图通过非常规手段即犯罪来实现文化上认可的目标,例如金钱上的成功等。
女性作为流动人口浪潮中的一个群体进入城市,与其他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一起寻找机会。在城市里,等待女性农民工的是大量的低薪工作,因为她们通常没有执业资格、特殊技能和社会资本。她们通常在低薪行业就业,包括劳动密集型行业、家庭服务业和性产业(30)Cartier, C. (2001). Globalizing South China. Oxford: Blackwell; Ngai, P. (2007). Gendering the dormitory labour system: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migrant labour in south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13(3-4), 239-258; Rofel, L. (2007).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Liu, M. (2012). Chinese migrant women in the sex industry: exploring their paths to prostitution. Feminist Criminology, 7(4), 327-349;Zheng, T. (2009). Red lights: the lives of sex work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由于这种社会经济地位,她们经常遭到过度剥削(31)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女性的现实似乎是矛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宣布两性平等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毛泽东本人也在社会主义时代提倡激进的女权主义(32)Freitag, G. (2010). Mao a femini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Studies, 1, 159-167.。人们期望女性外出工作,并对家庭收入做出与男性同等的贡献。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也越来越期待她们在财富创造方面与男性竞争(33)Shen, A., & Winlow, S. (2013). Women and crim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Applied Criminology, 38(4), 327-342.,然而,中国女性解放的愿景并未成真。事实上,女性的不平等不仅是性别上的,还有阶级和代际上的:在就业市场上,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机会更少(34)Attané, I. (2012). Being a woman in China today: a demography of gender. China Perspectives, 4, 5-15.,而且,农村女性与她们那些素质更高、资源充足的城市姐妹相比,竞争力要弱得多。性别歧视和阶级分化的社会条件给女性,特别是女性流动人口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她们在城市社会中被严重边缘化。有人认为边缘化使个体变得脆弱,容易犯罪(35)Shen, A. (2015). Offending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gender and pathways into crime. Basingstoke: Palgrave.Sun, I., Luo, H., Wu, Y., & Lin, W.-H. (2016). Strain, negative emotions, and level of criminality among Chinese incarcerated wo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60(7), 828- 846. Bakken, B. (2005). Introduction: Crime, control and modernity in China. In B. Bakken (Ed.), Crime, punishment,and policing in China. Plymouth: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流动人口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并不罕见(36)Marshall, I. H. (Ed.). (1997). Minorities, migrants, and crime. London: Sage.Melossi, D. (2015). Crime, punishment and migration. London: Sage.Palidda, S. (Ed.). (2011). Racial criminalization of migrants in the 21st century. Surrey: Ashgate.Tonry, M. (Ed.). (1997). Ethnicity, crime, and immigration: comparative and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在国际研究中,流动人口与失序和犯罪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对流动人口犯罪行为的分析通常是为了制定国家流动人口政策(37)Aliveti, A. (2013). Crimes of mobility: criminal law and the regulation of immig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为了提高关于不平等、社会排斥和犯罪控制的研究水平(38)Aas, K. F., & Bosworth, M. (2013). The borders of punishment: 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exclus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在中国,过去关于流动人口、越轨和犯罪的研究关注了年轻的流动人口中的毒品问题及被视为流动人口犯罪结构性因素的农民工公共政策缺失问题,并将现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流动人口犯罪研究,检验已确立的命题或理解改革时代犯罪模式的变化(39)Liu, S. (2011).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o, T. W., & Jiang, G. (2006). Inequality, crime an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2), 103-118.Zhao, S., & Kipnis, A. (2000). Criminality and policing of migrant workers. The China Journal, 43, 101-110. Cheng, J., Liu, J., & Wang, J. (2017). Domestic migration, home rentals, and crime rate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4, 8. https://doi.org/10.1186/s40711-017-0056-3.Liu, J. (2005). Crime patterns during the market transition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5, 613-633.Zhang, L., Messner, S. F., & Liu, J. (2007a).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risk of household burglary in the city of Tianj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7(6), 918-937.。到目前为止,对流动人口犯罪主观因素的探索还很少,女性流动人口参与城市犯罪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本研究旨在探讨女性流动人口参与犯罪的情形,以期填补一些空白。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一个更大的中国流动人口、犯罪和惩罚项目(40)Shen, A. (2018). Internal migration,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 inquiry into rural migrant offenders. Switzerland: Springer.,该项目对原始数据的收集采取了定性的方法。这是因为定性研究侧重于个体经验的主观意义,有助于获得对女性生活经历的丰富探索性见解(41)Hesse-Biber, S. N. (2007). Feminist approaches to mixed-methods research. In S. H. Hesse, Biber, & P. L. Leavy (Eds.), Feminist research practice. London: Sage.。该样本是从中国东南部一个大型监狱中取得的,该监狱隶属某女子中队,但由另一个地方的司法女警管理。
我们的实地调查于2016年5月在该女子中队进行。为了获得每位女民工罪犯的叙述和经历,我们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11名从农村到城市的女囚犯参加了访谈。她们每个人都充分了解研究参与的自愿性和保密性。采访在女子中队的一个大型活动室秘密进行,持续时间为30分钟到1小时左右,并通过笔录保存。访谈结束后,我们对现场笔记进行文字处理并翻译成英文。数据是人工处理的,访谈被逐一分析,以确定参与者提出的新论点。
该样本中的女民工罪犯年龄在23岁至51岁之间,其中大多数在20多岁。而受教育状况明显不同,从高到低排序:4名本科毕业,1名大专生,5名小学毕业或肄业,1名是文盲。在就业方面,11名参与者中5人有工作,其中包括3名“犯罪公司”(表面上是合法公司,但在商业环境中有系统地从事犯罪活动)的雇员和2名娱乐业服务人员,2名属于自雇,4名失业。犯罪类型方面,11人共参与了六类犯罪(如表1所示),都没有前科。
本文主要分析了从案例研究中获得的数据及次级数据(从公开资料和公开来源收集的知识和信息)。案例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不针对特定数据收集方法的研究设计(42)Yin, R. (2009).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4th ed.). Thousand Oaks: Sage.,哈特利则认为,案例研究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自主设计(43)Hartley, J. (2004). Case study research. In C. Cassell & G. Symon (Eds.), Essential guide to qualitative methods in organisational research. London: Sage.。案例研究通常是深入调查未知或模糊不清的现象,同时“保留现实生活事件的整体性和其他有意义的特征”(44)Yin, R. (2009).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4th ed.). Thousand Oaks: Sage.。世界著名的案例研究设计权威罗伯特尹指出,案例研究可以获得严谨的数据(45)Yin, R. (2009).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4th ed.). Thousand Oaks: Sage.,但案例研究需要多少案例才足够严谨或有效则没有硬性规定,事实上,一些杰出的女权主义研究结论就是从案例研究中得出的,例如恩盖(46)Ngai, P. (2007). Gendering the dormitory labour system: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migrant labour in south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13(3-4), 239-258.的工厂女工研究。

表1 涉及女性参与者的犯罪类型(n = 11)
在本文中,笔者选择了女性参与传销的案例作进一步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可以注意到,如今的女性可能在传销和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中发挥主导作用(47)Shen, A. (2017). Women judg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gender, judging and living. London: Palgrave.。通常,传销是由犯罪集团经营的,是一种有组织犯罪。同时,我们对女性参与其中的情况知之甚少,而通过该案例可以进行详细的研究。其次,在这11名女性参与者的随机样本中,有2名女性被判处犯有传销罪或与传销有关的犯罪。她们参与了两个不同的传销计划,但扮演了相似的角色。因此,它似乎可以称为“典型案例样本”,可以从中收获一些成果(48)Layder, D. (2013). Doing excellent small-scale research. London: Sage.。
本研究有两个局限性。第一个是与面试数据相关的“内部有效性”(49)Jacques, S., & Wright, R. (2014). A social theory of drug sales, gifts and frauds. Crime & Deliquency, 60(7), 1057-1082.,除了“印象管理”(50)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Edinburgh: The Bateman Press.之外,参与者还可能撒谎或提供重建的、模糊的或扭曲的信息(51)Sharpe, G. (2012). Offending girls: young women and youth justice. London: Routledge.Shen, A. (2015). Offending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gender and pathways into crime. Basingstoke: Palgrave.。这种局限性应该被以下事实所抵消:参与者没有参与同一传销,但她们对犯罪企业类型的描述和她们的参与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可以互相印证。方法三角测量(52)Denzin, N. (1978). Sociological methods: a sourcebook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也有所帮助,在下文中,二级数据会被用来验证案例参与者所说的话。在每次访问前和访问期间,还应通过确保保密性和匿名性,将研究局限性降至最低。为了履行这一义务,本文中所有参与者的姓名和地点均为化名。值得注意的是,同行审查作为一项重要措施,本应予以采用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然而,从中提取原始数据的访谈是在监狱环境中进行的,在监狱环境中,外部研究人员所能做的工作受到很大限制(53)Shen, A. (2015). Offending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gender and pathways into crime. Basingstoke: Palgrave.。因此,实际上不可能进行同行审查。
在访谈研究中,偏见当然可能来自研究者自己(54)Willis, J. (2007). Foundation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pretive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Sage.。此前,学术研究者如霍尔等人(55)Hall, S., Winlow, S., & Ancrum, C. (2008). Criminal identities and consumer culture: crime, exclusion and the new culture of narcissism. Cullompton: Willan.就有过解释学家的主张。这些老牌学者认为,我们所了解的现实是社会建构的,研究者自身对研究对象的固有思想和观点必然影响和塑造研究本身。格拉泽(56)Glaser, B. G. (2007). All is data. Grounded Theory Review: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6). http://groundedtheoryreview.com/2007/03/30/1194/. Accessed 2 Feb 2019.则进一步指出,数据不存在偏见、客观、主观或其他因素,数据是研究者作为人类所接受的。以霍尔(57)Hall, S., Winlow, S., & Ancrum, C. (2008). Criminal identities and consumer culture: crime, exclusion and the new culture of narcissism. Cullompton: Willan.等学者为榜样,我试图保持数据的真实性,并尽可能准确地报告研究结果,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研究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第二个限制是“普遍性问题”,即基于较少参与者的定性研究是否具有普遍性。杰克斯和赖特(58)Jacques, S., & Wright, R. (2014). A social theory of drug sales, gifts and frauds. Crime & Deliquency, 60(7), 1057-1082.让我们相信,虽然与典型的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可能会存在有效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但它确实有其自身的优点。在目前的研究中,11名参与者的样本看起来确实很小。鉴于样本量较小,且这是只针对两名女性的个案研究,对传销中的所有女性罪犯得出概括结论是有风险的。然而,这里的重点是案件的参与者,我们的目的是详尽地了解她们的经验,以深入了解女性参与犯罪活动的情况。此外,参与非法经营的人及其经历是典型的。在这种情况下,这里使用的数据应该是有效的,研究结果应该具有更广泛的价值和适用性,这些结论显然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检验。
值得重申的是,访谈是在监狱环境中进行的,接触囚犯极其困难,实地工作受到条件限制。这项探索性研究中收集到的证据,只是为更多更严谨的研究开了个头。
四、案例分析:参与传销的女农民工
有媒体透露,传销(也称为“金字塔式销售”或“连锁式销售”)在中国十分猖獗。2014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传销案件28万件(59)Zhi, G., & Hong, L. (2015). Research into legal issues about organising and leading illegal pyramid schemes and countermeasures. Criminological Research, 5, 67-78.,2016年警方共查处传销案件2826件。2018年5月8日,广州市一个大型传销组织“云连会”被警方破获,其中的主要成员也被逮捕。因此,传销是当代一种问题重重的商业行为,在中国可能构成严重犯罪。
(一)传销的性质与我国关于传销的法律规制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将传销列入了刑事犯罪,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一规定明确了该犯罪行为的作案手法和欺骗性、集体性。由于传销的复杂性,使这部法律最初显得很尴尬。ZJ——一位来自陕西农村的23岁年轻女性提供了一个详细的例子:
“我们的项目叫资本运作,是一种投资产品。它是从外国进口的,现在几乎中国所有的省会都在实施类似的计划。简单地说,它涉及资本积累和再配置。其目的是将所得收入控制在一个封闭的圈子内,最终所有会员都会发财……新人必须缴纳7万元的入会费才能加入,然后在第一个月获得固定数额的工资。入会费一交,就可以开始招收下线(下等会员)和分红。我们公司采用三层制,这意味着你可以从你下面的三层成员那里获得红利。显然,你招聘的越多,你得到的红利就越多,你的职位也就越高。
“在这项计划中,每个人的最终目标都是退出,因为一旦你退出,你就可以拿钱走了。退出这个计划有两种方式:一是赚了一千万元就可以自然退出。那是最好的出路。第二个是被踢出。例如,成员之间发生性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时,就会被踢出,这些行为在我们公司是严格禁止的。自然退出意味着你赚了很多钱,你可以用这些钱创业,比如说开一家商店,如果你被邀请的话,还可以成为这个计划的组织者之一……”
这段采访记录显示了传销计划的复杂性,以及它看起来是多么合法和吸引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ZJ的公司经营着一种“投资产品”的连锁销售,其中的高回报率是可以预期的。有人指出,对潜在成员(投资者)来说,金字塔计划的运作通常被描述为公平、透明和经济上可行。因此,许多人自愿加入连锁销售,在执法部门干预时他们经常否认被骗。
ZJ就是其中之一。她心甘情愿地加入传销组织,并且成功地说服了其他人加入,甚至在被判违法后接受采访时仍然否认其活动的非法性。显然,这名年轻妇女受雇于一家犯罪企业,其表面上是合法的,通常实行公司式治理,包括正式的组织规则和程序,但事实上是在系统地进行着非法经营。对于像ZJ这样的传销组织的普通成员来说,这些公司的商业行为看起来绝对正常。ZJ的说法得到了ZYY的支持,ZYY是另一位年轻女性,她在一家经营类似计划的公司工作了一年多,她发现这与任何其他(合法的)公司都没有区别。由此可见,女性流动人口参与了一种由集体制定的犯罪市场中的“公司犯罪”(60)Gottschalk, P. (2012). Gender and white-collar crime: only our percent female criminals. Journal of Money Laundry Control, 15(3), 362-373.,与通常在黑社会犯罪中泛滥的犯罪手段(61)Steffensmeier, D. (1983). Organisation properties and sex-segregation in the underworld: building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sex differences in crime. Social Forces, 61(4), 1010-1032.相比,传销更多地伪装了其真实性质。而且,与金融犯罪一样,它也是利益驱动的。
如前文所述,传销在中国是一种新的犯罪。它和其他任何法定犯罪一样,定义是法定的(62)(63)Ashworth, A. (1991).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可能不被视为“真正的”自然犯罪。因此,如果公民不理解或可能无法理解犯罪活动的性质,则可能违反与此有关的法律。在这里,ZJ在采访中坚称,如果没有警察的干预,她很可能拿到钱,自然退出。尽管就法律而言,是否明知行为触犯法律是无关紧要的,但这解释了为什么案例中的女性违法者没有表现出多少悔恨,也没有像一般的女性罪犯那样承认有罪(63)Steffensmeier, D., & Allen, E. (1996). Gender and crime: toward a gendered theory of female offend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1), 459-487.。
事实上,传销涉及的“资本运作”不会持续太久。只有少数金字塔顶部的人可能会获得收益,而绝大多数成员在某个时候会赔钱(64)Zhi, G., & Hong, L. (2015). Research into legal issues about organising and leading illegal pyramid schemes and countermeasures. Criminological Research, 5, 67-78.。不幸的是,参与传销的人通常并不理解这一点,他们通常希望通过很少的工作来快速赚钱(65)Nie, L. (2016). Research into the patterns of the law against pyramid selling involving university graduates from a contemporary leg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Jilin Engineering Normal University, 32(11), 66-68.Yang, W. (2011). Research into several issues in relation to organising and leading pyramid schemes. Cross-Strait Legal Science, 3, 47-52.。如果不确定传销带来的危害,“经济邪教”(66)Yang, W. (2011). Research into several issues in relation to organising and leading pyramid schemes. Cross-Strait Legal Science, 3, 47-52.会吸引很多人,被吸引的人通常是农民工(67)Shi, B., & Cao, K. (2013). Discuss illegal pyramid selling. Legality Vision, 4, 233-233.——这是他们的一种赚钱机制,或一种职业机会,或两者兼而有之。“少数”犯罪组织在金字塔顶端利用了这一点,包括本文的案例中在传销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女民工在内的普通传销人员都是事实上的受害者,而且往往蒙受了重大损失,我们将在本文后面部分看到这一点。
(二)女性流动人口参与传销及其动机
在采访中,我询问了女性参与者,她们最初是如何参与传销的。这是来自26岁的ZYY的回答,她来自福建的一个村庄,是一名大专毕业生:
“……我最初在一家制造磁铁板的工厂工作,工资很低,为了多挣点钱,我在业余时间做保姆照顾孩子。工厂的工作毫无前途,我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后就离开了。后来我在一家卖女式内衣的小店做销售助理……2014年,我在那里结识了一个男人,他告诉我,他在省城的一家大时装公司工作,我在那里会有一份更好的工作。我和他一起去了……我发现他们实际上做传销……朋友让我相信几年后我会有很多钱……很诱人……我家的情况不太好:我妈妈几年前受了重伤,不能工作……”
可见,ZYY是因为虚假陈述而加入传销组织的,后来则是出于贪图传销的潜在利益,这些都是参与传销的个人的共同经历。ZJ是一名拥有计算机会计证书的大专毕业生,她是在网上看到这个公司招聘会计的广告。对于ZJ来说,这个职位的招聘要求是:能够在公司内部协助进行会计和财务、培训和综合管理工作,这对ZJ来说是一个理想的职位:“这些是我想做的……”,而且“这种工作,像我这样没有本科学历的人通常是找不到的”。她可能是对的。在中国,对于一份白领工作来说,大专文凭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求职者会进入更高的管理层。
通过对农民工的采访发现,对于只有基本执业资格的女性来说,找一份有职业前途的工作是很困难的。来自中国农村的年轻女性在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由于缺乏精英素质和必要的社会资本,她们往往会发现自己是高不成、低不就。因此,对于年轻农民工(68)Nie, L. (2016). Research into the patterns of the law against pyramid selling involving university graduates from a contemporary leg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Jilin Engineering Normal University, 32(11), 66-68.,尤其是年轻女性来说,表面上合法的公司,比如那些经营传销的公司,更可以为她们提供难得的赚钱机遇和职场发展(69)Shi, B., & Cao, K. (2013). Discuss illegal pyramid selling. Legality Vision, 4, 233-233.。之前的研究(70)Shen, A., & Antonopoulos, G. A. (2016). Women in criminal market activities: findings from a study in China. In G. A. Antonopoulos (Ed.), Illegal entrepreneurship, organised crime and social control. Switzerland: Springer.和本研究中的数据似乎表明,女性参与传销与性别和阶级边缘化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例研究中的女性流动人口参与非法经营的动机是经济利益,而不是特殊或直接的金钱需求,而且她们还有其他动机。ZJ解释说,在犯罪企业的工作确实为她提供了个人和职业发展的机会,这使她有责任感、成就感和自我价值感:
“对我来说,钱不是一切。公司给了我职业发展的机会……在公司被查封之前,我已经是29名以上的业务员(普通会员)的经理了……这份工作也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我认为它会改变你,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例如,它对我们进行了礼仪培训,这项工作提高了我的整体素质,那里也培养了我的管理、沟通和领导能力。通常,我认为这份工作之所以吸引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公司的许多人把它看作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份工作,因为我们年轻人想要成长,但机会不多。(在公司里)每一点进步都让你感到能力提升……一开始,你只关心自己,但渐渐地,你开始学会照顾自己手下的人。我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成就感。你所处的职位越高,你觉得自己越老练。太棒了……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不断学习。事实上,我在被警察逮捕之前还拿到了注册会计师资格。我喜欢这家公司也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有销售业绩(字面意思是“销售数字”,这里指的是佣金)才重要……”
这种自白之所以引人注目,有两个原因。第一,很明显,女性流动人口似乎并不打算从事犯罪活动。这使我们很难将ZJ等犯罪企业中的一些女性归类为女性“有组织犯罪分子”,尽管她们积极参与了违法的商业活动。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女性的工作机会似乎增加了,但女性参与犯罪的机会(71)Alder, F. (1975). Sisters in crime. New York: McGraw-Hill.Simon, R. J. (1975). Women and crime.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也在增加,许多女性在灰色产业和犯罪集团就业。
第二,传销,顾名思义,是具有掠夺性和“有组织的”。通常,犯罪企业为其雇员提供培训、支持和“职业”一条龙规划,以实现长期生存、扩张和最大限度地获取非法利益。这一事实进一步模糊了合法企业和非法企业之间的界限。然而,不同的是,在不合法的商业世界中,晋升和高地位往往主要与“销售业绩”有关,正如ZJ所说。因此,相对于主流社会中的女性来说,在这里性别和阶级的不平等的障碍会被扫清:谁的销售数字越高,谁的处境就越好。这意味着,对于雄心勃勃还有能力的女性来说,她们可以实现自我发展,她们的职业追求不会由于性别歧视和缺乏资源而受阻。在这里,销售业绩肯定了女性流动人口的个人价值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企业给了女性流动人口一种目标感和职业前景,并提高了她们的自尊心,这反过来成为一种动力,激励她们更加努力地工作,招募更多的成员,增加销售数字,学习更多的知识,成为更有能力的职业女性。然而,她们错误地理解了传销给普通成员(包括她们自己)带来的现实后果,即非法经营的危害。
(三)女民工在非法经营活动中的作用
传销通常以犯罪企业的组织方式进行。在之前的一份关于女性的中国司法部门的研究报告中,一位女法官指出,在传销中女性普遍非常积极,还有些人担任领导职务(72)Shen, A. (2017). Women judg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gender, judging and living. London: Palgrave.。在案例研究中,ZJ和ZYY都可能是该计划的积极参与者,她们在法律上“诱导”或“胁迫”他人参与非法贸易。在这个过程中,ZYY犯下了人身犯罪。
在ZYY参与的计划中,参与者住在一个大院里,不允许出去。这是一种中国传销常见的运作模式。为了在这项计划中扮演监督员的角色,这名女民工曾将一名新招募的业务员锁起来,阻止他离开,后来她因此被判非法监禁罪。对她来说,“这是公司的惯例……我在做我的工作,我不知道那是犯罪行为”。鉴于这种情况,传销中的女性流动人口虽然活跃,但似乎与中国恶性犯罪集团中的“女性暴力罪犯”(73)Shen, A. (2016b). Female membership in the black-society style criminal organisations: evidence from a female prison in China. Feminist Criminology, 11(1), 69-90.并不相似。
与ZYY不同的是,ZJ是一名会员,同时也是一名经理,负责“照顾”29名普通会员。据她自己说,她有能力做这项工作,而且很喜欢做。法院认定ZJ是这一传销计划的“组织者”,但她否认。在中国法律中,“领导”和“组织”传销有明确的定义。然而,究竟什么是“组织和领导传销”,中国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74)Chen, X. (2016). The crime of organising and leading the pyramid selling activities: nature and boundary.Tribun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34(2), 106-120.Shen, C. (2016a). Conceptualise illegal pyramid selling and regulation through criminal law. Journal of Huna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5, 78-82.Yang, W. (2011). Research into several issues in relation to organising and leading pyramid schemes. Cross-Strait Legal Science, 3, 47-52.。
根据《关于传销活动适用刑法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3年联合发布的法定解释),ZJ可以认定为“领导”。她承认,作为一名运营经理,她有一些管理和协调责任。可以说,她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诸如招募参与者和收取入场费等措施都是欺诈行为(75)Huang, T. (2009).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venth revised criminal law. People’s Procuratorial Semimonthly, 6, 5-21.Yang, W. (2011). Research into several issues in relation to organising and leading pyramid schemes. Cross-Strait Legal Science, 3, 47-52.。但对此观点存在争议,例如有人认为,一些拥有30个及以上业务员的高层管理人员,也对组织的运行没有影响,他们自己甚至可能会亏损,因此不应被归类为“组织者”或“领导者”。ZJ可能很适合这一类(76)Zhi, G., & Hong, L. (2015). Research into legal issues about organising and leading illegal pyramid schemes and countermeasures. Criminological Research, 5, 67-78.。然而,实际上,“经理”在金字塔计划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是被假定的,而不是根据事实来评估的。因此,法院认定ZJ为“组织者”,并据此定罪和量刑。
看起来,表面上进行正常商业行为的犯罪企业不同于斯特芬斯梅尔定义的在黑社会中从事明显违法行为的犯罪组织(77)Steffensmeier, D. (1983). Organisation properties and sex-segregation in the underworld: building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sex differences in crime. Social Forces, 61(4), 1010-1032.。因此,女性流动人口在中国从事传销活动可能无法与女性在有组织犯罪上游的渗透(78)Simpson, S. S. (1987). Women in elite deviance: a grounded theory. Montrea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或女性参与跨国有组织犯罪(79)Siegel, D. (2014). Women in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 Trends in Organised Crime, 17(1-2), 52-65.相提并论,她们似乎也不太适合“粉红领犯罪”中的女性(80)Daly, K. (1989). Gender and varieties of white-collar crime. Criminology, 27(4), 769-794.Haantz, S. (2002). Women and white collar crime. The National While Collar Crime Center. http://www.nw3 c/org. Accessed 12 May 2018.,鉴于她们在违法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动机,本案例研究是有组织犯罪中复杂的性别动态的一种展现。
(四)传销中女性流动人口的得失
在案例研究中,所谓快速致富的商业活动,参与其中的女性发现她们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如ZJ所示:
“这(传销计划)有什么坏处?我看到有人因为卖房而无家可归……当我们的团队(指公司)被解散时,我们(普通会员)变得一无所有……在我们公司停止运营后的某一天,我遭到了我的业务员的抢劫。他一拳打在我头上,逼我拿出8000元给他,他还咄咄逼人地逼我给他写了一张5万元的欠条。现在想起来仍然让我发抖,感到恶心。我没有报警,因为是我招募了他,当时他父亲病得很重,他需要快钱,他借了很多钱加入传销组织。”
前面我们看到这位年轻女性对她在犯罪公司工作中的收获心怀感激,这证实了传销往往会吸引没有职业的年轻人的说法(81)Nie, L. (2016). Research into the patterns of the law against pyramid selling involving university graduates from a contemporary leg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Jilin Engineering Normal University, 32(11), 66-68.。事实上,他们可能因参与非法活动而蒙受巨大损失。对ZJ来说,除了定罪、监禁和将来会对她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的犯罪记录外,还有债务,以及惨痛的情感遭遇:正如我们在她的自白中看到的那样,作为暴力犯罪受害者受到的创伤和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愧疚。
事实上,ZJ和ZYY都没有在传销中获得任何金钱收益。她们的工资和佣金甚至没有抵消她们为加入该计划而支付的费用。ZJ向父母借了7万元,父母都是低薪农民工,在公司倒闭后,她还欠他们4万多元,后来还遭遇了抢劫。ZYY也有债务。计划失败后,她在一家服装店当售货员,直到被捕。显然,在这起案件中,从事传销活动的女性罪犯的文化背景比其他从事“挣钱工作”的女性罪犯更糟(82)Daly, K. (1989). Gender and varieties of white-collar crime. Criminology, 27(4), 769-794.。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并不是犯罪金字塔顶端为数不多的赚钱者。
此外,如果在当地的城市中不存在社会联系,农民工更倾向于通过私人社交网络招募成员(83)Shi, B., & Cao, K. (2013). Discuss illegal pyramid selling. Legality Vision, 4, 233-233.,这在案例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数据显示,对于女性流动人口来说,她们的损失还包括她们以前与家人、亲戚和朋友的亲密关系,她们从这些人中进行招募或借钱。
五、讨论和结论
本文以中国的女性犯罪者为例,研究她们在传销这一有组织犯罪中的经历。需要重申的是,本文的分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一个小样本中获得的数据,引入案例研究是为了说明女性犯罪行为的一些特点、女性进入犯罪企业的过程以及她们在犯罪企业中的作用。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通过中国的有组织犯罪和传销得出女性犯罪的普遍结论,但本文提供的数据,特别是案例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妇女的“犯罪的可变性质”(84)Daly, K. (1989). Gender and varieties of white-collar crime. Criminology, 27(4), 769-794.。
首先,女性流动人口罪犯与正常女性流动人口一样具有相同的社会经济和户籍地位,但她们在年龄、教育程度、就业和志向方面各不相同。然而,她们似乎又是符合主流性别角色的“普通”中国女性:到合法、灰色或犯罪的商业部门工作,养活自己和家人。
其次,数据表明,本研究中的女性犯罪者大多与他人一起共同犯罪,包括在犯罪公司工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犯罪企业,违法行为有时被当作正常的商业行为,犯罪企业不仅为这里的女性提供赚钱的机会,而且也为她们提供方便,因为她们往往资源有限,在就业市场和合法的商业世界中处于不利地位。调查结果还揭示了(流动)女性犯罪与一些法定犯罪之间的联系,这些罪名是为解决复杂金融和商业环境中的有组织犯罪活动而设立的。
第三,与此相关的是,经济利益似乎是促使女性流动人口参与违法活动的主要诱因,这些活动通常是有组织的,能带来“快钱”,但不同的是女性的问题不仅包括经济需求,还包括由于雄心壮志与现实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而导致的日常挫折,例如参与犯罪企业的女性流动人口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等基本理由。该案例研究表明,女性和男性一样,也希望获得“完全受人尊敬”的待遇(85)Giordano, P. C., Cernkovich, S. A., & Rudolph, J. L. (2002). Gender, crime, and desistance: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4), 990-1064.。这对于没有竞争资本或特殊技能的女民工来说,很难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因此,这项研究支持了戴利的观点,她认为女性罪犯参与犯罪的动机往往是多种动机的结合(86)Daly, K. (1989). Gender and varieties of white-collar crime. Criminology, 27(4), 769-794.。
此外,本文中的案例研究也说明了女性流动人口积极的一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女性流动人口在犯罪企业中的动机和能力所表现出来的是“现代女性”(87)Wylie, C. (2004). Femininity and authority: women in China’s private sector. In A. E. McLaren (Ed.), Chinese women - living and working. London: RoutledgeCurzon.的角色,而不是“悲伤、病态”的女性罪犯(88)Kruttschnitt, C. (2016). The politics, and place, of gender in research on crime. Criminology, 54(1), 8-29.。可以说,她们做出了理性的选择(89)Becker, G. A. (1968).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2), 169-217.才去从事违法活动。一方面,“独立理性代理人”(90)Anderson, E. (2001). Should feminists reject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n L. M. Antony & C. Witt (Eds.), A mind of one’s own. Boulder: Westview Press.有能力、有责任满足自己的需求(91)Strassmann, D. (1993). Not a free market. In M. A. Ferber & J. A. Nelson (Eds.), Beyond economic ma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换言之,这些女性本可以理性地选择不参与犯罪。另一方面,她们走上犯罪的道路是无法选择的,她们的理性是基于性别,而女性在决策中的“理性”可能受到各种条件的影响,包括她们对社会认可的渴望、性别角色和“广泛的性别动态不平等”(92)Chin, K.-L., & Finckenauer, J. O. (2012). Selling sex overseas: Chinese women and the realities of prostitution and global sex trafficking.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最后,本文论证了女性在犯罪企业中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尽管经验数据不能更全面地描述女性在有组织犯罪中的地位,但它表明,女性似乎确实在有组织犯罪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她并不仅仅是被动参与者(93)Clarke, C. (2014). Gender, crime and criminology. The Manchester Review of Law. Crime and Ethics, 88(3), 88-100.Siegel, D. (2014). Women in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 Trends in Organised Crime, 17(1-2), 52-65.。这可以理解为女性对她们所处的社会条件的反应以及她们在流动过程中的性别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本文主要通过案例研究,揭示了有组织犯罪中复杂的性别动态。
诚然,在一个特定区域背景下的特定群体,如中国的女性流动人口,无法完全界定女性的奋斗和女性犯罪的原因(94)Arsovsak, J., & Allum, F. (2014). Introduction: Women in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 Trends in Organised Crime, 17(1-2), 1-15.,也无法充分展示女性在犯罪企业中的角色和地位。尽管如此,收集到的当地的数据和分析越多,我们就越了解女性违法行为的多方面、复杂和动态性质,尤其能够了解女性在有组织犯罪中的参与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