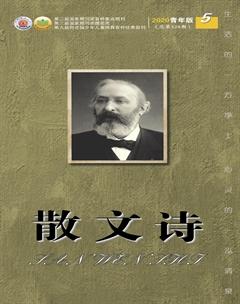动物集
杜辉
“绘入地图的水域比陆地更安静,它们把自身波浪的构造借给陆地”,毕肖普在《地图》的最后几行写道。地图绘制者构建了世界向地图的映射,诗人使这一映射变得可逆,它也因此才完整。
动笔之前,我正在一张地图里劳作,使用颜色、线条以及符号指代山川、河流和房屋。它们准确而具体,甚至还带着有限的象征。地图是真实世界的过滤与提纯,或者也是某种进化(或倒退)。那么动物与人呢,是不是也存在这些?
去年12月初,我读阿雷奥拉的《动物集》,完全被他的想象力所征服。“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也开始写《动物集》。在这次实践里,我尝试着在比喻里嵌套比喻,比如:“从受伤的树干钻出芽苞,他大多数时候静止:思考、苦行、默立,像见习僧侣”(《壁虎》)。同时,写动物与写人似乎密不可分。就像阿雷奥拉写鸵鸟时想到了穿超短裙的女子,毕肖普写蟾蜍时想到了拳击运动员;王小波先生在《黄金时代》里有关于考拉熊的著名比喻,史蒂文斯在《看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里说:“黑鸟在秋风里旋转。它是哑剧的一个小角色。”
那么,动物与人之间的映射是否可逆?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我就曾经写过一个句子:“打哈欠打成河马”。更多地,我推测,世间万物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可逆的映射。
河马
博茨瓦纳的巨大哈欠,飞出一只水鸟,减肥失败的河马,在下游的泥浆里度过无聊周末。失眠症痛击这面移动的墙,它的肿眼泡疲惫得如同守夜人的灯,只有宽大鼻孔依然机敏,两个铜喇叭,随时发出低吼。坏脾气,来自于无聊参观者的骚扰。田野不再坚持,倒挂于岩壁上的最后一只蝙蝠醒来,雨滴被星辰摇落。幼河马,像一群玩具,在细雨里奔跑。
单向路标,生长于空中的黑手,指向寂寞动物园。驾驭电音者选择沉默,只有一盏潮湿的电灯晃动,没有头颅和手臂的黑模特,在光线里试戴钻石项链。雪白斑马线分割阴影,寒流从地图上袭来,降雪不可避免。管理员为河马升高室温,围栏以内,患消化不良症的主角,它的皮肤褶皱里藏有废弃的臼齿。少量听觉在等待中发霉,光滑的河马呼喊,但它并没有用它来抗议。
鸽子
你的白发,在暮光里细微而专注。灯火遥不可及,马铃薯花在远方盛开,蜜蜂的听觉失效,田野幽深得有些悲伤,只因再看不见你的白发。
沉浸于自身,白色鱼鳞的铁之门紧闭。疲惫脚步声惊醒你洁白的梦。月下,你的呼吸笨拙而坚决,打开一条指向自身的通道,虫鸣不断被重复。身后,正在凋谢的向日葵小径。发黄的钟声响了12下,月亮漏出的青铜不断堆积。
黄鼬的凸凹舞步消失于地平线。白沙拂过你的双脚,北斗的长尾伸进凉爽河水——时间深处的啜饮。你在窗下低述,乡音醇厚。夜风弹拨杨树叶子,那部高大风琴无人认领。流星坠落于屋脊,你披上新外套,打开一小片天空,孤单身影悬挂在楼群窗口的右上角——那飞行中的多边形。
起锚,破晓的柔软波涛。风在你休憩的桅杆之上颠簸,星星点起微弱灯火。翻越无数个黎明,在梦中航行。
鸽子是天空的道具。
壁虎
从受伤的树干钻出芽苞,他大多数时候静止:思考、苦行、默立。像见习僧侣。干燥的水泥平台或者潮湿玻璃上唯一移动的音符,脚印被翻唱者装进旋转的激光唱盘。
他的身影是多年前遗失的那把钥匙,或者地铁灰色车厢里随机陈列的脚,像平行轨道上的木讷碎片,无法重复的喧嚣;或者是小雨途中的黑鸟,在无限延伸的电线上驻足。
壁虎是忘记长大的雏鳄,是拒绝进化的恐龙。有一次,他从迟疑问突然启动,让我想起那些劳作中的铁器,某种捕捞,在人行道苍老的秋天里不知所措。
坠落中的吉他,试图从孤独的悬挂中逃走。壁虎是身披甲胄的朋克乐队,或者是梦境叙述者:广口瓶里,时间福尔马林中的哑儿。它的歌声是一种通感,来源于知识和雕像。
翠鸟
翠鸟的蓝色脸与绿色脸重叠,在银器的撞击里。光破碎,雄鸟筑巢。从真实流向虚构的唯一绳索:赤脚者种植贝壳,最后的飞机是一只雌鸟。含有细盐的风,让芭蕉树下的黑衣女子,害怕正在开裂的稻草面孔。
众神放开长线,两颗星在半空中交头接耳。月亮的滚动声越来越弱,遥远的砂糖洒落,翠鸟突然刺穿池塘,剩余的冬天并不凶猛。
饥饿袭击:高跟鞋和半透明黑色长筒袜,以及遗失在街角的大卫。深南大道:“高壓危险,禁止攀爬”。荔香公园:“水深三米,严禁游水、垂钓”。饥饿袭击:翠鸟从正午的禁忌出发,抓起水面的糓纹,迅速而有力。
她嗓音甜蜜,细小嘴巴在树洞里铸造一把谎言的铁钩。冬天年老的垂钓者枯坐成景物,那阴翳眼神在树阴下画水。
鳄鱼
精心冶炼,黑暗水塘,大地几乎忘记它的存在,偷窥者潜伏在雨林的碎屑里。湾鳄的双眼从晴朗水平面突出,缓慢得如同新鲜的鸡皮疙瘩。打开世界之门,表情无辜而充满倦怠。
直至它那用旧的铠甲裸露,背部的缺口开始移动,或者整个村庄在倒退,狭长波纹在云朵里穿行。机械钟从失眠者的午夜突出,偷猎时光,以重复和惯性。与鳄鱼不同,它在光滑皮肤以下藏有狰狞的刺。
凯门鳄是外表斯文的暴君、沉默的独裁者:它的皮肤上坠着宝石,牙齿缝合如拉链,打哈欠时也打开半个身体。大多数时候,它饥肠辘辘,没精打采,不情愿地滑入沼泽,如同一台干瘪的潜水泵。
掠食者,捕猎之前“先用意念消化一下猎物”(阿雷奥拉语),然后,唾液自眼眶流出——咸水鳄是被忽略的井、生命收割机。机械钟也是一眼井,用细小吊桶捕捞昼与夜,那长短不一的牙齿,以及消化一切往事的漩涡。
猫(之一)
秋日草地里,一只肥猫,独自享用整个下午。阳光在它圆溜溜的身体上起伏,如麦浪翻滚。它的主人,修长的身体靠在短墙边,打盹。草帽似一架UFO,在苍白的石子路上降落。
影子伸了一个懒腰。
城市生活:或取悦于人,或取悦于己。中田先生却是个例外,它取悦于猫君——那些食人间百味却不食人间烟火的小兽。它们经常忘记了祖传技艺,热衷于装神弄鬼。你听,两只野猫合唱,旅馆隔壁是它们的戏仿者。
从绿宝石俯视里投射,魅惑。华贵礼服裹紧她的腿,漫步于仰视与鲜花丛中:白色、黑色或者花狸色的幽灵。随即,潮湿瓦楞上坠落一道闪电,那团暗火沉浸于自身的神秘。绯闻缔造者,她的一次回眸让所有异性安静。
盗汗,梦游太虚——灵魂安歇之地,秒针短暂停顿,它披着橘黄色灯光走来,月色长满小径。突兀的“嘀嗒”声长成气根,巨大的睡眠的榕树枝繁叶茂。斯芬克斯无毛猫,在它海边别墅里的石制寶座上,升起一颗残缺的头颅。
猫(之二)
镜头放慢,上升中稠密的雪,狂欢。凉亭华盖,黑猫优雅跳跃,整个上午都滑动着它的绿宝石。杂乱奶油,涂抹蛋糕最顶层。春季假唱者,世界仅有的黑皮肤,它试图保存这珍贵物种——雪野的唯一缺陷。
怕冷的春季时装周,各色毛皮在电音里复活,鲜嫩河蚌披着苍老的外壳。雌性散发着致命气息,她们的目光像无数利刃,把T台下的一切无情屠宰……
在裙裾里逶迤,道路尽头的回眸。微笑从片头剧情里坠落,目光富有弹性,歌声慵懒。似乎并不需要额外的装饰,它本身就是一个动词,活在假设里。比喻,更多时候,它是一些粉末状的药剂,让异性在午夜里癫狂。
把纷繁的上午小心舔食,时钟蓝宝石,在瞳孔里冻结。或者,谣言闯入,世界仅有的黑皮肤,变成条状花纹,变成焦虑。池塘泛起规则的波纹,忽又闪念,梳理中的平滑毛发,变得斑驳、棕黄、凛冽。
那随着呼吸起伏的肋骨,寄居着猛兽,让人顿生恐惧。
蛙
从树林里、草地上以及池塘边射出自身。运动和静止一样猝不及防,哦,那可怕的拳击手套。万物毫不知情,它的致命手枪——一个伪君子,在枣树发情的季节,享用廉价的巴菲特午餐。肉食者的双眼凝视并突出,有如一对车灯,在黑暗中窥视,直至蝉噪升级为空难,蓝夜埋没于井边。
在古井里,被一句成语揶揄,无法还击。后来,它们毫不在乎:使用池塘扩音器,与金龟子、扁担钩、胖蝼蛄和稻草人合唱。水缸里或者牛皮鼓里蒙蔽的第六感,它的锯齿状歌声令流浪者无法思考。
秋天试着让一切孤立,铜质荷叶矩阵,新筑的鸟巢,悲伤的壁虎,严肃的雕像。直至冬天,柔软淤泥里,青蛙在自身的精美刺青中熟睡。那天,我用雪白钢铁切开大地的沉默,一小面侧壁,不规则地布置着佛龛。握住一只青蛙,如握水中玻璃,光滑身体让人来不及尖叫。它的细小骨骼让人想起婴儿。
马
半匹马穿过冬天的乏味,独角在陶土器皿上休息;吹鼓手围绕广场,纸质心脏容易共鸣;废旧池塘突然长出鱼类和青苔,石膏的阴霾无法掩饰那些情绪裸露的马,举着自己的骨头行走在街道上的马,送行者在十字路口狂欢。
音乐喷泉:从此经过的,有美妙的长发,也有屠夫的低吼;所有人都隔着误解和时间,品尝更加模糊的歌声。我却只关心岩石中唯一可能的动物,黑暗里不断磨损自身的白马。
新闻:湖豚放慢了灭绝的速度,鲟鱼却不告而别。幸亏此时,普达措,更简单的月光投掷,一匹黑马,在草地上漫无目的地摩挲。
阅读到底裹挟着什么,或者,写作能够兜售什么:一个神圣的阴谋。纸马、石膏马、铁马、白马、黑马真能概括所有的马?
鹅
全副武装,高昂起充满隐晦的脖颈,独自饮用夕光中破碎的金。强有力地跨越河流——雨后车辙,一个优雅的趔趄,翅膀不由自主地弹出,像是一架迫降的轰炸机。紧接着,它的傲慢在泥泞的小路上继续蔓延,毫无节制。
一只鹅统治树林,朝霞在额头隆起。高视阔步,如同肥胖贵族,巨大脚趾在溪边画下一连串枫叶。一群鹅排着狭长的队伍,拒绝飞行,拒绝跳跃,拒绝相互抄袭。看起来有些杂乱的摇摆,律动而富有弹性。尚未进化出膝盖的族群,肥硕肌肉收缩,如一把曲柄——或者烧鹅店里的彩照。
会移动的白色高尔夫球杆,把一个下午消磨在水塘里,它脚掌的桔黄,使整个秋天清澈——那挂在水面以下的果实。年幼的骆宾王,把池边的儿歌念了一千多年。然而,世界怎么了?曾经的乌托邦,曾经的叛逆者,曾经的参议员。面对舞台和话筒,只能以沉默酝酿山洪。
不必试图与它们争论,那些大嗓门,一旦开口,就必将大获全胜。直至青砖墙外的夕光中,泥泞小路上,一群鹅被顽皮儿童追得走投无路,开始学习飞行。
斑马
受困于自身的条码,那健硕臀部,无与伦比的弧线,正如古籍上说的“夜照白”;又或者是穿着紧身睡裤的女士,那互相平行的图案在夕光里踱步。
侧耳倾听,枯草的些微摩擦声,雷暴还在远处酝酿,水源已经枯竭,平原温暖却并不友好;地板发出丝丝不祥的哀鸣,尤物,在凶猛凝视里被提前撕扯和享用。
斑马静止时像裸露的油页岩,或者覆盖条形桌布的晚餐,不对称的食欲;像披着条格状雨衣,互赠必要的礼貌,湿漉漉的脸下垂,然后互相触碰,嘟囔了些什么一一
令人不快的坏天气。
巨大的中午包围着被拆除的树林,以及山火或者洪水筛选过的土壤,斑马随时准备把剩余的草地装进身体,以修缮它最与众不同的皮肤一一
如何区分,沐浴中的女子?
多彩世界的反对者。过滤所有光谱,如一部黑白电影:吞噬周遭,然后释放被洗涤过的景物。草丛以及灌木,因斑马的出现而饶有生机。那眩目栅栏如一架钢琴,突然启动,跳跃和吵闹,戛然而止。纤细绒毛在微风中涌动。
斑马,就是画着脸谱的驴,或者涂着硅藻泥的姑娘。
灰喜鹊
下雪时,窗口干净地悬挂着几只长尾夹,灰喜鹊近在咫尺,它们的圆眼睛灵巧眨动,干枯的树枝在风中自在摇曳。夜晚,它们是蓝色栅栏之间静止的传教士,宽大道袍立在黑夜里,像一尊雕塑,弦月要包围不属于它的一切。灰喜鹊的沉默,是无法逃离的寂静隐喻,直至暗夜穿行者用一连串咳嗽击碎平衡,风开始弹奏那把竖琴。
苍老街道,他的十字形佩剑在黄昏里排列整齐——路灯亮起。燕尾服的自由落体,歌剧的开场白,灰喜鹊稳稳着陆,为此,草地升起白色三角旗——鸽子惊飞。
患白斑病的梧桐在暮色里诵经。拥抱艾蒿,灰喜鹊优雅踱步。虔诚耕作者小心移动步子,田地里是一串串“人”字形祈祷。一定存在某种联系:时间在建筑外墙上的锯齿状画作和灰喜鹊的双节奏鸣叫中流逝:“咔哒……咔哒咔哒……咔哒”。这是雨季来临前的最后一次礼拜。
菜畦边,机井木把手高高翘起。晨光里,似有物体自树林顶部快速脱落——滑翔和停靠富有韵律——那电线一端的高音谱号,余下空白处,似乎永远缺少一只灰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