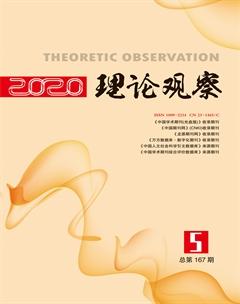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挑战与应对
李洋
关键词:香农模式,国家形象,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04 — 0124 — 03
一、作为分析框架的“香农模式”
美国数学家克劳德·香农在其著作《传播的数学理论》中提出了一种信号传输模型,后来在传播学中被称为“香农模式”。即信息通过信源编码转变为信号进入传播渠道,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克服外来干扰的影响,最终抵达信宿,通过对信号解码进行吸收,同时信宿对信源会有反馈效应。随着符号学的兴起,“香农模式”中无论信源对信息的编码,还是信宿对信号的解码,都与符号的建构与解构,传播与阐释之间产生了广阔的交集,为我们利用“香农模式”作为分析框架探讨国家形象传播创造了跨学科的空间。
二、作为分析对象的“国家形象”传播
国家形象是一国获得的相对稳定的评价。构成国家形象的要素有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指构成国家生存和发展基础的自然和物质条件,即硬实力。精神要素主要指国家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影响力,即软实力。国家形象具有整体性,存在多个维度,具有稳定性和可塑性。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决定不同国家建构各自国家形象的传播活动之间存在排他性。
参考“香农模式”,在国际传播活动中,国家形象存在于信源、传播渠道和信宿三个空间内,即一国(信源)要建构的国家形象,传播渠道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国家形象,以及由他国受众(信宿)通过解码进行阐释和理解的该国形象。
国家形象建构除了上述自塑的形式,还有他塑的形式,即其他国家对该国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在实际操作中,国家形象主动的自塑与被动的他塑扭结在一起,体现为两种传播活动在具体传播场域中的互动。
在受众一端,一国形象是自塑和他塑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互动过程展开的传播场域并非仅限于大众传播媒介,还包括长期以来受众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和宗教环境。这其中包含着一国长期积累的形象特征。这些传播场域中的环境因素在很多情况下形成受众对一国的刻板印象,影响着自塑和他塑的策略选择与呈现形式。所以,现实中“香农模式”的传播链条往往叠加,传播效果不断反作用于信源、渠道和信宿。这既是对传播环境的积累,也对未来传播活动形成反馈和影响。
三、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挑战与成因
我国的国际传播活动中,作为信源的国际传播媒体和负责对外叙事的单位对国家形象的编码程序和目标高度趋同。它们希望外界了解到的中国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迅速的,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但在受众一端,尤其是西方国家受众那里,由中国自塑建构的国家形象信息在传播渠道内受到来自西方媒体较大干扰。受众所在传播场域内存在着中国的刻板印象。中国的国家形象往往走向负面,被视为实施落后政治制度的异类。中国的崛起被刻画为对西方的威胁。例如,中国为此次新冠疫情防控做出巨大贡献,但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却将其塑造为罪魁祸首。以“香农模式”为框架分析,上述中国国家形象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出下列原因。
首先,西方受众所处的传播场域中基于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各领域内长期占有统治地位,对任何非西方的信息要素都会产生排斥和异化作用。西方媒体及文化传播机构对中国信息符号的误读在客观上也加强了这一场域内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这些因素对中国自塑渠道的形象产生了明显干扰。
其次,中国国际传播媒体和文化传播机构在海外的话语权不高,传播渠道有限,信息抵达率偏低。尽管中国大幅提高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领域的投入,但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依然在议程设置能力上存在较大差距。在针对第三方国家和国际热点事件的传播上,发达国家占据了国际舆论场的主动权。我国还未形成发达的国际传播网络,无法对第三方受众形成有效的服务、争取和说服。
再次,中国的信源在围绕国家形象符号进行编码和传播时,未能充分考虑受众所处的政治和文化差异,因此信息产品很难被受众有效解码和阐释。我国的国际传播单位普遍缺乏对受众反馈和市场需求的调查,无法及时调整传播策略,造成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差异明显,如何将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和符号转化为符合西方受众接受习惯的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给国际传播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最后,中国能够作为有效和可靠信源的国际传播参与方较为单一,以国有媒体和对外文化传播单位为主。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在国际舆论中占据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参与方的多元化。它们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合力。以美国为例,在媒体层面,不仅有美联社、彭博社、《纽约时报》、美国之音这样的市场化及国有媒体的参与,更有诸如好莱坞、美职篮等文化体育市场的行为体作为信源,智库、出版机构、社会组织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多元的参与可以保证对“香农模式”涉及的整个传播链条和网络的有效覆盖和干预,有效降低目标受众因为政治和文化差异产生的梳理和隔阂,从而实现信息输出的多元化,同时依靠市场调节机制还可以形成有效的傳播效果反馈。
四、如何应对国家形象传播的挑战
新时代下,为建构国家形象创造了历史机遇。经济全球化加速,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家现代化和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世界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推动包容性增长,及减贫和环境治理上都有重要作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关系格局中地位显著提升。我国参与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的步伐加快,在一些地区和国际重大问题上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着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相关实践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这些有利因素为应对上述挑战创造了条件,也为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提供了现实素材。
要把这些机遇转化为能够被受众有效解码和阐释的信息符号和叙事方式还需要各方的调整。根据“香农模式”,就如何在国际传播活动中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分众传播。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国家形象传播活动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传播主体应加大对受众的分析;在针对不同国家制定和实施不同传播策略的基础上,对重点国家内部受众分化程度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分析,有的放矢地影响那些可以争取的中间派,坚定果断地回击那些敌对派,积极主动地扩大友华派。对受众的分析是编码和传播策略的基础。做好分众化传播有利于提高传播效果。传播主体还应注重通过第三方市场和民意调查机构制度性地针对具体议题和媒介事件进行传播效果调查分析,不断改进信息产品的生产模式和投放机制。传播效果分析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问题和不足,不应主管夸大传播效果。只有客观地建立起受众对信源的反馈机制,才能让“香农模式”形成“有传播-有反馈-与应对”的开放式的良性循环。
第二,多方参与。形象是一种客观基础上的主观印象。中国国家形象需要依靠精彩的中国故事,精巧的中国符号,晓畅的中国话语,有效的中国方案和独特的中国智慧去一步步建构。这些元素的编码和传播过程应该有多种信源和社會行为主体共同参与,发挥所长,在各自领域形成合力抵御传播信道中干扰,确保解码和阐释的过程尽可能按照信源的编码程序展开。中国的智库、出版、电影电视,以及体育、电商、游戏、社会组织等行业在塑造国家形象上比传统的国际传播媒体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大的自由度。2020年3月在美的中国媒体被美国政府认定为中国政府“代理人”机构。这再次说明中国的国际传播必须让参与方更加多元,利用市场机制建构国家形象。
第三,重视社交媒体。不论是分众传播,还是多方参与,以社交媒体兴起为代表的媒介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为这两者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尽管社交媒体有明显的去中心化特征,但微观层面看“香农模式”依然适用,只不过传播链条更加扁平化,传播网络更具延展性。鉴于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国家治理和人际交流领域扮演的重要角色,特别是社交媒体本身具备的强大的议程设置的能力都决定了社交媒体是构建国家形象的必争之地。但当下主要的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均为美国企业控制,其数据库和技术研发核心也都在美国。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既需要鼓励国内各参与方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加大融媒体产品的投放力度,积极主动地设置议程,参与国际舆论战,同时又要大力鼓励诸如“抖音”国际版那样的中国自主的社交媒体平台走出去,尽早形成属于自己的平台。
第四,调整叙事方式。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都迫切需要转化为有效的国际传播叙事才有助于将其转变为建构国家形象的具体载体和范本。但很多鲜活的好故事被僵硬的叙事和苍白的话语变成了宣传材料,表明我国在做和说之间存在的传播鸿沟。政治和文化可以有差异,但好的叙事方式归根结底必定要遵从逻辑和理性,才能最终诉诸感性。因此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活动叙事方式应区别于单纯的对外宣传,应在贴近中国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努力贴近目标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他们的思维和接受习惯。这样才能在“以我为主”和有效传播间实现动态平衡。既不是自说自话,又不是一味地迁就目标受众的口味。好的传播是在受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的。对信息的编码、建构、传播、抗干扰、解码、阐释和反馈诸多机制都应与受众的需求、传播活动的规律、文化产品的市场和国际舆论热点的发展相契合,更多的时候是在乘势而为的过程中满足需求,获得信任,设置议程,传播价值。
第五,实现从宣传本国到解读他国,从信息传播转向价值传播的转变。要减少传播渠道和受众场域解码过程对信息阐释的干扰,就应努力获得国际受众的认可和信任,因为对信源的信任可以大大降低信息传播损耗和接受成本。因此,我国的国际传播要从宣传本国逐渐向深入报道和解读目标受众国家转变。我国媒体可以充分发挥外来者的优势,以独特的角度深入报道和解读相关国家的舆论热点事件,还应更多地把注意力转向对第三方国家和国际热点事件的阐释和评论上。以美国为例,美国关于本国的报道和解读多是为了国内受众打造的,而美国对他国的报道和分析出了服务部分本国读者的需求,更多地是为了海外受众量身定做的。这样做不仅体现了大国应有的视野与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姿态,也为国际传播从单纯的信息传播向价值传播创造了条件。
事件本身的多义性决定了以事件为基础的信息传播在编码、抗干扰和解码过程中往往更容易被歪曲和误读,而附带了价值关怀和观点表达的传播行为则更容易保持其本身的刚性和展现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国家形象建构归根结底是对国家软实力的宣示,是对一国制度和精神价值和文化魅力的传播,是国家间围绕具体事件抢占道义制高点的竞争。因此,国家形象建构应更加紧密地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注重在国际视野和国际事件中突出我国的价值关怀。
〔参 考 文 献〕
〔1〕 〔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2〕 张坤.国家形象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Claude Shannon and W. Weaver,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49.
〔责任编辑:杨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