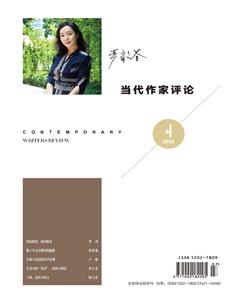英语世界王安忆小说研究的社会历史视角探析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不仅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而且具有独特的创作风格与卓越的创作成果。王安忆小说引起了海外,特别是英语世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學者立足于西方视角,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对王安忆小说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研究特色,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英语世界研究者非常注重从社会历史角度对王安忆小说进行研究,其成果具有重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对国内的王安忆小说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对王安忆小说历史观的分析
英语世界研究者高度关注王安忆小说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意义,注重从社会历史视角对王安忆小说进行研究,对王安忆小说所体现的社会历史演变与辩证历史观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解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华裔学者王斑(Ban Wang)。王斑在Position:East Asia Cultures Critigue(《东亚文化评论》)2002年冬季刊上发表了Ban Wang,Love at Last Sight:Nostalgia,Commodity,and Temporality in Wang Anyis Song of Unending Sorrow,Position: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Winter 2002),p.669-694.Love at Last Sight:Nostalgia,Commodity,and Temporality in Wang Anyis Song of Unending Sorrow(《最后一瞥之恋:王安忆〈长恨歌〉中的怀旧、商品和暂时性》)一文。该文以历史演变与历史观为主要分析框架,对王安忆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历史书写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是英语世界王安忆小说社会历史视角研究的一个代表性文本。
首先,该文分析了《长恨歌》怀旧情结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内容,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融入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怀旧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王斑指出,怀旧是《长恨歌》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国未来的几十年里,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怀旧情结是划时代变化的一个特征。这些变化可分为两个互相联系的支流:现代化和现代性。如果说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现代化这一概念只有模糊理解,那么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现代化已经并入了现代性这个大熔炉里。全球资本的大规模输入和市场能量的释放,加速了现代化进程。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和社会关系模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明显,强烈的现代化观念已经弥漫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现代化建设不断加速,它给人们带来喜悦和冒险的同时,也带来了创伤和损失。在这种大背景下,怀旧情结的出现就不难理解了。市场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消费社会快速崛起。现代性被视为是对未来社会结构的合理重建,但它却给人们带来了焦躁和不安,失业人数的增加,社群支持网络的收缩,这些都促使人们向往记忆中过去美好的生活,而属于这些年代的贫穷和残酷的生活条件却被人们抛诸脑后。
王斑还分析了怀旧情结在王安忆小说中的重要地位。王斑认为,怀旧是联结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史衔接点,怀旧是对底层野史、日常的生活世界与刻板的同质历史长时记忆的综合调用,应当揭示在统一历史掩饰下的未被揭露的鲜活的“自然历史”。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怀旧情结为遭受现代化折磨的受害者和它最积极的支持者都提供了一个缓冲器。人们需要找到处于过去却能预见未来的衔接点。因此,我们就有了怀旧情结,它不超越当前事务状态去挑战自己,而是设法去寻找一个衔接点,并以过去的辉煌来掩盖当下快节奏的发展。同时,存在于统一历史下的未被揭露的鲜活的“自然历史”从上海的多维城市影像中浮现出来。
其次,该文指出,王安忆小说体现了另一种历史——商品生产与商业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恨歌》主人公王琦瑶最初的故事也是商品化胜利的故事,王琦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上海商业文化的象征。她在选美比赛中一跃成为“上海小姐”,这是有效的大众传媒机制、可视化技术及市场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涉及电影制片人、摄影师、新闻工作者、设计师、公关人员与选美比赛的经理等众多人物。仅仅是因为比弄堂里其他女孩好看一些,不是风华绝代并缺少经济支持的王琦瑶却能被冠为“上海小姐”,她的成功是大众消费文化中形象生产所带来的结果。国民党军官把她包养作情妇一事也证明了她的商品化性质。作为一个对可替代暂时性“浪漫”的想象,怀旧情结不仅可被理解为对替代物品共同的心理渴望,还可被理解为位于统一资本主义矩阵核心的差异标志,并且这个矩阵由商品、劳动、交换和消费所组成。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也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文化发展的历史,其中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是我们分析与理解人类社会运动规律与发展趋势的钥匙。
最后,该文指出了《长恨歌》的主要贡献在于进行历史反思和确立辩证历史观。王斑指出,虽然《长恨歌》对上海的商业文化及其历史发展进行了详尽描述,但如果认为《长恨歌》是对商品经济的颂扬则是不对的。在他看来,这部小说的贡献首先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高度发达的新社会构架下,对历史进行的积极反思。中国在迅速实现市场化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就是深层次的中国特有的历史传统的消失。王安忆这部小说最大贡献就在于,它通过对上海近现代社会三个历史阶段的分析,确立了一种新的辩证的历史观。《长恨歌》这部小说三部分结构明确地展示了上海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以民族资本和市场经济为特色的现代时期、计划经济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时期。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怀旧者眼中,第一阶段商品经济的辉煌景象是现如今更欣欣向荣的市场的一面镜子。王安忆小说重拾了商业文化的重要残余,它也唤起了人们对20世纪80年代的记忆,这一时代对物质生活、民主和个人自我实现的热情,似乎与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相一致。这种历史变革把个人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把异质的社会生活变为同质的历史连续体。王斑指出,在王安忆小说中,在偏僻的角落里躲了30年后,王琦瑶作为一个真正的经典,一个被遗忘的传说,一个使所有的复制品都黯然失色的真实模特,终于强势“回归”。作者把回归这个词加了引号是为了使老上海和他所谓的复兴成为一段从未中断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时期的思想观念需要去发现这之前的历史,那就是浪漫的商业化上海景象。这样,王安忆《长恨歌》的历史书写就呈现出了上海这个大都市近现代历史发展中“否定之否定”“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
二、对王安忆小说新历史主义方法的解读
英语世界研究者不仅分析了《长恨歌》三部分所表明的现代中国社会三大历史时期,而且还指出,王安忆运用新历史小说的写作方法来表现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并且,《长歌恨》不是通过抵制商品经济而是通过对其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唤起人们对老上海的商业文化记忆来达到这一目的。小说试图去营造一种尽量接近真实的氛围,以平凡的叙事表现其重大历史意义。在王安忆笔下,无时间性的商品幻境转化成了由时间和记忆堆积起来的历史轨道。
英语世界研究者指出,《长歌恨》第一部分展现了解放前上海商品社会的奇观,人际关系、大众意识、人类欲望、日常生活,整个社会都似乎被商品及其无所不在的影响所渗透和统治。20世纪90年代,张爱玲在上海怀旧作家中广受欢迎,一部分原因是她能够把传统风格融入上海市民的现代生活中。王安忆继承了这种技巧,并且超越三大历史形态把它延伸到了一种更宽广的历史维度中,体现在王琦瑶身上的这种商业奇观的繁华社会,为怀旧提供了一个框架。这部小说历史书写的特征在于它把故事置于不同的时态中,王琦瑶和她的密友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歷史旷野里:一个是接连不断的革命性变化的历史,一个是沉浸于过去以商业经济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英语世界研究者还以王安忆对上海弄堂的描写为例,具体分析了她的新历史主义书写方法。他们认为,王安忆和她的同伴在弄堂这个拥挤的空间里创造出的这种仪式和传统,不是来源于中国传统习俗和习惯,而是来源于对上海物质文化的记忆,这种文化不以选美皇后、电影明星或豪华宴会为载体,而是存在于草根阶层。当外界正处于变动之中,他们却在狭窄但整洁的公寓里通过茶话会活动来追忆往昔,在这些仪式性活动中,这种相互联系、团结、欢庆的亲密场景,是在瞬间中抓住的一刻永恒。他们的谈话中蕴含着一种互相慰藉的情感,暖锅里的滚汤说的是炭火的心里话。正是这种琐碎铸造了他们得以生活的港湾,使他们成为在风暴中得以幸存的一小股历史潮流。这种以日常生活为对象,以片段性乃至碎片化的叙事方式为特征的历史书写,显然属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写作方法。新历史主义小说是历史外衣包裹下的现实实在论的变体,它的兴趣在于探讨过去事件的偶然性、片段性,以及隐藏在人们记忆深处的东西。它不关注重大历史事件,也觉得没有必要去理解历史的发展动因。新现实主义小说只是纯粹详述个人的生存状况,其中的人物并不力图去理解和塑造历史,而只是一种有巧妙生存能力的幸存物去努力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幸与不幸。历史的发展就是一个编年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用中国人最喜爱的一句谚语来说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过去的历史时刻与现实的日常生活相混,于是它与让人沉溺的现在不可分辨。
2003年时,王斑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当代中国期刊》)11月刊上发表了History in a Mythical Key:Temporality,Memory,and Tradition in Wang Anyis Fiction(《神话线索里的历史:王安忆小说里的时代性、回忆与传统》)Ban Wang,History in a Mythical Key:Temporality,Memory,and Tradition in Wang Anyis Fic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Winter 2003),p.607-621.一文,重点从两个方面分析了王安忆小说历史书写的主要特征。
首先是从人们共同生活经历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来解读小说的历史书写特征。王斑指出,鲜活的历史就是:如果若干个男人或女人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们就分享了共同的经历,在过去的工作中他们互相帮助,他们对彼此来讲是透明的,因此他们的过去的共同经历并不会消失。他们并没有感觉到时间的不足,也不认为时间走得太快或者爬行得太慢。他们不会去抱怨某些事情来得太早或者来得太晚,他们没有注意过时间,他们共同的生活经历就是鲜活的历史,传统的礼制和节日或者是集体活动一再地把个人的回忆与集体的经历结合在一起。在这些新的文学形式下,生活经历就是鲜活的历史,作为一种共享的公共经历,人们的共同生活经历既疏远甚至脱离人们的社会历史,同时也贴近与展现人们的社会历史。
其次是从回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来解读新时期女性作家作品的历史书写特征。在王斑看来,王安忆、陈染等新时期女性作家曾尝试运用复苏童年的回忆来书写童年或青春期的经历,知己、自我与挚爱,这种回忆和有争议的个人化写作相关联。这种无意识的回忆可以与有意识的回忆和谐相处,而有意识的回忆就是在自觉地、理性地塑造生活经历。
2008年,纽约大学华人学者张旭东(Xudong Zhang)出版了学术著作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China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后社会主义和文化政治:20世纪最后10年的中国》)。在该书第四章“上海怀旧:王安忆90年代文学作品中的悼亡与寓言”中,张旭东也分析了王安忆的新历史主义书写方法。张旭东指出,在王安忆的小说里,上海既擅长隐藏自己的秘密,又擅长以最琐碎敏感的方式来揭示这种秘密。正如王安忆另外一些写于90年代的小说一样,在《“文革”轶事》中,她召唤出了一种超越阶级和社会盛衰变迁的城市生活的神秘性;召唤出了精致的世俗日常生活,它用自己的怀旧增补物,即一种消费方式,瓦解和吸纳了历史的震惊,取代了它的宏大叙事。张旭东进一步强调,在王安忆所有的上海书写中,读者可以感觉到不断出现的怀旧和忧郁之感共同编织了一个紧密的寓言空间。然而,怀旧和忧郁不仅仅是形式技术,两者都构建了某种情绪氛围,凸显了某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从王安忆笔下人物的世俗关切和世俗奋斗中被大声呼喊了出来。Xudong Zhang,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China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181-211.
2001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Chi-she Li写作了博士论文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Historical Fictions by Toni Morrison,Thomas Pynchon,Wang Anyi and Zhu Tianxin(《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想象——托尼·莫里森、托马斯·品钦、王安忆和朱天心的历史小说》),探讨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包含两个层次叙事的历史小说的新特征。Chi-she Li.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Historical Fictions by Toni Morrison,Thomas Pynchon,Wang Anyi and Zhu Tianxin,Ph.D.Thesis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1.该文首先探讨了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北美洲和东亚地区的历史小说,包括托尼·莫里森的《宠儿》(1987)、托马斯·品钦的《瓦恩兰》(1989)、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1993)和朱天心的《古都》(1995),把北美洲和东亚的历史小说放在一起,进行对位阅读。
Chi-she Li认为,历史小说是一種通过情节、人物和细节来结合历史趋势或催化事件的以文学类体裁为主的小说。在历史小说体裁中,一个过去时代的概念将代表个人发展以及群体或者团体的发展。换句话说,历史小说是由两个层次的历史叙事构成,即宏大的历史叙事及与此相继进行的小故事叙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进行日常生活小叙事的同时,反映全球化的大叙事内容。
在该论文第四章,作者研究了在历史主义城市的空间下王安忆等中国女作家的作品,并在其中看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效果,或者城市的局部全球化的生活状态。Chi-she Li指出,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是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寻找家族的根源。这部小说由两条主线构成,其中一个就是元小说性质中的“我”,以告白式的自传和“我”所幻想的上海这座城市中,从“我”的家族起源开始进行的关于穿越时间隧道之旅的故事。这部小说试图把城市生活的根源用告白的形式诉诸历史。然而,在故事的最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告白式的叙述是为了展现上海这个现代化的大城市。“我们”已经错过了风起云涌的英雄时代,“我们”只能作为平凡的人生存在这个城市里。自我告白式的叙述、忧郁的目光,都指向了一个在现代上海这座城市里不可能存在的田园式的家族生活。
三、对王安忆小说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分析
英语世界研究者们还阐释了王安忆小说所诠释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其代表性研究文本为王斑的《最后一瞥之恋:王安忆〈长恨歌〉中的怀旧、商品和暂时性》一文。该文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王安忆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历史轨迹及其循环性,这不仅显示出王安忆对有进攻性的商品形式中固有的可能性的高度敏感,也显示出她思想的开放以及批判精神。同时,王安忆向回忆和怀旧的转变,也可理解为是对快速退出视野的熟悉的生活世界的哀悼。即使这可能是一种固执的、退化的怀旧,她的作品仍表现出人们对现代化进程是如何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理解。最后,王斑指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描述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其一,信任和亲密的坚固社会关系被抽象为多变且冷酷的金钱关系;情感和伦理上的社会关系沦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其二,20世纪80年代的集体呼吁和五四启蒙运动都共同反映了一个主题:要求自主权。现在这个主题被分解为零碎的消费品和一时快感,并且被溶解为自由漂浮的“主观性”或精神分裂性的自我放纵。这些发展派生出大量的针对当代文学中回忆现象的讨论。
王斑在《神话线索里的历史:王安忆小说里的时代性、回忆与传统》一文中,主要关注王安忆小说里的神话力量,借助小说里的回忆及与它相关的传奇、神话与传统,对现代历史的加速发展进行评论。王斑援引英国历史学家、作家艾瑞克·霍布斯邦的观点指出,加速的现代文明进程打破了曾在过去把人类编织成社会结构的线程。这些社会结构是回忆的编织物,不仅包含人类关系和他们政治组织的形式,也包含各自特定角色的行为。由于人们越来越多地注重经济、行政和贸易发展,那个曾经连接个人与社会、过去与现在的价值基石已经失去了自信和凝聚力。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反思中,知识分子试图解构革命和民族的主导历史。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资本全球化的魔力下,这种对革命历史的解构被抹掉历史的自由消费主义所替代。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们试图到过去的生活中寻找答案,来理解现实和把握未来。王斑指出,作为一名作家,王安忆在时代变化的大漩涡里强调严肃对待历史。在1995年的《长恨歌》和2000年的《富萍》中,王安忆用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现代性,取代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现代化经历,用不同的写作风格去解读急剧变化过程中充满问题的疏离感、精神分裂和无根感。这种时空的转换是对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持续现代化的综述,它使我们看到一个“同质性的历史”是如何同时容纳资本主义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趋势的。
Chi-she Li的博士论文《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想象——托尼·莫里森、托马斯·品钦、王安忆和朱天心的历史小说》第四章以“忧郁的两个东亚大都市的历史: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与朱天心的《古都》”为题,阐明了基于中国历史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诠释了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城市叙事故事,以一个家族的“故事”寓言来预示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共同历史。作者指出,在东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必须提高这一地区的文化素养来应对这一时代变化的问题。东亚地区经济的后福特主义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资本流动的加剧,使中国各个领域的技术加速进步。王安忆认为对历史传统的改造是东亚跨国发展的主导性逻辑。传统文化是一个资源池,因而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处理自己的经济问题上存在分歧,其中一些人认为东亚国家必须走人类现代文明的共同大道,另一些人则认为自己国家社会和城市的发展不一定要重复西方的路径。因此,在一个传统观念与全球化的“灵活运用”一体化的可能性出现之前,我们还有一段颠簸的路途要走。
综上,英语世界研究者高度重视王安忆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研究,关注王安忆小说所体现的历史进程和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注重对王安忆作品的历史书写、历史反思与历史观的研究,阐释王安忆所运用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写作方法。英语世界从社会历史角度对王安忆小说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借鉴意义。中国研究者主要是从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研究,忽视了王安忆小说所体现的历史书写与社会价值。因此,我们应当合理借鉴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重视对王安忆等新时期女性作家作品的社会历史视角的研究,如对小说主题及内容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研究、社会意蕴的研究、传统与现代之间密切关系的研究,探讨作品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分析作品所体现的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分析作品所表现的各种紧张的社会关系。研究王安忆等新时期女性作家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趋势与社会变革问题的思考,能够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女性和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简介】于桢桢,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李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