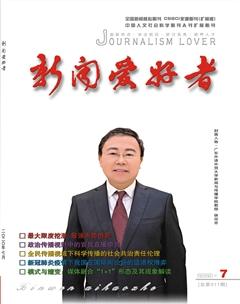何以为家,处处乡关处处情
王安忆的短篇小说《乡关处处》收录在小说集《红豆生南国》(2017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写的是一位从故乡绍兴乡下去上海做钟点工的女性。主人公月娥大约六十岁,小说集里三个中篇写的都是人生辗转、乡愁氤氲,但是与其他两篇身处香港和美国的主人公相比,月娥好像离普通百姓的生活更近,如同王安忆自己在谈这部小说时所说的那句话——“一棵草顶一颗露,出生为人,就得一份生计。”作为践行着自身独特美学观念和文学实践的小说家王安忆,始终关注平凡世界普通人的生计问题,月娥的故事从她一贯擅长的工笔细描里超拔出生活的世俗,酝酿出生存的诗意来。
一、流动的乡土——现实背景下的家庭离散图景
小说发生的背景一半在乡村,一半在城市,还有在往返城乡的路上,月娥从乡下到上虞再到上海,再回到乡下,总处在一个流动的状态。小说中寥寥几笔勾画出乡村的变迁:月娥的婆婆一个寡母带着六个小子“从四明山下来,参加合作社的农业人口登记,田里收成虽薄瘠,总比没有的好”。这是农村合作社时期婆婆那一辈人的乡村;月娥自己“有一点记忆回来了,欣欣然,勃勃然的喜悦——包产到户,分地分林,田里是牛犁的吆喝,山上斧斫声声”,这是大包干时期月娥和丈夫五叔这辈人经历的乡村;月娥的儿子“至今三十多岁,从来没往山里进去一步,就也不知道自家的山林在哪一片,有意或者无意,规避着命运的覆辙”,这是当下中国真实普遍的流动乡村图景,诚如王安忆的观察——“自给自足的日子依旧不够循环,这里那里缺了口子,需要进入交换经济。所以,男人必得外出打工。下一代呢,也是外出、上学读书,书上的知识多是关于山外面的那个货币世界”。曾经依赖生存的土地已经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只有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加起来才能维持一个农村几口之家正常的生产消费。进城务工的青年、留守乡村的儿童和老人、逐渐荒芜的田地和消失的篱笆,这样的乡村图景浮现在现实中和新闻里,也应该被反映在文学创作里。
王安忆这样写乡村人流动到城市“想不到什么时候,公路像一条鞭子,刷地劈开山崖树林,横在脚底,引得青壮年都往外跑,不几年,村落就只余下老的和幼的”,关注现实的作家敏锐把握到全球化后工业时代下人口离散、家庭难圆的政治经济现实,小说中月娥一家五口人分居四地,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这样的家庭是不完整的。类似这样分离的家庭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普遍特征,随着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布的大幅度调整,从乡下到城里,从县城到省会,从三四线到北上广,流动是当今中国的常态。在故事情节设计上,王安忆有意布局以春节后月娥的离乡进城为故事的开篇,又以春节前月娥的离城返乡为故事的结局,这既符合当代中国城乡人口迁徙的时间规律,又是作者企图赋予乡村离散家庭完整性的情感表达,小说中这样描写春节由城返乡的流动“过年回家,夜半起身,肩上挑根扁担,硬是从长宁走到南站,去乘火车。乘的是慢车,一走一停”。这样的返乡场景发生在春运期间的绿皮火车上,发生在飞驰的高铁上,也发生在数十万铁骑大军的摩托车上,这种返乡是流动的中国人在年关所做出的共同选择,和月娥一样即使历经艰辛也要回家过年的人们用春节团圆的仪式感来实现家庭的完整性。
写现实中农民个人和家庭的流动,王安忆在美学上处理了当下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全球化时代里人的漂移和家庭的離散,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当下的土地流转,时代的变迁给农村社会和农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作为知名作家的王安忆关注时代变化下的乡村流动,思考劳动人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塑造出新的审美意象。
二、劳动的女性——日常生计中的市井人物刻画
在王安忆笔下,月娥是钟点工,是大城市底层平民生活里的普通劳动者。曾经城乡二元区隔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不是被看成一种“职业”,而是被看成一种“身份”,市场经济发展到当下,公平、平等、开放的要求赋予月娥作为一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她一天做五份钟点工,住所就在和独居老人同住的格子间里。这样的生活无疑是辛苦的,可月娥作为一位年过六十且不识一字的农村妇女,在商品经济社会里能立足下来——“一个月至少赚七八千”“一分一厘赚来,攒起,带回家”。月娥用自己的劳动在现代社会谋得工作岗位维持家庭生计,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践行了王安忆所认可的小说不应该忘记“生计”问题的创作理念。
而对如今的境遇,月娥是满意且庆幸的:“幸亏,幸亏走出来,看到大世界。倘若不是这一步,少赚钱不说,还错过多少风景,岂不可惜死!”月娥有着朴实积极的生活哲学和吃苦耐劳的生命底色,她最不愿错过的风景正是自己的生命风景。王安忆笔下的底层世俗写作,在满足温饱和生存欲望的同时,劳动者同样拥有敬畏、同情、善良和爱的能量,这些能量落在生活的艰难实践之中,也落在有情之人的见证之下,带来新的生命力量。如评论家们所指出的“月娥在生活的历练下把日子过得踏实而欢腾,浓浓的烟火气、人情味和昂扬的生命力,支撑起《乡关处处》里丰厚的精神天地”,月娥从初到上海时因不识字心生的胆怯,到熟稔地骑着电动车像条鱼灵活地穿行在车阵里,作为读者看到这样的转变是欣慰的,因为这不仅符合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再现,也符合中国人古老基因里默许的天道酬勤观。
小说擅长刻画劳动的细节,比如月娥在工作中学到了用小熨斗伸进袖筒周转着熨衣服的场景细腻生动,还有月娥在返乡后收拾家务的几处描写行云流水,充满着日常生活的气息,也流露出真正家庭生活的烟火气。这些日常劳作经常被人忽视,而联系到全球疫情影响下个体需切断依托外界外力回归家庭日常的现实,才让人感受到生活中这些烟火气的劳动才是生命的底蕴,诚如王安忆所说“持久的日常生活就是劳动、生活、一日三餐,还有许多乐趣,这里体现出的坚韧性,反映了人性的美德。”这是王安忆小说审美创作中建构的“日常生活里的庄严”的体现。
三、感动的情谊——世俗生活中的恒常人性书写
小说里,月娥的第一份工作来自同乡的举荐,她在同乡的帮扶下熬过初到上海的日子,与大都市里“上海的人就是海里针,手一松就没有了”的无常相比,乡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知根知底,有着稳定的情感羁绊。而在极其重视乡土观念的江浙一带,离乡在外的村人用工只在同乡人间互相介绍,分租房屋,休息日玩耍,也只和同乡人搭伴。如费孝通所言,这种乡土社会里“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互相拖欠着未了的人情”。这种稳定的情感羁绊在王安忆看来,代表了一种人际关系的理想,成为流动状态下形成共同体的准备,也是对家的替代。
王安忆试图以一种独特的逻辑重建人与人的关系,除了描写乡土情谊,她也用这种情感处理“陌生人社会”里的经济关系。《乡关处处》里月娥照顾着独居老人“爷爷”,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般对待,称爷爷的女儿为“大妹妹”,爷爷的儿子为“小弟弟”。当爷爷的女儿嫌月娥照顾不周时,两人将二百元钱掼来掼去,“不像是主雇,倒仿佛一对负气的姊妹,计较赡养父亲,谁付出多,谁付出少”。而在爷爷住进养老院之后,月娥张罗周末休息时把老人接来共聚一餐,让孤独的老人感受到陪伴的温暖。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正气十足,和善亲切,在日益喧哗、物质至上的都市空间成为难得的佳话。
小说中月娥始终以乡土社会的温情与他人交往,这让她到哪里都可以随遇而安,故事里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月娥和她捡到的一只流浪猫之间的情谊读来也让人动容,这只毛色雪白,一只白耳朵、一只黑耳朵的猫崽被月娥取名叫做“爹一只娘一只”。随着月娥换工作、搬家、返乡,猫的住所也随着月娥的流动而变化,它的脾性也如同月娥一般,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极强,仿佛应了爷爷所说的那句话——“谁养的像谁,很快它就会踏电动车了”!在都市变幻流动的时间和空间里,物种不同、境遇相似的人和猫有着共同的失落和对家的向往,这种跨越物种的情感交流,形成了新的共同体,重新定义了故乡,也是王安忆用樸素人情协调传统乡土与现代生活之间关系的美学理想体现。
四、结语
小说发表于三年前,评论家们广泛指出“《乡关处处》的故事没有重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伤感,而是秉着对最平凡生活的敬意,生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达观。”这份感情真挚动人,是王安忆致力于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美感与温情的产物。在充满变幻、流动和不确定性的当下,飘零和离散已成为某种常态,如何让城市与乡村获得和解,重建亲密的关系,如何克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裂,重建健全的社会,王安忆选择从民间世俗人生中汲取永恒的价值,写下这个以寻常生活打底,包裹着恒常人性的温暖故事,有助于个体读者唤起对日常生活的热情,进而坦然面对高低起伏的人生境遇。
当然现在看来,《乡关处处》这部小说中内含空巢老人、夫妻异地分居、养老、低保、外来人居住难、春运等问题,现实中这些问题依旧没有离我们远去,需要政治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以理性的角度直面问题本身,需要更多的创作者们从现实生活中打捞素材加以呈现,也留给普通读者足够的空间去思考体悟。而这其中,真实地反映出其间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感情世界,也许就是王安忆笔下现实主义题材小说的魅力所在。
(郑思宇/文学硕士,河南工业大学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