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讲道理说服一个人,怎么就这么难?
沈大园
越来越多人抱怨,在社交媒体上,愈发没道理可讲了。这事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比如从前的互联网恰好集中了最诚心诚意讲道理的一批人,以至于它的讲道理指数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就像茨威格的昨日世界,美好时光说没就没了。我们当然仍可以往好的方面想,比如即便是今天,互联网仍然要比外面的世界好一些。因为在网上,大家除了认真辩论,能动用的最恶劣的手段无非是举报封号,虚拟身份被杀死总比人身受到伤害要好。既然额外手段有限,道理的权重就自然高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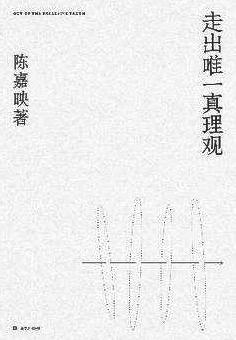
这么看多少有点灰暗,我从哲学家那里学到另外一个角度——不要对讲道理的效果期待过高,想通过讲道理来达成共识或到达真理本就不是易事。这本《走出唯一的真理观》是陈嘉映教授的新书,其中许多文章都和说理、真理有关。有人说,陈嘉映讲的哲学老妪能解。这一说法按字面理解恐怕言过其实,他的书当然要比康德海德格尔好读得多,但仍须时不时停下来细细思量。这个评价不如说是,他思考的哲学问题,不是在奇怪名词里打转的那种,而是能切中我们真实的困惑。比如,想通过讲道理说服一个人,怎么就这么难。
摆事实讲道理,一定有用吗
从小我们就知道说话要摆事实讲道理,长大经常也看到这种修辞,“铁一般的事实”。事实似乎是一个特别确定且有力的东西,可曾国藩到底是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哲学家提醒我们,事实从来混杂着人的经验、感受、欲望一同向我们呈现,非得如此它才能被理解,所谓纯粹的事实只会让人迷惑。举个例子,我听说过一个关于“蜗牛”的离奇故事。1970年代初,中国想从美国引进彩电生产技术。于是派了一个考察团去美国调研几个关键部件的生产线,其中提供玻璃面板生产线的是康宁公司,如今我们手机上的屏幕大多也来自这家公司。一切都挺顺利,临走康宁还送了考察团成员每人一只玻璃蜗牛,以示友好,不料这酿成了一场风波。有人给江青写信,称送蜗牛是美国人在讽刺挖苦中国的“爬行主义”,江青抓住此事,坚称这是“丧权辱国”,要求把蜗牛送到美国驻华代办处去,并通过外交渠道正式提出抗议。同时她还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收受外国礼品的清查工作,查出送了乌龟的表面是祝愿长寿,实际是讽刺我们发展慢;送了黄牛雕塑的是骂我们“老牛拉破车”。作为最早批准彩电引进的国务院,只好硬着头皮应对,在请教了驻美使节和华裔学者、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后,外交部写了一份《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结论是:蜗牛只是蜗牛,建议不必退回蜗牛或进一步外交交涉。是啊,蜗牛只是蜗牛,说起来是个简单的事实,你却永远不知道可以生出什么理解。我们并非要一路退到“没有事实,只有解释”,但显然,想要靠摆事实解决问题是挺难的。那讲道理呢,某种意义上,大家都在“讲道理”,只不过“理”各不相同。江青找了一些事实,编织了一番解释,批评外交工作不力。外交部呢,找了专家,写了调查报告,说明蜗牛就是个普通工艺品,在美国是常见赠礼,并无什么阴谋。那事情最后怎么解决的呢?周恩来把外交部的报告呈给毛泽东,后者圈阅表示同意,事情就平息了。
虽然嘉映老师把哲学称为穷理的活动,但他并不因此偏袒说理,他提醒我们,“要改变他人的看法,说理不见得是最有效的手段。训练、实地考察、征引权威或大多数人的看法、恳求、纠缠,这些途径若非更加有效,至少同样有效。此外,还有‘不言而教,榜样往往比道理更有说服力。最后,还有宣传、欺骗甚至金钱利诱、武力威胁等等。”当然,如果对方并不真的有自己的看法,他是出于别的原因反对,那说理就更用不上了。
庙堂之事比较特别,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愿意跟反对意见说一通道理的,一则是指望通过说理和论证说服对方(因此难免对说理的效果期待过高);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我们下意识地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对方之所以持相反看法是因为他错误、愚蠢,甚至邪恶。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景象,某人声称自己在真理面前无比谦卑,但在转身向其他人讲述的时候,常常就变成了宣谕模式,像个口含天宪的传旨太监。
我们太容易把真理想成一个现成的东西,“发现真理”“掌握真理”这样的说法加深了误导,好像真理就跟传国玉玺似的,抢到了可傲视天下。对于这种误区,嘉映老师有服很好的对症药,叫真理掌握我们。他认为,“在一场诚恳的交流中,所有参加争论的各方都向着真理敞开心扉,等待着真理展现,让真理来掌握自己”。也许最后有一方是对的,也许都不对,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理赢得了争论的各方,而不是某些人战胜了另外一些。所以,讲道理这种活动如果有什么根本规则,那就是让真理显现而不是坚信自己就握有真理,想要说服对方可以是初始动机,但进入这个活动就得遵循规则。
现在的问题是不遵守规则的人越来越多,网上争论经常就变成了谩骂,有些人甚至不再论证对方是多么错误,而是直接攻击对方多么邪恶,至于他自己的立场,那是先定的,绝无商讨的余地。这就像下象棋,对方非说马可以走直线,要把你将死,自己的帅是不死金身,这棋无论如何他都输不了,但也玩不下去了。在这个意义上,不好好讲道理的人是无法被说服的。但我觉得,这并不是真理的损失,更不是苛责它的理由,我们应该对不守规则的人感到失望,而不是对说理求真失望。
在无法对话的世界里继续发声
如果对话并不能让我们达成共識,我们该怎么办?有一种想法是,那就从最基础的共识开始,一点点往外推,比如人都是求生存的,那把世界搞坏了对谁都没好处。把共存作为起点恐怕并不稳当,且不说有人就愿舍生取义,也还有张麻子这样的人,他会对黄四郎说,“没有你,对我很重要”。我们不能通过不断降低标准的方式,来求一个共识,这并不能克服冲突。
想要从一个基础出发,推演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理念大厦,这跟把道理当玉玺一样,都把道理想成了一个唯一和整全的体系,只不过达成的路径各不相同(后者常常是寄望于高度抽象,比如“道生一,一生二”)。真理在诚恳的对话中显现,但我们也不能像举行淘汰赛一样,两两辩论,胜者晋级,像得出总冠军一样得到一个总真理。正如书名“走出唯一真理观”所示,没有这样一个终点,当目的地不存在,走哪条路都到不了。那既不保证共识,也没有终极答案,对话还有意义吗?嘉映老师说,它能带来新的理解。
我想起有一档辩论节目这几年挺火,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办下去。有人因为它插科打诨太多,觉得失去了论辩的真义而不喜欢它。也有人是因为不喜欢没有答案,两方各有道理争不出结果让他受不了。辩论节目肯定无法达成共识或完成说服,否则就变成家庭调解节目了。不过更多人喜欢这档节目,觉得在好玩之外,选手们也常给人新的启迪。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那个辩手,拿到一个话题,选定立场。然后你要搜集资料,整理逻辑,甚至琢磨好哪些点上该用打动人的金句,这个过程必定让你对辩题的理解更加深入。如果你还有一个合格的对手,他的论证和反诘迫使你不断周全自己的立场、完善自己的逻辑,那真是再好不过。一场高质量对话带给你的收获,远大于多一个立场支持者,甚至让旁观者都受益匪浅。
我们有时候甚至需要依赖这种说理来构建和支撑自己。以色列也得跟巴勒斯坦对话、跟整个世界对话,解释它为什么需要在这里建国,它要做出论证、为自己辩护。有人可以说,所有的道理都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背后靠的还不是军事优势和美国的撑腰。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些道理对形成和凝聚以色列这个国家意义重大,没有它们就几乎不可能有这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不停地讲出道理回应世界的各种疑问,是至关紧要的问题,价值远不止于谈判桌。
但就像前面说的,现在最糟糕的问题是,有些人根本不愿意遵守规则,也就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对手乱走确实是没法下棋的,但下棋这个比喻会有点误导,正常下棋是摆好子,从一个齐整的局面开始,但实际的争论几乎没有从起点论的,都是有一个现成的局面、有一些确定的条件,这更像是面对一盘残局。在残局里,有一个相当的对手自然更好,如果没有,也不妨碍你自己一个人琢磨,精进棋艺。所以,就算眼前没有说理的对象,或是只有胡搅蛮缠的人,在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下,你仍然可以坚持说理,并且从中获益。
哲学家的论证到此已经足够完整,但我还有一些哲学以外的看法想添加进来。说到底,在网络上论理其实是面向所有人的,尽管极端的人总是最吸引眼球,当要说点什么的时候,好像就是冲着他们去的,其实听众还有很多,有些人是同盟,有些人摇摆不定,有些只是路人。你的言说不仅仅对自己重要,对他们也很重要。在公共领域坚持发声,就像是走夜路时唱歌,你知道到处是魑魅魍魉,歌声也许会招来更多攻击,但也会给另外一个行路的人安慰和勇气,如果他也不再沉默,一起哼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汇成大合唱。
我还觉得,诚恳地讲道理自有其魅力,它的求真精神、平等原则都让自由的灵魂一遇难忘。就像读过经典之后再难理会三流作品,即便人生不幸要以阅读糟糕的作品为业,也难以从心底抹掉这种审美能力。所以我们要保证這个图书馆里有好书,这对于新踏进图书馆的人至关重要。
有时候,对方不是不知道该如何好好对话,该如何求真,他们只是故意不做。我们无法诉诸更有力的手段,至少就我个人而言,图穷匕见既不在意愿清单里,也不在能力清单里,根本上这也不是常人该有的生活,但保持诚恳,坚持求真,拒绝沉默,在我理解,离了这些就难言正常生活。
(摘自6月11日《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