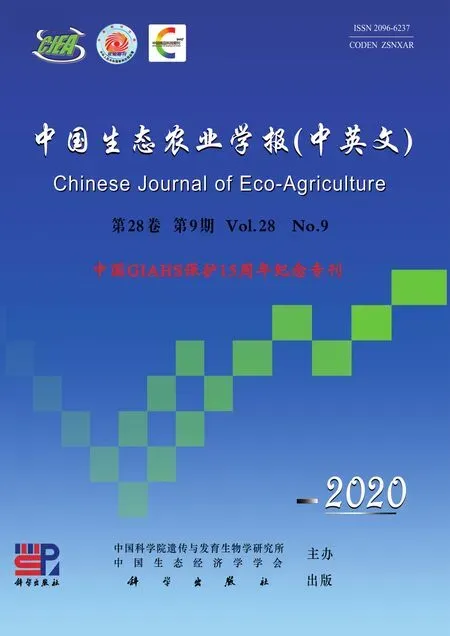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产业发展的价值研究*
吴合显, 罗康隆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产业发展的价值研究*
吴合显1, 罗康隆2**
(1. 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吉首 416000; 2.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吉首 416000)
由农牧民创造并维护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对乡村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其一,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蕴含有丰富的生物、技术和文化等因素, 深入认识这些因素在乡村产业中的地位和价值, 不仅可为乡村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而且还可推动乡村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其二, 充分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本途径。这集中体现在传统品种和知识技术的保护利用,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利用, 生态产品和现代社会消费群体的有效对接。其三, 创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些创新主要包括: 创新消费对象, 明确目标消费者的界定; 创新服务功能, 强化生态维护的价值; 创新服务内容, 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创新服务空间, 推广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各种资源; 创新服务手段, 发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国家政策充分结合的优势。总之, 借助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创新, 时下的乡村产业发展可选择不同途径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可持续性。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乡村产业发展; 保护、利用与创新
全球各地有着诸多独特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 这些系统不仅维护了农业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增强了生态系统的恢复力, 在数千年中给当地居民提供了经济、文化、产品与生态服务。随着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经济奢望的不断攀升, 这样的传统农业系统正在被旨在提高单位面积效率和规模发展的现代农业系统所取代。然而, 现代化农业引发的各种生态弊端, 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这些有价值的本土知识资源库的重要性, 其中就包括在适应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土地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丰富的传统文化[1]。为此,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 并提出动态保护理念: 农村与其所处生态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 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还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2]。
GIAHS项目旨在建立一种与其密切相关的生物多样性高、食品和生计安全以及文化景观优美的价值体系, 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和响应, 使之成为乡村发展的源泉与基础[3]。该项目启动之后, 中国有关的实践工作进展很快, 特别是从国家层面推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 取得了显著成就。从2013年农业部公布第1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现已公布了5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要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振兴, 关键在于创新利用民族地区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及其产品优势, 在外来资源的激发和调动下, 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产业发展的内生路径[4]。为此, 保护、利用和创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不仅有助于壮大乡村生态产业、提高农民经济收入, 还可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1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蕴含有丰富的生物、技术和文化等因素, 深入认识这些因素在乡村产业中的地位和价值, 将助推乡村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从而为我国乡村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由农牧民创造并维护的特定农业系统和人文景观, 其潜在价值已成为提高乡村内生动力的重要引擎[3]。作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农业系统与人文景观是各遗产地民众的生计体系, 更是其农业文明的创造, 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并切实加以保护[5], 确保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
不管是怎样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其技术体系无一不具有先民的在地性特点。所谓在地性, 就是指尊重所种作物的生物属性的前提下, 凭借世代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 对当地自然与地理环境, 特别是当地生态系统属性, 凭借先民们的聪明才智, 启动相关民族文化与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协同演化,达成所种作物与环境的互惠共存, 从而形成适用于当地相关作物与所处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 并实现相关技术体系的可持续利用目标。只要当地环境不发生改变, 当地各民族文化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那么这样的技术体系在当地就可以永葆青春。类似的文化、环境和作物的系统匹配关系, 还可以在类似的空间环境中进行推广利用, 并实现相关地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运行, 甚至实现现代化的创新。
湘西州花垣县“子腊贡米”已获得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立项保护。子腊村地处低山丘陵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中的低温沼泽湿地环境, 本来不适宜水稻()种植, 但该项遗产的技术体系却能使当地顺利产出优质稻米。当地自然环境下, 由于高山的阻隔, 丛林的隐蔽, 再加上大气降水绝大部分会穿越山体石灰岩的溶洞, 再以井泉伏流的方式, 成为山间湿地水资源的主要补给源, 水中富含从古生代海相沉积中溶解出来的磷和钾肥分,水质比平原稻田中的水质还要优越, 然而水温偏低是水稻种植的致命杀手, 因此在这样的沼泽地种植任何品种的水稻, 稻秧可以返青, 但不会分蘖。即使分蘖后, 由于终年水温保持在17 ℃以下, 以致于开了花, 也无法结实。加上这样的山间湿地, 四周都有高山环抱, 丛林隐蔽, 种上水稻后, 每天能接收到的直接日照, 平均不超过2 h, 强行种植水稻后只长稻秧, 不产稻谷。
苗族先民面对这样的环境, 自然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局之中。就是肥分不缺, 缺的是水温。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种植水稻, 顾得了水温, 却顾不了肥分; 顾得了肥分的充分利用, 那么偏低的日照和终年恒定的低水温, 又会让水稻只长稻秧, 不长稻谷。而此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技术特色正在于将当地盛产的原木采伐下来, 铺填在沼泽淤泥之上, 以期达到抬高稻田海拔高度的目的, 实现将井泉低温的凉水与山体坡面径流下泄的常温水分割开来, 从而弥补了低温水环境的缺陷。随着稻田种植面海拔提高数米后, 稻田水面每天能接收的直接日照实数也大致可以提高3倍, 达到每天6 h左右, 从而满足了水稻种植水温的需求。与此同时, 来自井泉凉水中所富含的磷、钾等肥分又可以被稻田下方填埋的木材所吸附。再借助水位的季节变法, 将这样的肥分上升到水稻根系的着生土层之中, 被稻田表面填埋的土壤所吸收, 水位下落后, 水去而肥留。这无异于在水稻着生的土层中, 设置了一套无需外加动力, 无需常年维护, 却可以做到可持续均匀施肥的地下人构装置。凭借这种看似粗陋的传统装置, 其精确性、低成本性和可持续收效性得到了全面满足, 堪称是一劳永逸的技术发明。
一些专家学者对这套技术装置的投入和产出, 至今依然多有顾虑。他们往往认为, 这样去营造稻田, 一次性的成本投入太大了。另外埋在地下的木材肯定会腐烂, 以后要重建, 花费的劳力和财力, 将会使当地乡民不堪重负。“子腊贡米”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成功后, 两位笔者亲自探勘了这批稻田的现有状况。发现只要赤脚踏进这样的充水稻田, 稻田淤泥中就会不断地冒出大大小小的气泡。与此同时, 捧起这样的稻田淤泥, 还会发现淤泥中所含的未降解的有机肥残积, 几乎找不到踪影。也就是说当年施入的有机肥, 当年就能全部降解。对此, 笔者的理解在于, 由于地下填埋的木材处于与空气完全隔绝的状态之下, 好氧类的微生物根本无法生长, 以致于明代造田时深埋的原木至今还在生效, 既没有腐烂, 稻田土面也不会下陷。其间的生物学原理在于当年埋下的木材, 只能支持厌氧菌的生长, 而厌氧菌所降解的木材, 却只生成CH4和CO2一类的气体。与此同时, 这样形成的气体本身也会形成静压力, 以确保稳定的稻田土层和优越的透气性能。CH4和CO2的气泡在水面破裂后, 又会导致土中留下的空间被表面的水所填满。这样的水富含O2, 可以支持水稻的生长, 从而不会烂根, 水稻也不会感染稻瘟病。稻田表层中的有机肥, 气体可以常态自动互换, 其降解速度比平原地区的稻田快, 而平原稻田土层中不同气体的自然交换, 得靠人力去翻动, 或者靠水生动物去翻动。因而其有机肥的降解速度反而低于子腊稻田。总之, 此项技术体系的优越性、可持续时效性和低成本性不仅属于古代, 也属于今天和未来。只要我们在低山丘陵带或高山峡谷地带种出稳产高质高产的稻谷, 那么这套技术体系就可以推广利用。如果要实现现代化的创新, 还可以动用现代化的建材和测量技术, 营建具有以上优越性的高标准稻田。建成的稻田不仅可以在山地环境连片布局, 甚至可以在连片稻田的周边, 架设硬化固定的钢轨。只要配上电动的农机具, 不需要推广拖拉机, 也可以实现山地农作的全机械化操作, 而且还可以实现土壤活性永葆青春, 当地的无机资源就可以免费就地循环利用。而且除了水稻外, 还可以随时根据需要, 轮作间作多种水生农作物。只要我们对待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思路, 真正做到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那么当前已经立项的每一种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不仅可以永葆其技术的青春, 还能为当代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既可传承, 又可创新的技术体系储备。有了这样因地制宜的技术体系, 乡村生态振兴的落实, 就可以做到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上述可见,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产业有着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 具有明显的可利用价值。对于二者的这种关联性, 国外也有一些成功的个案值得借鉴。意大利学者Mantia等[6]的研究表明,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农业生物多样性维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其他地中海小岛一样, 意大利兰佩杜萨岛(Lampedusa)的农业生产活动在20世纪下半叶急剧下降。因本土农业系统的消失, 该地区43种本土植物物种灭绝, 其中一些植物不仅在地方, 而且在区域和国家水平都是极其稀有的物种。该研究认为, 推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复壮与发展, 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农业文化多样性的维护是必要, 而且可行的。另外, 墨西哥学者Lira等[7]对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农民经营了数千年的一种称之为“Milpa”的套种制度[玉米套种豆类、南瓜()、辣椒等其他作物]进行研究, 认为这种传统农业系统不仅可以保障粮食安全、经济稳定, 还可以保护地方农作物资源, 保留许多与传统农业系统密切相关的作物品种。这些传统农业体系对维护本土技术价值、农业生物多样化, 以及乡村产业发展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上述国外个案对我国“三农”问题有很大的启示。长期以来, 受“现代化”的影响, 我国很多地区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方式, 直接引种外来作物品种, 放弃本土传统品种, 导致一些本土物种绝种。加上生产过程中过多施用化肥, 致使土壤肥力下降, 土壤污染, 生物多样性也面临严重的危机。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 各民族有着丰富的农业文化。因此, 如何更好地挖掘、保护和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推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实现中国农业绿色发展, 是目前应着重考虑的问题。而这样的发展目标, 恰好是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使命和担当。
韩国学者Choi等[8]认为, 保护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不仅需要完善保护制度, 还需创新管理政策和管理计划, 但前提条件是必须确保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持有人——农业生产者的积极参与。如今立足于乡村发展的需要, 则要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参与性, 高度关注和充分认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推动遗产地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合理转型, 使之有效地服务于乡村产业发展。
FAO启动GIAHS项目, 不仅在于肯定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 而且要借此指明未来乡村产业发展的走势, 特别是要强化人与自然和谐共荣关系, 倡导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 维护农业生物多样性, 保护乡村资源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9]。从这一理念出发, 加强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可为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如今, 随着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不断增多, 为乡村传统产业的发展和生态振兴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充分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本途径
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实质, 在于通过农业文化遗产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维护, 促进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适应了本土生态系统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通过遗产地农民对传统技术的管理与传承, 确保了地方粮食安全和农业多样性的维护。因此, 对其充分利用, 不仅可以稳定粮食产量, 促进粮食产出多样化并获取最大化回报[10], 还具有提高生物多样性、保障食品和生计安全、优化人文景观等多重效用[11]。
重视对传统农业知识技术的利用, 有助于提高乡村民众的生计能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经济效益[12]。而同时完善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后续工作, 有助于获得新的投资、技术、人才以及体制的支持, 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稳定的途径。可见, 充分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壮大乡村集体经济, 提高村民经济收入, 同样是推动乡村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Appendini等[13]对墨西哥瓦哈卡州(Zapotec)土著家庭的调查发现, 尽管平均总生产成本比市场销售的玉米价格高400%以上, 很多土著居民却坚持种植和食用传统玉米品种, 而非现代玉米品种, 原因是他们认为传统玉米品种不仅味道好、质量高, 而且还具有营养优势。由此看来, 制定我国产业调整中农产品价格的结构优化对策,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产品的价格定位, 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然而, 这些工作已远远超出农业农村管理部门的职能范围, 而是涉及整个国家的产业优化和匹配政策。如果相关配套政策不到位, 不仅会影响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利用, 还会降低其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服务成效。
闵庆文等[14]认为, 现阶段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核心内容主要是价值挖掘与多功能拓展开发、动态保护和适应性管理。因此, 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利用, 需要做出动态的应对[9]。即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服务于乡村产业发展, 需要对其升级换代, 才能达到有效利用, 但具体思路却值得深思。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方面是其自成体系的社会文化建制, 是人类社会与所处生态环境高度适应的具体体现, 有明显的生态价值; 另一方面, 因其源自传统, 必然与现代社会的需求存在一定差距。为确保其有效利用, 不可忽视其与现代化的结合。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服务于乡村产业发展, 其基本途径主要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
1)加强传统品种与知识技术的保护利用。农业文化多样性的体系, 包括从基因—物种—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尺度梯度, 从耕种方法到景观、文化的组成, 都属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内容。而传统品种在农民之间的流通, 对于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维护至关重要[15]。事实上,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涉及的生物物种本身就是作物育种的基因来源。
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 当地群众在对自然环境长期的适应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这些经验在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而且成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6]。如今, 成套的抗旱防灾种植技术、复合种植技术等, 都受到了现代科学家的重视。例如, Isakson[17]对上文提到Milpa套种模式进行研究, 发现这种农业多样化的生计方式, 有效维护了当地粮食和经济的安全与稳定。另外, Ferro-Vázquez等[18]对埃塞俄比亚孔所(Konso)梯田系统的研究发现, 当地民众能利用侵蚀来控制土壤侵蚀, 具体做法是: 收集被冲进河道的土壤, 将其储存在可灌溉的河边沉积区, 然后修建山坡梯田, 有效利用新的土壤“重新种植”被剥蚀的山坡, 让土壤侵蚀构成一种新的农业生产资源, 并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在我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甘肃永登苦水玫瑰农作系统”的种植技术在当地规模性推广。这里的玫瑰()种植生态系统十分独特, 其地处黄河上游的河谷台地, 上方是连片的荒漠草原, 而河谷台地地下水位相对较高, 土壤中丰富的地下水很容易渗出地面, 渗出的泉水因富含氯化镁而带有苦味, 其地名“苦水”也因此而得来。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 玫瑰种植技术也具有特异性, 地表覆盖、黄河水与泉水混合灌溉, 以防止土壤盐碱化。进而不仅确保了玫瑰花的优越品质和稳产、高产, 而且对所处生态系统的干扰也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为此, 传统农业系统的本土知识技术是农民的宝贵财富, 应该得到专利保护, 形成农业知识产权, 其拥有者还应分享专利补偿, 而且在这样的过程中,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持有者应该获得相应的法律援助, 并与乡村产业发展合并考虑。这样,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才更具可利用性。
2)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利用。在这一过程中, 各种各样的本土知识和技术技能要与现代的应用相结合, 这是历史的必然, 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求[19]。据此, 当代的信息技术和电商体制, 也应当成为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现代化手段。原因在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范围小, 总产量不高, 知名度的提升受到种种限制, 借助现代科技的电商平台, 不仅可以直销, 而且可以提高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产品的品牌效应和旅游产业的知名度。“品牌化”过去被认为是一种商业策略, 将其作为乡村振兴的一种途径, 目前还很少有人关注。其实, 本土品牌不仅是促进乡村发展的内动力, 还可以通过品牌共同价值观和品牌扩展共同效益而受益[20]。日本政府早在2004年, 就发起了“日本品牌发展援助计划”, 为地方社区寻找和培育区域品牌提供支持。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识别和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品牌[21]。Rausch[22]还对日本津轻漆器(Tsugaru nuri)和津轻三味琴(Tsugaru)等本土文化品牌进行了分析, 认为通过与具有时代意义的现代形式相结合, 大力推进本土品牌发展和提升品牌形象, 能有效带动偏远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当下我国的乡村振兴中, 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现代形式和技术相结合, 不需要太大投资, 就可以让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当地乡村产业发展中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
但是, 在推动本土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的过程中, 也必须注意到,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一项整体系统, 要实现对其有效利用, 主体必须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持有人, 应让现代科技和社会需求服务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利用, 而不是分道扬镳、本末倒置, 让现代科学技术去替代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换句话说, 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利用, 应当重视其主体作用, 推动二者的结合, 政府和科研部门只能从中起到协调、支持的作用, 而不是发挥主导作用。
3)加强生态产品与现代社会消费群体的有效对接。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文化模式》中指出, 自然环境的多样化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生计方式, 文化生活中首要任务就是进行选择[23]。其中就包括人们对食品消费的选择。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形成的产品, 虽然可以认定为生态产品, 但如何实现生态产品与现代社会消费群体的有效对接, 其间涉及到人们的消费心理问题。消费心理并非凭空而降, 往往也不是按值论价, 其间存在着文化偏见和误导。这就意味着, 人们消费心理的调整, 应当成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利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罗祎等[24]指出, 中国应建立以农业生产者为主体的政策支持体系, 加强对有机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 特别是加大对农业生产者和社会消费者的宣传教育力度。
我国拥有丰富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储备, 乡村产业发展要实现可持续性, 理应强化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有效利用, 充分发挥其特优产品的优势, 提高本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此, 发掘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有助于坚持农业育种的多元化方向, 克服过度追求产量的单一化育种倾向, 有助于实现良种选育的优质化、特色化、地方化目标; 重视传统优质品种的提纯复壮和推广利用, 形成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优势, 还有助于进一步发掘并利用好地理标志品种资源和农业良种资源[25]。
3 创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是农业生产系统和景观, 这种保护是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的重要创新和有益扩展[26]。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我国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创新工作, 不能只在保护项目数量上走在世界前列, 更要在社会经济效用上发挥重要的创新作用, 其中之一就是使之有效服务于乡村产业发展, 促使其成为我国农村农业振兴的必由之路。
时下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 大多是前工业文明类型的产物, 受现代集约化农业负效应的影响较小, 其产品质量可以达到生态产品和绿色产品的标准[27]。这样的质量就成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农产品的品牌效益和商业形象, 使其产品, 无论是农业产品、畜牧产品、林业产品, 还是相关的再加工产品, 都可获得高质量的产品认证, 从而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这样的目标一旦实现, 遗产地民众就可以在自己的地区内, 为其生态产品创造市场, 凭借乡村特色产业提高生活质量, 而不必再依赖国家财政的扶助[28]。因此, 如果通过国家层面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让国有企业对生态产品拍卖, 当地民众就可以从中获取合理的补偿,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更能直接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凡属传统都需要创新, 不会一直保持不变。在保持和创新之间, 必须建立起辩证统一的关系。乡村产业与当地生态环境协同演进, 对当今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价值。那么, 创新利用需要做的, 就是为传统提供服务, 而不是放弃或者置换传统本身。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推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服务于乡村产业的发展, 需要做好如下5个方面的创新:
1)创新消费对象, 做好目标消费者的界定。既然按质论价,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产品就理应以高价销售。然而, 这样的生态产品目前还只服务于高端消费群体。在整个产业结构没有实现全局优化之前, 普通民众只能部分分享这些产品。然而, 要确立更宽泛的消费对象,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立项仅是一种手段, 具体的市场运作, 还需要政府部门出台相应政策支撑。例如, 为大力推动农产品的销售, 日本政府将施政重点放在支持地方品牌市场的举措和政策上, 重视地方品牌的推广, 形成了把创新与现代灵感相结合的“本地传统现代性”(local traditional modernity), 使本土品牌成功推动了农产品的市场销售[29]。另外, 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到其产品市场定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都需要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广泛宣传, 树立高端特优农产品的社会舆论导向, 只有做到这样的创新工作, 生态产品高附加值的回报才能有望顺利实现。在这方面, 美国学者Altman[30]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生计方式的分析, 提出了国家、市场、传统“三位一体”的混合经济模式, 三者共同投入旅游、文化和产业等市场中, 通过国家政策等手段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2)创新服务手段, 发挥其与国家政策充分结合的优势。几个世纪以来, 许多精巧的农业系统塑造了新颖而富有弹性的景观, 并在此过程中维护了高水平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在很大程度上, 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支持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延续, 保护了农业生态生产的多样性[31]。从实质上看,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必然伴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遗产等无形资产[32]。而这些农业文化遗产的总汇, 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 如果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立项为契机, 并与我国时下推行的乡村产业相结合, 那么, 生态文明建设投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投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投资等项目, 都可以相继转化为农村群众的直接收入。为此, 无论是通过在这一过程中投工投劳的回报, 还是牵动的第三产业转型所带来的收益, 都可以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3)创新服务内容, 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创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服务内容, 不仅可以生产出优质的生态产品, 还可以形成持续优美的生态景观和人文景观, 借其品牌效应和产品质量效应, 只要做好服务转型并利用于乡村旅游,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就可以顺利地实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 进而为游客提供优质食品、休闲观光服务, 并从中获取合理的经济效益, 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社会基础和条件基础。例如, 日本大分县国东半岛(Kunisaki Peninsula)的乡村旅游发展就是很好的实证。2013年初, 日本国东半岛因其传统社会生态生产文化景观被立项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半岛曾是历史上的宗教与文化枢纽, 近年来, 由于遭遇了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正面临快速衰退, 通过推动传统农业资源文化景观旅游产业, 为该地区的乡村振兴铺平了道路, 特别是半岛低碳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农业在其间也发挥了巨大作用[33]。
这样的创新内容, 我国“浙江仙居杨梅栽培系统”同样得到证实。此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历史悠久, 声名远扬, 其生态维护价值难于估量。然而, 仅仅因为杨梅是一种保鲜和加工难度大的水果, 加工后的附加值低, 甚至加工后的使用价值还会明显下降。然而依赖此前的物流体系, 新鲜杨梅难于顺利到达消费者的手中。近年来, 当地居民借助乡村旅游, 让游客现场参与杨梅采摘, 就地消费。借以这样的经营方式, 此前的各种障碍因素都得到了有效化解。
4)创新服务空间, 推广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各种资源。一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 传承受阻, 甚至濒临灭绝, 但并不说明这些农业文化遗产没有价值。现代化背景下, 只要进行有效的创新, 其价值完全可以充分利用[32]。从实质上看,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传统知识和技术技能长期积累的结果, 无一不拥有整套的本土技术积累和技术配套, 也拥有相应的生态、生物物种资源。尽管一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明显的在地性, 但如果经过科学的论证和规范的试验, 各种资源就可以获得创新和推广的空间,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持有人也可以通过技术和知识的转让获得丰富的经济补偿。
关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各种资源的创新, 湖南保靖“黄金寨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就很有典型性。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吕洞山镇的黄金寨, 占地面积不到400 km2, 现存古茶树共5 923株, 分属108个株系。经专家认定, 这些古茶树并非当地原产, 但是能够保存如此繁多的品种, 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因此, 凭借遗产项目效应, 当地群众仅通过出售优质茶树苗木就可以获得比种茶更大的经济效益。而且, 这样的历史积淀还可以支撑当地成立一个“活态的茶树博物馆”, 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支柱。另外, 众多的茶树品种资源, 通过育种技术创新利用、升级换代, 对乡村产业的贡献将无可限量。不仅湘西州如此, 在我国其他民族地区, 水稻、油茶、生漆以及各种畜牧产品和林业产品, 都拥有极其丰富的品种资源和生物基因储备, 以及成套的知识和技术体系。如果能将它们申报立项的同时, 做到创新推广, 不仅能使乡村产业发展的效益更具可持续性, 还能确保当地农村农业产业的兴旺。
5)创新服务功能, 强化生态维护的价值。立项的重要文化遗产项目, 往往有独特的资源利用方式, 能够高效利用的同时, 兼顾生态系统维护。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既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典范, 那么在整个产业生产实践中可以发挥直接的生态维护功能。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地而言, 由于独特的地理区位, 其生态屏障功能更可以得到彰显和扩大。Naveen[28]对印度西高止山脉柯达古地区(Kodagu)进行研究, 认为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优美景观实施生态补偿(payment for ecological services), 不仅可以降低当地农民的贫困程度, 还可以为恢复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生态平衡和产业发展提供条件和机遇。如果我国能够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制化、常态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而且实施市场化运作, 那么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民众就可以凭借自己所从事并且熟悉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升级操作, 公平合理地获得额外的生态补偿。与此同时, 一旦有了法律保护、制度保障和规范市场的支撑, 乡村民众从中获取较好经济效益的同时, 还能获取生态维护的回报。
上述5个创新仅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直接效应而已。事实上, 各民族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有益于当地社会的建构与维护、民族关系的团结和睦、地方社会治安、社区家庭的有序运行。这些间接效益的实现, 对健全和完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产业结构, 以及对传统知识和技术技能的利用, 也照样能发挥效应。总之, 借助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创新, 时下的乡村产业就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途径, 确保其可持续性。但成败的关键则取决于人们习惯性思维模式的转换, 不能孤立对待项目的保护与创新工作, 而需要有意识、有目的地把项目保护与地方建设、第一产业地位的提升, 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 做到协同推进。只有这样, 农村农业的兴旺才能做得更好, 乡村生态振兴战略也才最终落到实处。
4 讨论与结论
“工业文明”是以追求利润为核心价值的社会运行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 发展工业可以在与自然环境基本隔离的人造环境里进行生产, 并把生产责任具体落实到人为创建的企业。企业所追求的是实现投资的最小化与利润的最大化, 导致了生产之外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相关问题。这样的发展模式已带来了工业文明的“负效应”, 造成人与环境的不兼容性, 并引发了各种危害人类生态、生计以及生命安全的灾害疫情。
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推进, 我国农村人口不断涌向城市, 造成乡村衰落、农业弱化、乡村产业凋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从2005—2015年, 农村人口从74 471万人下降为60 599万人[34]。另外, 有数据显示, 2005—2015年, 全国村民委员会的数量从62.9万个下降至58.1万个[35]。因此, 有效应对当下我国农村诸类问题,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势必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国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创新利用工作, 近年来虽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绩, 但仍然未能完整地反映我国农耕文明的特色, 还需要对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行深挖细掘, 进行多样化的保护与永续的开发利用[36]。过去因为没有深入认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生物多样性、食物和生计安全等方面的功能, 特别是在乡村产业中的基础地位, 对已立项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创新与利用方面, 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即使有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成功, 当地民众却没有从中获得较多的实惠, 甚至连其产品也难于销售。这就导致民众对自己拥有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完全没有自豪感。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 在我国广大的西部民族地区显得尤为迫切。随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日益凸显, 为乡村产业发展发挥效用的功能也日益强势。保持与创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也必将成为我国乡村发展的基本动力和不竭之源。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持有人在很大程度上不了解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此, 帮助村民深入认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 弄清楚保持与创新的实质则至关重要。总之, 充分认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就是要认可其产品属于高标准、高品质的绿色生态产品, 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如果这一思路没有把握好, 含糊不清, 不仅难于很好地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服务于乡村产业的发展, 就连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精髓和价值也可能会被置换掉。基于这样的认识, 探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持与创新的关联性,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就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乡村生态振兴。
由于我国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 因此发展过程中利用的途径、保持的传统、做出的创新, 不可能完全一样, 更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一刀切”地执行。只有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 探索适合自己的最佳途径, 才能实现农业文化遗产地乡村生态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1] KAZUHIKO T, OSAMU S, HIROTAKA M, et al. Resilient Asia: Fus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ystem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M]. Berlin: Springer, 2018: 151-187
[2] 闵庆文. 关乎未来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 中国科学报, 2015-05-29(2)MIN Q W.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A Legacy for the Future[N]. China Science Daily, 2015-05-29 (2)
[3] KOOHAFKAN P, CRUZ M J D. Conservation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of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J].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11, 2(1): 24–30
[4] 安治民, 任坤.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生路径[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 40(12): 46–51 AN Z M, REN K. The endogenous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uizhou minority areas[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19, 40(12): 46–51
[5] 苑利, 顾军.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容易出现的问题[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33(2): 111–118 YUAN L, GU J. Several common problems involved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practice[J].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6, 33(2): 111–118
[6] MANTIA T L, CARIMI F, LORENZO R D, et al.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of Lampedusa (Pelagie Archipelago, South Italy) and its key role for cultivar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J]. Italian Journal of Agronomy, 2017, 16(2): e17
[7] LIRA R, CASAS A, ROSAS-LÓPEZ R, et al.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useful plant richness in the Tehuacán-Cuicatlán Valley, Mexico[J]. Economic Botany, 2009, 63(3): 271–287
[8] CHOI J U, KIM D Y, YOON S D, et al. Perspectives on the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nd management scheme of sacred Dangsan forest in Singi-ri, Namwon-si as an agricultural heritage[J]. Journal of the Korean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6, 34(3): 115–123
[9] PARK J J, KIM S B, LEE E C. Adoption and future tasks of Nation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J]. Journal of Korean Society of Rural Planning, 2013, 19(4): 161–175
[10] ALTIERI M A. Linking ecologists and traditional farmers in the search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J].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14, 2(1): 35–42
[11] PARK H C, OH C H. Flora, life form characteristics, and plan for the promotion of biodiversity in South Korea’s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the traditional Gudeuljang irrigated rice terraces in Cheongsando[J].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2017, 14(6): 1212–1228
[12] EAKIN H. Institutional change, climate risk, and rural vulnerability: Cases from Central Mexico[J]. World Development,2005, 33(11): 1923–1938
[13] APPENDINI K, BARRIOS R G, DE LA TEJERA B. Seguridad alimentaria y ‘Calidad’ de los alimentos: ¿una estrategia campesina?[J]. European Review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2003, (75): 65–83
[14] 闵庆文, 张碧天. 中国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进展[J]. 农学学报, 2018, 8(1): 221–218 MIN Q W, ZHANG B T. Review o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y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in China[J]. Journal of Agriculture, 2018, 8(1): 221–218
[15] PAUTASSO M, AISTARA G, BARNAUD A, et al. Seed exchange networks for agro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 review[J]. Agronom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3, 33(1): 151–175
[16] 张丹, 闵庆文, 何露, 等.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特征及其保护与利用[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16, 24(4): 451–459 ZHANG D, MIN Q W, HE L, et al. Agrobiodiversity features,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hina’s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J].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16, 24(4): 451–459
[17] ISAKSON S R.: The agrarian question, food sovereignty, and the on-farm conservation of agrobiodiversity in the Guatemalan highlands[J].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09, 36(4): 725–759
[18] FERRO-VÁZQUEZ C, LANG C, KAAL J, et al. When is a terrace not a terrace?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landscape evolution in studies of terraced agricultur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7, 202: 500–513
[19] 杨庭硕. 本土知识的发掘在农业文化遗产认证中的参考价值[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33(3): 50–55 YANG T S. The reference value of excavation on local knowledge in authentica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J].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6, 33(3): 50–55
[20] DONNER M, HORLINGS L, FORT F, et al. Place branding, embeddedness and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Four European cases[J].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2017, 13(4): 273–292
[21] IKUTA T, YUKAWA K, HAMASAKI H. Regional branding measures in Japan —Efforts in 12 major prefectural and city governments[J].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2007, 3(2): 131–143
[22] RAUSCH A. Japanes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ality and potential of cultural commodities as local brands[J]. Japanstudien, 2009, 20(1): 223–245
[23]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M]. 王炜,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BENEDICT R. Patterns of Culture[M]. WANG W, trans.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2009
[24] 罗祎, 陈文, 马健. 美国有机农业的经验借鉴及对中国推进乡村振兴的启示[J]. 世界农业, 2018, (7): 144–148 LUO W, CHEN W, MA J. The experience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s promotion of rural rejuvenation[J]. World Agriculture, 2018, (7): 144–148
[25] 闵庆文, 曹幸穗. 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振兴的意义[J]. 中国投资, 2018, (17): 47–53 MIN Q W, CAO X S. The significance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J]. China Investment, 2018, (17): 47–53
[26] 李明, 王思明. 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什么与怎样保护[J]. 中国农史, 2012, (2): 119–129 LI M, WANG S M. Agro-cultural heritage: What is protected and how to protect[J].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2012, (2): 119–129
[27] 吴合显. 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当代创新利用[J]. 中国农史, 2018, 37(1): 115–121 WU H X. Analysis on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outstanding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J].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2018, 37(1): 115–121
[28] NAVEEN A S.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PES in reviving the social and ecological fabric of Kodagu[J]. Procedia Technology, 2016, 24: 1758–1765
[29] IKUTA T, KOU Y, HIROSHI H. Regional branding measures in Japan — Efforts in 12 major prefectural and city governments[J].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2007, 3(2): 131–143
[30] ALTMAN J 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ptions on Aboriginal Land: The Hybrid Econom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entre for Aboriginal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2001
[31] HARROP S R.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as protected area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07, 121(3): 296–307
[32] MORING B. Land, labor, and love: Household arrang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eastern Finland — Cultural heritage or socio-economic structure[J].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1999, 4(2): 159–184
[33] VAFADARI K. Exploring tourism potential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A case study of the Kunisaki Peninsula, Oita Prefecture, Japan[J]. Issues in Social Science, 2013, 1(1): 33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 国家统计局. [2019-04-20]. http:// 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0_1346151.html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muniqué on the main data of the 1% national sample survey in 2015[EB/OL].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9-04-20].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 0420_ 1346151.html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EB/OL]. 民政部门户网站. [2019-04-11]. http://www.mca. gov.cn/article/sj/tjgb/20160715001136.shtml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istical communiqué on social service development 2015 [EB/OL].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Network. [2019-04-11]. 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60715001136. shtml
[36] 彭兆荣. 论中国农业遗产的生态智慧——以梯田为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51(6): 55–62PENG Z R. On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erraced fields[J].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51(6): 55–62
Value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WU Hexian1, LUO Kanglong2**
(1.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2.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IAHS) that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by farmers and herder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re unique and of considerable val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due to their functions in maintaining agrobiodivers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enhancing ecosystem resilience; providing economic,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services to local population. Firstly, IAH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They are rich in biolog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s of IAHS in rural industries not only is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development,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their sustainability. The specific agricultural system and cultural landscape created and maintained by farmers and herders has been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internal power of the countryside. The agricultural systems, cultural landscapes of IAHS should be highly valued and effectively protected to ensure IAHS become important part of local farmer’s lives, and the foundation for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econdly, making full use of IAHS is a basic approac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arieties,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can improve the livelihoods of rural people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biodiversity; while the transmission and protection of IAHS may attract new investments, technologies,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combination of IAHS and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ough applying modern methods, techniques and means in IAHS may reinforce the IAHS effectiveness in rural industries development.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ffectively connect ecological products of IAHS and modern social consumer groups through consumer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for IAHS utilization. Thirdly, the innovation of IAHS is an inevitable wa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The innovation is to provide services to tradition, rather than replace the tradition.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AHS in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ive aspects on innovation are necessary: 1) the innovation in terms of consumer targets and definition of the target consumers well in advance; 2) the innovation of service means and fully integration with national policies; 3) the innovation of service content and promotion of rural tourism; 4) the innovation of service spaces and promotion of the resources of IAHS; and 5) the innovation of services functions and reinforcemen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short, by preserving, utilizing, and innovating IAHS, current rural industries will have various approaches to ensuring sustainability of agriculture.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eservation, utilization and innovation
, E-mail: mdlkl@163.com
Mar. 31, 2020;
G3
10.13930/j.cnki.cjea.200237
罗康隆, 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民族学。E-mail: mdlkl@163.com
吴合显,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民族学。E-mail: 1102394910@qq.com
2020-03-31
2020-05-08
*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6ZDA157, 16BMZ121).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157)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MZ121)资助
吴合显, 罗康隆.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产业发展的价值研究[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2020, 28(9): 1305-1313
WU H X, LUO K L. Value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J].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20, 28(9): 1305-1313
May 8,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