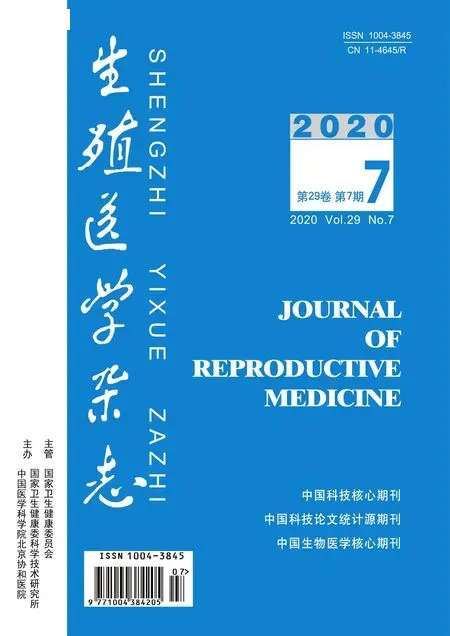心理干预对二胎不孕患者辅助生殖技术妊娠结局的影响
马丽影,窦倩,朱颖,禹果,赵冬梅,肖冰,谭丽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中心,郑州 450014)
随着我国二胎生育政策的调整,据估算,符合生育条件的1.4亿对夫妇中,60%在35岁以上[1],这些高龄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有着各种风险,比如遗传性疾病的发病率升高、妊娠期并发症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增高[2],同时由于年龄增大导致生育力下降,部分女性需要接受辅助生殖技术(ART)来助孕[3]。这些问题,不可避免的会给这些高龄女性带来各种心理压力,这种刺激会成为一种心理应激源,通过神经体液等介质直接影响孕妇的心理健康,制约全身各个系统及器官的正常功能[4]。本研究针对有轻度焦虑症状的高龄、有生育二胎意愿的女性,分析她们的心理特点,探讨加入的心理干预,能否改善ART的妊娠结局,以及降低产褥期精神障碍的风险和帮助患者恢复心理健康。
一、资料与方法
1.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我院生殖中心接受ART助孕的124例女性不孕症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符合不孕症的诊断标准[5];无ART禁忌证;已经生育过1个子女;具有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能够进行良好沟通和交流;既往和现在无精神异常和意识障碍;初次就诊时心理评测存在轻度焦虑症状;最近3个月没有服用过精神类药物。排除不能良好沟通及中重度焦虑的患者。
2.心理评估工具:使用自制的信息调查表收集资料,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进行评分[6]。信息调查表包括一般资料、病史、生育前孩情况、不孕对工作家庭生活的影响等;SAS量表包括20个评价项目,将20个评价项目的得分相加为粗分,将所得粗分×1.25为标准分值。SAS标准分的分界值为50分,50分以上提示存在焦虑症状,其中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评分中重度以上者建议到精神心理科就诊。
3.研究方法:心理测评:患者初次就诊时填写信息调查表及SAS自评量表,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测评量表的发放和评分。患者自评为主,不能填写的由专业人员协助填写,现场回收测评量表,尽量保证有效回收。胚胎移植日再次进行SAS心理测评。
分组:根据处理不同,将接受心理干预的53例患者纳入干预组,未给予心理干预的71例纳入常规组。常规组接受常规的ART助孕;干预组在常规治疗的同时,接受针对性的强化干预措施,调整患者的心理状态和不良心理特征。心理干预在促排卵前、促排卵中、取卵后、胚胎移植后持续进行。
ART助孕:根据不同患者的情况选择短效长方案、长效长方案、黄体期促排卵方案、微刺激方案等降调节,达到降调标准后开始注射促性腺激素(Gn),根据阴道超声结果和激素水平调整Gn用量,达到促排标准后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扳机,扳机36~38 h后取卵。根据病史选择受精方式,取卵后第3天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决定鲜胚移植或胚胎冷冻,胚胎移植后给予黄体支持治疗。移植后14 d抽血检测β- HCG水平,阳性者移植35 d行腹部超声,可见孕囊者为临床妊娠。
心理干预的方法:常规ART过程中进行宣教和科普。加强心理干预方法如下:(1)心理咨询师一对一会谈:倾听与观察,帮助患者认识和调节不良情绪;(2)团队咨询活动:鼓励患者交流沟通互相帮助;(3)家庭支持干预:鼓励患者与丈夫/家人/朋友沟通交流,获取更多情感支持;(4)放松训练:通过一定的程序放松肌肉,达到心理的松弛;(5)对治疗过程中焦虑症状较重的患者,进行专业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请心理咨询师进行一对一的访视。
观察指标: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纳入研究时和干预后的心理评测变化,临床妊娠率、流产率等妊娠结局。

二、结果
1.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常规组患者年龄25~46岁,干预组患者年龄26~45岁,两组患者的年龄、不孕年限、文化程度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具有可比性(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s),n(%)]
2.两组患者SAS评分比较:两组患者进入ART周期前的SAS评分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常规组患者胚胎移植日的SAS评分显著高于干预组(P<0.05)(表2)。

表2 两组间SAS评分比较(-±s)
3.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础FSH(bFSH)、bLH、抗苗勒管激素(AMH)水平、窦卵泡数、Gn启动量、Gn总量、Gn天数、获卵数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表3)。

表3 两组间临床资料比较(-±s)
4.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比较:干预组的临床妊娠率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流产率和异位妊娠率略低于常规组,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的多胎妊娠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表4)。

表4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
三、讨论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单独一孩的夫妇约有1 500~2 000万,虽然有超过60%的家庭有生育二孩的意愿,但由于观念和经济条件的影响,80后和90后等年轻群体的生育意愿较低,主要生育人群是70后这些年龄超过35岁甚至40岁的高龄女性。高龄产妇在生育过程中存在各方面的风险[2],首先是遗传性疾病的发病率升高[7],其次是高龄产妇妊娠期并发症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增高[8];此外,这部分人群在生育一胎时正处于中国剖宫产率最高的时期[9],再次生育时面临瘢痕子宫/子宫破裂等风险。这些问题,让高龄产妇面临各种心理压力,这些刺激会成为一种心理应激源,通过神经体液等介质直接影响孕妇心理健康,制约全身各个系统及器官的正常功能[4]。有观点认为,年龄是影响产后抑郁的独立风险因子[10]。
不孕症患者与正常人相比有更多的负性情绪,且以抑郁和焦虑为主[11]。有研究调查了110例接受ART的高龄不孕女性,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在32.72%和23.63%,心理测评评分亦明显高于正常人群[12]。焦虑和抑郁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又是焦虑和抑郁的影响因素,形成恶性循环[13]。心理压力过高会导致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反射性升高,影响排卵功能[14],加重不孕症,影响妊娠结局。研究发现,ART助孕失败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且焦虑程度高于成功患者[15]。因此临床工作者应当帮助患者评估心理状况,对有负性心理倾向的患者,进行心理干预能够有效缓解不良情绪,提高妊娠率[16]。最新的中国高龄不孕女性辅助生殖临床实践指南中,就建议对接受ART治疗的高龄女性进行健康教育,部分患者必要时接受心理咨询或干预[17]。
在前期的调查访谈中,我们发现二胎不孕症患者的心理特点和没有生育过的患者不同。没有生育过的患者压力集中在不孕症相关的生理因素,二胎患者则面临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比如对孩子性别及健康、年龄、卵巢功能减低、促排效果不好、治疗过程长、自身体力精力下降等产生的焦躁情绪,对不孕和ART信息接受程度也较差,常表现为紧张、焦虑、缺乏活力、不自信等;尤其前孩是女儿,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较重的家庭。但同时二胎不孕患者通常已有1个子女,夫妻关系相对稳定,能够共同对抗一定的外界压力;经济状况也较为稳定。这些发现与之前的研究[18-19]相似,因此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心理干预方案。
国外的心理干预已较为成熟,其在心理学理论体系指导下,改变患者的感受、认知、情绪和行为,改善患者心理状态、行为方式甚至各种躯体症状[20]。国内关于不孕症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均处在探索阶段,尚缺乏完善的心理预案。目前大部分生殖中心基本都能在治疗过程中进行健康宣教,安排科普讲座,但这些通常是面向所有患者的,如何针对不同表现的患者实施有效的心理干预,是需要关注和探索的问题。目前对于轻度焦虑的患者,我们采用放松和情绪转移的方式,帮助患者缓解和消除不良情绪;中重度焦虑的患者则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建议转到精神心理科就诊。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存在轻度焦虑的二胎不孕症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心理干预对情绪改善和妊娠结局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患者的SAS评分明显降低,负面情绪减轻,干预组的临床妊娠率显著高于常规组,且流产率有低于常规组的趋势,提示心理干预可能对妊娠结局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针对性的心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焦虑症状,改善ART妊娠结局。但由于样本量较少,心理测评不够全面,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些偏差,后续需要更大样本量、设计更全面的研究加以探讨。以期完善不同心理状态患者的心理干预策略,提高患者心理健康水平,改善ART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