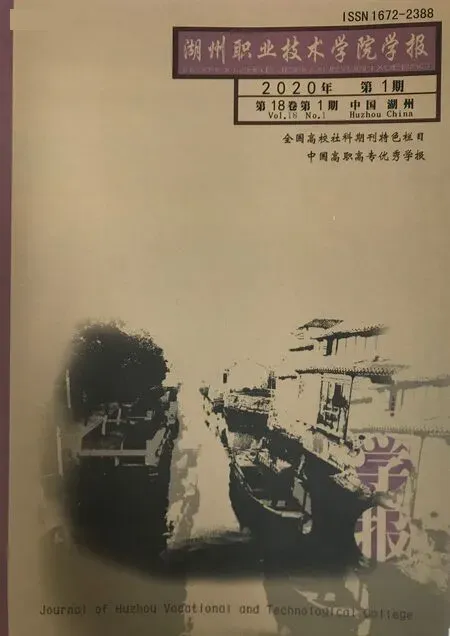庞德英译本《华夏集》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
褚慧英 , 金美兰
(湖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年)是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是西方意象派诗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创作的诗歌,尤其是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作品,在世界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成为西方现代诗人汲取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更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典诗歌和中国文化元素的跨文化传播。本文尝试以英译作品《华夏集》(1)祝朝伟:《构建与反思:庞德翻译理论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390页。(Cathay) 为跨文化研究个案,从译作对诗人自身创作的影响、对西方现代诗歌语言范式的转变及诗歌抒情方式的转变三个维度,探析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所做的创造性翻译和创新性传播,为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世界文学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20世纪《华夏集》的跨文化传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种语言背后都有各自的文化支撑。翻译作为一种语际转换手段,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行为,是一个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不可或缺的媒介。所以,诗歌翻译本质上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庞德通过美籍东方文学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手稿,邂逅东方文学和中国古典诗歌。他从150多首诗歌和注释中精心挑选了19首诗歌进行“二次创作”,涉及李白、陶渊明、王维、郭璞等中国诗人的作品。1915年4月,英译本《华夏集》问世,在西方读者中获得如潮好评。艾略特(T.S.Eliot)的评价是:“庞德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丰富了英语诗歌,是20世纪诗歌的杰出典范。”[1]xvi-xvii祁德尔(Mary Paterson Cheadle)认为:“庞德的汉英翻译抓住了作品的神韵。”[2]30
“跨文化传播就是不同文化之间以及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活动,以及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流动、共享、渗透和迁移的过程。”[3]4这个概念中的要素,对应了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的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众和传播效果[4]14,即传播者发出讯息,通过一定的媒介渠道到达受众,引起受众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的变化。其中,传播效果是传播四要素里最终也是最关键的一环,直接反映了跨文化传播活动或者说翻译活动的最终成效,是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传播效果有短期的、直接的和微观层面的,也有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和宏观层面的。有的传播能改变受众的态度、观念和思想等,甚至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进而推动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只有在正确的环境中使用正确的传播策略,才能产生“强大的效果”,这种效果并不能普遍地或简单地产生[5]308-309。
庞德的《华夏集》恰是在当时的西方主流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创造性的翻译方式,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深入人心,促使中国文化对英美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1954年,由奥斯卡·威廉斯(Oscar Williams)编写的一本广为流传的现代英美诗歌选集《袖珍本现代诗》(A Pocket Book of Modern Verse),收入了《华夏集》中的《长干行》(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全球各大图书馆几乎都收藏的大部头美国文学集《诺顿美国文学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的各个版本也收入了这首诗。可以说,《华夏集》使中国古典诗歌融入了西方主流文学圈,是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为中国古典元素的跨文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华夏集》的翻译特质
20世纪60年代,尤金·奈达(Eugene A.Nida)把通讯论和信息论的成果运用在翻译研究中,认为语言的理解是开放的,翻译的效果取决于两种语言最大程度上的“功能对等”[6]120,其实质是构成了翻译学和传播学的互相结合。此后,许多西方学者把这种理论应用到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庞德用中国古典诗歌简洁明快的语言范式,客观精准地向西方世界呈现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美景和壮阔情感,这恰好同奈达的解构主义的现代认知翻译方法不谋而合。
(一)对自身创作产生的影响
庞德是意象派的领军人物,其意象主义主张大多来自于中国古典诗歌和自身诗歌创作的结合。庞德虽不精通中文,《华夏集》也是其通过费诺罗萨的手稿翻译而来,然而他熟知其他多国语言,对语言所承载的意义和文化有一定的把控能力。通过研究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关系,他发现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汉字的象形、会意、指事功能,使它与其所代表的实物或现象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二次创作”过程。对庞德的诗学与译学的关系,谢明做过这样的评述:“庞德的翻译激励并加强了他的诗歌创作,而诗歌创作又反过来引导和促进了他自己的翻译。庞德的诗学基本上是翻译诗学,他为20世纪诗歌翻译的本质和理想重新下了定义。”[7]204《华夏集》作为庞德的代表译作,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的许多诗歌创作都有中国古诗的影子。意象并置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技巧特征,在庞德的《诗章》中大量出现,如《诗章》第49页:

Rain;empty river,a voyage,雨;空江;行旅 Fire from frozen cloud, heavy rain in the twilight冻云火,暮色中大雨①①蒋洪新:《庞德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254页。
诗句中没有出现一个动词,雨、江、行旅、火、云和暮光等意象词并置写景,非常简洁明快,这正是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模仿。作者采用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并置的手法,留给了读者无限的解读空间,从而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这成为庞德诗歌语言的一大亮点特色。
在翻译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句法等中国诗歌的其他要素也被庞德引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例如,脱体句法(disembodiment)(有意模仿汉语原诗的无冠词无系词的句法)[8]232-233也出现在《诗章》第49页:

Sun up; work日出而作sundown; to rest日落而息dig well and drink of the water凿井而饮dig field; eat of the grain耕田而食Imperial power is ? and to us what is it?帝力于我何有哉? ①①蒋洪新:《庞德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254页。
庞德此诗略去了一部分冠词,不用指示代词和主语,比如sun前面无冠词,work前无主语等,人称时态都不确定。在此诗中,中国古典诗歌的抽象、简洁、模糊一览无余。
(二)改变了西方现代诗歌的语言范式
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通常建立在译者的立场和态度上,更取决于受众民族对他族文化的强烈要求或内在需要。庞德把读者的需求放在首位。因为翻译所面对的读者是同时代的读者,所以译者必须调整思路,改变策略,译语必须符合现代人的思维方式、阅读习惯和语言规范,表达应该是自然、流畅、凝练而具体的。如果用原来的语言规范约束译语的表达,译作不可能做到完全与原文“对等”。唯有将中国古典诗歌进行现代化转型,将中国古典诗歌的特殊文本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现代诗体,才能满足西方读者阅读东方文学的需求,并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因此,“自由诗运动的方向之一,是以中国方式写作,即使没有费诺罗萨,没有庞德,为当时流行的直觉审美所引导,这也是一个注定要探索的方向。”[9]196
基于这种有效性的策略,庞德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在客观上促进了20世纪初的英美诗歌的现代化转型。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经济飞速发展,引发了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嬗变,尤其是在狄金森和惠特曼逝世以后,美国诗人竞相效仿英国维多利亚的诗风,过分“讲究措辞谋篇”“矫揉造作,凄婉多情,有时甚至无病呻吟”[10]45。浪漫主义的不实文风以“自我”为中心,构建自我的浪漫世界,追求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唯美主义文学继承了浪漫主义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但丧失了其积极的批判精神,企图借助艺术的自足性和娱乐性来逃避现实。而庞德则以西方文化规则和话语方式,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本土化改造,实现了它的“重建”与“转化”。以《华夏集》为主导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渐渐推动了英美诗歌语言的变化。中国诗“注重‘意象’‘神韵’‘简洁’‘音乐’等”,恰好与庞德的“不要用多余的词”“不要沾抽象的边”“不要用装饰或好的装饰”的诗学观不谋而合[11]4-5。庞德用朴素平实﹑亲切自然的语言风格替代了辞藻华丽﹑奇特花哨的维多利亚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诗歌典型特点,打破了维多利亚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请看译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故人西辞黄鹤楼,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烟花三月下扬州。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孤帆远影碧空尽,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唯见长江天际流。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①①祝朝伟:《构建与反思:庞德翻译理论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77378页。
在此译诗中,没有多余的形容词的堆砌,每一个词都是为了客观呈现。中国古典诗歌式的简洁朴素﹑自然清新﹑用词精确﹑准确表达诗人情感的特质,替代了当时英美诗坛流行的维多利亚诗歌式堆砌形容词﹑充斥着多余的抽象词的浮华之风。以《华夏集》为代表的诗集在英美诗歌现代文学转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借中国古典诗歌的东风,自新诗运动起,英美现代诗逐渐变得明快简洁,这与中国诗的影响分不开。
(三)改变了诗歌的抒情风格
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传播者对信息进行收集﹑选择﹑加工和处理,都包含着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跨文化传播活动也是一种跨文化创造活动。当本土的某种文化势力要颠覆既定的秩序时,往往会借用翻译这种跨文化传播工具进行创造,以他山之石攻玉。以色列学者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曾指出:当翻译文学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的时候,翻译文学就成为“革新力量的组成部分”,因而“常常跟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12] 193。庞德也说:“伟大的文学时代也许总是伟大的翻译时代;或者紧随翻译时代。”[13]3
一般认为,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导,尤其是儒家的伦理,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家敬天礼地,这个“天”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人头上的天空,天地始终没有摆脱其物质性与自然性。儒家文化对现世生活的执着,使得世俗性成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特征。这种世俗性特征对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影响甚大,而且是唐诗、宋词等各种文体的渊源。儒家敬重天地万物,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超越生命的自然主义,使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亲近,因而,中国的自然文学特别发达。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体现在中国文学中,人与自然、物与我是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学的物质性与自然性在中国古代意象概念的形成过程中都有所体现,如魏晋文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在他们的作品中,自然与山水是交融的,诗人亲近自然,寄情山水。意象主义与其如出一辙,不说教,而是通过客观呈现意象和情景实现情感表达。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学有许多可与西方现代文学认同的处所,中国诗歌直接催生了现代西方的意象派诗歌。”[14]67
在20世纪初的欧洲诗歌界,从文学背景上看,长时间受制于旧的诗歌范式,本土性或本位性突出,保守怀旧,专注于缅怀失落的历史光辉,渲染铺陈伤感的情愫。这样的状态压制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亟待颠覆。西方文学的发展借助于异域文学,批判本国文学,既而开辟了文学发展的新道路。以庞德为代表的诗人们,正是借助源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客观呈现意象和情景实现情感表达的方式,来代替不注重客观呈现﹑为抒情而抒情的维多利亚浪漫主义诗人的作诗方式,从而实现了对维多利亚诗风和唯美主义的批判和反拨。
受庞德中诗英译间接或直接的影响,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在《秋日》(Autumn)中,通过客观精确地呈现意象和情景,如枝叶﹑坟墓﹑一大伙人﹑道路﹑老人﹑山羊﹑草等,获得了诗歌美和情感的释放。中国的文化遗产在域外的现代文学话语中流传,有力地推动了跨文化传播。

AutumnA stand of people 在野外by an open枝叶茂盛中的grave underneath一个坟墓旁the heavy leaves一大伙人celebrates欢天喜地地庆祝the cut and fill新的道路的for the new road挖方和填方where 也就在那里 an old man一个老人on his knees跪在地上reaps a basket为他的山羊ful of收割了matted grasses for 满满一筐his goats乱蓬蓬的草①②①②彼德·琼斯:《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131页。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trymagazine/browse?contentId=21820。
在洛厄尔(Amy Lowell)的诗歌《秋天》(Autumn)中,通过葡萄藤﹑叶子﹑水﹑月光和银等意象的叠加,使得“诗中有画”:

Autumn
总之,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的传播是一种软性且又浸润式的传播。一种文化的跨国传播不可避免地要学习、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长,并在相互影响中得到发展、丰富并提升。庞德以其独特的思维、创新的方式,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人文知识、审美方式和价值取向,创新性地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为经典化了的中国古典诗歌转化为英语诗歌并融入世界文学,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开拓性贡献。《华夏集》的译介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使得中西文化碰撞并相互影响;同时,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主义的创作手法和汉字形象表意的特点,赋予了庞德意象主义的诗学主张,对西方现代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为后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和翻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