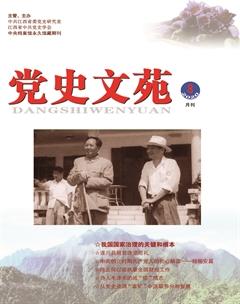粟铁匠救我父亲
朱宁娣


我的父亲朱镇中,是江西省瑞金县壬田乡洗心村人,1932年参加红军,先后在红军瑞金补充师第二营和红一军团当战士。长征时父亲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第八连的一名班长。
1934年12月初,红一军团第一师受命在广西全州黄沙河一带阻击敌人,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父亲随三团从大坪渡口渡过湘江,进入脚山铺(又称觉山铺)阵地后,顾不上强行军的疲劳,立即投入战斗。突然,父亲的左脚感到一阵痉挛似的疼痛,他低头一看,只见草鞋内侧被子弹打了一个洞,左脚踝骨部鲜血直流。政治委员让卫生员给父亲简单地包扎了一下,让他到另一个山背后去找救护站。这时父亲疼得直想掉眼泪,但他想起“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的口号,咬着牙,忍住疼痛,越过了几个丘陵,来到全州至桂林的公路上。公路上来往队伍很多,当时前方部队被敌人火力压制,后面部队显得拥挤、混乱。敌机不停地向公路上扫射,父亲连走带爬、东躲西藏,走到天黑,才找到救护站。
第二天清晨,当父亲醒来时,部队已转移,他和其他伤员只好各自分散行动。为避免被敌人俘虏,父亲咬紧牙关,沿着部队走过的山路奋力向上爬,一心追赶部队。
经过两天多的跋涉,也不知摔了多少跤、流了多少血,父亲总算翻过了大青山(即越城岭),来到油榨坪。父亲爬到了山脚的一座桥头边,由于极度疲劳加上伤口剧痛,昏迷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父亲隐隐约约听到声声呼唤:“共产党伢仔,小把戏……”父亲睁眼一看,只见一个两手黝黑、红黑脸膛上带有铁末灰、约莫40多岁的汉子,和善地蹲在他的身旁。那汉子见父亲醒过来,连忙扶他坐起。父亲看准他是个铁匠,急忙问道,“老板,你知道红军开到哪里去了吗?”铁匠小声地说:“开往大青山,过老山界,到贵州那头去了,已经走了3天啦!”轻易不掉泪的父亲,一听说部队已经走远,顿时像失去爹娘的娃娃,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铁匠坐在父亲的对面,用手摸着父亲的伤脚,劝慰说:“哭么个,伤成这个样子走不得了!”父亲对铁匠说自己是江西瑞金人,父母都去世了,家中没有人,在红军队伍里是个勤务兵。铁匠说:“我姓粟,叫粟传谅,大家都叫我粟铁匠。听说你们红军是好人,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你就在我家里把伤养好了再去找部队,要得不要得?”父亲含泪点头。粟铁匠弯下腰将父亲背起来,一口气走了两三里路,背到粟家院子(现名龙溪村)废墟菜园的草堆下隐藏起来。第二天,粟铁匠又将父亲背回了家。
粟铁匠在家排行老三,村里人都尊称他为三爷。没过几天,粟铁匠请猎人用草药给父亲治伤。粟铁匠家里人听说南瓜瓤能治伤,就用瓜瓤给父亲敷伤口,自己家里的用完了,就到邻居家去借。粟铁匠听说吃蕨菜伤口会化脓,就不让父亲吃,并把借来的大米煮给父亲吃,像待亲儿子一样,为父亲治好了伤。粟铁匠看到父亲还穿着过冬时的棉衣,就卖掉了刚打好的鸟枪,给父亲做了件新衣裳。
父亲多次对我们说:广西资源县龙溪村是他的第二个家乡,粟铁匠就是他的救命恩人。龙溪村的春景与父亲老家瑞金差不多,空气清新,河边葱绿,远处青山如黛,这里是一片美丽如画的土地。尤其是龙溪村口碧绿的潭水,清澈见底,像一面明亮的镜子。上山砍柴的青年男女们,每当休息时,都会来此照照自己的容貌。
第二年春天,父亲的伤口逐渐愈合,虽然走路还一跛一跛的,但他不愿做个闲人,打算用劳动来报答粟铁匠一家的恩情。父亲先是给铁匠家放牛,当牛倌。这里的牛有一个好习惯,前头的牛倌敲着竹梆“哒咯,哒咯”地响,各家的牛就会自动跟着走,后面的牛倌只需数一下数,不让牛掉队、乱跑、吃人家庄稼就行了。牛吃饱之后,听到竹梆一响,就自动走到一起。牛倌把牛嘴上套上口罩,敲着梆子,领着牛回村。进村后,各家听到竹梆声,只需到牛栏里检查自己的牛进栏了没有,再把牛栏关好。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多亏粟铁匠救了我父亲。虽然父亲负伤掉队,但有相对祥和的环境治病养伤,才安全地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10个月后,当父亲伤愈要去找部队的时候,粟铁匠卖掉一些谷子凑了4块大洋给父亲做盘缠,三娘把大洋缝在破斗笠里,又给了不少干粮和大米,让父亲带着路上吃。
父亲返回江西的时候,身边还有其他三个战友。粟铁匠备好的盘缠和食物,很快就用完了,于是他们只能沿路乞讨。一路上,公路上的涵洞、田埂下、禾草堆或茶亭子都是他们的“旅舍”。有时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涵洞,只好走夜路,常常走到下半夜才能找到个稍能藏身的地方睡下。路过白区时,他们为避免麻烦,决定不走城镇,绕道走乡村小路。从地图上看,广西资源到江西瑞金,大约1000多里。那时父亲他们手里没有地图,又缺乏地理知识,方向全凭问路,走了很多弯路。父亲日夜不停地走,走得伤口复发,脚踝红肿,脓血直流,但他咬紧牙关,一瘸一拐地坚持走。两个多月后,父亲终于回到了瑞金的老家,全程大约走了2000多里路。
父亲返回江西后很快找到了红军游击队,重新回到革命队伍。游击队不久改编为新四军。父亲后来相继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部队院校和总部机关学习、工作,曾任总参测绘局顾问,1982年年底离休。
虽然离开了龙溪村,但父亲一直牵挂着救命恩人。只记得粟铁匠住在桂湘黔交界的地方,当时叫大埠头、油榨坪,粟铁匠的三个儿子分别叫年宝、矮子和满仔。
经过多方打听,父亲知道了粟鐵匠的具体地址。1956年,父亲给粟铁匠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广西省资源县油榨坪粟三爷收”,信中简单写了自己当年在粟家养伤经过和自己的真实姓名。父亲特意画好了路线图寄去,并附上路费,邀请粟铁匠到南京家中做客。父亲很快就收到了粟铁匠那边的回信。粟铁匠是由女婿陪同来的,在南京住了七八天,父亲给他买了一件皮大衣(值30多元),还做了一件衣服送给粟铁匠。他们畅谈了解放以后各自的变化和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当听到奶奶和三娘已去世,父亲心里很难过。父亲还携姐姐宁晓与粟铁匠及女婿合影留念。
1962年1月,当时已任农业合作社社长的粟家珉,即粟铁匠的三儿子,邀请父亲重返龙溪村看看。父亲第一次回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中锋乡龙溪村看望粟铁匠一家和乡亲们,共叙在那段艰苦的岁月及同生死共患难的深情厚谊。粟家珉打电话给县委希望能邀请父亲在资源县做一次讲座。于是,县领导邀请父亲到县城,请父亲给机关干部职工和中学生做了一个多小时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讲座。
1963年10月13日,粟铁匠应调到北京工作的父亲之邀,在其大儿子和三儿子的陪同下,乘火车到北京我们家中做客。那时,我们尊称他为“三爷爷”。我依稀记得粟铁匠带来一大包糍粑,由于路途遥远,糍粑上面已经长了些绿霉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视为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几个孩子把糍粑上的霉斑一块块地刮掉,洗净晾干后煎着吃,仍然很香。粟铁匠还送给我父亲一把他亲自打的斧头,质量非常好,我们家用了好多年。
1981年,父亲听说粟铁匠病重,立刻汇款给他治病。1982年秋,父亲又带着儿子再次回到龙溪村,探望救命恩人。那时,我弟弟刚大学毕业分配在公安部门,起初领导未同意弟弟的请假,后来听说是他陪老红军回去看望救命恩人,就破例准假。那时粟铁匠已处于昏迷状态,卧床不起。父亲到他身边,呼唤“三爷,我来看你了!”粟铁匠睁开眼睛,含泪望着父亲,拉着父亲的手,此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1986年6月20日,父亲随中央电视台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电视系列片第二集《坎坷的征途》摄制组,第三次重回龙溪村,看望粟铁匠家人。因粟铁匠已于1983年1月去世,父亲亲自买了花圈到恩人的坟前祭拜。父亲双臂紧紧地抱住墓碑说:“50年前,您不顾危险救了我的命,我永远也忘不了您的恩情!”这集电视片于当年10月11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后,在全国反响很好。
父亲在回忆录中曾经深情地回顾说:老区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救护我,倾注全部心血关怀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这支与人民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革命军队;他们爱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而是共产党领导的整个红军和革命事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父亲曾说,粟铁匠一家救我图的是什么?图的就是革命早日胜利,老百姓早日得到解放。老区人民用自己的生命和血汗支持红军,支援革命,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为革命作出的贡献!
粟铁匠和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和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演绎了一个动人的故事。1995年父亲去世后,他与粟铁匠家之间的深情并没有中断。作为父亲的子女,我们和粟铁匠的子女仍然来往不断,传承续写着这个感人的故事。
2008年11月,我来到资源县龙溪村。当我一踏上这片土地,一种崇敬感油然而生。这里有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山山水水,还有舍身救助他的亲人。我刚走到村头,就见到满叔(家珉)出来迎接。满叔带我走进老屋,屋内有一张床,还有一扇通往屋外的小门,便于逃身。当年满叔年仅四五岁,父亲喊他“小狮子”,他就过来,模仿狮子张牙舞爪、活蹦乱跳的样子,给养伤的父亲带来了很多欢笑。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父亲在粟铁匠家养伤的日子,感谢粟铁匠全家的救命之恩。满叔又带我们来到现在的住处,拿出多年珍藏的父亲写给他的信、寄给他的照片等。满叔特意告诉我,有关父亲的纪念文集,他保存了两本。中午,满叔还用土特产招待我。
2019年3月,我的姐姐和弟弟也到资源县龙溪村看望粟铁匠的后人,并冒雨给粟铁匠扫了墓。当年父亲翻越的越城岭已经开通了高速,在龙溪村有一个出口。资源县有关部门在粟家老房子设立了粟铁匠救红军的展板,父亲挑过水的水井依然清澈;藏身的庙虽然部分坍塌,但遗迹尚存;村外是父亲砍柴、种田的地方……
粟铁匠救红军以及我们两家交往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中国人,也被写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收录了父亲朱镇中撰写的长篇回忆文章《负伤掉队以后》。
这个在桂北流传的粟铁匠救红军、红军的后人与铁匠的后人常来常往的故事,是军民鱼水情深的一个缩影,象征着红军的红色基因正在代代相传。
(作者系朱镇中的二女儿)
责任编辑 / 陈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