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与抒情的魔法
李商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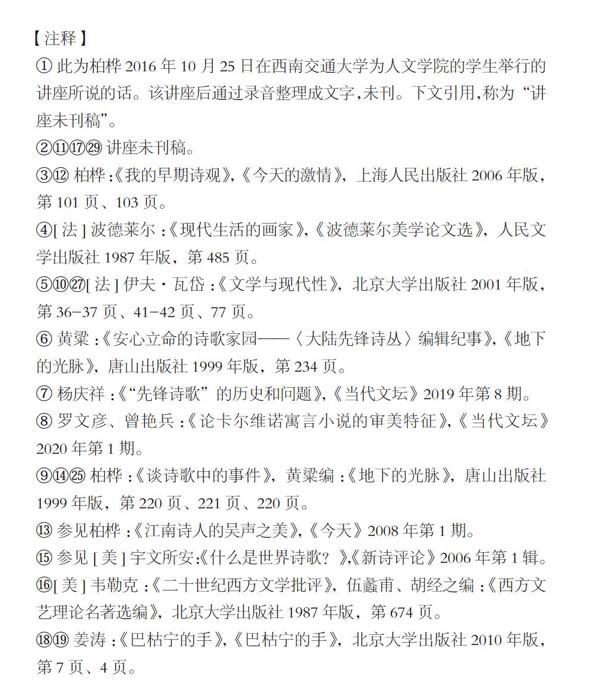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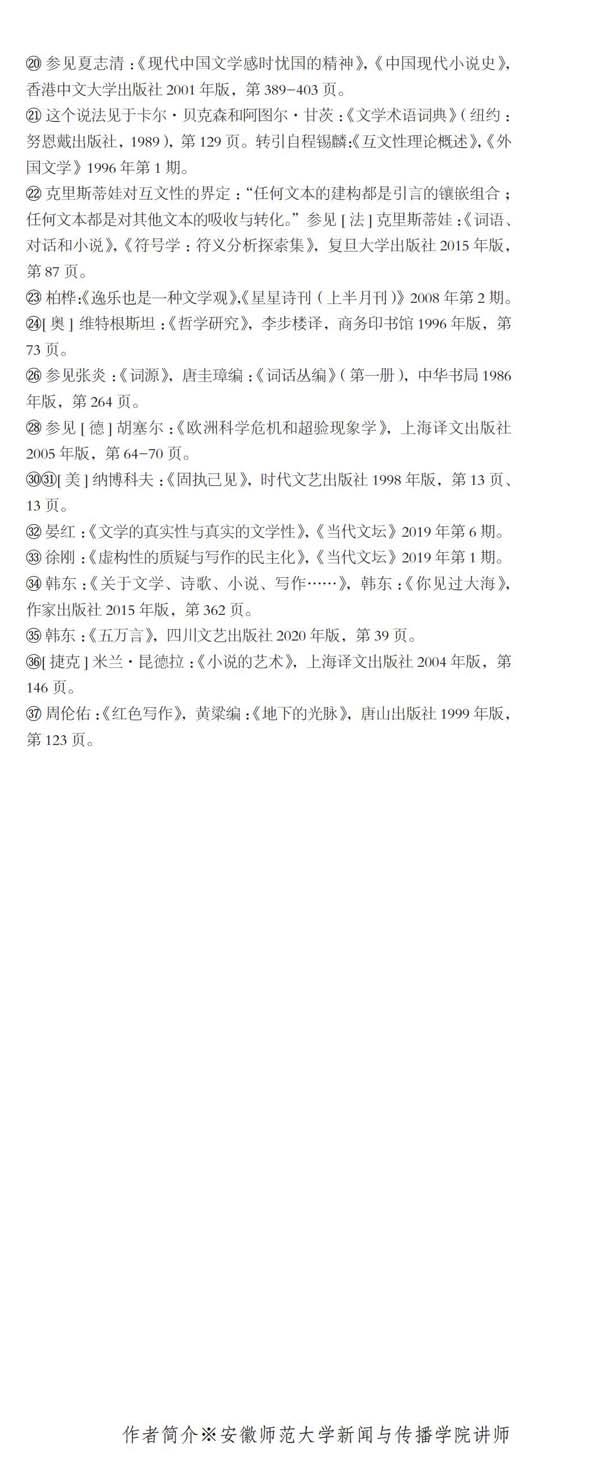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研究诗人柏桦的文献里,几乎没有针对他的诗学、诗艺的研究。柏桦作为当代一位重要的诗人,同时,由于他的写作的独特性,有必要专文来讨论他的诗学和诗艺。在学术界和诗歌界,往往将柏桦视为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这个代际定位,更像是一个僵硬、窄化和空洞的标签。也许对柏桦的诗歌写作实际情况作具体的讨论,比标签化更能理解这位诗人。
对于熟悉当代诗歌的读者而言,柏桦诗歌的独特性是无需赘言的。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柏桦都不属于任何流派,独此一家。所谓的“四川五君子”也只不过是人为贴上的另一张标签,因为这五位诗人(柏桦、张枣、翟永明、欧阳江河和钟鸣)的写作,除了张枣与柏桦有局部交集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将之视为一个小团体或流派。柏桦写作的独特性使得我们应该重视他的诗学和诗艺。
柏桦的诗歌写作包含了三个最基本的关键词:声音、意象和故事。这三个方面是一个结合体,但本文是分开讨论的。这三个关键词中,首先,声音是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它是柏桦诗歌的驱动,是体现柏桦诗歌第一性,或者说是让柏桦诗歌具有某种特殊品质的要素。其次是意象,意象使诗歌具有某种意义。在声音作为前提的情况下,意象的意义首先是体现出某种身体性的、现象学意义上的意义。再次是故事。故事使得叙事和虚构成为可能,对于柏桦而言,“故事”,犹如纳博科夫所说的魔法——纳博科夫称自己是“魔法师”——它与声音和意象组成的结合体,使得柏桦的诗歌像施了魔法,使现代汉语具有了迷人的“诗”的魅力。
一
1984年,柏桦跟张枣说了这样一番话:汉语诗歌是一种有别于西方诗歌的诗歌,它的民族性体现在它的声音和意象上。因为声音和意象也是有国别之分的。在诗歌写作过程中,简单和复杂应该有一个起起伏伏、虚实相间。也即,作为一种诗艺,诗人应该有一种虚实穿插的本领。正如中国画,在一幅画中,画家要既能密不透风,又能疏可走马。诗人应该有能密能疏的才能,在这之间把握一个度。a这番话,今天看来,几乎成了柏桦诗歌的注脚。
柏桦诗歌的一部分秘密就在诗的声音,这声音可以是一种语调,一个调式,或者说,是在呼吸之间,一种生命的气息。柏桦通过这种声音来写作,是他将生命注入诗歌的方式。他的诗往往由呼吸带动节奏——用词的选择,词语的成色,在何处分行,都与呼吸有关——确切说,诗的声音由呼吸控制。声音的意义在于,它本身带来意义和思想。b柏桦说过:“诗和生命的节律一样在呼吸里自然形成。一当它形成某种氛围,文字就变得模糊并溶入某种气息或声音。此时,诗歌企图去作一次侥幸的超越,并借此接近自然的纯粹,但连最伟大的诗歌都很难抵达这种纯粹。”c可见柏桦对诗的声音的看重,声音是他诗歌的核心秘密。
柏桦所谓的纯粹,其实应该就是诗歌所应该有的第一性,它是一种感觉、感受,但是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感觉、感受。呼吸的意义,柏桦没有强调的是,它与身体相关。柏桦说的“生命”,是具有身体特点的纯粹。呼吸就是生命,生命与身体密切相关,因此,它的诗歌的身体性体现在这里。首先是身体性,其次才是意象和故事。这种由呼吸构成的声音带动的写作,并不仅仅为了构成一个“极为出色的意象”、一幅有意味的画面,它还具有叙事功能。
《夏天还很远》是柏桦最广为人知的诗歌之一,但关于这首诗的讨论并不多。我认为,这首诗是一种以身体为前提,由声音(呼吸、气息)、意象(包括畫面)和故事三种元素组成的结合体。这个“结合体”,暗含着一个难以为人察觉的、与时代乃至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传统主流相偏离的东西——身体。这个“身体”,巧妙地绕开了意识形态因素,将诗歌还原到梅洛-庞蒂意义上的知觉现象层面。所以这里的“身体”,与多年以来的身体写作完全不是一码事。后者更多地是在文化研究的层面上带有某种反抗意义的“政治正确”,仍然是意识形态的。但柏桦的诗歌绕开了这些。
这让人联想起波德莱尔的美学现代性。波德莱尔定义的现代性完全从美学出发:“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d这个定义,和韦伯、哈贝马斯等人从历史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研究和定义截然不同。波德莱尔是“从纯美学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性进行了定义”,“彻底排除了所有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干扰”。e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柏桦从早期就开始接受了来自波德莱尔的影响,就可以自觉地在二者之间建立起美学上的私密关联。柏桦的写作从早期到当下,都可以看作是“纯美学”的写作,即布罗茨基所谓的“美学优先于伦理学”的写作。
本来,就文学而言,美学优先于伦理学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偏偏是,就我们国家文学的“载道”“言志”传统,以及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有着夏志清所说的“感时忧国的精神”的现代文学传统而言,这个具有常识性的文学问题变成了一个麻烦的问题。麻烦就出在写作中应该将“历史意识”即意识形态置于何处。所以,当我读到黄粱文章中这几句话时,我想,跳出大陆的文学史来看当代诗歌,或许会有一个新的角度:“诗歌不是玩戏,尤其是沉重的中国大陆诗歌。它的文化纵深与历史感,时代环境与诗歌互为肌理、血泪苍茫的背景特征堪称世界诗歌史上的一大奇观。”f事实上,有些人不允许“跳出”,无论从批评还是写作的角度,他们都希望自己呆在五四的体系里,谈论诗歌,必须谈论历史(其实是一种历史意识)。这其中有一种复杂的执念。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中国的先锋诗歌与历史语境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诗歌与历史语境相互建构。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诗歌“进入到了一个更加复杂纠缠的历史语境中,它本来可以在反思1980年代的基础上通过更为具体的写作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准,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结果”。g
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上述问题在诗歌领域被前景化。一些诗人将一种具有反思和批判的气质加诸写作之中,从而使得在一个时代的写作中,产生一种被绝对化的东西,让人不得不正视、重视:那就是诗歌中诗人的知识分子身份问题。这种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看重,根本上是诗歌与历史语境纠缠的表征和结果。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康德和福柯在关于启蒙的讨论中所谈到的反思,以及气质、态度。诗歌本应该是轻逸的——这种“轻”,“并不是使之轻浮、简单,而是用轻松、盈捷的方式表现严肃沉重的主题”h——但在诗歌中加入历史意识,文学即变得非常沉重,这样做,文学中的伦理学成了第一要义,美学退居其次。而且,通过修辞手段并不能让文学变得轻逸。
知识分子写作,实质上是一种在诗歌中发展历史想象力的写作,是必然包含意识形态等庞然大物的写作——而且这种写作,将这些因素放在了原则的位置上。柏桦的写作与此不同,他将“感受”置于脊椎或脑神经的位置。他的“每一首诗都是由感受而发的”,i“感受”在他的写作中,与“呼吸”一起,成为他诗歌的第一关键词。它们都具有身体性,并以此在诗歌中,柏桦发现或发明了一种以身体感受为基点的诗歌想象力。这也是在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的根本分歧。而这种身体感受的想象力,也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在韩东、于坚等人那里。
在伊夫·瓦岱对波德莱尔的研究中,他对另一位研究者亨利·梅绍尼克给予了很大关注。他说,梅绍尼克认为,现代性“存在于创造主体和主体的目光之中”,“几乎我们所有的独特性都来自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烙印”。j其实,这是梅绍尼克对波德莱尔现代性作的发挥,但恰恰是这种发挥显示出它的启发价值。我在考察柏桦诗歌的时候,同样注意到他诗歌的主体目光。在他的诗歌中,“物”——也包括“事件”——明显地带有這种目光,这个目光就是瞬间和现时的“时间”打在“感觉上的烙印”。从《夏天还很远》这首诗可以发现它的时间问题——一系列由感觉,也即感受组成的“瞬间”,它们构成了诗歌的画面和意象,而推动这些画面和意象朝前流动的,就是呼吸的节奏。比如该诗的第三节:
偶然遇见,可能想不起
外面有一点冷
左手也疲倦
暗地里一直往左边
偏僻又深入
那唯一痴痴的挂念
夏天还很远
这一节里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它会用它自己的节奏带着读者走,但读者并不知道这些诗句具体意味着什么。“偶然遇见,可能想不起”,是从哪里突然来的这句?这是一种感觉。“外面有一点冷”,这是感觉。而“左手也疲倦/暗地里一直往左边/偏僻又深入”,这可能仍然是感觉。据柏桦说,这是“那种说不清楚的神秘的体验”。“这是关于身体的。”“我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冬天,感到很疲倦,它疲倦到什么地方,疲倦好像在漫游。漫游到我的身体里,我把握不住,我只感觉到它暗中在往左边走。这是关于生命,关于时间。”k
所以,呼吸,几乎可以视为柏桦诗歌的引擎。它带起的声音、节奏,自身构成了文本的意义。这个意义并非语义的,而是能指的层面,有一种类似于对能指的执着。这固然可能隐含着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为一些人批评的诗歌写作的能指狂欢。但要客观来说,能指写作在第三代诗歌那里对驱逐、清理意识形态对词语的语义污染居功至伟。如果没有这种驱逐和清理,汉语诗歌将永远停滞在所指的意识形态的宰制里。
对柏桦而言,由呼吸带动节奏的诗歌写作,因为其身体化而包含生命形态。它并不仅仅是对“纯诗”的追求,也非“及物-不及物”这种二元对立的命名可以价值判定。呼吸对柏桦诗歌的声音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决定了他是一位抒情诗人。这种影响体现在他的诗歌写作中是以感受为起点,他发展了一种独有的诗歌想象力。他的“游于艺”,是呼吸驱动下的游于艺,是对“诗歌技艺庄严、纯粹的呼应”,l因此,声音对柏桦写作的意义,就是第一性的。他以感受为起点的诗歌想象力,通过呼吸带动意象,并由虚实相间的意象,来讲述一个故事或事件,三者成为一个结合体。
柏桦在《江南诗人的吴声之美》一文中,引用了《册府元龟》卷八七五中音乐家赵师评吴歌与蜀声的话:“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绵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若激浪奔雷。”m从柏桦的自身经历来看,作为一个四川人,他曾经有过在南京生活的经历,这种经历对他的诗学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柏桦的《往事》一诗1988年写于南京。这年夏天,柏桦到南京农大任教,他真正地置身于“江南”,并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四年。柏桦说,这首诗“不仅是我生活的写照(形式上对读者来说是熟悉的),其中还弥漫着南京的气味,树木、草地、落日的气味,江南游子,身世飘零,其间又夹杂一点洋味。是我如此,还是南京如此,或许有某种命运的契合吧”。n柏桦说的“气味”,就是南京气息,或者江南气息,这是柏桦诗歌的“在地性”(Localization),但它是由听觉产生的。这首诗歌在形式上,与以往的诗歌一样,是呼吸带起节奏,进而带起意象,进而产生神秘的气味——这一切与他的生命,他的命运相契合。因此,柏桦的诗歌在“及物-不及物”这对当代诗歌重要诗学概念之外,也缘于他的写作实际。
二
根据宇文所安的看法,一个鲜明的画面也可以视为意象。o这是对意象的一个拓展,其意义在于,柏桦的诗歌由呼吸带起的词汇——意象是什么样的画面。柏桦有首诗叫《回忆(二)》,这是他写的以“回忆”作为标题的第二首诗。看一下他的这首诗如何以呼吸联动词语和意象:
森林展开了,
1909、1987、1989……
在蓝得不像真的天空下,
在岷江,在黑水河谷;
在白云山下,
在明故宫前,
在紫色的春夜!
我的一生终归有多少次呼吸?
索桥像秋千高悬,摇晃……
(那里的人们高华而长寿
并不都是慢吞吞的)
她的高傲是为了救一个人吗?
她的眼泪是为了突然爱上……
我将忆起你,锡兰,
忆起你的叶,你的果……
我将忆起你,南京,
忆起你的唇,你的大学的云南。
注释一:“我将忆起你,锡兰,忆起你的叶,你的果……”(克洛岱尔),见维克多·谢阁兰著,邹琰译:《谢阁兰中国书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第8页。
2012年7月7日
这首诗需要读者念出声来,反复念,画面会越来越清晰。
第一节,显然是一种舒缓的语气,一种低语,森林和时间依次展开,它的视角比较客观。第二节,可以看作是主观视角,五行诗全部以方位副词“在”开始,一共六个“在”;两个“在”之间,一次换气,短暂停顿,诗歌主体在讲述,画面如流水铺开。第三节,只有一行,这一行较前两节的任何一行都长,这需要一个长呼吸,而后,是较长时间的停歇,仿佛陷入了暂时的黑暗。
接着,第四节是客观视角,事物呈现。“索桥”这个意象或画面犹如电影中的固定镜头,是中性的,不带个人的感情色彩。而且这个镜头比较长,景别也足够大,除了索桥,还有人物。第五节,节奏陡然一转,切换成主观镜头,虽然句子字数较多,但它是急促的,声调稍稍激昂,这个声音起于远景画面的平静,就像大鱼猛然跃出水面,但它却以省略号结束。这意味着,主体的声音在陡起的激昂之后迅速转为怜惜、缅怀的深情呼唤——这是最后一节的声调:两个“我将忆起你”。通过注释我们看到,最后一节的前两行是引文,后两行则与之对称。在这里,“锡兰”和“南京”,犹如两个有些哀愁的晶莹之物,它们被嵌入在此,因声音而美丽。这一节里,同样,“叶”与“唇”形成对照,这种对照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们后面的对称被打破,“果……”与“大学的云南”。
如果仅止于对这首诗做一番简单的细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样的解读,有成为瓦莱里“纯诗”论注脚的危险。在瓦莱里看来,一首诗“是声音与意义的联锁,使我们难以区别内容与形式。詩……是比喻,又是符咒:是声音与意义的妥协,这种妥协通过诗的常规,甚至出于武断,以完成理想的艺术品,后者是统一的、超越时间的、绝对的”。p可以看出,所谓“声音与意义的联锁”,其实就是一个“结合体”。这个“结合体”,有溢出瓦莱里诗论的成分。这至少有三个方面,我在这里并没有太多考虑声音的成分,而只是就其意象而言。
首先,诗歌中的某些意象可以连接民族的文学。柏桦在讲座中用“断肠”一词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古人用的‘断肠这样的词,这个词就是典型的中国意象,只能中国有,其他国家都没有。从音乐到意象都有国别之分。”q今天看,当代新诗的当代性在哪里?姜涛认为在“介入”,这是相对于现代诗而言的当代性之所在。r我难以赞同这样的看法。这种看法产生于1990年代初特定的社会环境,它其实有个传统,这个传统简单说就是“五四体系”。
姜涛在分析当代诗的“当代性”时,他是以卞之琳《断章》开始讨论的。他以卞之琳作为现代诗的代表,认为卞之琳的诗是一种“历史的‘风景化”,是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历史面前一种疏离的态度的表现”。s且不说姜涛在谈诗歌时谈“知识分子”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在1990年代的诗坛曾引发过很大的争议——就说他以卞之琳作为“现代诗”来看,我以为并不能很好地说明整个现代时期中国文学的风貌。在这方面,可能夏志清在《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提炼出来的“感时忧国”这四个字更符合现代文学的特征。t虽然说夏志清主要谈小说,但是他谈论的是整个国家的文学风貌和内在的精神。这可以认为就是中国文学的“五四体系”。
以此标准看,姜涛谈论的《巴枯宁的手》,包括诸多的“1990年代诗歌”,其实基本都在这个体系里。然而,柏桦的诗歌却不在这个体系,而是在另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就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时间非常长,包括了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应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谈及的边界里去理解。
如果这样,柏桦关于意象的使用,是在“五四体系”之外,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使用的,并且具有风景化的倾向。《回忆(二)》中的风景,成为了民族的绝对风景,读者从这种风景里,不会想到这首诗是“及物”的,还是“不及物”的。它比所谓的“介入”诗歌,或者说“及物写作”更显出合法性。
其次,是存在于柏桦诗中的“知识”——他诗中的“知识”,往往是以一个意象和画面的形式出现——这使他的诗歌具有醒目的标识性。他还会将那些“知识”尽可能以注释的形式指出出处,譬如《回忆(二)》即是如此。怎么看待柏桦诗中的这种“知识”,也是近年来在诗人中间引起颇多议论的焦点问题。诸多评议中,不乏怀疑甚至批评的声音,集中起来,主要意见在于,这种“知识”成了掉书袋,甚至变成了“非诗”。
这种说法其实站不住脚。且不说我们经常拿来当常识的艾略特的一句话“小诗人借,大诗人偷”,u就说自古而今,这种所谓“知识”的“掉书袋”,合法与否,只要看看艾略特本人的诗歌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不想在此拿一种看似本质主义的说法来讨论文学文本实际上是个拼图,因为这涉及到另一个非常麻烦的话题,即文学作品是原创,还是互文。后者来自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个说法。v不管是强调天才的原创,还是文本的互文,如果将之绝对化,都是不太符合实际的。难道《荒原》仅仅是艾略特天才的原创,抑或掉书袋的结果?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柏桦有一个他的说法:三分原创、七分传统。此说可能更贴近诗歌创作的实际。中国古代的诗歌,互相交叉的情况非常多,说白了就是直接把前人的作品拿来据为己有。李白这方面就非常大胆、“肆意妄为”。估计那时候的诗坛,也没有抄袭一说。李商隐的“掉书袋”就更加为世人熟稔,自不必多说。
诗歌中“知识”的合法性,需要以我们的常识去检验。如果没有大量的“知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会是何等面目,这是无法想象的。即便拿最受中国人待见的《红楼梦》而言,它也是由“知识”拼装成的。诗歌如此,小说亦如此。至于散文更不要说了,周作人《夜读抄》可能是现代文学以来最有力的佐证。
以上的话,似乎“跑题”了。我并非要证明柏桦诗歌中引文构成的“知识”合法性。在柏桦的诗中,他的引文作为构成文本拼图的一部分,其实并非真正的知识。柏桦说的“三分原创、七分传统”,这个原创是起决定作用的。诗人在传统中,这个说法会错吗?虽然时下某些诗人未必十分赞同,但至少文学史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诗歌中原创的意义是大于互文的。原创是决定性的,这关乎诗人的个人才能。
柏桦的原创性,他的个人才能,主要体现在他对诗歌的声音的把控方面。将一首诗变成一种绝对,将一个瞬间变成永恒,这在柏桦,就体现在他以个人的才能去驾驭一种非个人化的声音。以《回忆(二)》诗中的声音为例,正是那种以呼吸带节奏的声音,将各种意象、画面、知识——这首诗里的知识,并非单是一处引文,它体现在如“明故宫”等多处——连缀起来,从而使得这首诗成就一种“纯形式的富丽”。
如果认为一首诗歌因为引文而沦为“非诗”,我倒觉得这是变相的赞誉。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在90年代曾被一些人认为是“纯诗”而加以抵制,并因之出现所谓的“非诗”。我倒觉得,柏桦的诗歌是“非诗”的“非诗”,即他的诗歌,是更进一步的“非诗”。这不是那个大家熟悉的“非非”,而是柏桦的“非-非”。它让诗重新回到了诗,而不是知识。知识,在柏桦的诗里并不具备知识应该有的认识功能,而完全是审美的。他的诗歌中的知识,是伪知识或后知识,它们完全被带进了呼吸和声音里,从而丧失了认识价值而具有了身体性。所以他的诗歌中的知识有生命属性和具身性。
当然,作为读者,我能理解柏桦的细心。出于为读者考虑,他往往会把引文标出出处,或者加以说明,而这些注释,竟同时也构成了柏桦诗歌的一部分——它们使得柏桦的诗歌在文体上有一种混杂的特征。这很有些颠覆读者对诗歌的认知。它的语言风格,与诗歌正文形成的反差,恰好构成了奇特的张力。这并非意味着柏桦有意去冒犯读者。这些引文,本身的画面构成的意象,与非引文的意象并置在一起,共同与声音构成了一个结合体。
再次,也即第三个方面,柏桦诗歌的意象,具有无差别并置的特点。瓦莱里的诗论中并没有强调这点,但是这点却极为重要。在柏桦的诗中,意象或者说画面,至少有两大类。来自日常生活的,这是最主要的一类,他的诗歌多是写日常生活,取材于身边事,有眼前景、当下事,也有对从前生活的回忆,比如对童年、少年的回忆,对知青岁月的回忆,对南京生活的回忆,对张枣的回忆,这也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回忆(二)》的内容,就涉及到了川西、广州、南京。
第二类是就是由引文构成的意象或画面。这种意象或画面细分就会比较复杂,而且手法也有直接引文和化用,它的来源比较多渠道,有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现当代作家作品、中外历史文献,也有时下新闻等等。“我将忆起你,锡兰,/忆起你的叶,你的果……/我将忆起你,南京,/忆起你的唇,你的大学的云南。”这是回忆加引文,引文成为了诗的一部分。
以上所谈三点,是柏桦诗歌中的意象的特点。
三
柏桦有一首叫做《礼物》的诗。这首诗的标题来自纳博科夫的小说《礼物》,也译成“天賦”。诗的具体内容,很难说涉及到了“礼物”或“天赋”,它是一个由对纳博科夫的引文和柏桦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构成的诗。然而诗歌中的场景或事件,读者又无法确知它是来自哪里,比如说第一节:
大雨中,她打开印刷厂的铁门
冲进社会主义排版室,查对
契诃夫选集中的一句原文。或许,
“锈渍斑斑的窗外飞着燕子。”
这里面明显有个“故事”:时间、地点、人物等都一应俱全,非常清晰。这首诗的语言,是典型的柏桦式的,很乖戾,又具有爆发性。他的语言从1980年代早期就呈现了这种特点。只是,这时,即2010年,柏桦经过90年代漫长的停笔,再次重新投入写作的时候,诗歌的风貌毕竟与早期有所差异。这个差异,我觉得是某种因素在强化。具体来说,就是“以逸乐作为一种价值的文学观”w的强化。随之而出现的是他对诗歌中“平凡”的强调,在诗歌的题材层面,他将更多的目光集中于日常生活中具有平凡价值的事物。
“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价值”,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即是说,他关注的是题材的日常性;同时,他从日常性中发现平凡的价值。正因此,他实现了维特根斯坦说的“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生活的使用上来”。x这显然不同于同时代的一些诗人,他们虽然也写日常生活的题材,但却用力在把日常生活形而上学化。
柏桦这么做的好处就是,他可以自由地使用词语了,他笔下的词语终获“解放”,得以从某种诸如意识形态、历史、思想等庞大之物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诗是“养小”而不是“托大”。“社会主义排版室”,这样的语言形式,依然和他的早年诗歌一样,有一种暴力扭结,但这种“暴力”在此已经不是急躁、狂暴,而是一击中的的敏捷。
“锈迹斑斑的窗外飞着燕子。”有一种惊人的美,这种美来自日常生活。读者看到这句带引号的诗行,定会以为它是一句引文。然而,这个意象/画面已经和我们的日常经验融为一体。在中国,古代的窗户是不会锈迹斑斑的,因为古代的窗户是木质的。现代的窗户是钢铁材质,因此它会锈蚀。但“燕子”却是永恒之物。窗户是短暂的,而燕子永恒。燕子来自哪里?是《诗经》,还是唐诗宋词?抑或就是来自柏桦的,或者你我的经验?
在这节诗中,“她”是谁?是柏桦生活中的一个人,还是来自纳博科夫的这本书?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柏桦在一首十六行短诗中的刚一开局,就为我们布下精确的迷雾。接下来,柏桦便铺开了这个“故事”,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提示读者,这是一首来自对日常的回忆,或者是一段感情故事:“饥饿、方便面、成长以及为难”,“热汤”以及“明亮的灯光和小玻璃桌”。人呢?开始是“她”(第二节,“她”变成第二人称“你”,这是一种小说笔法),后来是“我们”,而后又转为“他俩”。这些人称的指代,始终让读者漫游在他布下的迷雾里。
但是,这首诗有一个核心意象——燕子。这是一只轻逸的燕子。“燕子”可能是柏桦最喜欢的一个意象,也代表了柏桦诗歌意象轻与快的特点。柏桦在题记中引了纳博科夫一段话,这段话读者最要注意的是,它除了是在讲恋爱,还在讲瞬间与永恒,讲轻逸和平凡:
《礼物》(按:也译成《天赋》)是我俄语小说中最长、最好、最怀旧的一部。……这本小说只有背景可以说是包含着某些传记笔触。还有一件让我高兴的东西:也许我最喜欢的一首俄语诗——是我给书中主人公的那首。……我解释一下吧:这涉及书中两个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站在桥上,夕阳映在水中,燕子低飞过桥头;男孩转身对女孩说:“告诉我,你会永远记住那只燕子吗?——不是随便什么燕子,不是那儿的那些燕子,而是迅速飞过的那只燕子?”女孩说:“当然我会永远记住。”
柏桦把这段话置于题记,让我想起他的一个诗观——情景交融。这四个字,稍具古典文学知识的读者可能都会以为习以为常而将之轻轻放过,但它对柏桦却并非如此。在写作的早期,他便将这四个字紧紧抓住,别有一番意味。他说,“情景交融”就是“一首诗包含着一个故事,这故事的组成就是事件(事件等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是任意的,它可以是一段生活经历、一个爱情插曲、一只心爱的圆珠笔由于损坏而用胶布缠起来,一副新眼镜所带来的喜悦,等等”,“这些事件组成的生活之流就是诗歌之流,也是一首诗的核心”。y要而言之,对于柏桦而言,“情景交融”就是故事,故事就是“情景交融”,故事必须要做到“情景交融”,故事是情景交融的故事。
《礼物》这首诗,就是一首情景交融的诗,只是,柏桦将这四个字现代化了,他赋予了这个古代诗法以现代内容,从而成为柏桦的诗法。“情景交融”说,原出于南宋张炎《词源》,原文是“离情当如此作;全在情景交炼;得言外意”,z强调的是“炼”字,也强调了作者的主体存在,我以为,这可能更符合柏桦所赋予该词的现代色彩。《礼物》中的引文,或者柏桦所征用的事件,可能是来自他的阅读,但他已经将这个间接经验,与自己曾经亲身经历的直接经验“炼”到了一起,分不清彼此。我们叫做“互文”的东西,在柏桦那里,他将之征用过来,稍作调整,成为自己的经验。
柏桦对诗歌中故事的强调,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是他的题材的日常化,这与宋词的“凡有井水饮处”的日常是一致的,是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是一种对精致、养小的追求。他追求的是一种刹那性,或者叫瞬时。“瞬时”的说法来自伊夫·瓦岱。瓦岱说,这是“一种感受时间的方式”,它在艺术中,是累积型时间、断裂时间类型之外的另一种时间类型,它无限靠近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累积型时间,在瓦岱看来,主要是一种以进步论作为感受世界的线性时间观,是对“新”的追求,“新”的胜于旧的。但瞬时是一个“纯粹的现时”,是一个“充实的现时”。@7
柏桦的这种做法,在当代的诗坛而言,不管其有意还是无意,都体现了最大的差异性。他以此将自己从这个时代众多诗人中标识出来,在美学现代性的意义上,他从社会、历史、现实等一系列庞然大物之中抽身而出,来到最根本的地方。他的写作因此是诗人写作,而不是伦理写作、道德写作、意识形态写作,或者知识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他题材中的日常生活,无意间回到了胡塞尔所说的前反思、前科学的日常生活。@8在他的诗中,其词语因此去除了不必要的意义杂音而变得澄澈,诗歌的声音,也因此是一种具有现象学意味的纯粹的声音。
其次,是他对诗歌的虚构的理解。柏桦认为,虚构,是一种想象力,“是一种虚构的美。虚构的美也就是说谎的美。……我会把一个不真的说得非常真,你會觉得这个绝对是真的,但是说穿了谜底,它就是假的。”@9这种理解,立即让人想起纳博科夫的一个说法:“所有的艺术都是欺骗,大自然也是个骗局。”#0我甚至觉得,这两种说法源于它们相同的对立面,也即我们通常对艺术之“真”的理解。柏桦这么说,我们可以找到当代诗坛的对应点,他的看法本身就是对这个对应点的发言。当代诗歌,正如姜涛在《巴枯宁的手》一文中对“现代诗”和“当代诗”做区分时所认为的,当代诗的“当代”,乃是对现实的介入,要及物。“介入”说的合法性的来源,乃是五四以来具有“感时忧国的精神”文学传统。因而,当代“介入”的诗歌也就在启蒙的大树树荫下了。说白了,“介入”的诗歌就是启蒙现代性的诗歌。
而柏桦的这种“虚构”说,是对启蒙现代性的偏离,他着眼点在于“审美”。我曾询问过柏桦本人,得到的是对以下这段话的高度肯定的回答:“我总认为诗是这么起源的:一个穴居的男孩跑回洞穴,穿过高高的茅草,一路跑一路喊:‘狼,狼,然而并没有狼。他那狒狒模样的父母——为真理而固执己见的人,无疑会把他藏在安全的地方。然而,诗却如此产生了。”#1这段话,估计对我们的见识是个颠覆。“狼来了”的童话是作为对说谎孩子的惩戒而存在于百姓的家教,也体现了那说谎孩子“狒狒模样的父母”对“真”与“善”的伦理执着。然而不破不立,但也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它针对的是当代诗歌的伦理化写作或及物写作的痼疾,这痼疾,仍然还是由伦理和美的先后次序引发。意识形态写作、伦理化路线,势必导致对于所谓“真”的极端化追求,从而忽略了艺术首先乃是艺术。
我无意于对当今流行的非虚构写作发言,它作为写作的一种样式(不是手法),有其存在的合法性。然而,如果非虚构写作将自己的疆域扩展到不恰当的地方,可能会导致文学的本末倒置。就目前许多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论者的发言可见,他们一致认为,非虚构不是虚构的对立面,非虚构写作是审美的,是一种文学样式,它有别于那种注重想象的写作,主要是“立足于真实的现实事件,作为虚构想象的文学真实化为具体现实事件的真实,其意义在于具体现实的真实作为一种‘特别的文学真实得以凸显”。#2这等于是说,非虚构写作,其实是要求历史介入文学。
一者,它有别于新闻写作;二者,它又有别于注重想象力的虚构性文学。实际上,只要我们回顾上世纪初新文学运动以来的那种历史意识在现代文学中的存在,就能理解,非虚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新型的或新兴的以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件作为取材对象的现实主义文学,是现代文学中那种“感时忧国精神”在当下的一种文学新形态,大而言之,是具有启蒙现代性的文学新样式。这种文学在当下中国的流行,具有一种道德上“我较你神圣”的价值优越感,根源在于文学应该伦理学优先的功利主义执念。
这当然是基于一种文学的伦理化,或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及物写作”的老调新弹。其中的逻辑大致是:“无论是涉及现实还是关于历史,非虚构写作往往比虚构类叙事作品更加震撼有力。在真实性面前,虚构陡然变得相形见绌起来。以至于最近有人追问,我们为什么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看一篇小说?阅读小说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3其实这种为非虚构写作辩护的逻辑就是文学有用论,论者可能有意避开了诸如伽达默尔等人对艺术与游戏发表的见解。这种辩护逻辑的伦理色彩和功利主义倾向不证自明。如果按照这种价值逻辑,我国传统文学中许多文学作品,比如《江南》 《春江花月夜》这样的诗歌,怕是要沦为鸡肋了。
要指出的是,在柏桦的写作中,历史是存在的,现实也是存在的,但并不是以这种伦理化的方式存在,而是以更加符合“艺术的”真实(即审美)的方式存在。“在‘真实高于一切的今天,文学是理解真实(对真实的理解),而非真实。何况,真实已经堕落为资讯,资讯堕落成流言”,#4因而,柏桦的写作,除了他对日常生活的重视、日常细节的观察和攫取,更大程度上,乃是一种韩东所说的“语言的现实”,这语言的现实也是语言的诗歌真实:“我们身处一个语言的现实,……诗的建设从对原材料的思考开始,但它不只是原材料的打磨和使用。诗呈现为语言又高于语言材料。”#5
在柏桦那里,他说的虚构,当然是反非虚构写作的,对他而言,虚构的想象,是通往艺术之“真”的途径。把一个不存在的事情讲得真,这就是艺术,是游于艺。把一个真人真事真诚地、用灵魂、用良心讲出来,这是可以的,但它未必是好文学;或者说,介入、及物、非虚构,未必一定要作为好文学的唯一标准。
卡夫卡的例子最有说服力,他是一个让众多中国作家非常佩服的作家。但他在写作的时候却是在玩骗术。米兰·昆德拉讲过一句非常有见地的话:“卡夫卡小说巨大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以及‘预言意义都存在于它们的‘非介入状态,也就是说在它们相对于所有政治规划、意识形态观念、未来主义预见而言所保持的完全自主性中。”#6此言,是对伦理化写作、意识形态写作最有力的回击。
第三,柏桦诗歌中的故事具有非个人化特点。有关非个人化的讨论,几十年来真是太多了。这个说法最初来自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经由卞之琳翻译传入中国。这个观念对柏桦同样影响巨大,他的诗歌有很显著的非个人化特点。但诗歌的非个人化在当代中国是遭遇到抵触的,就如它曾在美国同样遭到抵触。
卡洛斯·威廉斯为代表的美国新一代诗人反对“非个人化”,“主张直接书写个人生活经验;反对艾略特诗风的贵族化语言,主张口语。”#7这大约也是中国当代的口语写作的一个渊源,但是非个人化写作,跟口语也并非一定抵触。这虽然是个很大的话题,但简单言之,“口语”的边界勘定都是个难题,极端化操作,其价值,可能更多的在语言符号的标出性,更多的问题,还是留给学界继续讨论。要指出的是,柏桦恰恰是以口语为主——杂以古典汉语、方言、西语词汇等——的写作,他的这种口语,就在呼吸之间,变为一种肉声。他虽使用口语,但写的诗不是口语诗。
柏桦诗歌的非个人化,为他在诗歌中的“表演”提供了必要条件。非个人化所带来的客观化,可以使作者戴上面具进行表演。这个说法来自叶芝,柏桦将之用于自己的写作,为他的诗歌的戏剧化和小说化提供了可能性。他的诗歌总是摇摆在小说化和戏剧化之间而更偏向于小说。小说之小,小在平凡,在叙事,在写日常生活。前文谈及,柏桦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养小”,在使得日常获得日常性,回到前反思、前科学的状态。他是做了这些准备之后,进行表演,将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将阅读获得的间接经验,将从它们获取的细节,交付给某个瞬间,使之成为一种饱满的绝对时刻。柏桦诗歌的表演性,让他的诗歌成为一种有匠心的艺术,它超越了自身的利害,仿佛是诗歌的魔法。纳博科夫常常说自己是一個魔法师,将这个比方用于柏桦同样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