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不泯 臻于纯粹
杨越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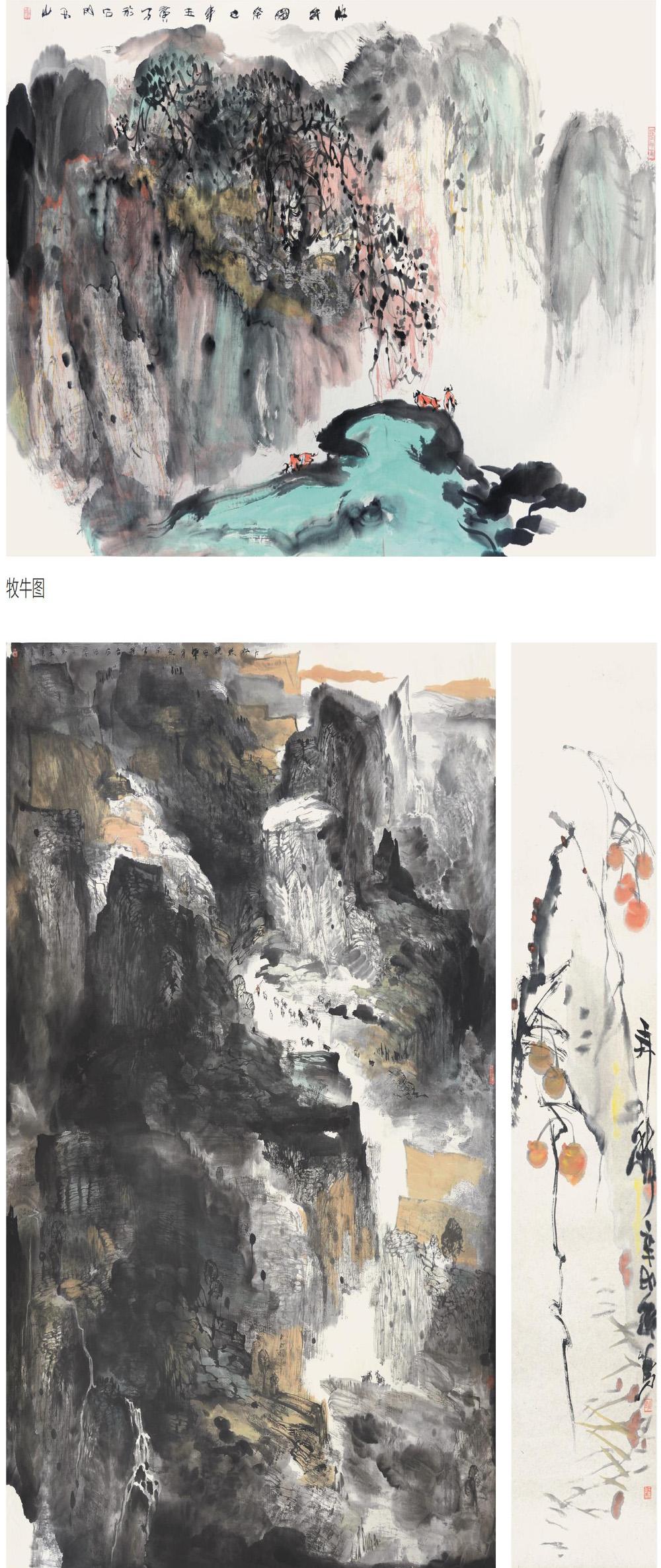

阜平人顾棣为中国摄影界所知,是他进入人生的暮年之后。然而,他对中国摄影的贡献,却肇始于抗日战争中的《晋察冀画报》,灿烂于对中国红色摄影史的爬梳整理。是的,或许他不是令人仰慕的显赫高峰,却一定是托起高峰的默默高原。而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我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谈论一个纯粹的人,有人会认为是一件可笑的事,一件奢侈的事。我对“纯粹的人”的概念,来自于毛泽东时代的“老三篇”,是小学课本里的《纪念白求恩》:“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反复对照,认定顾棣先生就是这样的人,纯粹的人。
纯粹的人,一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骨子里荡漾着浪漫情怀,不管他外表多么普通,在人前表现得多么木讷。他的心胸一定很开阔,在世间常态下无论面对何人都能表现出涵括天地的包容之心;而他的心宇又很封闭,可以把世间的纷扰、浮躁、丑陋,一律隔绝在外,而保持内心童话般的纯净。我与顾棣先生相识约有十年的样子吧。他留给我的印象却始终没变,那就是罕见的纯粹、童真。我们相识时,他重听已久。我曾推想,他能保持童真、纯粹,或许得益于他的重听:听不见、心不烦。但我马上就否定了自己,因为我发现他的纯粹是随生命而来的,甚至在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流血、硝烟,和无数次政治运动的淘洗之后,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今天,他依然故我,这就只能归结于他的风骨了。
他的纯粹,源自内心的自甘微芥。他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感觉他的心理永远定格在作为沙飞学生的时代;即便是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的时候,他也感到惶恐不安:我只是沙飞的学生,这样的荣誉应该属于老师沙飞他们;自己只是固守本分,按照老师的教导,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沙飞的女儿王雁曾和我说,沙飞能有今天,除了她这个能折腾的女儿之外,还有赖于顾棣老师和司苏实老师。顾棣先生,好像是天才的沙飞安排在中国摄影棋局上的一颗重要棋子。
他的纯粹,来源于内心的感恩情结。他的感情永远寄生于恩师沙飞,永远停止在做沙飞学生的阶段。谈到六七十年前的往事,谈到沙飞,他还会像一个孩子一样痛哭落泪,痛苦于自己无力挽救老师天才的生命——于中国革命有大贡献的生命。他永远感恩别人的帮助和给予,甚至一点来自家乡晚辈微不足道的土特产礼品,也会让他手足无措、惶恐不安。少小离乡老大回,他没有感到荣耀,而是感到惭愧,感到为家乡做事太少。这一点和阜平同乡陈勃先生高度一致。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索取,不能奉献良多就觉三生有愧。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人生信条。
他的纯粹,表现在人生的真诚,处事的缜密。他年届九十,却依然保持写信的習惯,是一笔一画地写,并且下面垫了复写纸:他是留了底稿的。当然,这些字就像一群羊,常常顽皮捣蛋、不服管教,散漫得七扭八歪。你或许难以想象,他坚持每天写日记,从十几岁的战争年代一直坚持到现在,除了做心脏手术那几天;这日记他写了几百本,巍然成一部生动鲜活的个人心灵史,信息丰富的社会史。毫无疑问,他创造了世界纪录,不管是否被吉尼斯收纳进去。
他的纯粹,还表现在不管他年龄多大,其内心永远是一株幼苗,永远在强烈地渴望着沐浴阳光、吮吸甘露,一味地不知疲倦地生长。他不知道自己已经随着年轮,成长为一棵大树,一棵独一无二的参天大树;不知道这棵大树为多少人遮风挡雨,制造了多少氧气与绿意。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大师,甚至在内心拒绝承认自己的成功;别人的赞扬,带给他的永远是内心的惶恐。
我相信,不管世界怎样变幻,顾棣先生都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这世界上势利、污浊的噪声,与他相隔遥远,远过星球间的距离,而他的内心,总是荡漾在纯净无尘的世界。
顾棣先生,理当获得中国摄影界乃至世界摄影界的尊敬,甚至也不止是摄影界。因为他定义了“纯粹的人”,为这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但愿不是孤独的标本,而是一棵绵延成林的巨榕。
编辑:刘亚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