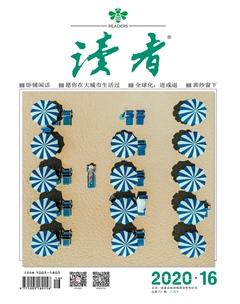后疫情时代的消费
李神喵

开始我们都以为,因为疫情在家濒临憋疯的人们解禁后会疯狂撒钱,吃喝玩乐,醉生梦死好一段日子,但想象中的报复性消费并没有到来。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8.07万亿元,同比增加1.7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6.47万亿元,同比增加4012亿元——我们等来的,竟然是报复性储蓄。
发明“报复性消费”这个词的学者单正平,曾复盘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人的几次报复性消费潮:一是改革开放初期,刚结束物资短缺的中国人开始大肆吃喝;二是20世纪90年代,压抑许久又有了点钱的人们催生了服务业的繁荣;三是刚进入21世纪,长期挤宿舍苦等单位分房的人们一窝蜂开始买房;四是北京奥运会后,富起来的老牌单车大国开始集中追求开私家车的出行体验。
报复性消费潮首先离不开全社会经济水平的突飞猛进这一物质基础,同时更需要有超越实际需求的情绪化消费作为心理驱动。
如让·鲍德里亚所言,“饱暖思淫欲”的使用价值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蠢蠢欲动和“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追求。过去人们报复性消费,是因为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花钱吃喝玩乐和买车买房,都包含着“阔起来”的自我证明。
意思是,我买大奔,不是因为别的车不能“奔”,而是因为我买得起大奔——在这段汹涌的变革期,消费产品的符号意义更为明显。
消费放大了欲望、阶级差异和攀比心理,但也刺激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20世纪初的美国烟草广告费尽心思把女人騙去买烟,无意间助长了女性的独立和平权意识;可口可乐和耐克的热血广告片,有时真能激励年轻人去勇敢打拼,挑战自己。
自由经济理论的祖师爷亚当·斯密相信,消费并不一定只会带来追逐奢靡的愚蠢轻浮,人总会慢慢产生更高级的需求。事实证明这个预测有点道理。
然而,消费主义营造的世界级拜物教很大程度上又成了众多焦虑的根源。我拥有,然后想要更多;我拥有的不如隔壁老王多,然后想比他多;累死累活好不容易比老王多了,发现楼上老李比我和老王加在一起还多——这是我们缓解焦虑的方式,同时也是我们焦虑的原因,因此我们一直无法快乐。
我们试图在诗和远方里寻找答案,结果让诗和远方也变成了消费的对象。
于是,生于黄金时代、看着西方社会打赢冷战走向巅峰的恰克·帕拉尼克在《搏击俱乐部》里怒吼:“广告诱惑我们买车子、衣服,于是我们拼命工作,买不需要的东西。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代,没有目的,没有地位,没有世界大战,没有经济危机,我们的大战只是心灵之战,我们的恐慌只是我们的生活。”
然后你猜怎么着?世界大战来了,经济危机也来了。疫情带来的死亡与恐慌并不亚于一场真刀真枪的热战,疫情制造的经济动荡影响远超1929年的大萧条。89岁的巴菲特经历过5次美股“熔断”,其中4次发生在2020年3月;同一时期,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巴菲特的同龄人被医院放弃治疗,以便将医疗资源用于救助年轻人。
最近几个月乃至未来的几年里,人类将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从有到无。生命、健康、亲人、爱人、财富、事业……种种构成正常生活的元素,在疫情面前都显得摇摇欲坠。很多东西跟空气一样,平时让人觉得稀松平常,一旦没了便生死攸关。
消费主义和消费当然会继续存在,但会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消费将趋向务实与纯粹,人们将更深刻地意识到:消费不能指挥生活,生活要指挥消费。消费主义会受到更严肃的诘问,以便为精打细算提供更充分的理论依据。
货币形态从沉重的贵金属变成轻飘飘的纸张,再到今天屏幕上的数字,这种演化在不断削弱我们对金钱的基本尊重——它或许正在被疫情重新唤醒。
当我们更理性地对待每一笔支出,更慎重地考量每一件心动的商品是否有必要买回家时,商品的生产者才有可能更深入地琢磨消费者的需求,严格把关质量和体验,消费才会真正迎来升级,并向它本质的功能回归——让生活更美好,而非更浮夸。
(云 谁摘自《新周刊》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