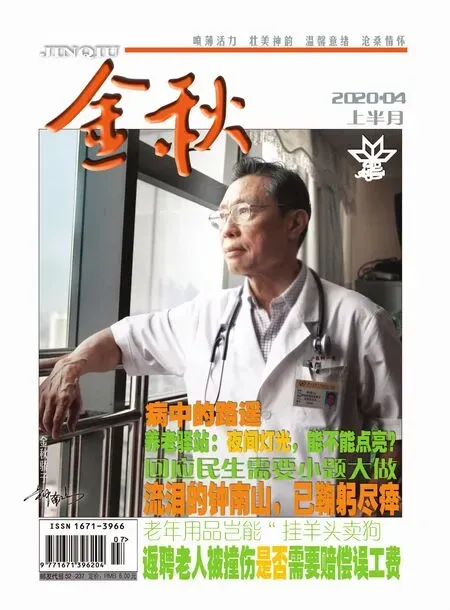病中的路遥
文/远村

路遥是我尊敬的一位作家和师长,也是我的同乡。他在西京医院住院期间,我既要照看他的女儿,又要去医院侍候他。我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快就告别这个世界,当这一切都在瞬间变为千真万确的事实时,我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悲伤。当时,有许多陌生和熟悉的报刊编辑纷纷要我给他们写点路遥在病中的情况,我一概拒绝。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好像还在医院里,不久,就能健康地站起来。事隔数月,路遥的生前好友金铮,一再鼓动我把那段与路遥在病中相处的日子写出来,以便世人对最后的路遥有所认识。写出来,也是对路遥的负责,至少,可以让人们越过一些道听途说者制造的雾障而看到一个真真切切的路遥。基于此,我提笔写下了这篇《病中的路遥》,也算是对路遥的怀念。
我是在1992年10月2日开始,每天去医院伺候路遥,一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在此之前,我只是照看他女儿的生活,每天只是抽空去医院看看他。10月1日路遥打发航宇去陕北,一方面跑他的五卷本《路遥文集》的征订,另一方面去搞偏方(因为他总是反复出现不能进食和大便不畅的现象)。所以,路遥就要我去医院看护他。

至今,有许多认识路遥的人,都认为路遥是一位沉思默想的作家。但躺在病床上的路遥,却总是要跟我们说这说那,我们有时尽量不去接话茬或者干脆不让他说,怕他劳累,他还执意要说。也许是他怕我和天笑烦,就说一些话逗乐,也许他真的有许多话,要向我们倾诉,天笑有时会跟他说一阵笑话,路遥就会愉快起来,眼中流露出一些惬意。路遥曾对我和航宇说:“这次害病麻烦了许多人,我欠人家的太多了。”在历数许多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名字之后,笑着说,“最过意不去的还是你们俩,不过咱亲着哩。”
大凡身患重病的人都会觉得前途黯淡,心灰意冷,但路遥却一直对生活抱着无限美好的向望。他对前来看他的朋友说,给他买几件过冬的衣服,还说出院以后要在外面走动,有一套款式大方又有些现代风格的运动衣更好。还问朋友什么地方环境最好,他出院后要疗养一段时间,听说棒槌岛风光好。他说这些时,显得很激动。同时,病中的路遥依然很关心国家的命运。在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他反复叮咛我,叫单位搬个电视来,他要看新闻。十四大召开期间,每天实况转播和新闻节目开播前,他就早早地戴好眼镜,摆好架式。看完后,又是一阵议论和分析。那几天,他还要我把《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拿来。他看报十分仔细,因为一只手上扎着吊针,一手翻报纸很不方便,我就手执报纸,让他阅读。作为新一届陕西省作协主席人选(省里已通过),他十分关心作协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他说咱们文人也要走向市场,不能光坐在岸上,看人家“下海”。他还让我给外面的朋友打电话,叫人家来给他讲讲外面的事情,他一边听着,一边还要说出自己的见解。
路遥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无论病魔如何折磨他,始终不曾屈服。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每天要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显得亢奋而振作。有一次,他要上厕所,我和天笑把他从床上扶下来,他竟然脚步利索地走进洗手间,我和天笑喜出望外,觉得这些天的辛苦总算有了回报,路遥能自己行走了。但上完厕所的路遥打算自己走向病床时,却怎么也迈不出一步了,我们就扶着他走,他抖动着胳膊企图摆脱我们,他一边咬牙一边用劲,但最终还是我们扶着他躺在了床上。他在床上躺着很不平静,也不理我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路遥独自行走。路遥一直胃口不好,大夫怀疑是肠胃出了什么问题,要给他做钡餐透视,一时人多,我们便在放射科的楼道里排队等候,而躺在担架车上的路遥竟然鼾声大作。轮到他做检査时,他把那个白色液体一饮而尽,站在仪器上,不让我和天笑扶他。天笑怕有闪失,抓住他的胳膊,他又甩开。

在医院里,最难忍受的就是一天十几个小时输液治疗。路遥一直咬着牙,刚强地日复一日地忍受着这个近乎伤残的过程。他的体质越来越弱,胃口也时好时坏,输液的过程却越来越长。由于肝病太重,病人必须依靠血浆和高血糖之类的药物增强体力,久而久之,血管渐渐硬化,一针扎进去,无论护士怎么摆弄,都不见药液下滴,只好重来。护士急得额头出汗,找不到好的血管,路遥一边咬着牙,一边还微笑着说,不要紧,慢慢来。后来他的双手上很难再找到一根好的血管来顺利地输液,只好换到双脚上。过一段时间,双脚也不行了,又换到双手上,而且药液滴起来也十分缓慢。路遥去世前10天左右,往往上午10点吊上输液瓶,直到后半夜才能输完,看护的人都支撑不住,何况已经骨瘦如柴的病人呢?最后,大夫建议双管齐下,也就是手和脚两个输液渠道同时进行。每天液体输完,他说他连被子都蹬不动了。看见他在痛苦中挣扎,我的心像刀割一样,我含着泪说,咱不吊了,明天就转院。转到中医院,吃中药就不用吊针了。路遥说,好,听你的。
古城的秋天,阴雨连绵,但10月15日这一天却阴云退去,太阳将柔和的光抛洒下来,我心中有了一丝美好而舒坦的欣慰。路遥戴着一个镜片已经碎裂的眼镜,极力向门外的世界望去,他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么晴朗的天气了,他看了很久。以前,路遥最喜欢在正午时刻坐在太阳下想他的心事。《延河》编辑部的院子是个四合院,有丁香和玉兰树,一到中午,刚起床的路遥就会搬一把藤椅坐在那儿晒太阳。1992年10月18日,他的五弟王天笑回陕北老家给他寻粮食去了。所谓粮食,不过就是些小米、豆子、咸菜之类。路遥高兴地对我说:“九娃长大了,一条汉子又站起来了。”路遥又开始回忆他们王家的家事和他自己的童年,讲到他的母亲时,眼睛都有些湿润。路遥说他的母亲很会做饭,他说只要回家吃上一个月母亲做的陕北饭,身体就一定能好起来。
路遥一直放不下的是他的女儿路远(他亲昵地叫女儿为“毛格蛋”)。前年冬天,写《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时,他对我说,他这一辈子唯一的财富就是远远这个宝贝女儿。去年夏天,西安气温高达40℃,他不顾朋友和四弟天乐的劝阻,执意要将房子装修一新,他说,要给女儿一个好环境。还记得8月底,路遥躺在延安地区医院里,我去看他,他高兴地说,房子装好了,远远一定呼噜噜地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
我每次去医院,他都要问家中孩子的情况,问保姆怎样,还要我把保姆带到医院,当面叮咛。他说路远的口味偏向于南方人的吃食习惯,喜欢吃炒菜和米饭,而保姆是关中人,擅长做面食,怕远远不习惯。路遥还给来医院看他的朋友交待,重新找个会做南方饭的保姆,孩子不能饿着。11月9日,是女儿路远的生日,路遥早在一周前就给我说,给远远订个生日蛋糕,还给前来为他送鸽子肉的金铮夫人吴军业嘱托,那一天,麻烦她给远远做顿饭,远远过生日还要请一些同学,怕保姆一个人忙不过来。到了路远生日那天,吴军业的父亲突然病重住院,她要去医院照护老人。刚从南方归来的金铮,放下家里的事情,为远远买来鱼肉蔬菜,并亲自掌勺,为路远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生日庆宴,同时还为远远和她的同学们拍了照片。金铮从下午5时一直忙到晚上8时多才匆匆离去,因为他家中的孩子还等着他回家做饭。第二天早上,我去医院,如实向路遥汇报了路远过生日的情况,他高兴地说:“过好了,过好了。”他说金铮夫妇真是好人,他这一次得病可把人家受害了,人家把家里的鸽子杀了给自己吃,还把鸽子蛋打进面条里,让他滋养身体。我说我给远远买了一个精制的花瓶和几束鲜花作为你给她的生日礼物,远远和她的同学高兴地跳起来了。他说好,还是你想得周到,你看我现在这个脑子,把这给忘了。
路遥从延安转到西安治疗时,就住在西京医院传染科的7号病房中。后来因病情一天天加重,长时间卧床不起,他的胯部肌肉溃烂,又搬到8号的高干病房。路遥不习惯睡软床,就跟夜间陪他的弟弟天笑把床调换了位置。天气越来越冷,路遥的病情在不断加重。11月14日上午,路遥又开始不能进食,他要我给霍世仁挂电话,请中医科的大夫给他看看胃。那天,路遥一天没有输液,上午睡得很香。醒来之后,问我他睡着了没,我说鼾声震得房顶响。他说睡了多久,我说2个多小时。他就一脸轻松地说“啊,舒服,睡美了,一满不要吊针多好。”
11月16日上午,我刚进门,躺在床上的路遥努力动了动头说:“远村,我不想在这儿住了,咱这就转院。”我说好,单位已经开始想办法了,你放心,天笑已给单位说好了。路遥一直在病床上翻来覆去,他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他说肚子里发烧,很难受,只想喝水,他说喝了那么多水,怕死人了。我说那就熬点清米汤,少喝点水。路遥说:“能哩。”但米汤熬好后,他并没有喝,没一点食欲,只在下午3点左右才喝了一口,就不让喂了。11月16日晚8时左右,我叫上航宇,又到医院去看望路遥。这时的路遥比白天要平静些,下午3点开始输液了,还没有输完。待了一个多小时,看到他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就问路遥,“王老师,你有什么事没?”他回答说“没有,不早了,咋回客?”
11月17日早晨,当我骑着自行车到医院,开门的护士说“人都不行了,你才来。”我以为她跟我开玩笑,说你胡说,昨晚还好好的。心里还是不踏实,就一路小跑冲向路遥的病房。但我来得真晚了,抢救的氧气瓶已被推出门外,路遥躺在病床上,五弟天笑抱着他嚎啕大哭。路遥就这样走了,许多人都感到意外,就连经常给路遥看病的康大夫也感到意外。那些一直关心路遥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是感到震惊,怎么会呢?他那么年轻。
1992年11月17日早上8时20分,是我和路遥阴阳两隔的时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