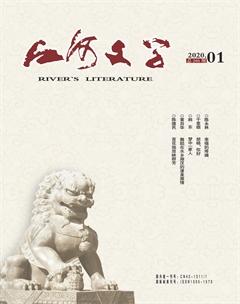悲切时间(组诗)
芦苇岸
清明
风一吹,草青了
风一吹,浊酒洒在地里了
风一吹,纸灰散了
风一吹,人走空了
风吹着风,吹干了坟前的泪
风啊,吹黑了树上的乌鸦
地下的亡灵
始终没有吭过一声
南风
水边码头,过客消费行色
他的盘缠已快用尽
而山高水长,前方绵延迢遥之美
船驶离的瞬间
沿河的芦苇就绿了,故国在岸上
挥舞着别时的悲伤
一生,都在赶路
袖口的风,眼眉的春色,帽沿的霜
辗转成遑遑流水的譬喻
那些在回忆里呼吸的脚印
被迟暮的晚霞,收进黑暗的账薄
一个立志出发的人
永远没有收尾的权利
包裹的不断扎紧与打开
仿佛尘世的爱与深情,失去又回来
只有那根握在手中的拐杖
铮亮无比,闪耀着时间的自证
回忆有一张悲伤的面孔
一棵树,回忆她自身
一定在落花时节,燕啄新泥飞走
树的前世,在山那边
一阵风,吹她家的祖坟,吹故人
把她的思念吹成此刻
新叶初长成,筋骨还很柔嫩
雨水顺着叶脉的泪痕
在下垂的叶尖上,积聚成悲伤之河
饱满、晶莹,吐纳默守的时间
情感在解冻,肺腑透明
树下独坐的人,被鸟叫声浸染
落花流水;一条欢快的小路
蜿蜒地绿……坚韧向远的决心
爬山虎的春日
它们要把发芽
拖成悬而不决的事情
经验之谈,只对好脾气的古墙说
或者对一片大过天空的安静
默许内心的真诚
有人总是紧随不远万里的
春风,站在修旧如旧的墙根
对着身旁的静水,清空重重心事
如此安好,便是最好
午后的江南,日照长长
有筋骨的爬山虎,在默默爬行
屋檐上?,鸟儿们抵不住咽扰
眼睛闭合一片梦境
羽毛的态度
春天,画风是渐变的
麻雀,先是一只,然后成一群
这股洪流似乎沒有什么
可以抵挡得了
也有喜欢独处的,如红襟鸟
在枝头,高调地清理羽毛
那红艳的襟怀,不失
照亮时间的忠诚,故日“知更”
鸟中情圣,多为雅士
昂着头,带着伴侣,不负好春光
每一步,都表现出
不爱江山的洒脱
但所有的鸟
在春天,都会回到自己的羽毛里
用飞翔与栖止描绘
满世界的热闹与安静
但所有的鸟
在春天,都会回到自己的羽毛里
飞翔或栖止,态度恳切
世界因此而多了一份安宁
雾中的光影
清晨,城市变成雾中沙漏
它隐藏尊容,放低身段
对接旷野,或文明溢出的部分
它退守的先锋
在雾中,仿佛犹抱琵琶的天桥
晨光,收割人间的一切
千万个窗口的呼吸
像出芽的韭菜,用生长诠释
一次回到内心的历程
莲花落
它并不准备对即将消失的日子
提起动议
它喜欢认春风为睦邻
在花红柳绿的热烈中填词、拓片
曲水流觞的美事
还得等上一些时辰
有时候,赋闲就是时尚
谒仙,访友,吃酒,传习韵律
在声音的内部,高谈阔论
乏了,就把身心交给马匹
像火焰一样烧灼焦虑
自弹自唱的远方
不打折,如一块掷地有声的原石
埋首尘世
不要装,真理已经死掉
忍冬花的枯叶下,一场薄霜刚刚收起
注脚。它们顾不得雾霾深重
潮水一样退去,像失去了对现世的耐心
在散开的草木中,安顿一颗心
对断头台说不,对活着多点耐心
与每一天的苟且都像是怀着赴死的决斗
在更低处,抱守日脚
埋首尘世,一腔热血,足够
妥协与抚慰
它的前爪在墙根下
闪着岁月之光……一切的琐碎
随时针慢慢走向正点
当那一声“喀嗒”让旁边的柳叶
微微颤动,然后停在一束
晌午的强光下
它反复回味在未来的位置上
获得引以为傲的确认
或者,作为一次短暂的休憩
它试着调整了一下哲学的睡姿
鼻息、胡须、黑眼圈
和偶尔扇动的两只小耳朵
在时间的寂静里,妥协
让一个梦倒在追赶另一个梦的路上
光阴的灰烬覆盖全身
它没有扑进人类的怀里
是因为,喧嚣不属于它的专利
温暖,也不仅仅是
一种合身的抚慰。这个正午
默许了它的决定
它的尾巴没有缩回去
哑剧般的空旷里,下着一场雪
呈现
在十三楼上远眺,视野蒙蒙很可疑
楼宇参差而霸道,企图瓜分我的双眼
日头偏西,它不会落进山里了
遍地阴影横陈,不讲理地阻塞人间
我将无法落脚,我独钟黑暗已久
赏月的另一种方式
看月亮的人都去天上了
我独留人间
吃晚饭时,夜色在筷子里破碎
而我其实是想用它们夹住
当空的明月
但是一场倒霉的雨
摸进了碗里,让我吃相狼狈
我在冰冷的夜里睡去
我在寂寥的时辰醒来
月亮,已被众生瓜分
唯有我的孤独还很完整
像这个浑圆的世界,明亮而寂静
黑暗如此闪光
令我猝不及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