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落幕
潘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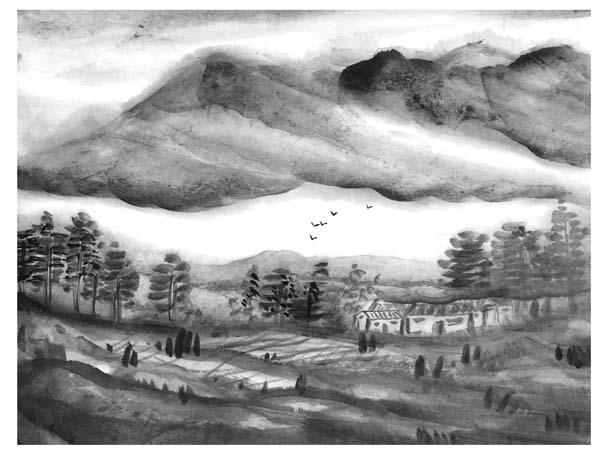
高台,是我夫家的族人对那几间平房所在位置的称呼。其实,高台算不得高,只比皖西路的地面高出十几个台阶,可陡峭的窄阶、未粉饰的黄砖褐瓦、门口杂陈的废品,突兀地夹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中,显得尤为颓废和醒目。
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台更像是对一个人的隐喻,因为这里住着整个家族中最有权威的女人——我丈夫的祖母。不知从几时起,人还在,高台也在,可渐渐都在家族中退隐了他们的地位,曾经的威望,已被风干,镶嵌在族人记忆的缝隙里,只剩一老妪手拄拐杖,暮色中,常于高台上低首,看着她的后人。
我始终不喜高台,那里除了有挥之不去的阴沉与破败,还有这个谜一样年迈又强悍的祖母。对于强势的女人,我潜意识里总是拒绝的。我对这位婆家祖母的感情,仅限于逢年过节呈上的红包,从没有过好奇去凝视她曾经富饶艳丽的内心,举止如同对待邻家老太的漠然,所有礼节只维持着浮在表面的敬重。大家族的概念,于我,仅仅残存在大年三十的那餐团圆饭里。我所知道的关于祖母的故事也极有限,呈碎片化,仿佛寥寥数字,就可囊括她丰厚的人生。
可一次又一次的闲聊,让高台上的一幕幕,透过久远的年代,带着温热的呼吸, 徐徐展现在我的面前,祖母连同她居住的高台,神秘面纱也由此层层揭开。
夫家本是合肥人,动荡的岁月,为躲避日寇高举的屠刀,举家搬迁逃难来到皋城。长途迁徙中,夫家一族只幸存了祖父和他哥哥——大祖父,其余几个,或死于战乱,或杳无音信。关于高台的来历,族人众说纷纭,有人说,高台是大祖父和祖父靠苦力挣来的,可我更相信另一种说法:高台是大祖父从赌徒手里赢来的。这种说法比较真实,带着神秘的江湖气息,也更符合大祖父的性格逻辑。据说,大祖父脾气暴躁,嗓门儿极大,稍不如意,就对祖父拳打脚踢。那时的高台,还是个带着天井的四合大宅院,后陆续有旁系亲戚从合肥投奔到高台。一时间,高台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家族, 渐渐在皋城扎了根,开枝散叶,从事贩夫走卒类的营生。
能够带着祖父在战火中幸存,又得这么一处安身之所,更是让大祖父觉得祖父亏欠了他,仿佛祖父不是他亲兄弟,而是跟高台的其他穷亲戚一样,都是他的长工。可怜的祖父只配住在破败的柴房里。大祖父对祖父还有多少亲情,是我无法想象的。我猜想,终年在大祖父的斥责里生活, 应该是祖父性格懦弱的主要诱因。我曾见过祖父的相片,脸庞清秀,长相不俗,可不和谐的是,他面色惨白,目光游离,一望,便是失了血性的苦命人。这样一个男人,唯唯诺诺,瘦小的身躯,前半生缩在大祖父巨大的阴影里,后半生,又迷失在祖母的威严里。
来高台不久,大祖父与大奶奶成了亲, 生下两男一女。善良的大奶奶看不过大祖父对祖父的苛责,时常偷些吃食给祖父,帮柴房里的祖父熬过一个又一个饥寒交迫的时日。尽管大奶奶很小心,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当她偷偷塞给祖父两个馒头时,还是被大祖父发现了。大祖父不顾大奶奶阻拦,举起鞭子朝祖父抽去。让大祖父遗憾的是,带着鹤唳风声的鞭子并没有落在祖父身上,而是抽在了大奶奶的额头。殷红的鲜血,一滴滴从大奶奶的额头淌下,模糊了大奶奶的视线,模糊了祖父的视线,也让怯懦的祖父侥幸逃脱。是的,他甚至没有勇气夺下鞭子。一道狰狞的伤痕,如同一个抹不去的记号,在大奶奶的额头永久地烙下。据说,自那以后,大祖父不再踏进大奶奶房门半步。
也许就是这一记鞭子,让羸弱的祖父终生对大奶奶有所亏欠,以至于在大祖父离世后,祖父背着同样强悍的祖母,千方百计地去接济大奶奶。这和大奶奶当初救济他时,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命运,总喜欢让人在同一处打转。我嘘唏不已。
后来,祖父经人介绍娶了同样来皋城逃难的祖母。成亲那天,天井中的一株梅, 鲜艳地怒放,开出一树红花。祖母进门后, 祖父的脸上才有了男人该有的血色,是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还是源自祖母那笔不菲的嫁妆带的底气? 族人不得而知。总之,据说,祖母刚进门的那段时日,高台是安稳的。祖母的嫁妆,为外强中干的高台提供了适时的养料。那时,大祖父仍主宰着整个家族,以一家之主的身份,理所当然地挥霍着,终日沉溺在抽大烟或赌钱上。我想,刚进高台的祖母,肯定把所有的强悍和韧劲儿都隐忍在了小媳妇的娇涩里,这使得大祖父低估了祖母的能量,認为她和祖父一样软弱可欺。
好景并不长久,时代的动荡,加之大祖父无休止的吃喝嫖赌,让祖母的那点儿陪嫁很快见了底,她与大祖父的矛盾也日益加剧。直到一天,高台上的族人还没反应过来,祖母已从大堂上撵下大祖父,成了高台的当家人。祖母是如何通过隐秘的手段使族人在最短的时间里都听从她的差遣, 这点已无从考证,祖母唯一的子女——我那耳背的婆婆,也不会细说。
这里,该为高台画一个句号了,高台上一个属于大祖父的时代已经过去,可是,高台的家底也空了,如同大祖父他们赤贫地来到皋城这片天地。吃,成了家族中每天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大祖父阴沉地退到四合院的一角,幸灾乐祸地看着祖母,看着这个细皮嫩肉的女人如何支撑一个空了的家族,如何应对越来越多嗷嗷待哺的人口。可大祖父再次失望了,直到他离世,高台都不曾衰落过,日子在同样彪悍的祖母手中,被梳理的紧实有序。我能想象到的
大约是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大脚女人,端坐高堂之上,闪着阴鸷的目光,用夹着烟卷的手指,一一指点族中的男男女女。堂下的每个人都战战兢兢,有着黛玉初进贾府的谨慎——恐多说一句话,走错一步路。我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因为丈夫曾无数次表示,他看见猪头肉就腻——小时候吃多了。在由粮票、油票、肉票等等票据构成的贫瘠年代,皖西大地上又有几户人家可以这样呢?
然而,事实并非我想的这样。
祖母安排好族人各自的生计,便褪去身上的绫罗绸衣,在黄大街的大树角,摆起了一个补鞋摊。一辆老式补鞋机,被祖母摇得咯吱吱响,破旧的鞋底在祖母手中,七拐十八弯,道道线丝将它补起来。祖母的手指粗糙了。也许就是那时,祖母的青丝掺杂了白发。高台在缝缝补补的日子里, 迎来了我婆婆的出生,也送走了大祖父。大奶奶三十刚出头便守了寡,拖着两儿一女。高台上的族人都在忙于糊口,没人去问,是大奶奶自己内心不愿再走他家,还是因为额头那道狰狞的疤而无法再嫁。更深人静,大奶奶的厢房里,时常传出一个女人的低泣。
祖母带着大奶奶还卖过开水——卖开水,不是卖茶水。皋城的街头,曾在一段时间里出现过这么一个奇异的行当:烧开水。一个硕大的灶台,掏出七八个洞,一起煨着几个黑黢黢的大肚子煨罐,咕嘟嘟地烧着开水。这个行当是现代人不能理解的—— 开水自己家不可以烧吗?皋城的卖开水, 不知兴起于何时,也不知何时戛然而止,我曾试着从厚重的《六安县志》里考究,结果一无所获。问问周边人,多数皋城人是不知道的。特殊环境下的某些特殊产物,总是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轻易就湮灭在历史的灰尘里,绝了踪迹。
那时,祖母和族人在高台下搭了烧水房,建了这么一个开水炉,维持着高台的活计。不烧水的街坊,可以提着热水瓶来祖母这儿买。大奶奶负责在灶台里添火,祖母则踮着脚,用巨大的长把水舀舀出,五分钱灌一水瓶,或是给人挑送去。烧水房里的水汽,终年氤氲着两个女人的身影,湿漉漉的。
当时的县黄梅剧团是祖母的老主顾。祖母高高的个儿,经常在下午五六点钟挑了一挑开水给黄梅剧团送去。高台人都习惯了,祖母不到七点不回来。她喜欢看戏, 尤其是这种无需买票的戏——常年供水, 跟剧团很是熟稔。戏台上,不论正演的是《沙家浜》,还是《梁祝》,她都能如痴如醉地看完。这个时候,她的眼泪是极其好赚的,《梁祝》她看了数遍,总是能在泣血的腔调中,哭到眼睛红肿。
前年我去独山,看见一个老式的戏台。戏台早已沉寂多年,不再有铿锵锣鼓、花旦小生,我凝视着空荡荡的戏台,突然萌生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此要强的祖母是否后悔过嫁给了祖父——他除了如清秀小生一般好看的皮囊,其余,空空如也。空荡的山风,低沉地呜咽,似在嘲讽我问得多余。可回去后,偶尔去高台探望,望着祖母道道沟壑枯如核桃的脸,我还是会想,祖母如此伶俐的女人,如果当初另觅良人,该是另一种富足吧?当然,生活不存在假设。
烧水炉没开多久,高台便又是另一番景象。有远见的祖母拆了烧水房,开了杂货铺,那个时候叫代销店。她进各种杂物, 比如白糖。白糖是紧俏货,祖母用秤称成一斤一斤的,用报纸包成工工整整的斧头状,再贴上红字条。还有各样散装食品。祖母把它装进透明的塑料袋,用带着锯齿的钢条对准烛火一溜边,封好了。我相信有人天生就有生意运,比如祖母,她做的每行生意都很好。高台上的日子很红火。她总是把钱财看得很紧,好像不一留神,祖父就把财物偷走给大奶奶了。这并非祖母多心,据丈夫回忆,他小时候就曾见过祖父偷偷给大奶奶买东西,印象里,还有过金戒指之类。我不去追问,既然是偷偷地,为何又弄得老少皆知?
祖母和大奶奶两妯娌彻底决裂,是因为小伯父——大奶奶的小儿子。祖母一直渴望有个儿子,不知什么原因,她和祖父只有我婆婆这一个女儿。大祖父去世后,祖母就撺掇祖父,要他把小伯父过继过来。祖父回来说,大奶奶好容易把孩子们拉扯大,舍不得。祖母恼了,自己找了大奶奶说这事。大奶奶自是拗不过祖母,就把小伯父过继给了祖母。说是过继,还都在高台, 吃同一锅饭,住同一个大宅院,小伯父连厢房都不曾挪过。可即便这样,大奶奶还是终日泪眼婆娑,夜不能寐。祖母终于顶不住族人异样的目光,把小伯父“ 还”了回去。祖母为这事一直愤恨着,多年都不曾原谅大奶奶。大奶奶等到儿女们都大了, 就随他们搬出了高台,只到去世,也始终没有再见祖母一面。她对祖母的感情,始终都是复杂的。
像高台这么一户外来人家,唯一的女婿一定是招赘入门,祖母所有的期待,都会如山一样,重压在女婿身上。我公公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有着物质上的舒逸,也必定有着精神上的惶恐,稍不留神就丧失了男人应有的骨气,迷失在小男人细琐的彷徨里。让人意外的是,听说公公很早就和高台决裂,带着婆婆过起了逍遥的小日子。我想,公公能够脱离高台,婆婆功不可没,她必定也早就厌倦了祖母的掌控。可是,如果当初依然在祖母的威压下生活,那位倔强的老爷子,恐怕不会初入商海被骗三十万?即便被骗后,也应该没有血性挨过那段被人追债的岁月吧?90 年代的三十万,不亚于现在的几百万。这些于我,如同看一部斑驳的老电影,除了几分好奇从中旁逸斜出,并没有激起我打探的欲望。
让我感兴趣的,还是高台。
祖母再强悍也没能留住自己的丈夫, 待祖父匆匆走完他怯懦的一生,高台终于成了祖母一个人的舞台。世事几经变迁, 高台下的那曾不起眼的一排排房舍已经变成寸土寸金的门面,眼镜店、首饰店、手机店,一个个带着明晃晃的斧凿之迹,生硬又规范地开拓了皖西路的繁华,祖母也因此加入了收租人的行列。只是高台上几间突兀的平房,被她执拗地留下,她仍住在低沉幽暗的瓦房,不愿搬进宽敞的小区。天井中的那株梅,几岁枯荣,零落的花瓣,偶尔还会暗香浮动。
等我嫁进门,祖母已经老了,风光早已不再,昔日高台上热闹一时的族人,早已七零八落,她的亲娚子侄不再事无巨细地汇报、聆听她的教诲,只在遇到难事时,才肯悲天跄地地前来求救——也许并非是向她求救,而是向她身后的我的婆家求救。往来高台的眉眼,大都充斥着俗世的狡狯。
我见祖母的次数屈指可数,尽管知晓了她的诸多故事,却始终无法把她当至亲, 总是游离于没有温度的亲情之外。祖母终年带着她的灰色毛线帽,围着蓝色布围裙, 喜欢用她一贯阴鸷精准的目光,在九墩塘公园的绿色垃圾桶里翻翻捡捡,如同寻宝。她的孙子——我丈夫,则开辆本田,护其左右。若是运气好,被她寻到笨重的废品,丈夫自是下车帮忙。多么滑稽的场景呵!我无比世俗地嘲弄丈夫:“难道汽油比垃圾便宜?”他憨实一笑:“都比不得她开心重要。”那时的祖孙俩,各自的内心定是都有着旁人无从体会的欢愉。
年迈的祖母似乎对钱着了魔,哪怕钱于她而言,已经失去了流通的意义,变成存折里一连串暮气沉沉的数字。她耳背,记忆力也衰退得厉害,但她能清晰地说清自己存折里的数字,记得哪天是收租的日子。前年端午,饭前我忘记奉上红包,九十三岁高龄的她突然对我的小姑子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我什么时候得罪过她?”众人一愣,随即满堂哄笑。我羞愧难当。若有人问她: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得大声连问几遍——等她听清,便笑了,右额上指甲大的瘊子在毛线帽下缀若一朵盛开的花:“给我大孙子留着!”长房为大!除了我丈夫,小姑子、小叔子在祖母眼里永远都排不上号。
古稀的婆婆搬去高台照顾祖母。她俩印证了遗传学在母女体貌性格上的神奇: 一样能干,一样执拗,一样大嗓门儿,一样耳背……如同惊人的复制!可婆婆高小毕业,喜爱追剧,又玩儿微信,岂能日落而息? 祖母总是精确地在下午五点把门紧锁,又拿了板凳牢实地抵上,容不得屋里再有一缕光亮,一丝声响。性格的雷同和生活习性的不同,使高台的小平房每天都有消弭不灭的战争。小姑子去时,常常见到这样的场景:两个老太太争吵得面红耳赤, 谁也不让谁。当然,她们总是各吵各的,甚至吵得都不是同一件事。她俩仿佛是天生的敌对。宿命的轮盘跟婆婆开了不尴不尬的玩笑:年轻时逃过祖母的掌控,年迈时又不得不回头来应对。婆婆问祖母饿吗?我给你买包子。祖母說刚吃过,不饿!转眼小姑子去了,祖母就会像孩子一样,泪眼婆娑着告状:她是成心想饿死我啊……是的, 祖母越来越像个孩子一样天真顽劣,耗尽所有迟暮的精力纠缠诸如此类的小把戏。婆婆含泪愤懑:这哪是娘俩?更像婆媳。祖母终于常卧病榻无力再争了,每天单纯安静得就像婴儿。俗世的任何声响,
任何事物都已进不去她自成一体的结界。她的胯骨已烂了个洞,黑黢黢如同地狱之门,往外汩汩地吐出祖母的血肉和精气神。医生也束手无策。我只潦草地瞥了眼小姑子发来的照片,已不忍再看第二遍。祖母的灵魂正在一缕缕消亡,内在的机体已经腐朽,冒着死气。一大早,祖母污秽了一床,小姑子一人清理不了,让婆婆匆匆吆喝了族里大婶来帮忙,大婶忙不迭地跑来一看,口无遮拦地笑了:“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要不行了呢!”——没人觉得此话不妥。然而,神志不清的祖母,一颗硕大的泪珠颤落。
一次又一次清理祖母的满身污秽,将族人的孝心和耐心殆尽,近乎麻木,男性小辈来了高台探望,遇见祖母赤身露体,也不再避嫌——没人当祖母是女人,甚至没人当祖母还活着,尽管她并没有真正死去。生与死的界限在她身上如此不明晰。倘若一生要强的祖母尚有一丝意识,能否接受这种没有质量、毫无尊严地活着?我垂下眼眸,无法替她回答。
疏梅筛月影,高台上的祖母呜咽一声, 短促到只像个没有任何实质的感叹号,她, 终于谢幕了,舞台依旧,幕布依旧……
责任编辑:黄艳秋美术插图:冯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