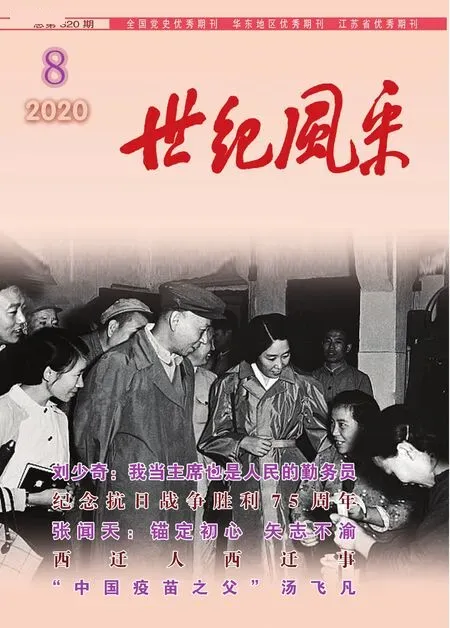“中国疫苗之父”汤飞凡
梅兴无

实验室里的汤飞凡
2020年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介绍,我国目前已有4种灭活疫苗和1种腺病毒载体疫苗获批开展临床试验。疫苗是战胜新冠病毒的根本之策,届时新冠疫苗将造福于全人类。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中国疫苗研制的先驱汤飞凡,他作为我国第一代病毒学家、免疫学奠基人,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各种疫苗,发现了沙眼病毒,为无数百姓的健康带来了福音。
立志做“东方的巴斯德”
1897年出生的汤飞凡,湖南醴陵人。他投身病毒医学纯属偶然。1912年,他考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金工科学习,1914年暑假,他去邻县萍乡煤矿观摩。一天,他与湘雅医学院创建人颜福庆及助手不期而遇,好奇地问颜提的箱子里装的什么,颜告诉他是显微镜,他们要用这部仪器给工友们检查钩虫。汤飞凡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动给他们帮忙。颜福庆手把手地教他使用显微镜,在标本上找钩虫卵。很快,汤飞凡就能独立在切片上找到钩虫卵了。颜福庆很喜欢这个好学的孩子,告诉他长沙即将成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欢迎他去报考。
于是,17岁的汤飞凡弃工学医,报考湘雅。湘雅是由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联合创建,教学全用英语。入学考试除考核医学基础知识外,还要考英语。汤飞凡没学过英语,就鼓足勇气向主考的美国牧师胡美请求:“请允许我暂免英语考试,进学校后再补考。”胡美被他的勇气和决心所感动,加上湘雅校长颜福庆的关照,他被破格录取了。为了尽快提高英文水平,汤飞凡每天苦背英文词典,一年翻破了一本英文字典,眼睛也变成高度近视,暑假回家错将哥哥认成了父亲,闹出笑话。功夫不负有心人,汤飞凡很快通过了英语考试。
求学期间,汤飞凡对显微镜下的微生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当下课后,他喜欢向研究微生物的颜福庆等老师讨教。但天有不测风云,家道中落,他的学费断了来源,只好到医院药房找了一份调剂生的工作,同时做英语家教,挣钱补贴学费。尽管这样,他的学业也没受影响,湘雅第一届招生30名,到1921年毕业时,只有10人顺利毕业,汤飞凡是其中之一。
20世纪初叶是世界微生物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传染病的致病菌被一个个地发现。汤飞凡认为这是解除人类疾病的治本之法,对当时国际顶尖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法国)和科赫(德国)非常崇拜。日本的北里柴三郎被称为“东方的科赫”,汤飞凡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一个‘东方的巴斯德’呢?”他暗下决心,终身从事细菌学研究,立志做“东方的巴斯德”。
从湘雅毕业后,同学邀他开业行医,他谢绝了,说:“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他报名考进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继续深造,在美籍德国人田百禄教授指导下,专门研究细菌。洗瓶瓶罐罐,造培养基,一般进修生不屑于做,汤飞凡却干得非常认真,还常帮助做实验的人观察动物,作病理解剖,分析实验结果,引起了田百禄的注意,很快被提为助教。汤飞凡在协和进修3年,不仅提升了理论水平,而且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实验技术。
1925年,汤飞凡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赴美深造。出国前,湘军团长何键把二女儿何琏许配给了他。这个何键就是后来叱咤三湘的“湖南王”。何、汤两家同为醴陵望族,向有通家之好。何琏秀外慧中,比汤小9岁,且身高也高出1.60米的汤半个头,但何仰慕汤的才华,非常中意这门婚事。
婚后仅两个月,汤飞凡即飞往美国,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学习。系主任秦瑟教授是世界闻名的学者,他见汤飞凡训练有素,就叫他直接参加了研究。此时病毒学正处于拓荒时期,哈佛医学院细菌系的研究重点转向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汤飞凡潜心研究病毒学实验方法,很快成为佼佼者。每次读书会上,他的发言见解独到,赢得老师和同学的赞赏。一次,秦瑟当着大家的面对汤飞凡说:“当今世界上搞好读书会工作的人,除了我以外,就是你了。”
哈佛的学习,使汤飞凡在细菌学研究方面得到长足进步。他在秦瑟的指导下,利用砂棒滤器、普通离心机等简单设备,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的、能离心沉淀的、能自我复制的、有生命的颗粒,是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他写的《疱疹病毒和脑炎问题》《对超滤的研究》等论文发表在美国《实验医学》《细菌学》《免疫学》等杂志上,引起美国微生物科学界的重视。
1928年,汤飞凡完成了在哈佛的学业。秦瑟一再挽留他留美工作。优厚的生活待遇,病毒学研究无比宽阔的视野,对汤飞凡产生了很大吸引力;但这时他又收到了恩师、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的来信,诚邀他回国服务,恩师在信中,没有许诺,只是如实地列出创办医学院的困难,同时充满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正是这种开诚布公,使汤飞凡改变了主意,决定回国,他说:“我的国家科学事业很落后,微生物科学更是一片空白。我希望为我的国家微生物科学的发展尽到绵薄之力。”
1929年春,汤飞凡回到上海,就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学院条件比他的想象还要差,细菌学系就是个空架子。汤飞凡就把从美国带回的显微镜捐出来,建起一个简单的实验室。在教学之余,汤飞凡开始利用简陋设备进行研究。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病毒学学科。
1932年,医学院从中央大学独立出来,改名国立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为教授,同时受聘为英国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细菌学系主任。他利用该所齐全设备进行复杂的实验,除了研究病毒外,还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肠炎都进行了研究。
1935年,汤飞凡赴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作短暂合作。某日,来院参观的日本人要和汤飞凡握手,汤断然拒绝:“你们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很遗憾我不能和你们握手。还是转告你们的国家停止对我的祖国的侵略吧!”汤飞凡住在离实验室2.5公里的地方,每日工作到深夜,然后步行回家。凭借在学术上的成就与威望,他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
从1929年到1937年的8年中,汤飞凡在病毒的方法学、牛胸膜炎的病原学以及沙眼病原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发表有价值的论文达20余篇,且多被权威性专著和教科书引为经典文献。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以他对科学的执着、严谨和敏感,以及病毒学研究的历史机遇,有望达成“东方巴斯德”的梦想。
然而,一场战争砸碎了他梦想。

1945年1月,汤飞凡(前排右三)与中央防疫处技术人员合影
研制出“中国第一支青霉素”
1937年,汤飞凡偕妻回到上海时,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火已烧到上海,8月13日中日淞沪会战爆发。汤飞凡虽身处上海租界,但已没有心思坐下来搞研究了,对何琏说:“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作了亡国奴,又有什么用?”他和妻子一起参加淞沪会战前线医疗救护队,他工作的救护站数次几乎被日军炮火击中,汤飞凡镇定而风趣地说:“我干这个最合适,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
接着,上海沦陷,南京失守。汤飞凡收到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的来信,邀他去长沙主持中央防疫处的重建工作。中央防疫处原设在北平,1935年迁至南京,1938年春又迁到长沙,濒临倒闭。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需要,汤飞凡毅然决然辞去月薪600银元的工作,携夫人直奔长沙,出任中央防疫处处长。
1938年6月,武汉告急,长沙岌岌可危,中央防疫处西迁昆明。此次迁滇困难重重,汤飞凡只得请时任内政部长的岳父何键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发电:“本部卫生署亦敝婿汤飞凡赴昆明筹设防疫处,到滇半月,尚未寻得地址,已嘱晋谒,请赐指教并望照拂。”
在龙云的帮助下,汤飞凡借到云南卫生实验所和省立昆华医院部分房屋。8月中旬,中央防疫处人员设备迁入,开始了紧张的重建工作。汤飞凡一手抓生存,防疫处仅存300银元,就争取银行贷款,组织员工养猪种菜,维持生计;一手抓基建,到1940年春,检定所、动物室、育苗室、菌苗室、血清室以及办公室、职员宿舍、器材仓库等相继落成,防疫处整体搬到昆明西山脚下的高峣村,开始了微生物药物研究和疾病防疫工作。
上世纪40年代,青霉素开始用于临床,大叶性肺炎、淋病、梅毒等病,都能做到药到病除。青霉素引入中国后,无论是抗战前方还是后方,许多人都等着用它救命,但数量奇少,价格奇贵,一根金条只能买到一盒青霉素。这极大地刺痛了汤飞凡的心,他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自己生产出青霉素!”
然而,青霉素的具体生产工艺在当时国际上属于军事机密,西方人虽然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但对生产、提纯的方法守口如瓶。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中央防疫处当时条件简陋,研制青霉素难上加难。汤飞凡说:“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要尽全力而为之。”
1941年冬,防疫处试制青霉素工作正式开始。首要的是找到能产生青霉素的菌株。在汤飞凡的带动下,防疫处掀起了“寻霉热”。自然界霉菌和孢子分布广泛,遇到适当条件就能生长。他们利用闲暇时间,随时留意鞋靴、旧衣、水果、古钱等物品上的青霉,取之涂布于培养基上,纯培养后再测定菌株的青霉素生产能力。一次次分离,一次次失败,可汤飞凡执着依旧。终于有一天,一同事从久未穿的皮鞋上发现一团绿霉,汤飞凡如获至宝,马上拿到实验室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株,这是国内首次分离出青霉素。经过上百次试验,到1944年春,他们总共得到30个本地菌株,其中产抗菌素的有13株,通过比较,还是来自旧皮鞋的那株菌株产量最高。
找到菌株不易,提取出青霉素更难。青霉看似普通,室内室外到处发霉,实则十分“娇气”,伺候它真不容易。第一,它对温度有特殊要求,在摄氏24度左右,所以必须专门为它建一个24度的恒温室;第二,它对通气有特殊要求,需要有足够的氧气供它呼吸,只能生长在液体表面,所以只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来培育;第三,它对营养有特殊要求,仅用一般的培养基还不够,必须给它加营养,几经调配,最后确定加玉米汁和云南的棕色蔗糖。
1942年,汤飞凡带领大家终于培育出了合格的青霉菌,他对接种后的青霉菌培养有着十分细致的观察和带着诗意的描述:“接种后,在室温摄氏二十四五度中,二三日内,培养基表面上即可长满霉菌,至四五日之间,霉菌颜色变青(芽孢成熟),有时青霉上常有呈金黄色之珠状水滴,其情形状况,殊似雨后荷叶上之水粒,灿烂夺目,备极美丽。至第五日或第六日,即可将培养液取出,而去其霉层。吾人每次培养,多为一二百瓶,至期全部取出,倾入大瓶,妥存冷藏室内,以待提炼。”
菌种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但由于经费缺乏,仍无法进行青霉素的工厂化生产。1944年春,汤飞凡的英国友人、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造访昆明,在李的斡旋下,英国红十字会向中国红十字会昆明办事处捐赠国币188万元。这无异于雪中送炭,汤飞凡写道:“承英国红十字会捐赠研究金一批,始将此近于玩耍之试探工作,纳入正轨。”
有了经费,汤飞凡处处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李约瑟在英国《自然》杂志发文对他的艰苦研制称道不已:“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但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他有一个效率高的培养、分装和检定系统。尤其有趣的是,他有一个自己的玻璃厂,能制造各种中性玻璃器皿;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过滤取水;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就自己制造。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毕都要检修,幸而没有发生事故。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
总装调试阶段,汤飞凡日以继夜地工作在机房,吃饭都是由妻子送,最终把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办成的事办成了。1944年9月5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在高峣村诞生。第一批出品5瓶,其中,1瓶自藏,2瓶送至重庆,2瓶分别寄至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鉴定,均获好评,随后大量投入生产,甚至能供欧美的盟军使用。
制造出青霉素后,防疫处可谓抱了一个大金娃娃。汤飞凡却没有借机敛财,而以1元1支的价格供应急需的军民。有些因寻花问柳而感染梅毒的富人提出用一根金条买一盒青霉素,被汤飞凡断然拒绝;而对需要救命的穷人,往往减价甚至无偿提供。
被誉为“中国疫苗之父”
在汤飞凡的带领下,中央防疫处成为了大后方绝无仅有的免疫学研究基地,通过提高研制水平,改善菌种,生产出狂犬疫苗、斑疹伤寒疫苗、牛痘疫苗,源源不断地供给在滇缅作战的盟军和云南各大机关学校、边区老百姓,挽救了无数遭受病毒感染的战士和平民的生命。汤飞凡也被誉为“中国疫苗之父”。
1942年,在滇缅战场作战的盟军发现天花病例。近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刚刚完成牛痘苗天坛株的重新筛选并研究出了新的生产方法。盟军立即派专家考察,发现防疫处的牛痘苗比印度苗更能有效地抑制天花病。于是盟军决定,不仅牛痘苗采用中国的,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都改由防疫处供应。随后一年,汤飞凡带领防疫处制成了中国最早的斑疹伤寒疫苗,并提供给在缅泰边境作战的盟军。
1945年,盟军又发生了“不明热”,严重威胁着部队战斗力。美军又求助于防疫处。汤飞凡派助手魏曦赶赴现场,通过调查和实验证实是恙虫病,进而采用针对恙虫的防制措施,“不明热”得到控制,魏曦因而获得美军“战时功绩荣誉勋章”。
抗战胜利后,汤飞凡随中央防疫处从昆明迁回北平。原防疫处已被日军破坏,他不得不再次白手起家。他四出奔走呼吁,争取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些物资和美国医药援华会捐赠的仪器设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兴建新址,1万多平方米的建筑物于1947年元旦落成,建立了中国第一座抗生素研究室(含青霉素生产线)和第一座实验动物饲养场。
同昆明一样,汤飞凡带领防疫处边建设边生产。1946年春,恢复了牛痘苗等急需制品的生产,支援解放区牛痘苗10万支。新址建成后又增加了青霉素、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的生产。
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汤飞凡拒绝执行国民党关于破坏中央防疫处的命令,将它完整地保护下来。他本人也面临人生新抉择:先是收到了去台湾的邀请,何键是国民党上将,他若留在大陆,这个政治包袱的影响不言而喻,但他仍选择留下;不久,又收到美国老师的邀请,让他携夫人赴美国工作,他心动了,他看重的倒不是美国优渥的生活条件,而是优越的研究环境。可临上飞机之前他改变了主意,他对何琏说:“我是炎黄子孙,应该为自己的祖国效劳才对啊!”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央防疫处改名为新中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任所长。他向卫生部门建议,设立生物制品质量管理中央机构。这个建议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向重庆当局提出过多次,但未被理会。这次他一提出,卫生部就采纳了,并委托他筹建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他不负厚望,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生物制品制造检定规程》,据此,我国有了生物制品质量管理的统一体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传染病肆虐,防疫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1949年10月,河北省北部鼠疫流行,需大规模接种鼠疫减毒活疫苗。当时国内没有,只好从苏联进口,但仍不能满足需要。政府要求研究所扩大生产,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领导一个组突击研制,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赶制出鼠疫减毒活疫苗900余万毫升,有效地遏制了冀北疫情大规模扩散。
1951年,国家卫生部门提出了“保障疫苗供应,控制传染病流行”的任务,汤飞凡迅速组织研究所大规模研发和生产,疫苗产量1951年比1949年增加了7倍,1952年又比1951年增加了13倍,保证了疫苗的供应,有效地控制传染病的流行。
为了扑灭天花疫病,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实行普种牛痘。生物制品研究所是牛痘疫苗的主要供应单位。该所使用汤飞凡选定的牛痘“天体毒种”和由他建立的乙醚杀灭杂菌的方法,在简单条件下制造大量优质牛痘疫苗,每天产量超过10万支,为全国消灭天花作出了贡献。据资料记载,我国在1961年就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16年。
从1949年至1954年短短5年内,我国烈性传染病得到基本控制。汤飞凡将工作重点转向常见病、多发病,特别是对儿童健康威胁极大的几种传染病。当时中国麻疹流行,冬春之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俗称小儿麻痹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一,常有爆发流行之势。汤飞凡很快分离出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制作出的麻疹活疫苗开始在北京的幼儿园内试用后,迅速推广。
汤飞凡还承担起黄热病疫苗的研制任务,为了解决病毒毒力变异问题,他利用1947年从美国获得的无毒病毒株17-D,很快制出了黄热病减毒活疫苗,解决了海港检疫接种黄热疫苗的燃眉之急。
此外,他还组织提高了白喉类毒素、卡介苗、百日咳菌苗、丙种球蛋白等制剂的质量,并扩大了生产规模。他一生研发疫苗硕果累累,在上世纪50年代,汤飞凡“中国疫苗之父”的名声已誉满神州大地。

汤飞凡(右)与李约瑟
国际公认的“衣原体之父”
1954年,汤飞凡几次去农村调查,目睹了沙眼的病患情况十分严重,这激起了他继续沙眼研究的强烈愿望。沙眼是一种传染性眼部疾病,因患者的眼睑长出形如沙子的颗粒而得名。在上世纪早期,国际公共卫生局估计,全球有1/6的人患沙眼,中国沙眼发病率55%左右,农村地区更是高达80%以上,其所谓“十眼九沙”。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汤飞凡就在沙眼病原体的研究上有很深造诣。那时日本科学家野口英世发表论文,称自己分离出了沙眼病原体颗粒杆菌,引起了巨大轰动。汤飞凡对他这个结论有怀疑和保留。在上海医学院实验室建好后,他就开始对沙眼病原体进行深入研究,他选出24个症状典型的沙眼病例,严格按野口的论文分离细菌。在长达7个月的实验中,仅有一次存在野口提到的“颗粒杆菌”,但他用这株菌接种家兔和猴子,均未产生沙眼症状。
汤飞凡的实验结果发表后,激怒了以野口为傲的日本人。汤飞凡备受舆论压力,但他淡定以对,继续对沙眼病原体进行系统研究,并把病原体接种到自己眼中,完全没有产生沙眼症状。事实雄辩地证明所谓的“颗粒杆菌”并不能引起沙眼。1935年,汤飞凡的研究结果最终被国际承认,彻底推翻了野口的结论。日本人引以为傲的野口英世,从此从日本的细菌学教材中消失。
“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医学科技人员科研的方向。”汤飞凡在1954年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辞去所长职务,恢复因抗战而中断近20年的沙眼病毒研究,他要找到危害人民健康的沙眼病的病根。
关于沙眼病原体,当时有两种理论:一是“细菌病原说”,一是“病毒病原说”。“细菌病原说”早已被他推翻,可“病毒病原说”尚未得到论证。沙眼病原研究需要临床配合,汤飞凡即与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张晓楼合作,每周他都带着助手到同仁医院沙眼门诊工作半天,采集典型沙眼病例样品。
一开始,汤飞凡把沙眼病人眼部分泌物分别接种给猴眼和小白鼠脑内试行分离培养,但结果全部阴性。接着他们又做了上千例实验,仍没有任何一组实验显示阳性结果。失败的情绪在研究所内蔓延开来,但汤飞凡没有丝毫放弃的念头,他意识到如果继续重复别人的分离方法,可能永远也没办法分离出沙眼病原体。
汤飞凡决定另辟蹊径,使用鸡卵黄囊作为实验材料对病原体进行分离。他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在没有任何可靠数据的情况下,他减少了抗生素的用量和抗生素与沙眼样品的接触时间。
1956年8月10日,汤飞凡与助手如往常一样来到实验室上班。这是新方法的第八次分离实验,传了3代后,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原体被分离出来了!汤飞凡异常兴奋,将这株病原体命名为“TE8”。T表示沙眼,E表示鸡卵,8是第八次实验。
在场的同事都无法抑制成功的激动,纷纷向汤飞凡表示祝贺。但他头脑非常冷静,说这次成功并不能排除其他偶然因素,一定要多进行几次实验才能确定分离方法是有效的。有了野口的前车之鉴,汤飞凡并没有急于发表论文,而是用了很长时间,继续进行病原体的分离、传代、动物实验。
1957年,汤飞凡的沙眼研究成果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公开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极大关注,但也有人质疑,如果不能证明分离出的病原体能够引起人类的沙眼,那便无法确认分离出的就是沙眼的病原体。
验证的唯一路径就是做人体实验,但实验有失明风险。许多人纷纷递交申请书,但汤飞凡还是决定由自己“以身试毒”,命令助手将沙眼病原体滴入了自己的眼睛。他的双眼很快就肿得像核桃一样,出现了明显的沙眼临床症状。别人都替他难受,他却非常高兴。在随后的40天里,他坚持不做任何治疗,收集了一批十分可靠的临床数据,无可置疑地证明了TE8病毒对人类的致病性。
随后,英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实验室都确认了汤飞凡的研究成果。汤飞凡是迄今为止唯一在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中国人,国际上把他分离出的沙眼病原体称为“汤氏病毒”。
由于沙眼病原的确认,使沙眼的治疗、预防有了科学的依据。根据分离出的病毒,科学家们研制出了新的治疗药物,沙眼发病率逐年降低,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沙眼病发病率不到6%。至今沙眼病几乎绝迹,彻底终结了这一世界难题。
1957年,汤飞凡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
士)。他感慨地对妻子说:“到底是在新社会,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在这样短的时间里顺利地完成这么多成果。”
1958年,一场悲剧降临到汤飞凡头上。在“拔白旗”运动中,“只专不红”的汤飞凡被打成了“白旗”,莫须有的罪名落在他的头上,有人诬陷他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是“国际间谍”;因他岳父何键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他又被诬为“特务”。在那个年代,这两顶帽子一般人是难以承受得起的,何况汤飞凡一介书生,心理防线立马被击得粉碎。他选择了自尽,时1958年9月30日,年仅61岁。
闻知汤飞凡的死讯,李约瑟给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写了一封信,称汤飞凡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公仆”,“人类的朋友”,“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断言“他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李约瑟所言不虚,科学界没有忘记汤飞凡的研究成果。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原体等几种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沙眼病毒”正式改名为“沙眼衣原体”,汤飞凡成为国际公认的“衣原体之父”。
1981年,“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有关国际组织拟将汤飞凡推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但因诺奖不授予去世人员,他失去了问鼎诺奖宝贵机会。在一次国际眼科学大会上,全场为故去的汤飞凡默哀3分钟,向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致敬。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为汤飞凡伸张了正义,恢复了名誉。1992年11月22日,中国邮电部发行了汤飞凡纪念邮票,以纪念我国这位世界上最早发现沙眼衣原体的著名专家,在其肖像左侧,就是那枚金质沙眼奖章。

1992年11月,中国邮政发行汤飞凡纪念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