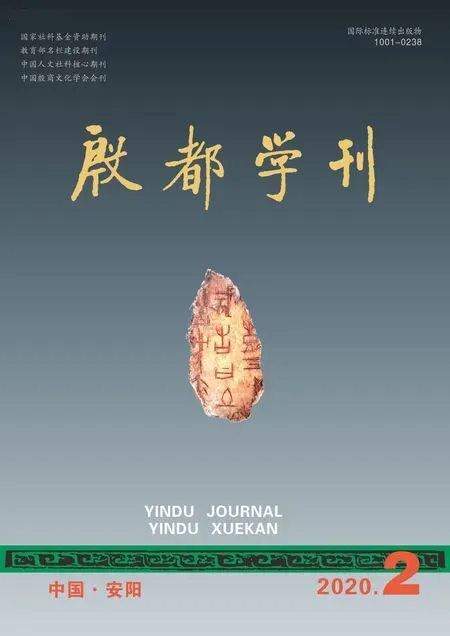论“女相如”称谓的生成与流变
汪 泽
(天津中医药大学 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天津 301617)
作为一个看似简单的才女代称,“女相如”于三字之间融合了古典人物的历史内涵及男女两性的反义组合。我们认为,语言凭借符号作用与文化发生关联,而人物称谓是维系日常交际与文字写作的重要语言行为,包蕴着鲜明的社会属性,受到政治、经济、伦理、教育等各方面的交叉影响,故而能够成为透视时代文化的窗口。
一、“女相如”的生成流变
《史记》《汉书》等记载了司马相如作为真实人物的生平事迹,凭借令武帝“恨不同时”(2)《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武帝爱赏司马相如《子虚赋》,初以其为异代人作,感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的文赋之才,司马相如得以拜官发迹、优游汉宫,更成就了“蔚为辞宗,赋颂之首”[1](P4255)的历史地位。相如的遗世之作,或以取悦、规谏君王为要旨(如《子虚》《上林》《谏猎》《大人》《哀秦二世》),或奉中央之命谕告下民(如《谕巴蜀檄》《难蜀父老》),或站在国家角度阐述兴衰安危之理(如《封禅文》),或以王侯为倾诉对象传达感遇情怀(如《长门》《美人》),皆带有强烈的宫廷文学属性。班固《两都赋序》明确将其定义为“言语侍从之臣”[2](P2)。
受其影响,魏晋六朝的辞赋、文序尝将司马相如塑造成奉制咏物及代言宫怨的御用文人形象——刘宋谢惠连《雪赋》杜撰梁孝王宾主兔园赏雪,相如为尊居右、率先吟咏;梁陆云公《星赋》写汉武帝观星昆明池,命篇于相如;萧统《昭明文选》所录《长门赋》序言强调说相如一赋值百金,感动武帝而重幸弃后,赞其才情与声名。
唐宋文人喜将“相如”作为文章才华对比的标杆,如李白《赠张相镐》自言“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3](P1760),杜甫《酬高使君相赠》亦曰“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3](P2446),此时期以司马相如为典故意象的文献在数量上超过了此前任何时代。但作为普泛化文才代表的同时,相如以文学能力侍从王侯的内涵依然保留——《新唐书·列传·文艺上》载初唐卢照邻为邓王李裕府典签,邓王爱重之,谓人曰“此吾之相如”[4](P5742)。
因典故人物的原初性别所限,诗文中“相如”所指代的对象原本为男性。但在唐代传奇小说《隋遗录》中,“相如”却发生了性别转换:
有郎将自瓜州宣事回,进合欢水果一器。帝命小黄门以一双驰骑赐绛仙,遇马急摇解。绛仙拜赐私恩,因附红笺小简上进曰:“驿骑传双果,君王宠念深。宁知辞帝里,无复合欢心。”
(帝)言曰:“绛仙不独貌可观,诗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谢左贵嫔乎?”[5](P372-373)
①在小区治理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不准确地使用了“社区治理”这一概念,为了尊重研究习惯,在综述部分本文沿用了“社区治理”概念。
“帝”即隋炀帝。绛仙乃炀帝宠姬,“相如”除赞其才调外,亦源于其宫廷侍君之身份,“女”则取其自身性别,以此形成了“女相如”之反义组合。
从现有文献看来,“女相如”在唐宋时期的使用频率较低。除却小说外,仅有北宋王仲修《宫词》:
良家选入侍仙都,性慧从来爱读书。记得茂陵封禅事,满宫呼作女相如。[6](P10198)
这一称谓移用于多才宫女,同样未能脱略内廷身份。

二、“女相如”的文化阐释
“女相如”由偶然搭配积淀为固定套语,最终成为浸润着审美情感的诗文意象,其产生与流行,俱不可脱离特定时代的文化底蕴。
(一)唐代女性的男装之好
在《隋遗录》中,“女相如”这一称谓出自隋炀帝之口。从人物原型来说,司马相如堪称文士才子之鼻祖;相比时代更早、命途坎懔的屈原,他因才得遇、善始且得善终,这迎合了传统乐感文化,不会使人产生类似“爱读《离骚》便不祥”[17](P69)的感受。《史记》所载其“琴挑”卓文君的绮丽情事,以及他“雍容闲雅甚都”[18](P3000)的风度仪表亦容易与女性产生微妙的关联。但我们不禁发问,隋代以前纵然才女数量有限,堪称楷模者仍不乏其人,即便限定在宫廷范围之内,亦有许穆夫人、班婕妤、左贵嫔等,缘何要将男性身份的“相如”作为中心语而贯以“女”字修饰?炀帝此语正史无考,我们宁毋将“女相如”的发明权归于《隋遗录》的作者,以此作者生活年代之文化背景为切入点,探讨这一反义组合的生成缘由。
《隋遗录》亦题作《南部烟花录》《大业拾遗记》等,宋代《崇文总目》归入杂史类,署颜师古撰,盖因其《跋》称此书于《隋书》(颜师古参与编撰)遗稿中寻得,又为颜真卿(师古后人)手书。依此看来,《隋遗录》应成书于唐初,但颜师古之著作权多不为后人认可。李剑国先生推测其出于晚唐文人之手,成书约在宣宗大中年间。[19](P557-560)
从直观现象来看,唐代女子多有男装之好。《新唐书·志·五行一》记唐高宗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4](P878);《列传·后妃下》载晚唐武宗贤妃王氏初为才人,每每伴君猎苑,“袍而骑,校服光侈,略同至尊,相与驰出入,观者莫知孰为帝也”[4](P3509)。《旧唐书·志·舆服》曰:“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20](P1957)《新唐书·志·车服》又称:“宫人从驾,皆胡冒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冒亦废,有衣男子衣而靴,如奚、契丹之服。”[4](P531)《大唐新语》卷十“厘革”有“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21](P85)之说。相关现象也被记录于诗歌作品中,李贺《荣华乐》(一作《东洛梁家谣》)言“军装武妓声琅珰”[3](P4440),李廓《长安少年行》明言“遨游携艳妓,装束似男儿”[3](P328)。
女扮男装的现象并非首现于唐代。但在此之前,无论真实历史还是文学虚构,易装女子迫于客观需要,身份多为参战女兵[22],例如著名的木兰从军故事。《南史》载南齐女子娄逞通棋术文艺,易装诈为男子,入朝为官并与公卿交游,后行藏泄露,被齐明帝勒令还家,改服女装,史臣仍斥其为“人妖”。而唐代女性身着胡服男衣,遍及各个阶层,纯然出于个人嗜好或时尚所趋,也未尝受到来自主流意识的制约。
《礼记·内则》曰“男女不通衣裳”[23](P836),两性易装原属禁忌行为,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服饰是一种礼制的外化,往往与社会角色的分类相为表里。社会角色作为一种个人行为模式,由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决定,需要符合社会所设定的种种规范。中国古代男女两性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周易·家人卦》彖辞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24](P185);班昭《女诫》曰“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25](P2788)男女两性维系着截然相反的文化范畴——内外、阴阳、刚柔、强弱。男子和女子的职属迥然有别,与生俱来的地位也高下分明。《诗经·小雅·斯干》云“乃生男子……载弄之璋……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弄之瓦……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26](P689-691)《礼记·郊特牲》曰“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23](P815);《说文解字》训“婦”为“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27](P614)。
唐代宫廷的一系列特殊政治现象在极大程度上动摇了正统礼教与性别观念。武则天执政称帝,颠覆了男性为尊的宗法制度;上官婉儿因才授职,统领词臣、大兴文治;太平公主、中宗韦后等亦操纵朝纲、得势一时。同时,唐代民族、区域之间交流频繁,游牧民族及西域胡地女易男装之俗流播中土,对于女子着装时尚乃至性别意识的改变起到推动作用。当然,女子干政及胡风化俗得以实现的关键,还在于唐代开明多元的整体社会风气,以及浪漫不羁而充满激情的文化特征。
但“女相如”的核心含义是女才士、女才子,再直白一些,是士人化的才女。唐代史料所载女性能文事迹不少,然其作大多散佚,所余零金断玉,尚不足形成气候。直至宋代,文辞非女子本务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
夫人幼有淑质,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欲以其学传夫人,时夫人始十余岁,谢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28](P2328)
苏瑑妻孙氏少年淑慧,却以“才藻非女子事”为由,拒学于李清照,陆游对于此事亦持赞同态度。
(二)明清才女的士人之行
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汉魏六朝妇女有著作传世者为33人,唐代22人,宋辽46人,元代16人;明代多达245人,确定生于万历以后者约占其总数的1/2;清代女性著述更是“超轶前代,数逾三千”[29](P5)。但就“女相如”称谓的普泛流行而言,女才妇学的空前兴盛只是基础和前提,更深层次的文化动因为晚明以来才女的士人化倾向。
首先,女性有机会接受男性化教育,才智杰出者被寄予承继家声的厚望,成为父母和亲族重点培养的对象。清初福建才女余尊玉,因母亲早寡无儿,自幼令服男装,延师教授;其人年仅十二即善诗文,可应对四方宾客。晚清浙江诗人闻璞亦为家中独女,父亲爱之如子,命着男子衣冠,从师学经,十四岁已工时艺。殉明文人王思任儿女成群,然出于对次女王端淑才能的盛赞,曾发出“身有八男,不易一女”[30](P38)之慨。乾嘉学者孙星衍之妻王采薇本有兄弟五人,父亲赏其才慧过男,教之一如教子。徐德音为清献公徐旭龄女孙,数岁即作五七言诗,祖父绝爱之,每遇宾客联吟即招德音侍侧,称“生男如是,当不误改金根”[30](P186)。
其次,江南地区出现了走向公众视野,以知识和才华获得经济来源的早期职业女性。明末清初黄媛介、王端淑作为诗史书画兼工的才女,皆生长于书香门第,后嫁文士为妻,面对贫穷与变故,不得不走出家门,以闺阁塾师的身份往来于各地。由于才学声名的相对逊色,她们的丈夫无力承担供养家庭的责任,或留守家中,或随妻出游。这种女外男内、妇唱夫随的家庭模式颠覆了正统的性别角色,且没有遭到家人以及社会的反对。黄媛介得到了吴伟业、钱谦益等男性精英人士的声援,王端淑之才名传至京城,清廷欲延请入宫,效汉代班昭教授妃嫔事,以端淑力辞而止。黄、王二人导夫先路,“到18世纪的早期和中期,(女性)职业塾师已更为常见”。[31](P134)
在兴趣趋尚方面,明末清初以来的女性乐于以结社、拜师等方式切磋文艺、交流创作,诗文雅集不再是男性士人的专利。晚明桐城方氏“名媛诗社”开风气之先,清代康熙年间林以宁、柴静仪等组建“蕉园诗社”,乾隆末期吴江张芬等创“清溪吟社”,道光年间京城顾太清、沈善宝等满汉女诗人合立“秋红吟社”。明末才女梅澹然以思想家李贽为师,清代女性受业于男性文人的现象更为普遍。吴绡、徐昭华、张蘩、徐映玉分别师承冯班、毛奇龄、尤侗、惠栋,乾隆年间以袁枚为师的随园女弟子、嘉道年间以陈文述为师的碧城仙馆女弟子皆多达四十余人。[32](P761)
在气质风貌上,明清知识女性同样表现出对珠翠粉黛、绮罗香泽的疏离。余尊玉、闻璞衣如男子,尚为奉父母之命、自幼习惯使然,柳如是、吴藻之易装则更多源于个人好尚。柳氏狷慧知书且豪宕自负,初为名妓,后为人妻,喜衣儒服交游名流学士,其夫钱谦益不加阻拦,且以“柳儒士”称之。吴氏生长于富商之家,作为著名闺秀词人,亦以男子衣冠示人,并自绘男装小影。另外,余德音作为官宦之女不御钗钿,常着墨迹斑驳之旧衣;蕉园诗社诸大家以“练裙椎髻”漾艇游湖,令“明珰翠羽、珠髾蝉縠”之邻舟仕女自愧弗如[33]。
明末乃至终清一代的小说戏曲作品中不乏士人风度的女性形象。《平山冷燕》作者抱定“旧日凤凰池固在,而今已属女相如”之意,笔下的山黛“美如珠玉”而“淡若烟云”[34](P353,201),身为宰相之女却喜淡妆素服,整日读书作文自娱,举止宛如寒素书生,有志以三寸柔翰再吐才人之气;另一才女冷绛雪出身村庄农户,被逼入山府为婢而毫不畏惧,反力争立身扬名、衣锦还乡。《玉娇梨》亦谓“千秋才子事,一旦属佳人”,主人公白红玉容色非凡、性情聪慧,知书能文如“女学士”[34](P137,2),令父亲不作生子之想。《林兰香》之燕梦卿被称作“女中丈夫”,洞识古今情,“虽一介弱女,欲与燕京人物分一席也”[35](P36)。《儒林外史》中的鲁小姐被膝下无子的父母爱如掌上明珠,“同男子一样”数岁开蒙、熟习经书时艺,所作文章“理真法老,花团锦簇”[36](P117)。《聊斋志异》中“女学士”颜氏因丈夫才智平庸而易装出试,科场连捷、芥视青紫,致使夫凭妻贵。
三、结语
“女相如”之产生与流变历程隐约反映出中国女性向男性看齐的历史诉求,在以“男女有别”“男尊女卑”为伦理根基的传统社会,不失为一道异样的文化折光。“女相如”诞生自唐代而兴盛于明清,从时空背景来看,女子干政、异端思想与异族统治导致了男权的相对式微,客观上为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创造了有利环境。从外在的着装习惯到内在的素质修养,从感性的个人好尚到理性的职属担当,从现实社会的人物原型到小说戏曲的艺术形象,女性通过模仿男性自觉不自觉间突破了传统,男性亦表现出默许乃至嘉许的态度。“女相如”以一种古雅、和谐、诗意的方式将女性的生理性别与人格角色完美结合,在封建社会末期,成为文人笔下的流行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