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写作的隐喻
唐棣
我是在二○一三年出版的“短经典”系列里,第一次读到以色列导演埃特加·凯雷特(Etgar Keret)的小说。篇幅都很短,并且故事通常发生和结束得都很突然。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书中的一篇同名小说《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一开篇就写作家身份的主人公,自言自语:“我是个写故事的,而不是讲故事的。”对于一个作者而言,或借主人公之口的“坦白”,一定要格外注意!这可能涉及作者对创作本身的思考。

与埃特加·凯雷特一同进入我视野的,还有“短经典”系列的另一本,《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作者是加拿大作家麦克劳德(Alistair MacLeod,1936-2014)。和凯雷特相反,麦克劳德觉得自己“是在讲故事,而不是写故事”。我开始好奇“写故事”和“讲故事”区别在哪儿?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个认识—写故事时,最好让读者感觉不到这是故事。看,那就是生活!是为“交融”。而讲故事必须让听众知道,这只是一个有创意的故事,所谓“间离”。
虽然,埃特加·凯雷特笔下的“生活”充满突变。但,这就是现代生活的变体。他的叙述是日常的,吃喝拉撒、插科打诨都有。还有主题之外,被捕捉到的生活里的灵光一闪。更重要的是灵光闪过,小说仍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本应该是生活给予我们的情意绵绵。可生活显然不够慷慨。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里主人公的反抗:“何况就算是写,也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受人逼迫。”读到这里,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太舒服的语气,预示着一会儿,第一声敲门声响起后,一个人突然闯入他的房间逼他做自己不喜欢的事。生活里总有一些意外。随着三声敲门声的响起,这个不幸的作家,又必须面对三个逼他讲故事的人—大胡子抢劫犯、问卷调查员、送比萨的人。到这里,故事已经混入了某种“危险”的生活场景。
小说继续写道:“他要写的不是关于政治或社会状况,而是关于人的状况—他自己正在经历的人的状况。”这时我才留意到关于“写”与“讲”的分歧,一直没有停止—也许这是重要的。其中一个听故事的人说:“我早就警告过你了,不要说敲门声!”主人公坚持要讲故事必须得说敲门声,不说敲门声就没有故事,三个人起先意见不一,产生分歧,于是故事又进入有趣又荒诞的状态,后来像所有生活里的样子,总有一方妥协。另一个听故事的人说:“给他点自由。你想说说敲门声?好,那你就说吧,只要能给我们讲个故事。”就这样,可怜的自由,也被一点点吞噬掉了。本以为终于换来了一点故事,这三个闯入者很高兴,在等待这个故事被讲起时,小说突然结束了。你会发现小说家,等于是写了一个“讲故事的人”的境遇。
小说结尾出现一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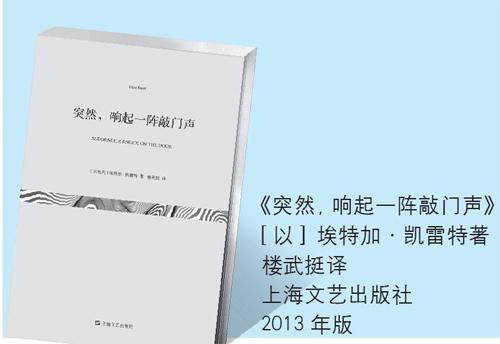
他怀念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的感觉……它存在于你的内心,作为新事物的一部分被你发现了,而整个新事物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
作家埃特加·凯雷特,说出了“无中生有”是毫无价值的。
关于“已经存在的事物”,赫尔曼·黑塞在小说《玻璃球游戏》里说:“向人们叙述某些既无法证实其存在,又无法推测其未来的事物,尽管难如登天,但却更为必要。虔诚而严谨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作为业已存在的事物予以探讨,这恰恰使他们向着存在的和有可能新诞生的事物走近了一步。”
是这个道理。作家凯雷特的写作,把记忆和历史、个人与时代植入当下,但又不完全是经历,它只是带着强烈的生活气息,走近了部分的“真实”—在第一个进门抢劫的大胡子口中是这样:“在这个国家,不管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争抢区区一个停车位,强力就是一切。我们只听得懂一种语言,那就是暴力。”人物受控于现有的社会生活,至此小说人物也被卷入了一场关于“真实”的讲述。
请看这一段:
城中各处,来自贫民窟的暴徒愤怒地冲击了富人们温暖如夏的住宅。几天后的新闻评论节目上,其中一名暴徒说,他们家里的太阳让我们气不过。因为没钱,我们连屁股都要冻掉了……说到这,那名暴徒突然号啕大哭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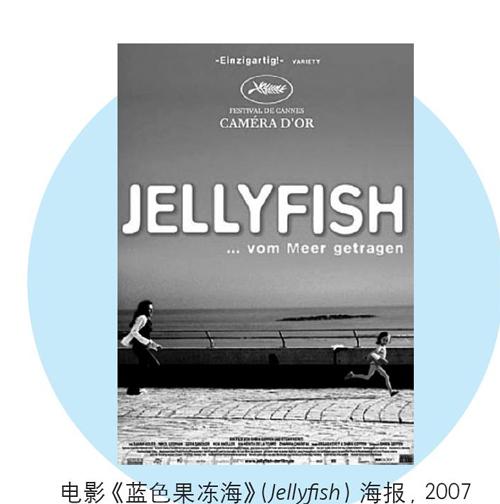
這些边缘的生活和社会状况,看上去也是故事讲下去的动力。事实上,凯雷特写的,正是“我们自己束缚自己,以至于无处发泄”的后果。每个人都会成为某个事件里“无辜”的参与者,没人猜中谁会是下一个。作为个人与历史夹缝中的人,他们似乎都已经对这一切,习以为常。
而凯雷特所做的,就是打破这种生活表面的宁静。打破之后,又像个孩子似的,灵巧地,逃走。
这让我想到了文字之外,同时作为当代以色列非常重要的电影工作者,凯雷特在二○○七年曾拍摄了一部叫《蓝色果冻海》(Jellyfish)的电影。这部处女作直观地反映出他热衷表现生活内部的浪漫本质,也印证了我的某些疑问,比如为什么在他那些书写困境的文字里,从来没有看到过绝望、污浊或者不寒而栗的东西,尽管他的文字经常有粗口、咒骂,但始终洋溢着一种诗意。
电影中译片名里的“蓝色”贴合浪漫的主调,而“果冻海”的俏皮劲,更是代表了他笔下的那些边缘人的个性。这个翻译比原来片名直译“水母”更动人。水母的隐喻性后来在电影中慢慢解开。紧接着,我们看到不多不少,又是三个闯入者—和《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一样—不肯拿掉游泳圈的小女孩、即将回国的菲律宾佣人、企图自杀的女诗人。
她们分别闯入了三段故事中每一个主人公的生活。本来,这几个主人公的生活状况都挺悲惨的,但小女孩使做婚礼服务员、孤独又无家可归的姑娘有了情感陪伴;菲佣令理解不了女儿演员生活、与女儿格格不入的母亲得到了慰藉;女诗人把总统套房换给了无处可度蜜月的新婚小夫妻。
一部电影三段故事,一段故事两个主角,一场生活六个人物,偶尔相遇或永不相见。
我最感兴趣的是那对新婚夫妻的故事。因为妻子的脚受伤,小夫妻不得不在附近酒店里“度蜜月”。不巧的是旅店只有一间总统套房。新婚夫妻住在普通房间,忍受着吵闹的空调声。妻子吵着要住总统套房。忽然有一天,新婚丈夫遇上住总统套房的女诗人,他说到了自己的麻烦。妻子知道这件事后,还嘲笑在总统套房写诗的诗人。当天,新婚妻子坐在梳妆台前写下一段话—
瓶中船,沉不下去
或布满尘埃,看上去很漂亮,浮在玻璃上
船小得无法驾驶,没有前进的方向
风不会扬起它的帆,它也没有帆。仅是一小片,一条裙子
和在它们下面的水母
尽管身处水域,它的嘴唇却是干枯的
只能通过睁大的双眼呼吸……
而那个风韵犹存的女诗人感受到了新婚丈夫的烦恼之后,慷慨地同意跟他们换房。交换时,女诗人跟有些敌视自己的新婚妻子说:“阳台上可以看到海,但我总是拉上窗帘,我讨厌光。”
诗人讨厌光,却拥有大房间,让我想起新婚夫妻想去度蜜月却被困在这个旅店的小房间里……如此种种,当下社会里,人的状况,就是如此。
更换房间后没多久,于电影五十分零二秒中断的那段关于水母的诗句,在电影一小时十分四十八秒处,在旁白中继续:
永远合不上的双眼
没人会注意到她的死去
她不会撞到岩石
她保持高高的姿态,还有骄傲
如果离开时你没有吻她
我的爱,如果你能
记得回来时给我个吻……
这时,女诗人已躺在新婚夫妻原来的房间里平静地死去。新婚妻子从总统套房焦急地跑到房间,看到了这张写着诗句的纸—正是她留在房间抽屉里的。她拿着那张纸,流下了眼泪。
其实,这一段诗包含了整部电影讲述的三个关于生活的意象—
“沉不下去”,就是指那个始终不肯摘下游泳圈的小女孩,形象很像一个水母,而她最终沉入了海底。
“船小得无法驾驶,没有前进的方向”,说的是菲佣抱着船模离开了老人,独自坐在不知开往何处的出租车上。
“風不会扬起它的帆,它也没有帆”,女诗人自杀成功了。没人可以改变这一切,不是死在总统套房,就是死在普通客房……
电影也会给人一种“故事就这么完了”的困惑感觉。可以这么说,凯雷特热衷的主题是,忽然闯入,掀起波澜,再悄然离去。但你仔细想想的话,可能又觉得其间似乎发生了某些重大的事情—它除了留下一串疑问、若干诗意瞬间,还留下忽远忽近的生活假象。
埃特加·凯雷特在电影和小说背后,熟练地掌握着这份距离感,让生活时真时假,但总是围绕着那些切实、粗糙甚至生活感极强的细节。生活无真相,他显然暂时认为,真相就是疑问(或者某些飘忽不定的因素),疑问就代表,至少还有人关心真相。在我看来,这就像是一个关于写作的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