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永无岛
黄天怡
开着车行驶在高速上,静静地欣赏着似乎阔别已久的平凡都市风光。时值黄昏,暮色四合,建筑的轮廓渐渐模糊。蓦然间,高速两侧的路灯次第亮了起来,两串温柔的橘光顺着淡灰色的路面延伸开去,仿佛有一出好戏正要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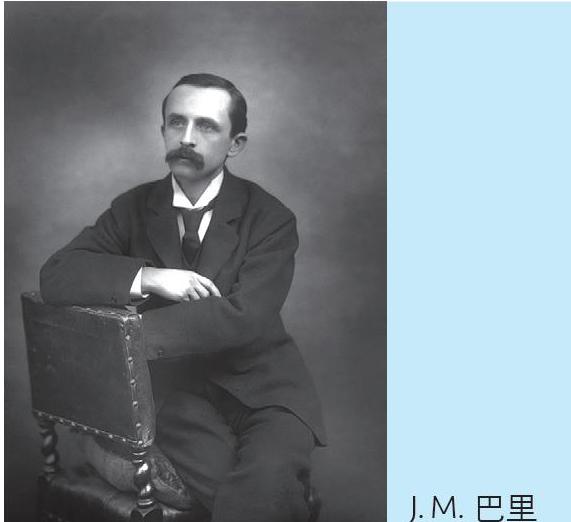
我从小就最喜欢黄昏,喜欢路灯。关于路灯最初的记忆是爸爸接我从幼儿园放学,我们总是会先去半路的公园玩上一会儿,直到华灯初上,爸爸才会把我放上自行车前杠,呼哧呼哧地踩着踏板带我回家。那时候我坐在前面歪着身子,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路灯。黄黄的,高高的,很亮,但却不刺眼,仿佛一只只温柔又慈祥的眼睛,静静地用橘色的光笼罩着灰扑扑的路面,给世界染上一丝暖意。
说也奇怪,每当我回忆过往,首先浮现的并不是那些通常意义上的高光时刻与重要瞬间,反而是這些琐碎平凡、不值一提的小事: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坐在走廊上喝的丝瓜汤、邻居院子里的葡萄、电视里播放的《八仙过海》、在表姐同学家的沙发上实在撑不住睡过去的跨年夜……一盏路灯,一片草叶,一丝若有若无的气味,组成人生的,不就是这些平平无奇的碎片吗?人生如同一条湍急的河流,一刻不停地朝着前方波光粼粼的大海奔涌。前方的广阔吸引着我们的目光,但是真正会硌疼皮肉的,却是脚底踩住的粒粒细石。这些河床细石或许才是我们的源头和来处。正是对这个来处的眷恋,构成了我们内心无从捉摸却挥之不去的奇特乡愁。
岛屿和来处
去年夏天我完成了英国作家J. M.巴里(1860-1937)“彼得·潘”系列的重译工作,包括小说《彼得和温蒂》《肯辛顿花园里的彼得·潘》以及剧本《彼得·潘》《温蒂长大了》,一共四部。在逐字逐句重新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我猛然意识到,这个在我记忆里已经显得过分熟悉的故事,原来并不只是关于不想长大那么简单。巴里笔下的永无岛,竟然像极了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来处”。巴里收起人生之河中看似无用却闪闪发光的河床细石,堆成了这座永无岛。它难以描述、难以概括,却永远令人向往。
岛屿对巴里而言似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意象。在他的剧本代表作中,有两部都是以岛屿为舞台。除了《彼得·潘》里的永无岛,剧本《可敬的克莱顿》(The Admirable Crichton)也是在荒岛上发生的故事。岛屿是巴里念念不忘的旧梦,在剧本《彼得·潘》的前言里,他这样写道:

这孩子如饥似渴地读着有关荒岛的书,他称之为漂流岛。……他在帕斯黑德农场的田里挖了一个洞,把自己的岛屿埋了进去。……他成年了……开始炮制戏剧,他发着抖,唯恐某些没格调的人去数戏里一共有几个小岛。……我们在思索,思索再多一个岛大家还受不受得了。
他说的这些岛屿是什么?是写作的题材?少年的梦想?接下来有一段这样的话,似乎为我们略微揭开了谜题的一角:
也许人的确会变,能保持不变的部分非常之小,小得就像视野里的一粒微尘。和那微尘一样,不变的这部分也会一直在我们眼前跃动,影响我们一辈子。我剪不断悬着这粒微尘的头发。
微尘也好,岛屿也罢,或许巴里想表达的是不论人生之河奔向何处,总有一个所在始终不变。即使我们无法再次登岸,却总能听到海浪声。它永远存在心灵深处,不会消失。它是童年,是最初的渴望,是不变的本色,是忠实的自我……它默默昭示着灵魂的起点。在巴里笔下,它就叫永无岛。永无岛像一个永恒的谜。它的地址语焉不详,仅仅是“第二个路口右转,一直走到天亮”;它的样子模糊不清,甚至“直视它有可能刺伤你的眼睛”。但是每个人都想再次登上去,都想再听一次海浪声,再看一眼环礁湖。这时候,彼得·潘出现了。他成了永无岛的向导。他穿着叶脉和蜘蛛网做成的衣服,满口乳牙,几乎没有重量,拒绝长大。他钻出遮盖着永无岛的幕布,跳进窗子,引诱人们重返那片神奇的土地。

巴里在书中写道:
彼得不在时,整座岛都很懈怠。可一旦海浪透露了彼得即将回来的消息,岛屿便蠢蠢欲动起来。
这正是在暗示彼得·潘只不过是永无岛的人形化身。他们是合二为一的存在,彼此不能分离。永无岛上的一切组成了彼得·潘,彼得·潘也掌控着永无岛的所有。最能说明这问题的,就是永无岛和彼得·潘身上共同拥有的一项特质:正邪不分。把永无岛与一般意义上的快乐天国、纯真乐园区别开来的,就是这个“正邪不分”。岛上既有美丽的环礁湖,也有阴森的海盗船。森林里还是夏天,湖面却已结冰。它时而令人欣喜若狂,时而叫人心惊胆战。白天的永无岛温柔可爱,到了夜晚却是危机四伏。野兽、海盗和走失的男孩们转着圈追逐,仿佛在玩可爱的儿童游戏,可一旦他们相遇却是在互相杀戮,激战过后地面上全是鲜血。美人鱼虽然会和五彩缤纷的泡泡玩游戏,但也会悄悄捉住温蒂的脚踝,想把她淹死。这样一个地方真是叫人又爱又怕。与其说重返永无岛是享受天真无邪的欢乐,不如说是一场深入丛林的秘密冒险。换言之,我们探寻来处也许并不一定能带来抚慰,认识自己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意外和恐惧。
彼得与胡克
再来看看岛屿的化身彼得·潘。一九一二年,伦敦肯辛顿公园里竖起了一座彼得·潘的雕像,巴里对这雕像并不满意,他的评语是“没能表现出彼得邪恶的一面”。没错,邪恶的一面是彼得·潘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的确非常迷人可爱,贪玩浪漫,但他绝不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小天使。巴里在故事中从不吝于表现彼得·潘的无情和多变。从刚开始我们就应该对此有所察觉:他在半路就差点忘记了温蒂他们,当迈克在半空中睡着坠海时,彼得·潘更多的是感到好玩,即使在紧要关头救回了迈克,但“让人觉得他感兴趣的其实是炫技而不是挽救人的性命……很可能下次再有谁掉下去,彼得却懒得管了”。书中还写到,为了遵守他制定的规则,走失的男孩们要是长大了,就会被彼得·潘处理掉。带着男孩们和印第安人对战时,他会突然变成印第安人,只为让战斗变得更加激烈好玩。彼得·潘代表着完全的自我,他完全忠于自己而活。

正因如此,我们在看待故事中的胡克时就绝不能把他看成一个简单的“反派”。胡克的确是彼得·潘的反面,但他们的关系绝不是英雄和坏蛋。他们都杀人,都偏执,都任性,甚至都渴望有一个妈妈。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从胡克内心所遭受的拷问可以看出来:
胡克总能在内心深处听到“嘎”的一声,仿佛生锈的门被谁推开,门外传来严厉的“哒哒哒”的声音,就像失眠的夜里听到有人捶墙。那声音永远在问一个问题:“你今天保持良好的风度了吗?”
“名声,名声,那个闪闪发亮的小玩意,它是我的!”胡克喊道。
此外,关于胡克为何痛恨彼得·潘,巴里也给出了再明确不过的答案:
彼得只是一个小男孩,这个男人干吗这么恨他呢?的确,他把胡克的胳膊扔给了鳄鱼。可……这件事……无法解释为何胡克对彼得的恨意是那么持久和恶毒。彼得身上的确有某样东西把这位海盗船长逼得发疯。不是他的勇气,也不是他漂亮的模样……是彼得的傲慢。
结合这两点,胡克是怎样一个人呼之欲出。他没有自我,永远都被外界左右,无法逃离世俗的评价和规则。尽管他是一个海盗,却依然注重衣着,甚至连当初在上流社会学到的步伐都不肯放弃,就连骂人的时候发音都要保持纯正。他在意自己的身份,在意自己的阶层。反观彼得·潘,却是始终睥睨一切,不受世俗桎梏。正是彼得·潘的尽情做自己激怒了胡克。因此可以说,彼得·潘与胡克的对立,是自我评价与外界评价的对立,是真实人格与规则评判的对立。巴里笔下的彼得·潘显然比胡克更加可爱迷人,他也许始终怀有与世界对抗的心理。他渴望尽情做自己,但又无法摆脱世界的评判。他认为世界无法理解自己,但又不得不屈从于这个世界的某些规范。这种纠结可以从故事的高潮部分窥见端倪。胡克和彼得·潘对决的最后,胡克落入了鳄鱼的嘴里,他死了。在他死后,巴里卻这样描写获得胜利的彼得·潘:

那天晚上彼得又做梦了,他在梦里哭泣了很长时间,温蒂把他紧紧地抱在了怀里。……彼得在船舱里坐了很久,嘴里叼着胡克的雪茄烟嘴,一只手紧紧捏着拳头,只有食指伸出来装成铁钩的模样。
怎么回事?彼得·潘竟然变成了胡克!也许这才是巴里想说的悲剧吧。胡克和彼得·潘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哪一面都无法单独存在。胡克消失,彼得·潘也会迷茫。尽管他渴望回归纯粹的自我,试图挣脱被外界评价束缚的自我,但也许,这两种自我之间的缠斗和纠结,才是他一生都无法逃离的主题。
爱,以及救赎
伟大的作品一定会提出救赎。巴里所描述的救赎既是故事的伟大之处,也是他的局限所在。
首先回到开头,看看当初彼得·潘为何要离开永无岛,冒险钻进达令家的窗子,带走温蒂呢?原来是为了让温蒂去永无岛上做妈妈。可这个妈妈十分特别,她被孩子们称为一个“很像妈妈的人”。彼得·潘在这段关系中扮演“爸爸”,可就连吃饭都能假装的彼得·潘,却无法真心相信自己是爸爸,他问温蒂:“我们只是在假装吧,对吗?假装我是他们的爸爸?”温蒂告诉他:“要是你不愿意,那就不是真的。”接下来温蒂问彼得·潘:“你对我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彼得·潘回答:“我是你的儿子。”
现在我们也许能看到彼得·潘,或者说巴里想要的爱是什么模样。这种爱比母爱更亲密,比男女之爱更纯洁。这种爱具有极大的包容,能彻底接纳最纯粹的自我,还能随时放手,让这自我来去自由。这种爱几乎都是付出,不需要对方给出任何承诺,就像母亲永远能对孩子给予原谅。在巴里的理解中,爱不是关系的产物,而是女性身上天然具备的某种能量,他要做的只是把它拿到手里。所以海盗们会说,我们只需要把妈妈抢过来,让她做我们的妈妈就行了。在海盗和孩子们看来,这种爱是可以单方面夺取的。
巴里对“爱”有这样任性的、一厢情愿的定义,和他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巴里六岁那年,他十四岁的哥哥大卫不幸夭折。大卫是巴里的妈妈最爱的孩子,他夭折之后妈妈的余生都陷入了极深的忧郁。小小年纪的巴里为了安慰妈妈,常常扮演成大卫的样子。巴里写过一本关于他妈妈的书《玛格丽特·奥吉薇》(Margaret Ogilvy),里面谈到了他如何安慰妈妈:
我把妈妈的笑记录在一张纸上,一道杠代表笑了一次。早上医生来的时候,我会骄傲地把记着笑声次数的纸拿给医生看。记得我第一次把划着五道杠的纸塞到医生手里,并且向他解释那些杠杠的含义时,医生放声大笑起来……他说我应该拿给妈妈看……在他的敦促之下我去了。妈妈笑了,当我在纸上记下这次笑的时候,妈妈又笑了一次,尽管那是个带泪的笑……
巴里一生最爱的人就是他的母亲,可由于大卫的夭折,母亲那份最浓烈的对孩子的爱永远地停留在了大卫身上—至少在巴里看来是如此。在余下的人生里,巴里一直在追寻这份缺失的爱。为了振奋妈妈的精神,巴里努力念书,考进了爱丁堡大学就读文学。毕业之后第一次向报社投稿,撰写的又是母亲曾对他口述的小故事。一八九七年,住在肯辛顿公园的巴里认识了卢埃林·戴维斯(Llewelyn Davies)一家,从此他一切的重心都转移到了戴维斯一家和他家的五个孩子身上。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巴里都和他们全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忽视了自己的妻子而导致玛丽出轨,不得不以离婚告终。
有关巴里和戴维斯一家的关系,坊间一直议论纷纷。有人说巴里爱上了塞尔维亚,有人说他爱上的是那五个小男孩。但在我看来,吸引巴里的是一份关系。不论是他和五个小男孩站在一起,给戴维斯妈妈做儿子;还是他和戴维斯妈妈站在一起,给五个男孩当爸爸;这两种关系、两种身份混合起来,成就的是巴里心目中最完美的爱和救赎。他渴望身处其间,享受这种双重关系所带来的满足。戴维斯妈妈就是温蒂,他就是彼得·潘。他一方面渴望和五个男孩一起当儿子,尽情享受妈妈无私的爱,另一方面却不愿付出承诺,既没能维持好自己的婚姻,最终对塞尔维亚也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求爱。我认为这种表现和他在彼得·潘的故事中描述的那种完美而奇特的“爱”是一致的。
巴里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止于通过这个故事表达自己对这种爱的渴望,而是不断在审视内心,这种爱是真实存在的吗?追求这种爱的自己,是可悲的吗?对“温蒂”来说,是公平的吗?在书中,温蒂执着于和彼得·潘建立起不同于母子的关系,并不断拒绝彼得·潘各种一厢情愿的任性要求。在海盗们想抢夺她的时候,温蒂大喊“绝不”。温蒂和达令太太像是连接彼得·潘与现实世界的钥匙。她们的坚韧和宽容让彼得·潘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这份反思最集中的体现,便是彼得·潘在全书中唯一一次真正因为动了恻隐之心而改变行动的一幕。他赶在温蒂他们飞回家之前来到了达令家,想把窗子关上,好让温蒂永远留在自己身边。可这时他看见温蒂的妈妈在一边弹琴一边流泪:
彼得:……她在用那个大盒子说话呢,她说“回家吧,温蒂”。你再也看不到温蒂啦,太太,因为窗子已经关上了!……她想让我们把窗子打开。才不呢!她真的好喜欢温蒂呀。可我也喜欢她。我们不能都和她在一起,太太!(彼得心头涌过一阵奇异的感受。)走吧,叮叮,咱们不要看这傻妈妈了。(他打开窗子,和叮叮铃一起飞走了。)
彼得·潘在那一刻仿佛看到了爱的真相。他突然感到囚禁温蒂换来的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说,他突然意识到那个想要的东西也许只存在于他的幻想里。那一刻他彻底放弃了温蒂,所以到了故事的结尾,走失的男孩们都被领养了,过上了正常且乏味的人生。但是彼得·潘永远不会回去:
再也没有比这更美的画面了。不过看到这一幕的只有正在窗户边凝视的一个小男孩。他的生命中有着数不清的、其他孩子永远也得不到的欢乐;可现在他透过窗子看到的这种欢乐,却注定永远把他拒之门外。
彼得·潘是骄傲的,是特别的,其他孩子永远也无法和他相提并论,无法体察他丰富多彩的世界,可是彼得·潘也无法和其他人构建起正常健康的关系,他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爱。
现在来读一下结尾吧:
温蒂最后还是让他们飞走了。……距离刚才发生的事已经过去很久很久。简长成了一个普通的大人,她生了一个女儿叫玛格丽特。每到春季大扫除的时候,只要彼得没有忘记,他就会来找玛格丽特,带她去永无岛。女孩会在岛上给彼得讲他自己的故事,彼得听得很专心。等玛格丽特长大了,她也会有一个女儿,到时候就由她来当彼得的妈妈。只要孩子们还是那样快活、天真、无忧无虑,这件事就会永远这样继续下去。
温蒂老了,飞不动了,可她让自己的孩子世世代代地陪伴着彼得·潘,永远都有一个“妈妈”为彼得进行春季大扫除,让彼得·潘再也不孤独。
过去读这一段,感觉字里行间满是对温蒂的怜悯,仿佛能飞去永无岛是最大的胜利,而容许温蒂和她的女儿们飞去永无岛才是彼得·潘对她们的恩赐。我们也许会误以为彼得·潘是那位英雄,他来拯救大人,让他们不要囿于俗世。可现在重新思索这一段的含义才会发现,真正的救赎是温蒂。是她一直守护着彼得·潘,传递着爱,重复地讲述她的故事。也许她会老去,会失去翅膀,可是她不会放弃彼得·潘,她会永远陪伴着他,让他不再孤独。这大概就是巴里对曾经爱过自己的女人们最终的致意。
借着童年那盏路灯的光,我窥见了一个属于我的永无岛。而其实艺术的本质应是模糊。伟大的作品如同一粒种子,一旦撒入人心灵的土壤,就将开出面貌不同的花朵。《彼得·潘》这部充满谜团的作品,创作它巴里几乎耗费了一生。诚然,他拼接的是与戴维斯兄弟们相处时闪现的种种火花与回忆,但用以缝补的针线却是只属于他的秘密。他拈起内心深处那根隐秘的细线,将童年过往、人生经历、对世界的看法、对自我的剖析,都缝了进去。如何解读和看待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故事能永久停留在人们心上,唤起心中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乡愁。不论那是对童年的眷恋也罢,對自我探求的渴望也好,能和一个伟大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共振,那也许就是作为读者的一份微小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