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花纹
黄昱宁
毫无疑问,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是我的翻译生涯里遭遇的最难啃的骨头之一。《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之后,我再次面对他的中篇小说《地毯上的花纹》(The Figure in the Carpet),既跃跃欲试,又一筹莫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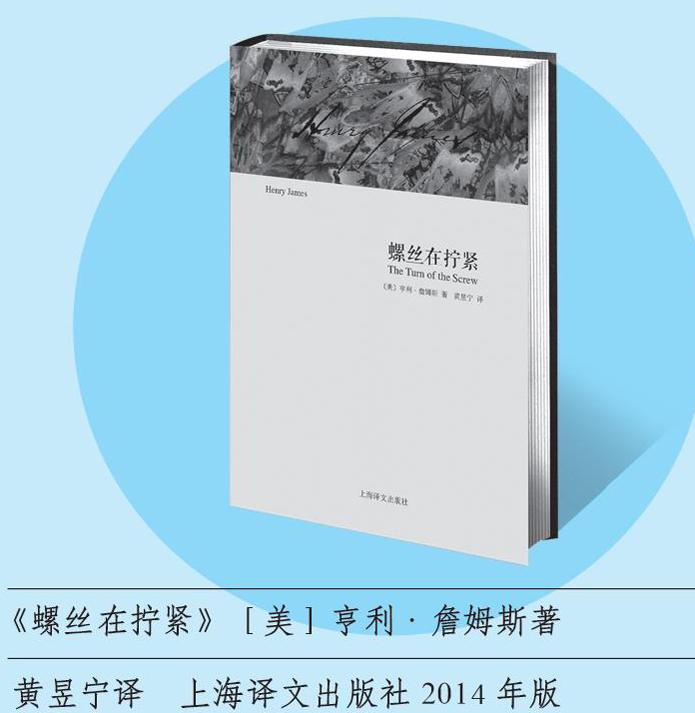
一筹莫展是因为,詹姆斯的文本,无论是对其语法的理解层面,还是对其意义的阐释层面,都有着让人深感受挫的难度。第一遍读下来,小说里的情节和人物都如鬼魅般忽明忽灭,躲开一切明确的结论—你横竖抓不住什么。十九世纪末英美文学圈的生态,隐约在小说中现出轮廓,有时细节纤毫毕现,有时又仿佛置身于半透明的罩子里,被看不见的手夸张而剧烈地摇晃。显然,这不是一部以古典现实主义准则构建的小说,它具有某种詹姆斯笔下特有的迂回而不安的现代性。
跃跃欲试是因为,这一篇虽然译成中文后僅三万字,却在詹姆斯的写作生涯中具有非常独特的风格和相当特殊的地位。小说首次发表于一八九六年一月号的《大都会》月刊(Cosmopolis),这本杂志虽然只存在了三年,却有过不小的排场:总部在伦敦,且在柏林、巴黎和圣彼得堡同时发行当地的版本,很吻合小说中描述的当时报刊日益“国际化”的风潮。同年,这篇小说被收入詹姆斯的中短篇小说集《尴尬种种》(Embarrassments),英国版与美国版同时面市。回过头来看,《地毯上的花纹》是这本书里影响最大的篇目,而标题“地毯上的花纹”也渐渐成了一个被后世频繁引用的文学典故。英国小说家、评论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曾经说过,自从这篇小说出版之后,詹姆斯的同龄人就开始追求“地毯上的花纹”,希望能将原本复杂难辨的“花纹”变成清晰可鉴的物质实体。在发表于一九四一年的散文中,T. S.艾略特几乎把同样的话又说了一遍:“如今,我们都在寻找‘地毯上的花纹。”
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个赚过一点稿费却苦于在圈里寂寂无闻的写手。明显比他更为资深,主要以写评论为主的考威克因为来不及完成著名作家维雷克新作的书评,把这个机会转给了“我”。“我”以为抓到了在文学圈里进阶的机会,不料却像是一头撞进了一座迷宫。维雷克对于这篇评论不屑一顾,并且抛出了一系列炫目的名词和意象,引诱“我”追逐对于其作品的终极破解:
在他本人看来,毫无疑问,那个让我们不胜迷惘的东西,明明是清晰可见的。那玩意,我猜想,就藏在最初的规划中;宛若波斯地毯上的一个复杂的纹样。当我使用这个意象时,他表示高度赞赏,而他自己则用了另一种说法。“它就是那根线,”他说,“把我的珍珠串起来的那根!”
此后的情节发展就进入了詹姆斯最善于营造的诡异疯狂的叙事链。“我”对于维雷克(毋宁说是小说这种文体)的“整体意图”的追寻,注定要像《螺丝在拧紧》中那个关于“庄园里有没有鬼”的命题那样,经受百般折磨,经受“真谛”在眼前闪现又幻灭的海市蜃楼般的瞬间。洞悉维雷克的秘密的人(或者说“我”以为洞悉秘密之人)一个接一个遭遇不测。詹姆斯得心应手地折磨着读者的耐心,在人物细节和对话里嵌入可以引发多重理解/误解的隐喻。熟悉詹姆斯套路的读者,几乎在小说进行到一半时就能判断:直到结尾,我们也得不到答案。
但我们还是会一口气读完它。我们知道,像很多具有元小说特质的现代主义作品一样,这是一部阐述小说观念的小说。小说里的小说家和评论家的关系,是一种近乎猫捉老鼠的关系。小说文本的“整体意图”被层层包裹,被繁复衍生,被渐渐失去节制地神秘化。批评家疯狂地追逐它,而小说家则似乎一直在使用各种障眼法躲开这种追逐,这样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奇特的仪式感。地毯上到底有没有花纹,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批评家和读者的兴趣和精力,在这个过程中被刺激、被撩拨,同时也被消解、被损耗—像表演、像爱情、像生死。作为由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对于时代风气的观察,对于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游戏的深层思考,都渗透在文本的肌理中。
在这篇小说里先后出现的几个命运多舛的人物,我们无法确认哪一个更能让詹姆斯产生代入感;我们同样无法确认詹姆斯是否要通过《地毯上的花纹》表达现代小说家和批评家的使命和宿命。(是使命多一点,还是宿命多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詹姆斯之后的写作者,越来越深切地体验到他在这篇小说里所传达的那种时而狂喜、时而虚无的复杂感受。“二战”结束之后陆续涌现的文学名词和小说流派,可能比此前的总和都多。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弄清现代主义究竟在哪个时间点进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与“新历史”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或者推理小说究竟分出多少亚类型,并没有太明显的意义。社会现实的动荡和传播方式的剧变,使得小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信任感渐趋微妙。叙事套路仿佛已经穷尽,连“生活比小说更精彩”都成了老生常谈。小说家进退两难,时而希望勇往直前,沿着文体实验的道路越走越远;时而又希望重温现实主义的荣光,回归古老的故事传统。
在现代文学的语境中,小说家与批评家,作品的创造者和诠释者,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默契,密码有没有可能被完美破解?我们从这个既抽象又具体,甚至有时候颇具哥特风格的故事里,看不到詹姆斯对此有任何乐观的表示。故事的荒诞走向甚至让人联想到那个著名的思想实验:A和B两位将军,各自盘踞在两座山顶,需要同时攻击山谷处的敌人,但他们之间的通讯只能穿过敌方阵线进行。A给B发了个信息:“明天出击?” B回答:“可以。”但B不知道自己的回复有没有到达,而A必须给B发送另外一条信息来确认已经收到了B之前的信息,从而确保B会行动—实际上,为了达成完美的共识,他们需要发送无穷无尽的信息。
《地毯上的花纹》就在这种看不见尽头的努力沟通中戛然而止。然而,也许,无论是密码被(简化地)破解,还是因为无法破解而失去对破解的渴望,都会使小说的魔法黯然失色。这真是个绕不出去的悖论,但叙事艺术的奇迹和荣光,也恰恰蕴含在这悖论中。毕竟,詹姆斯狡黠地在绝境中也留着一星微暗的火:
如果说,她的秘密(按照她的说法)便是她的生命—这一点,从她越来越容光焕发的样子就能窥见端倪,她那因为意识到自己享有特权而流露的优越感,被她优美而仁厚的举止巧妙化解,使得她的容貌教人过目难忘—那么,迄今为止,它并未对她的作品产生直接影响。那只是让人—一切都只不过让人—越发觊觎它,只是用某种更美好更微妙的神秘感将它打磨得圆润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