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智正:为孩子们改写《西游记》
孙凌宇 林澜

圖/本刊记者 梁辰
牌局开始前,每人先往牌桌上充点钱。有的做个假动作,空手一伸一缩,就当是扔下了十块钱,还有的拿了张50,往钱堆里一搅和,跟众人说自己充了100。喝了酒的夜晚,多数人晕晕乎乎,难以察觉,偶尔发现对不上数了,一般也碍于情面,睁只眼闭只眼。但孙智正不,他一定会从人群中噌地坐起来,非得揪出这个老千。
拆穿后,有的坚决不承认,怂些的,就赖着脸说刚刚忘了啊,你盯得这么紧干嘛。接着有人打个圆场,算了算了,但下一次,孙智正又会准时冒出来,不肯就此松懈。他探身喝了口咖啡,立马把下拉的口罩重新戴好,身体往后靠,认真地说:“我是非常认真的,非常遵守规则的。我觉得做任何游戏,假如不认真,会不好玩。吊儿郎当的,不上心,就特别不好玩。”
四五年前,他搬到通州,从此每天在公交车上来回通勤的时间延长到三小时,一路上,不论是花枝招展的女子,还是卖保险的男子,但凡有人好奇他在看什么书,他一律连名带姓认真作答,“这是张洹,讲行为艺术的”,“这是法国新小说的谁谁谁。”他脸尖鼻大,低声絮叨的样子越看越像伍迪·艾伦,不少人这样说过,但他依然不觉得,似乎是认真比对后举出证据,“我脖子比较粗。”
这份较真、耿直,放到他多年的写作上,便体现为拒绝比喻、放弃修辞、像厌恶牌桌上不规矩的小动作一样厌恶语言里的假大空,最好是真诚直白,没有臆造的字词和别扭的句式,小学三年级便能看懂。在他看来,好的文学语言应当像空气般透明,想法或感触则是空气里清晰呈现的树木;而坏的语言就像有雾霾、有云彩,把那些东西都遮住了。“有很多写作者喜欢玩弄文字上的技巧,在我看来都是‘字障,让大家看不到你本身要呈现的那些东西了,是舍本逐末”。
十几年来,他执着地推广“无技巧”写作,但规避所有技巧本质上也是一种技巧,像人突然放弃直立行走,需要操练。“用最简单的词,把文字做得非常简单、质朴,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孙智正承认,“不让你比喻,那你要如何表达出来呢,得想办法。实际上,我们说的话里面隐含特别多的信息、暗喻。你忍不住会想卖弄,你怕人家说你这个人不会写书,不会写东西。所以返璞归真不一定对,但一定是很难的。”
不仅要自我较劲,这种审美趣味还得时常面对外部的不解甚至攻击。他的朋友、因“废话体”走红的诗人乌青,写过一首《对白云的赞美》,就曾作为反面、嘲笑的例子出现在语文课堂上——“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特别白特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
这首让语文老师不屑一顾的诗在孙智正看来“非常天才”,他解析道:“我觉得他是一种反讽,他不是不知道怎么去写,但他就故意把所有摒弃掉。‘像棉花,‘像面包,都是没用的,我直接就说很白。因为实际上当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东西的时候,心里直接的感受就是太美了。”
课堂上有个学生被这种风格吸引,哪怕是孤例,也给了孙智正十足的倡导动力,他并非要与比喻为敌,只是不希望审美变得狭窄,以免唯独修饰繁复的、文学技巧强烈的才能流传下来。“我觉得只有一种风格,那就是单调。大家一直以为文学首先追求美,但我觉得文学跟科学是一样的,它首先追求的不是美,是真实。为什么孩子的话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可爱,或者觉得他说出一些真理来?因为他没有伪饰,而且用的也是最简单的语言。所以我觉得我们写作上,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干?”
七个坏蛋
他第一次这么干,是26岁时写处女作《青少年》,讲一帮青少年在高中毕业后的两个月里到处游荡,一开始他预计只写十万字,写到第二节时,突然感到就应该这么平铺直叙流水账式地写下去。
想写点什么的心情由来已久。高中时,他读余华、贾平凹、莫言,觉得都不是自己喜欢的路子,但自己的路子是什么?不知道。从浙大教育系毕业后,他通过系里老师推荐,在杭州的《家庭教育》杂志工作,一年后便辞职。“这不是我这辈子真的想干的,我想干的就是写东西。”
当时在年轻人中间流行“假如你想搞文艺,即使是条狗,也要去北京遛一遛”的说法,2003年,23岁的孙智正来到北京,他迫不及待地在网页上输入“先锋文学”、“地下文学”等字眼,很快在一个叫乐趣园的网站上找到了无数制作简陋的诗歌论坛,其中最令他惊喜的是“橡皮”先锋文学网(2000年由杨黎与韩东、乌青等人创办)。在那里,他陆续认识了一圈子尚未在地面出版物上露脸的人,他们大张旗鼓地宣扬“废话”写作,追求直接、准确,在语言里面不要玩弄任何技巧,甚至不要有知识的含量。
无论写诗歌还是小说,只有一个准则,识字的人能完全看懂即可。这让孙智正欣喜万分,“我觉得这样的路子是成立的,而且之前已经有这么多人在走了,只不过大家看不到而已”,像是终于得到了一种确认。
他住在朋友家,看到了法国新小说(以罗布·格里耶等人为代表、力图描绘出事物的“真实”面貌)和让-菲利普·图森的《浴室》,再次给了他写法上的冲击,“我非常喜欢他的那种写作。他虽然没有说像废话流派这种反对什么或者要怎么写,但他实际上就是在这么干的。”据孙智正描述,这本书讲的是一个男的莫名其妙地离开家,待在一个旅馆里面,每天会给家里打个电话的故事。“他表达的三观我非常喜欢,那种非常清冷的、非常当代的、很疏离的感觉,写出了当代人的生活。因为我觉得中国没有真正的城市文学,像这样的我就非常能体会到这种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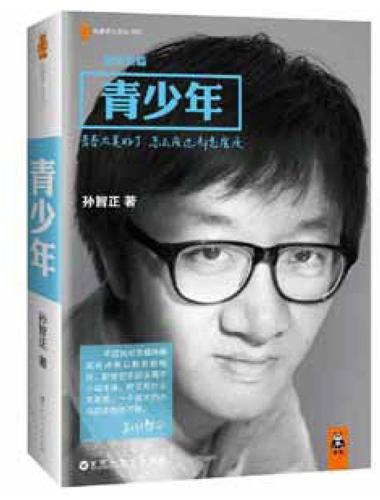

接著启发他的是《金瓶梅》那种事无巨细、什么都摊开来说的坦然态度。在这些作品的滋养与鼓舞下,他完成了四十多万字的《青少年》,母亲拿来一看,“太啰嗦了。”
大约在2009年,孙智正的老乡、来自浙江嵊州的诗人张羞发起“坏蛋独立出版”计划,旨在宣传身边几个在写作上有独特才华却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发表和出版作品的朋友,把他们的作品结集成册,以使更多人能看到。孙智正与曹寇、乌青、竖有幸成为第一辑拟定的人选,后来又补充了杨黎和张羞,加上当时还未引进内地的美国酒鬼作家查尔斯·布考斯基。每部作品限量印刷200册,标价100元。
即便搁在十年后看,“坏蛋”出版的那批作品依然风格鲜明。光说封面,布考斯基的诗集《醉钢琴》,夹着烟的手与另一只同样长满汗毛的手做弹琴状,手指下是歪七扭八的酒瓶;孙智正的《青少年》,阴郁的孔雀蓝打底,竖着一根惨绿的、透着青光的中指,比后来正式出版的、以他个人头像为封面的版本确实酷得多。
“坏蛋”版《青少年》的编辑赵志明,曾经回顾当初决定出版《青少年》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写作观念(不言自明的通篇废话)以及他的写作耐心(《青少年》是一本四十多万字的砖头巨著)。不独孙智正本人,我们也坚信:《青少年》是更为纯粹的先锋和实验之佳作,坚持这样的写作(孙智正陆续推出《句群》和《南方》),后果“不堪设想”,不远的将来,“必引世人(全世界的人)与后人(全世界的后人)侧目”。
翻写《西游记》
从那之后,孙智正一直在思考,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或者一种文本,把这个圈子对写作的理解向大众传播出去。直到2017年,他把目光看向了《西游记》。“这个故事已经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所以说用这样一个故事作为载体,去表达我对写作的理解,或者是对文字的一些追求,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对我们这样的写作者来说,反倒故事是载体,文字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个故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他们的注意力会转移到你的文字是怎么使用的,你为什么用这么简单的、浅显的、直白的词汇去讲这个故事?”
为什么不是《水浒传》、不是《三国演义》呢?孙智正的回答是“因为没有孩子气”。在他眼里,《西游记》里的人说话都逻辑奇怪,带着童真,四个主角对起话来插科打诨的,像群口相声。九九八十一难的线性游戏过关模式也是很好的,符合我们对时间最基本的感受。而众多神怪更是冷不丁地出现,“可能作者下意识地觉得这些都是当时听众和读者的背景知识。事实上,生活中的人就是这样,像鱼一样倏忽而来、倏忽而逝。”
他参照汉典网里的一本古籍,与人民文学出版的《西游记》,总共100回,除开双休日,每天规定自己翻写半回。那段时间,他还在一家青少年月刊工作,大概一个星期就能完成当月任务,剩下的坐班时间,他就把办公室当成一个容纳着一两百人的大网吧,专心写自己的东西。

拍摄于北京通州运河公园。图/本刊记者 梁辰
《给孩子的西游记》按照他的计划,用了一年时间完成,并于近日出版。他绝不是兴之所至的写作者,写《青少年》的时候,也严格要求自己必须每天在女朋友下班回家前写够5000字。他自认是个非常急躁的人(不管电脑开着多少个窗口、运行着多少程序,都直接摁关机),因此在急着完成很难一下完成的大部头时,就会分割成一块一块,“这一块完成我就会有成就感,就继续让我完成下一个。”
接下来,他还打算改写《封神榜》和《镜花缘》,它们和《西游记》一样,都让孙智正感到一些有趣的、孩子气的、神神怪怪的民间故事趣味。“其他的古典小说,比如像《红楼梦》和《金瓶梅》。它们写得太好了,你没办法去改,(改的话)简直就是一种破坏。另一些乱七八糟的明清小说,我觉得不值得改。要么就太好了,要么就太坏了。”
类似这样的很白话文的《西游记》改写之前没有吗?也许有。但孙智正不愿与之相提并论,“他们那种改写方式跟我好像不太一样,他们可能会删减,我基本上是没有删减的,完全按照那个情节下来。而且他们的那种语言方式,不是一种文学创作的态度,我是把它认认真真当作一个作品去创作的,我有我风格上的追求。市面上我翻过几本,那种语气故作活泼,就假装加‘啊‘嗯,把小孩当成小孩,我非常不喜欢。实际上小孩不小的,小孩啥都懂。”
儿子四五岁的时候,孙智正常常给他讲《西游记》作为睡前故事。现在儿子长到十岁,已经能自己给自己讲故事了。最近一次,他关灯后,说了一则与生活的对话——“生活啊生活,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枯燥?为什么每天都要一样?今天是这样的,我明天起来你还是这样,生活大爷你能不能改一下?”孙智正曾经特意把新书拿给儿子看,翻到扉页写着“给孙阔”的地方,他看了一眼说“哦”,就走开了。
孩子当然包括在他改写的目标受众之中,但他最初并没有想到要把这个群体单独拎出来,在他看来,这应该是一本全年龄段的读物,大人小孩都可以读。好友赵志明在长长的书评中写道:“《西游记》问世以后,除了连环画、动画,很少有人想到要在文本上有所建树,让孩子也能从头到尾进行阅读。如果我在十岁左右看到这本《给孩子的西游记》,我估计会欣喜若狂,就像我在初中时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偷看金庸一样。可以说,孙智正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他在纯故事和纯文学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我甚至可以断言,孩提时看过《给孩子的西游记》,然后到青年时期又阅读了足本的《西游记》的人,将会在语言、思维、情感表达诸方面受益良多。由简洁而入繁复易,由繁复而入简洁难。这也是为什么即使看了很多世界名著,一些人的语言和文字依然枯燥生涩的原因,正应了‘欲速则不达‘画虎不成反类犬的陷阱。”
只有生活,没有感悟
初步改写完《西游记》,2018年7月,如往常一样在办公室的孙智正突然被送进医院,被诊断为患上了发病率为万分之一的“烟雾病”,并导致脑溢血。他死里逃生,“生活就像玻璃杯,突然被打碎。”
病发后,他辞掉了工作,提前步入老年生活,每天晚上10点按时睡觉,不敢再拼命用脑过度思考,中午和傍晚都要休息,没法尽情尽心地生活,就连啤酒都不能喝。
偶尔会想念以前每周五晚上和朋友们打牌的时光,康复后去过一两次,但发现体力跟不上,很快就回家了。
他依然在写作。不再像以前那样着急,如今心态更放松,每天三五百字地在手机上记录生活。大病初愈后的一年里,他累积了20万字左右的日记,准备出版成书。一开始取名为《历史》,后来改成恢弘的《史诗》,按素材内容分为植物、动物、吃饭、睡觉、地面移动、历史共六七卷。
每天走同样的路,去同一家难喝的、养着十几只猫的咖啡馆,他常常点一杯美式,放着不喝。“但每天看到的真的会不一样。比如今天上来的是黑猫,明天上来的是白猫,有时候它们两只猫一块上来,就是有一些非常细微的区别。”
他坚持写身边的事情。只写熟悉的,只写能写的。下雪了,就写《雪》。不写和自己“无关”的东西。不会写到“知更鸟”,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鸟。“我觉得不要给别人讲道理,你的道理对别人未必适用,你只需要呈现你的生活状态就行了,比如我今天早上起来带孩子,然后出去买菜。别人是能感受到的。”
他心里一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他认为文学研究实际上就是做科学研究,只是通过语言去做,去研究人类的感触。“但是我不懂你的感触,甚至我也不懂我妻子和孩子的感触,我觉得我最懂的就是我个人,实际上我不是天天要写自己的东西,而是想把我个人作为一种人类学研究的样本去呈现。”
这股蛮劲在有些人看来是无用功,但也有一部分人深受感动。彭剑斌赞赏说:“作为小说家,孙智正好像不知道自己有权利去虚构。当然他肯定是知道的,只是他的内心促使他选择了反其道而行。在中国,还没有小说家敢如此贴近自己的存在、自己的生活去写作,还没有人有如此勇气敢让大家去认识这样一个几近赤裸的全方位的自己,去认识以自己为代表的这么一群活生生的人。”
更极端一点,他甚至有用文字复制一生的想法。《青少年》之后,他以故乡为蓝本写了《南方》,但,是不是“乡土文学”不重要,“文学的关注”不是他的关注。他的最终目的只是把这些“素材”用文字排列起来,最后这平铺直叙的一生全部组成一本书,叫《一万页》。
“孙智正式的写作”意义何在?套用赵志明的回答:“不是忠于这个时代(时代都是高大上也就是假大空的),而是忠于生活(他自己的生活,他耳聞目见的生活);不是迎合读者(很难想象北方的读者能看懂《南方》满篇奇崛拗扣的方言),而是满足自己(我就是这样度过我的一生的);写作不为炫技(尽量做到客观),叙述不为讲什么意义(不带感情褒贬);基于此,写作在孙智正那里终于摆脱了崇高的意义、丰富的技巧,而归于生活本身,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私写作和生活史写作。”

